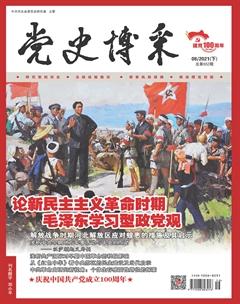中共革命史研究新視角:個體生存感受性路徑的探索
[摘要]《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么建立起來的》一書根據大量原始檔案,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深入農村,在農民中進行動員、組織,策劃武裝暴動,實現革命道路轉變的真實面貌。該書通過中國共產黨初期農村暴動的實施與所遇到的情況以及暴動后的抉擇及其在鄉村的深入,強調了農民與革命的關系主要是個體的生存感受性,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從動員到割據的一系列基礎性的問題,介紹了黨在處理宗族組織、會黨、土匪關系的實際情況及軍隊建設、鄉村的深入問題,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動態的革命史畫卷。現將其研究的新視角與傳統視角進行對比梳理,并歸納出一些特點,僅供學界參考。
[關鍵詞]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個體生存;研究視角
[作者簡介]俞劍英(1985-),女,漢族,江西上饒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文博館員,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中圖分類號] K25,D23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8031(2021)08-0055-03
《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是復旦大學姜義華主持的《革命與鄉村》系列叢書之一,集中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鄉村社會變動。該書作者黃琨,從關注中國革命根據地是怎么樣建立起來的微觀角度出發,對農民與革命以及革命過程中的諸多現象進行了重新審視,探究了革命運行的內在邏輯與理路,采用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和獨特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的跨學科運用,豐富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方式方法。
一、全新的研究視角
(一)避免了以往的宏大敘史方法,注重從微觀角度去研究革命問題。在學界研究革命史一般對重大歷史事件往往采用宏觀敘事法,形式一般都是在引入革命斗爭的序幕時,先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形勢展開介紹,然后再論及馬列主義的傳播及其對國民革命運動的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拿起武器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多見文山會海,少見鮮活的歷史人物;多見戰爭、革命、政治、政黨、權力、非此即彼,少見和平、發展、經濟、文化、和諧寬容。①從史學研究的客觀層面上說,這種寫史方法是從共產黨建黨、革命根據地的已有成功經驗和意識出發,進而論證其走向成功的必然性。然而,革命實際上是充滿了偶然性和風險性,從農民參加革命暴動的個體生存感受偶在性出發,來看待革命道路的發展過程。把視線轉向底層民眾的心理反映,從微觀這一角度去分析農民的參與選擇的心理層面,以微觀角度去透視整個社會的大環境,這是該書不同于以往各類歷史研究的亮點。“敘事不妨細致,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②該書汲取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國革命史視角之精華,并以此為起點觀察整個革命發展勢態。如此一來,研究問題大大突破了以往突出政治事件高層角度的分析論述方法,打開了革命史研究的新視野。
(二)避免了傳統的必然性因果關系式的解析,而注重了歷史偶然性的研究。黃琨在該書研究中關注的不是根據地為何能建立起來,而是怎樣建立起來。“為什么能建立起來”其實是在探究它發生的歷史必然性,而“怎樣建立起來”則其中包含了許多未知的偶然性因素。這一研究方式的基本確立,也使其在革命過程中的敘述中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復雜性,對農民的“個體生存性感受”的實際描述是這樣,對革命的具體走向亦是如此。事實上,革命道路上沒有定路。“不同的存在使革命過程中具有多種可能性,關鍵的時刻個人判斷和選擇決定了具體革命的走向和面貌。”③黃琨對那些固成說法的歷史史實的解釋的翻新,使人們更加深刻地洞察歷史的變因。如此,作者把“前瞻性”研究方法運用得恰到好處。
前瞻性分析和回顧性分析是史學研究的兩個對立的研究方式。回顧性分析往往從事件的結果出發分析其發生的多種可能性,根據結果,這一連串的可能性被否定,從而證明結果發生的必然性。前瞻性分析不同于回顧性分析,它擺脫了目的論的社會理論,同時又堅持“過去是可以解釋的”理念的基礎。可以從思考社會理論如何使各種歷史經驗變得有序出發,轉而思考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二、獨特的研究方法
(一)避免了以往重“前進性”輕“曲折性”的研究取向,而重視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實際困難的研究。以往多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經驗出發來看整個革命過程,對于其曲折性的一面則是一筆帶過,或者淡化地去描寫,因為“它已被成功的經驗戰勝”了。而該書中,黃琨則著手了一項基礎性的研究,嘗試著從共產黨政策或實踐的不成熟到成熟的曲折性角度來看,把黨在革命時期鄉村割據所面臨的困境及其變數提上了議程。他認為:“每階段歷史都是歷史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正視歷史需要正視歷史中出現的曲折。”④中國共產黨創建革命根據地和革命的過程實際是一個艱難而曲折的探索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正是從失敗中一步步走出來的。何人能言,它是按照成功的腳步走出來的?因此,正視黨在革命過程中的曲折性,反而證實了中國共產黨走到今天的偉大性。從困難的角度去闡述歷史發展的曲折性,把黨的組織建設、根據地建設、民主制度建設等創建過程中遇到的不同困難體現出來,根據不同情況探索不同路徑和方法闡述,這樣,歷史的脈絡會更清晰。黃琨重視“曲折性”這一研究取向,為研究黨史提供了新視角。同時,這也是寫革命史過程中反證法的運用,值得借鑒和學習。
(二)避免以往單純的靜態研究歷史的方法,而采用了動態的研究歷史方法。黃琨認為,在鄉村很難用階級觀念來動員農民去參與革命,并且農民參加革命了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有了階級意識。很多時候,農民參與革命的原因是復雜的。正因為這一復雜性,而歷史又是動態的、變化的,史學工作者的任務不是要展示一幅幅靜止的照片,而是要展示一種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有時在作研究的時候,往往是以一種先驗的形式對農民參與革命進行分析和討論的,這樣的方法就像給歷史定點拍照似的,社會群體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及其心理活動都定格不動了。所以,在革命史研究過程中,應該摒棄這種思維定式,把關注點適當轉移,把歷史人物的動態作為以及復雜的心理描繪出來,全局與具體細節兼顧,把歷史寫實、寫準、寫活。該書即拋開了先見研究思維的束縛,以農民自身為立足點,把其放在“自由狀態下”進行分析和研究,去看農民的價值觀念對革命變化的認識和取舍,這種動態的歷史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學習和參考。
(三)避免強理論弱實踐,而應重史料考察和多面觀察,增強歷史生動現實性。黃琨根據大量的原始檔案,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深入農村,在農民中進行動員、組織、策劃到武裝暴動,實現革命道路轉變的真實面貌。從書中的注釋可以看到黃琨的資料收集工作是做得相當扎實的,特別是對于原始檔案資料的收集和運用方面,顯示出本書的優勢和扎實之處。其次,對回憶錄、口述史、報告、講話等資料的整理利用,黃琨做得也非常謹慎和細心。在挖掘大量原始檔案的基礎上,把口述史料與檔案史料進行相互比照印證。該書羅列了大量引文出處,但其文并非對史料的簡單堆砌,而是恰如其分地使用。正如黨史研究泰斗張靜如所說:“材料引證的目的,是為作者的分析和結論找根據,這在寫實性文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不要以為越多越好,有一個原則,叫做選材適當。不是編資料,而是寫論文、專著,不能讓材料淹沒了觀點。”⑤黃琨在分析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比較有分寸地把握了史料利用的尺度。此外,對黃琨如何查找資料與處理資料以及如何利用大量的檔案資料的方法方面可以學習借鑒。
三、多元的跨學科運用
(一)避免了傳統研究的諸多預設,把關注立足點突破性地從黨轉向農民群體身上及其心理層面。以往人們總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角度出發,去看待革命發展和農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宣傳的反應,而黃琨從心理學的角度,從共產黨的動員對象出發,以農民為主體,共產黨為客體,來看革命的內在邏輯發展。黃琨認為,共產黨應是以組織者身份進入農村發動革命的,而不是以發動者的身份去做農村動員工作的。以往認為農民具有天然的革命積極性,認為“愈貧者愈革命”。事實上,這只是一部分。群眾熱情與黨的領導并非簡單的“干柴遇到烈火,一點就燃”的情況。實際上對于宗族鄉村來說,共產黨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外來者,農民有排斥心理這一點不容忽視。共產黨作為外來組織者,用何種辦法才能打動農民并使其追隨革命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在這里,農民是主體,共產黨是客體組織者,黨要根據不同的農民個體的實際情況來判斷和運用革命策略。農民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他們會根據革命形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革命取向。
例如,1927年到1929年,國共兩黨在農村各有軍隊占據。兩軍如何爭取民眾,民眾如何抉擇,是相當重要的問題。據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統計,湖南敵軍合計20個師又2個教導團。⑥共產黨在軍備物資和軍隊數量上不敵國民黨,那么就更需爭取民眾。但民眾也不是完全無知的,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利害小算盤。作者正是以農民為主體,從農民自身的觀念出發,解析他們的革命心理取向。老百姓判斷紅軍的好壞,既要看共產黨的政治宣言,還要看共產黨的實際行動,能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利益和實惠,還有能給他們帶來多久的安全感。共產黨提出和實行的方針政策都是圍繞和考慮民眾利益的,特別是土地政策,滿足了廣大農民特別是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迫切要求,因而得到絕大多數農民的擁護。然而,他們也有很強的小農自我保護的潛在意識,一旦情況有變,就不干了。如在“弋陽、橫峰,共產黨發現民眾跟著自己的只有一部分,跟著國民黨的也有一部分,其余大多數的農民尚在渾噩之中,誰武力占據葛源,即順著誰走”。⑦由投機心理造成的宗族組織與暴動的結合是不牢固的,一旦面臨國民黨軍隊的“清鄉”,形勢不利時就極易反水,這是當時大量反水情況出現的重要原因。⑧由此可以看出,黃琨這一立足點的轉移,突破了革命史研究中政治革命斗爭傳統諸多主角預設的慣性思維,創新性地把關注點轉移到農民這一群體身上,并且注重對農民群體的個體感受性研究,更深層次地解讀革命需求的原動力。
(二)避免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式條框,把第三方農民的矛盾提上議程。以往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更加注重革命和階級斗爭的主體和客體矛盾的闡釋,考察和研究主要圍繞政治斗爭來展開。研究的范式和框架以民主革命時期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矛盾為主要分析范式,但是這樣一來,很容易忽略人民群眾的需求矛盾在現實中的反映和表現,及其與階級斗爭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定位。這里面實際存在著很多關系的互動、沖突和矛盾,往往會因為分析范式的限制,沒有列入到革命史的考察范圍內,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中共革命史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出現了單一分析模式到多元化分析模式的轉變,從中心化框架的“現代化”范式到去中心化的“后現代”范式,再到現在的多元化分析趨勢,體現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科學化進一步增強。黃琨正是從研究內容和主體的多元化角度出發,打破常規,把農民的矛盾擺在研究主客體的重要位置,把鄉村的社會經濟背景、農民的需求矛盾與多方勢力矛盾體現出來,從而從側面凸顯中國共產黨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優秀組織力和高超智慧。
(三)避免了單純以時間為重大事件順序敘述的邏輯,轉向以重實踐邏輯的順序安排。該書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深入農村,在農民中進行動員、組織、策劃到武裝暴動,實現革命道路轉變的真實面貌。黃琨從共產黨如何進入鄉村進行動員和組織以及暴動是怎樣進行的實踐中的復雜情況,到革命道路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以及共產黨是如何獲得農民支持的,給人們展示了一條清晰的實踐邏輯路線,即革命的內在邏輯理路,彌補了傳統研究僅以時間為敘事邏輯可能會遺漏的問題與空白。這一從純理論到實踐過程研究的轉變,實際上填補了黨史研究的重要空白,這也是本書閃亮點和值得學習之處。
不可否認,該書也難免存在瑕疵,概括起來就是在內容分配上,涉及共產黨中央和地方配合協調的篇幅比例較少。例如在組織研究方面,把目光集中于農村民眾的個體心理反應上,從而去分析中央一級的組織工作就有點難度。但是從總體來看,黃琨的一些獨到的見解和治學的精神,對于深入中國革命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啟迪價值。
[注釋]
①沈傳亮.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新趨勢分析[J].教學與研究,2004(12).
②[美]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62頁.
③④⑧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頁,第3頁,第85頁.
⑤張靜如.引證和注釋[J].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2):70-71.
⑥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52-53頁.
⑦弋陽、橫峰工作報告(1928年8月)[G]//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7—1928年),第2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