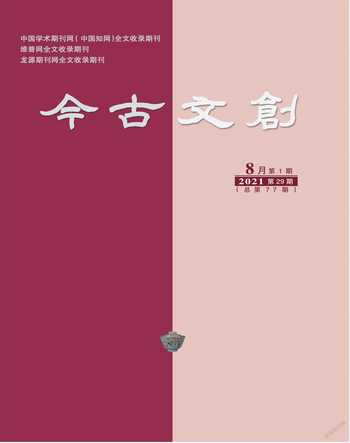“驚嚇背后”
【摘要】 新晉獨立電影廠牌A24出品的恐怖電影具有其獨特的恐怖美學,即在題材內容方面追求人文視角介入,視聽語言方面重視創新表現形式,并獨具深度哲學視角。本文結合A24出品的幾部恐怖電影代表作,分別從敘事內容、視聽語言、哲學元素三個維度切入,解析A24系恐怖電影的美學特點,以見出其擁有構建嶄新恐怖電影圖景的巨大潛力。
【關鍵詞】 A24; 恐怖電影;恐怖美學
【中圖分類號】J90?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29-0089-02
A24公司成立于2012年,由三位從業多年的電影人創辦于紐約,主要發行成本預算低于1000萬美元的中小成本電影,在當下商業電影大行其道的市場中,A24電影票房上出色的表現令獨立文藝電影異軍突起并實現盈利。他們所發行的影片始終秉持獨特的創作風格,具有非常典型的“獨立美學”的標簽,從而形成了獨具A24氣質的品牌文化。
近年來,A24已出品多部屢獲嘉獎的影片,比如獲得第89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以及獲得多項提名的《龍蝦》和《機械姬》。而恐怖驚悚類型的影片是A24更為青睞的領域,《遺傳厄運》《仲夏夜驚魂》《女巫》《燈塔》等影片在廣受影迷的同時,也呈現出其精致而獨特的恐怖美學,“A24系”恐怖片由此成為在恐怖圈識別度話題度雙高的標簽。
下面將結合A24出品的幾部恐怖電影代表作,分別從敘事內容、視聽語言、哲學元素三個角度切入,解析A24系恐怖電影的美學特點。
一、更多元的人文背景,突破好萊塢恐怖片的
類型化敘事
不論是阿里·艾斯特《遺傳厄運》中無處不在的神秘學符號、《仲夏夜驚魂》體現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奇遇”,還是羅伯特·艾格斯《女巫》以及《燈塔》的百年前新英格蘭民俗傳說,抑或是歐格斯·蘭斯莫斯《圣鹿之死》的神話寓言,都豐滿了傳統恐怖電影“嚇人”背后蒼白的故事背景,通過人文背景的交融令恐怖片不再是一種單純追求心理刺激的“花瓶式電影”,從而賦予影片深邃的文學生命力。
作為青年導演阿里·艾斯特的長片處女作,《遺傳厄運》講述了一個家族異教詛咒的故事。這部影片沒有立足于更具現實意義的宗教故事,而是站在神秘學的邊緣異教的角度進行隱喻,打造了一個有距離感的“異度空間”,觀眾可以在反復的觀看中解讀出更多影片含義,甚至考據出許多歷史中的邪教背景。充滿理據性的細節和伏筆,形成了A24公司出品的電影的一貫風格。
事實上,宗教淵源在東西方恐怖電影里是十分常見的,而西方恐怖電影中又以《圣經》故事作為其重要的取材寶庫。在《圣經》的《啟示錄》部分,重點描繪了地獄的恐怖,殺戮、饑荒、瘟疫充斥在由末日審判籠罩的世界背景之下,生動的語言和神秘可怕的末日圖景,給眾多恐怖電影的創作提供了絕佳的前文本。早在1973年的經典恐怖片《驅魔人》中便出現了大量《圣經》中的魔鬼典故,而到后來大衛·芬奇的《七宗罪》等影片,也站在圣經故事中人類原罪的角度建立起頗具象征意義的心理恐怖敘事。
除此之外,希臘神話也是A24系恐怖電影敘事的重要前文本。2017年上映的《圣鹿之死》,內容取材自古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的故事。看似超自然能力導致的怪病籠罩在神秘詛咒與人性試煉之中,諷刺性地戳破了家庭內部的血緣情感,使影片成為一部悲劇式的神話寓言。而在羅伯特·艾格斯導演的新片《燈塔》中,同樣也吸納了希臘神話中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以及海神波塞冬的形象,故事內核則是將克蘇魯神話以及新英格蘭民俗恐怖志相結合而成的志異怪談。
二、更豐富的表現形式,拓展傳統恐怖片套路化的視聽語言
A24的電影還采用了多樣化的呈現方式來探索和拓展傳統恐怖片的視聽效果,減少使用已經開始令觀眾倦怠的Jump Scare或是那些扭曲爬行的鬼怪形象,而致力于將實驗性的表現形式同詭異的故事氛圍整合,構建起統一性極強的戰栗空間。
《仲夏夜驚魂》號稱極具小清新氣質的恐怖片。由于村莊故事發生于瑞典接近極晝期間,時時刻刻都是白日當頭,夜戲十分少,因此不同于眾多恐怖片的冷色調,影片反而突出了溫暖陽光的明亮色彩。被“死亡”籠罩的輪回儀式等場景,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在刺目的艷麗與明亮背后,恰恰為詭異恐怖的氣氛帶來了強烈反差,視覺和心理表現力反而更加搶眼。
相比之下,同樣以“明色”美學著稱的法國恐怖片《鬼天使》盡管使用了大量白色來進行氣氛的烘托,色調卻仍然是冷峻無比的。而2017年的大熱恐怖片《小丑回魂》雖然也使用了偏溫暖的清新色調,但幾乎都存在于與恐怖故事線索相平行的青春故事線索中,因而并未形成與恐怖氣氛相伴相生的統一整體感。
值得一提的是,A24出品的電影在樂音效果上也表現出色,《遺傳厄運》的配樂充滿復古感,令人想起20世紀早期懸疑片,烘托出古老宗教的詭異氣氛。而貫穿全片的彈舌聲也成了電影的一大經典元素,許多觀眾對這部影片印象最深的部分不是某幅畫面,而是妹妹查理彈舌的“滴答”聲令他們心有余悸。聲響不再僅是視覺的配角,而在視聽作品中獲得其獨立地位。
三、權力問題與家庭倫理——A24電影中的哲學
命題
(一)解構家庭倫理與血緣霸權
不同于傳統恐怖片中常將女性作為色情或惡靈表征來表現,《遺傳厄運》中的女性角色成為一種權力形象,令父權話語體系在電影中則始終處于缺失的狀態。通過身份權力的置換,對血緣倫理關系進行了解構。在西方后現代哲學思想中,血緣人倫建制的基礎不是親情而是權威①,是一套前現代社會建立起來的社會價值體系,在現代社會中這種血緣紐帶逐漸被理性紐帶所取代(個人主義的不斷壯大),而到了后現代社會,“新式家庭倫理”的歸屬感缺失問題則在這種趨勢中更為深刻地顯現。電影中正是通過極端的邪教回歸結局進行了一個寓言式的反諷,體現出家庭關系中每個人都身陷孤獨之處境。
(二)探索理性國度之外的“瘋癲”
《仲夏夜驚魂》無疑是一部個人風格非常獨特的電影,而全片充斥的迷幻體驗以及怪誕的群體儀式,都會讓人聯想到劍走偏鋒的詭異邪典影像。電影中所描述的北歐村落代表了遠離主流社會理性文明的異質文化,人們或許會用瘋狂、野蠻、原始來形容這些看似反人性、反社會的怪異儀式,但正如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所認為的,“瘋癲”存在于“理性”國度之外,而何為“理性”,則成了一個在社會權力身份約束下的主觀命題,并通過“非瘋癲”語言來交流和辨出自己的同路人。因此電影并沒有對這個村落中的文化進行正義或是非正義的評判,只是讓異質的價值觀與現實相碰撞,從而引發觀眾去思索這種所謂的“非理性”。
縱觀以上分析,能夠清晰地感受到,A24恐怖電影熱衷于探討權力、家庭倫理等人性議題,尤其是權力在家庭內部的身份關系,因此可以從中看出A24的恐怖美學植根于恐怖心理之外的諸多后現代哲學元素之中。在伊·彼耐多的論文《娛樂性恐怖:當代恐怖電影的后現代元素》中論述到當代恐怖電影讓善與惡、正常與變態、現實與幻覺變得難以分辨②,人們所熟悉的類型在其中分崩離析,由此反映了后現代界限模糊化、碎片化的表象。雖然彼耐多認為1968年以后的恐怖片都具有后現代主義的特征,但在進入20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A24的恐怖片更加凸顯了后現代主義必須面對的倫理問題和身份權力問題,并在向經典致敬的背后閃現出大眾文化的轉向——不盲從于市場主流,也拒絕曲高和寡的自娛,卻獲得越來越多的觀眾青睞,一方面,體現了大眾文化的泛審美化及泛藝術化的現象;另一方面,A24將藝術性與商業性完美融合,不也正是后現代主義所表現出的對現代主義所劃分的高級文化(藝術)與低級文化(大眾)之區隔的挑戰嗎?
自有聲電影時代初期,恐怖片便成為一種重要的電影類型,20世紀20—30年代環球公司出品的《德古拉》《弗蘭肯斯坦》等都成了時代經典,之后20世紀40年代怪物影片大熱、20世紀50年代以思想控制為主題的恐怖片盛行,再到后來血腥畫面占據西方恐怖片主導,以及如今所謂的好萊塢式恐怖和亞洲式恐怖在套路中掙扎,恐怖電影急需尋找一條新的路線,探索更具時代意義的表現方式,獲得新生。A24便是這樣一個實驗者與先驅者,它希圖通過更加多元的人文背景、更豐富的表現形式,以及更具后現代意識的理論視角,去構建一幅嶄新的恐怖電影圖景。
注釋:
①任雨田:《遺傳厄運:密閉空間營造的家庭倫理恐懼》,《藝苑》2018年第6期,第14-16頁。
②伊·彼耐多著,王群譯:《娛樂性恐怖:當代恐怖電影的后現代元素》,《世界電影》1998年第3期,第21頁。
參考文獻:
[1]戴維·斯卡爾.魔鬼秀:恐怖電影的文化史[M]. 吳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馬克·揚克維奇.定義邪典電影[M].李聞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
[3]楊春宇.西方恐怖電影的宗教淵源——圣經[J]. 時代文學(下半月),2009,(12):73-74.
[4]任雨田.遺傳厄運:密閉空間營造的家庭倫理恐懼[J].藝苑,2018,(6):14-16.
[5]伊·彼耐多.娛樂性恐怖:當代恐怖電影的后現代元素[J].王群譯.世界電影,1998,(3):21.
[6]沈壯娟,高月峰.試析西方恐怖美學研究的三個維度[J].山東社會科學,2006,(5):128-130.
[7]李漫.英美電影的恐怖美學文化[J].電影文學,2017,(11):46-48.
作者簡介:
果基伊辛,四川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學理論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思潮與藝術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