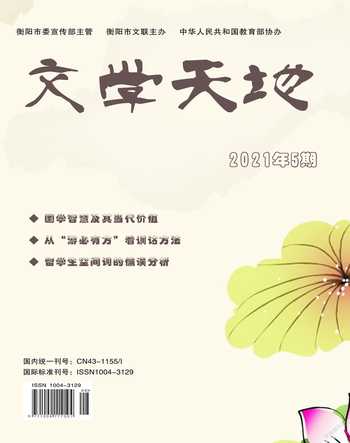從文本“搖擺”設計到教學邏輯
萬維瑋
摘要:《清兵衛與葫蘆》這部小說是日本著名作家志賀直哉早期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作品,小說在情節的“搖擺”和“延遲”中,通過講述清兵衛熱衷葫蘆、購買葫蘆、沒收葫蘆、砸碎葫蘆、放棄葫蘆、改變愛好的故事中,在情節的因果關系中批判了家庭的專制、世俗的觀念和學校的保守對天才的扼殺。作者以冷靜的筆觸暗示了偽教育是如何把人毀滅的。在教學中除了引導學生感受“呼喚人道主義”、“尊重孩子的天性”的主題之外,更需要探究小說故事講述的方式,即“如何寫”,培養學生身臨其境式的"個性化閱讀",培養可供借鑒的閱讀規律。
關鍵詞:人道主義 尊重天性 搖擺 講述方式
一、從選材的普遍與個性中關注教學的起落點
《清兵衛與葫蘆》這篇小說選自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選修教材《外國短篇小說》第五單元, 是日本“白樺派”代表作家之一志賀直哉的短篇小說,語言簡練、自然。這篇小說向人們表達了作者追求個性化的解放,呼喚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后人對志賀直哉的評價,充分肯定了他在現代小說研究領域上的突破和成就,尊其為“小說之神”。同時他的小說作品中體現了反戰思想,追求并始終堅守人道主義的精神。
通過高中語文教學實踐發現,因考試制度的制約,在語文教學中一直強調標準思考、標準解讀、標準答案。從文本到教學,其思維模式主要圍繞考試這個固有的中心。人教版高中語文外國小說欣賞(選修)前言中提到,“這是一種語文教科書,而不是一般的小說選本,更不是用于講授外國小說史的資料選編”“世上道理,高中生還無法領會的大概已不太多。關鍵不在道理的深淺,而在講述這些道理的方式”。因而,對于高中語文教學,不論是為了適應新時代課程改革的方向,還是為了教學,都必須構建并應用好課文文本與教學過程的邏輯思維關系,才能提升學習主體——學生的文本認知和文本構建方法的能力。
《清兵衛與葫蘆》故事起源自于志賀直哉在1912年11月前往四國的輪船上所聽到的故事以及他在尾道的經歷,他在《創作余談》中提到:“這篇小說的創作源于自己不服父親對他所撰寫小說的不滿,小說是他們父子關于自己的人生進路發生了意見沖突時,結合自己的耳聞素材并迭加藝術構思才能完成。”小說所要講述的故事也很簡單,一位名叫清兵衛的小學生雖然對葫蘆十分熱衷,但是在他的父親和長輩以及教師的強烈反對下,只好放棄喜愛的葫蘆。藝術源于生活,這個孩子的愛好和家庭、學校之間的矛盾,在所有學生的生活經歷中,都或多或少存在類似的情況,這是選題的普遍性。而清兵衛的喜好,又和大多數孩子喜歡的繪畫、彈琴、玩耍、手工、干家務等普遍性愛好不一樣,他有自己獨特的愛好“周正的葫蘆”,這就是個性。作者選題源自生活,具有普遍的生活熱門話題,作者選題又有獨特的個性,從葫蘆破題出新,表明這個故事與功利無關,展現出獨特的個性。
從文本內在邏輯思維來看,這個短篇小說故事情節簡單富有生活情趣,結構簡練便于把握,內容淺顯容易為讀者接受。從高中語文教學的邏輯思維來看,文本內容的知識性好把握,但文本背后的方法論并不容易掌握。在語文教學中,對于作者簡介、小說背景、文本內容都比較好理解。但如何在選材的普遍中突出個性,是小說文本教學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學生在文本閱讀中需要掌握的重要方法。志賀直哉選擇了一種對立的而又統一的方式,來推動主題的突破,進而推動情節的發展,那就是清兵衛的愛好——“葫蘆”,這是當地富人的雅玩愛好,難以存在于普通人家。父親和客人對葫蘆的品鑒僅局限于“名”和“利”這兩個標準,認為“馬琴”的葫蘆就很“出色”,而清兵衛對葫蘆的喜歡完全出于一種天性。小說在選題上突出了孩子的天性和世俗的標準之間的碰撞,為矛盾的沖突指引好了方向。在教學中,對于“呼喚人性自由”和“尊重孩子的天性”的主題其實并不難理解,重點不是“寫了什么內容”,教學的關鍵在于文本是“怎么寫”,而這種方法與思維,是在教學中應重點向學生引導的文本思維。教學梯度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在培養學生思維的批判性的同時,將專業知識嵌入教學,體會情節與細節的關系,對人物形象進行合理的解讀,增強在閱讀鑒賞中對文本細節的敏銳感,進而促進語文核心素養的培養,
二、從情節“搖擺”的突變中分析“如何寫”
小說情節的“搖擺”,就是通常所說的“一波三折”,“在一個戰爭小說中,即使它的故事開端和最終結局都很簡單,作者絕不會因為可能讓這個主要角色或者其他一個人物自己本身選擇了一條捷徑從而一口氣就把它當成跑路走到底的,而是必須一定要做到讓他千折百回,最終才讓他能夠真正到達美國取得戰爭勝利的高潮彼岸。所以,搖擺就可能意味著這部短篇小說在正常身體運行的任何時候,不是毅然決定地朝著原來的寫作方式向前奔突,而是希望能夠在絕大部分的時間里仍然表現得超出一種猶豫不定的狀態。”①不論是“搖擺”,還是“戲劇論”,指向的都是小說文本的故事情節運行方式。“一部不能把它編成好戲的短篇故事并不因此而非良好的短篇故事;然而,卻從未有一個好戲而無法被改寫為一部好書。”故事情節作為小說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按照因果關系聯系起來的對一系列事件的逐步、循環式展開。
在《清兵衛與葫蘆》一文中,清兵衛的興趣與眾不同,“異常專心”,“呆呆”,居然把一個年邁的老人禿腦袋地看成了葫蘆,并隨后層層鋪墊清兵衛對葫蘆的癡迷,進而引出得到一個心儀的葫蘆時忘乎所以,以致忍不住在課堂玩耍從而激發與教員之間的矛盾。作為清兵衛的施教者,一個武士道精神的忠實追隨者,隨著教員的家訪,教員的專制和對清兵衛愛好的反對最終導致了父親對清兵衛愛好的粗暴踐踏。其實每個環節都可能發生“搖擺”,小說文本每一個情節的發展,通過平常生活式細節進行推動,展現出生活中的因果常態,但是在生活常態的發展中,又隱藏著突變的根源,那就是精神與物質、兒童與成人思維的不同。有這些對立的"因",終究發展到沖突爆發的“變”。
首先,圍繞著“什么樣的葫蘆是好的”這一話題,通過對話寫出清兵衛與成人世界的沖突與審美對立,構成對話式的“搖擺”,構成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三人彼此的對話中暗流洶涌,頻生波瀾。以客人的否定句式話語和父親的附和、不滿甚至是不屑一顧的態度中,文本不僅通過語言的雙重否定、倒裝、省略句式的運用,同時在對人物的神態、動作和心理描寫中,我們感受到了孩子的天賦和獨特的鑒賞力在世俗的環境中舉步維艱。
其次,圍繞“校役向古董店老板賣葫蘆”的這一創作主題中,通過對古董店老板耐人尋味的言語、動作的描寫,如從“橫捧豎捧地仔細瞧了半天”,再到對作品故作漫不經心,神情冷淡,展現出一個精明狡詐的商人形象。文本對葫蘆價值的反復強調和校役和老板之間拉據式的金錢交易中反襯出清兵衛獨特的審美眼光,形成“拉回來又蕩出去”式的搖擺,展現了成人世界的虛偽和狡黠。
其三,小說在教員來訪時,情節達到高潮,重點描述了父親“發現葫蘆”到“逐個砸葫蘆”,展現出伏筆式的大“搖擺”,“一個一個砸碎”毀滅的不光光是清兵衛的葫蘆,還有孩子的個性愛好與自由。
在引導學生在對細節的比較分析中,我們發現教材對“搖擺”的知識進行了精簡和省略。如毛剛飛所說:“進入語文課程的‘短篇小說基礎知識’必須能夠有助于培養學生自身在接受語文科學教育中對其實際活動應用的掌握能力及對其語文教學素養的全面認識提升。”②在課堂教學脈絡中,小說情節發展的教學一直都是作為重點。對于高中學生來說,文本的情節的起承轉合,應該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如何實現情節發展的方式就比較難以掌握。因此在教學實施中,應該對情節展開方式進行重點分析,需要對本單元的話題——情節進行深刻學習,引導學生通過文本的閱讀和分析,進行“個性化閱讀”,形成對文本解讀的“身臨其境”,理解作者“搖擺”敘述方式的巧妙運用,找出文本案例中作者隱藏的使用方法和技巧,進而達到理通文通,為小說文本的廣泛閱讀提供可以借鑒的閱讀規律。
三 從結局的閉合回環中展現悲劇的命運本質
《伊勢貞丈家訓》中說道,“縱然丈夫如何無理,作為子女,不能對父親表示不滿和反抗,此天下大法也。”作為一位木匠,他希望兒子能夠像其他人一樣,哪怕隨波逐流,也好過整天擺弄那些“沒出息”的東西,所以最終以極其粗暴、專制的方式制止了兒子的獨特愛好。孩子珍貴的天賦在成人世界顯得不堪一擊。教員的簡單粗暴,母親的哭泣和父親的暴怒,古董店老板和校役買賣的拉鋸戰導致校役的隱瞞到底,清兵衛茫然不知自己喜愛的葫蘆竟然是一件珍品。葫蘆得到專業人士的認可其實暗含對清兵衛愛好的肯定以及對教育和父親等形象的辛辣諷刺。所有人都沒有發現清兵衛獨特的審美鑒賞能力,他的天賦就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小說中對母親的形象描述很少,在教員來訪只會“哭”和“怨”,母親軟弱到父親暴打清兵衛時,也未能及時阻止。夫權一手遮天,女性完全依附于男人,“不需要有主見和智慧,不需要話語權和存在感”。③文本最后兩個段落描述了在清兵衛拋棄了他的愛好葫蘆之后,雖然換取了父親表面上的和平,但是對繪畫的愛好依舊面臨著被他父親強烈反對的遭遇,如同他那種熱愛葫蘆的行為一樣,他的新興趣愛好在他父親眼里依舊是不務正業,上不了臺面。典型的“歐亨利式”的結局,結尾既出乎意料,又是處于情理之中。
故事的結局批判了家庭的專制、世俗的觀念和學校的保守對天才的扼殺。教育本應該培養人才,但是本文卻向我們展示了教育如何以愛的名義毀滅人才,甚至將這種毀滅無休止地延續下去。無知的教育者卻掌握著教育的權力,掌控著受教育者的喜好。作者以冷靜的筆觸暗示了無知、專橫的偽教育是如何把人毀滅的,體現出作者對獨立意識的重視,肯定自由的“自我本位”思想和個人主義的覺醒。
參考文獻
①曹文軒.《小說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②毛剛飛《從語文課程層層審視〈外國小說欣賞〉的“小說知識”》,《語文教研》,2008.5.
③岳倩.從《女大學》看日本近世女性的理想像[J],文學教育(中),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