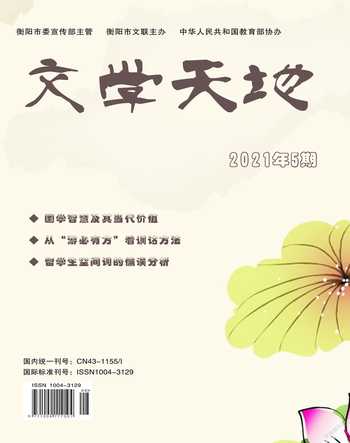“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再探尋
黃小楊
中國“五四”民間文學家們通過研究民間文學,對中國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見解。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既有縱的一面(即上有儒家的“上層文化”下有農夫村婦的“下層文化”),也有橫的一面(即既有殿堂之學也有不同地方的方言和區域文化)。“五四”民間文學家們發現了那些久被人漠視的歌謠和傳說,通過對于民間文學的認識,“五四”民間學家們打破傳統的“中國文化一元論”的看法,進而對中國文化有了一種比較全面和客觀的評價。
中國民眾所傳承的民間文化,雖存活在各個歷史時期并不斷為民眾的生活和精神需要所服務,但那些掌握文字和知識權利的傳統文人學者卻鄙視甚至敵視這一文化,只有極少數的文人學者偶爾注意到它們并給以記錄或稱贊,很長時期里它們被摒棄在正統文化殿堂之外。這種情形從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末期已經多少有些變化,而“五四”時期“到民間去”的提出,伴隨著一個知識群體自我認知與反思的過程。在近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意識到自身存在著問題更談不到有自我改造的意識。在對“民間”的關注及對知識分子與民間關系的定位上也是如此。當然,也有少數先覺者曾意識到這一問題。清末,嚴復在闡述致達富強之途時,曾再三強調開啟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稍后梁啟超作“新民說”,對作育新民以保種救亡之思想。顯然,嚴梁二人已經觸及到了晚清以來包括二人在內的知識界忽視“民間”這一問題,故而有呼吁重視民力之論。遺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社會大變動中,嚴、梁二人的言論未能得到及時的回應。
五四運動的發生既是一種要求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又是一個致力于社會革新和啟蒙的文化運動。有些文人學者開始有意地收集歌謠、諺語及笑話,或參與小說、戲曲的寫作及評論,但那較大的轉變卻要等到清末。由于民主意識的初步覺醒和西洋文化、思想的啟導,一些先覺的知識分子,對于民間傳承文化的觀察評價,有了較大的變化。城市民眾的文學樣式(如小說、戲曲、時調等)被肯定乃至于利用,民間歌謠、笑話等得到新的注視或評論,原始文學的神話也開始被用科學的觀點去解釋。
五四時期從提倡“到民間去”到真正走進“民間”,知識分子逐漸對“民間”這一概念有一個清晰的理解。從當時史實來看,這一時期知識界關于“民間”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民間”指的是人民大眾中間,且大體上經歷了由城市及于鄉村,由寬泛漸至具體并最終落實到“鄉間”的過程。在這里,中國知識分子通過對民間文學研究,發現了民眾的重要性,最后更發現了自己的社會角色和文化使命。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五四時期的文學家們對農民群體的認識大多有浪漫主義的成分,他們尚未意識到農民要世世代代為生存做痛苦的掙扎,其賴以生存的農業社會和農耕生活都毫不浪漫。魯迅一生對自己的故鄉浙江紹興魂牽夢繞,曾寫過不識字的鄉下人、默默無聞的村人仆婦怎樣善于講故事和唱民歌,他說:“農民們有一點余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在對浪漫主義與民間文學的關系詮釋時,浪漫主義學者普遍認為文化的進步大體上是對自然的一種破壞,浪漫主義作家對這種所謂的文化進步,特別是工業化造成人性的扭曲的后果十分不滿,他們對逝去的事物抱有懷舊的傷感,認為只能在歷史中找到真與善。中國民俗學者也擔心“外來因素”會像洪水猛獸一樣涌進農村,破壞民間文學,由此搶救民間文化成為民俗學者刻不容緩的任務。但是,正如德國格林兄弟曾明確宣布他們“研究民俗學的目的就是要重塑人們與德國的歷史”那樣,他們二人生逢民間文化久被遺忘難以重放光輝的浪漫主義思潮興起的時代,他們認為“民間文化中的神話、故事、語言和法律等長期被忽略,這是不公平的,事實上,它們都是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五四時期同樣如此,事實上,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從來都不對立,反而相互影響相互借力,為什么人們那么真誠地相信傳說?他們為什么相信長城能倒塌?化蝶結局對民眾觀念的真正寓意是什么?為什么人們對祝英臺的女性特征描述那么津津樂道?這些問題的實質在于傳說在這些方面道出了民眾心底的呼聲,這些民間文學是民間生存狀態的呈現、民間情感的關注、民間價值觀的剖析展現,民間文學自有自己獨特的價值作用。
在五四時期,民間文學研究者的目的是從民間文學中提煉出“反傳統反封建思想”的精神,用此喚醒全民族的自我意識,傳播新的思想。一方面,面對保守派的指責,這些主張變革的學者從流傳已久的民間智慧中找到反駁的證據;另一方面,愈發僵化和言不由衷的上層文學讓這批學者對鄉村生活和農民充滿了浪漫幻想,將所有民間看作是真誠的純粹的,從而希望能從他們身上找到治愈巨大精神災難的妙方。因此,上層文學和下層文學的概念被刻意放在了對立面,二者之間被認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而過分強調差異便很難宏觀地看出事物間的聯系,上層文學固然從下層文學中汲取了養分,但也不斷地向下層滲透,這種相互流通性和重合性成為了這些持二分觀點的學者在文化全景角度中的空白點。
民間文學研究者過于的浪漫主義至今仍然會出現在作家與學者群體,這多多少少體現在很多民俗文化研究作品的字里行間。現代知識分子自身的“負疚感”讓五四時期產生 “到民間去”的趨向,認為自此可從民間那里得到“樂土”,他們更多的是把民間文學當作了寄予藝術想象與民族希冀的功利性工具,大多五四時期的文學家與研究者并未真正脫離上層視野與趣味,不過,他們做了基礎的資料收集工作,也發現民間以及其中的時代性與功利性,為樹精英文學的假想敵而故意拔高。以民間文學研究為媒介體現的是五四知識分子精神史,民間文學能在百年前被“發現”,應放于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去看,那時的民俗學者普遍強調上層文學與下層文學二元對立,而放在今天我們更多需要強調多元性和去界限。“五四”時期“到民間去”的口號,進而一場帶來一場有關民間文學與民俗文化的運動,這一時期,民間文學與民俗文化本身雖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它承載著反封建反傳統的使命,這樣的運動已經彌足珍貴,在當下更有現實意義。我們從小應該是聽著自己的故事、唱著自己民謠、說著自己的方言長大,但這一現象在信息化智能化數據化的如今正逐漸變味,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們尚且還能做到對民間文學探尋以啟發人性,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民間”真的消失,我們又該怎么理解自己呢?
參考文獻
[1]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2]吳星云.“到民間去”:民國初期知識分子心路 [J].東方論壇,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