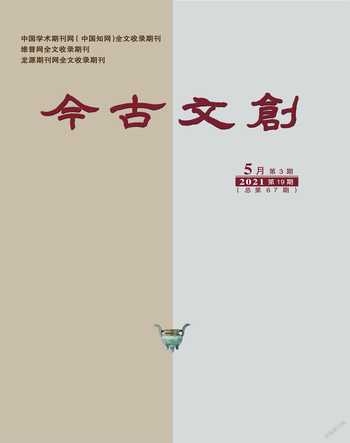淺談史鐵生《合歡樹》的“真善美” 價值追求
曹宇軒
【摘要】 作為經典的懷人抒情主題的散文,史鐵生筆下的《合歡樹》自發表以來便揚名萬里。在文本中,作者史鐵生借助“合歡樹”這一自然物象,旨在抒發其對于母親最真摯的熱愛與懷念。除此以外,這份難以言喻的濃濃深情久久縈繞在萬千讀者的內心深處,奏響了一曲曲頌揚親情的華美樂章。本文力圖深入探究《合歡樹》一文中,史鐵生不幸患病前后所展現出的激烈起伏的心理狀態變化,并企圖開辟嶄新視角,將視線投射于潛藏在暗處且時刻關注孩子情緒動向的堅強而隱忍的母親形象,二者結合,從而致力于進一步剖析《合歡樹》中簡簡單單卻又感人至深的點點滴滴,在平淡中體悟深情,在簡約中蘊含真、善、美。
【關鍵詞】 《合歡樹》;史鐵生;母愛;真善美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19-0013-02
誠然,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皆旨在追求真善美相統一的理想境界。就文學理論的專業知識而言,“真”指的是客觀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定規律性,顧名思義,追求真就是要求人的實踐合乎規律性;“善”意為善良、善意,常常用作形容人的美好品德的詞匯,旨在呼吁世人投身于社會、奉獻于他人,體現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合目的性;而“美”則透徹地體現了社會生活的純粹本質以及規律的具體形象,在某種程度上,追求美即要求世人在社會實踐中顧全大局,不僅注重事物本身的審美屬性,而且強調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辯證統一。
換而言之,真是美的基礎,善是美的靈魂,美是真與善的結合。因此,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都不能隨心所欲、肆意妄為,而必須遵循真、善、美的高度統一。史鐵生筆下的《合歡樹》一文,恰好凝練直觀地體現了文學藝術作品的“真善美”屬性,或許也正是由于這一顯著特點,才使得該文久久屹立于文壇之林。
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錢虹曾經談到:“《合歡樹》是一篇情真意切的懷人散文,也是一首頌揚母愛的動人樂章。”故而從文本整體可知,《合歡樹》既包含了作者本人及其母親命運的悲苦遭遇,又通過采用合歡樹的生長與開花暗示了小男孩的誕生和成長,不僅歌頌了母親的偉大與母愛的無私,而且展現了作者對生命與命運的認識。與此同時,作者的思想亦隨其階段角色的變化而在不知不覺中經歷了由悲苦無常到永恒不息的轉變,種種轉變皆顯示出了生命的脆弱與生生不息的希冀并存的深厚而復雜的情感,筆墨不多,要言不煩,可謂匠心獨運。
一、真:內容平淡 結構簡約
十九世紀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曾基于創作經驗斷言:“獲得全世界文明的不朽的成功秘密在于真實”“藝術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這個人體里去,把描繪變成真實。”因而,文學作品作為作家在假定的情境中,以主觀的感知與詩藝性的創造反映社會生活與自身感悟的物質載體,理應具備真實性與準確性的特點,也正是由于其真實而準確,方能促使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更為豐盈的精神財富,在不知不覺中塑造更為正確的價值觀念。
就《合歡樹》整體而言,該文是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藍本,采用一種平實、簡約、淡泊、洗練的筆調撰寫而成的一篇敘事懷人性的抒情散文。文本雖然僅有短短的一千余字,但史鐵生卻用類似剪影的形式拼接了“我”與母親相處的三個時間細節:十歲、二十歲與三十歲。這三個象征著時光流轉與時間推移的詞語匯集而成品讀文章的重要時間線索,不僅使得讀者能夠清晰透徹地了解到作者的生活軌跡,而且字里行間還蘊含著他對于亡母的深切緬懷與懺悔。
就《合歡樹》細節而言,開篇第一件事即“我在一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在交代了真實的事件的同時還與后文中史鐵生憑借撰寫小說聲名鵲起的事件遙相呼應;第二件事則為在史鐵生意外癱瘓后,其母為幫其治病而做出的種種努力,“母親的全副心思卻還放在給我治病上,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笨拙的舉動與真摯的行為無不從側面透露出事件的真實性。而最后一件事則呼應了文題中的“合歡樹”,一方面它自始至終都在伴隨著史鐵生與疾病做斗爭,而另一方面它在頑強生長的同時亦始終與史鐵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在文末,“我沒料到那棵樹還活著”,寥寥數字,既體現了史鐵生對生命出現奇跡的意外之情,又促成了他對自我生命的重新認識和再次定位。與此同時,這十個字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不僅與上文有關母子生活的畫面交相呼應,而且給予讀者豐富的想象空間,結構明晰、語言質樸、內容翔實,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暗含深意。
二、善:母愛無言 人文關懷
在眾多各不相同的題材領域中,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都擁有著獨屬自己且獨一無二的內容。誠然,人文關懷作為古往今來一切優秀文學作品的總主題,它不僅體現了“善”的終極價值觀,而且與歷史理性共同筑起了全新的文學功能價值體系,即兼容真、善及美。據資料記載,人文關懷來源于人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指的是對人性的關注和理解,旨在滿足廣大人民的正當需要,維護廣大人民的合法利益,從而實現人權的基本尊重。因而對于現世文學作品而言,人文關懷顯得尤為重要。
在史鐵生的《合歡樹》一文中,“人文關懷”的一面主要體現于其母親對其無微不至的關心與愛護。一般而言,贊揚母愛的文章總離不開對于母親的形象、性格及其音容笑貌的描述。而《合歡樹》卻是通過只言片語,將母親的形象零星拼湊而成的,譬如文章開頭,史鐵生寫道:“母親那時候還年輕,急著跟我說她自己”,一筆帶過正值風華正茂的母親,平直的語調中流露出母親的著急與可愛,而后又提及:“不過我承認她聰明,承認她是世界上長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給自己做一條藍底白花的裙子。”寥寥數字又高度濃縮了母親智慧的頭腦與漂亮的臉頰。
在后文中,“母親那時已不年輕,為了我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發”一筆帶過,對母親的肖像進行了簡單的描寫。“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表明母親為治療“我”的腿疾煞費苦心,一幕幕為兒奔波的畫面浮現于讀者腦海,一個含辛茹苦、飽經風霜的母親形象躍然紙上,給予共鳴。
而在文末,“她到處去給我借書,頂著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電影,像過去給我找大夫,打聽偏方那樣,抱了希望。”史鐵生雖然沒有任何一句溢美之詞,但字里行間依然能夠促使讀者認識到一位任勞任怨、寬厚仁慈且善良美麗的母親。在文章的最后,母親雖然已經逝去,但合歡樹卻依然在健康生長,暗喻母愛長青,母愛永恒。與此同時,這份母愛,也會像夜空中閃爍的星光,始終陪伴著“我”走出迷茫和孤獨,又悄無聲息地隱身在黎明里。因而,當史鐵生時時憶念母愛時,得到的不僅是溫暖和力量,還有鞭策與責任。
總而言之,盡管史鐵生只字未提自己對于母親離去的傷痛與懊悔,但卻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對母親近乎全部的情感與希望寄托在合歡樹這一意象上,促使合歡樹的投影在無形之中演變為自己對母親情感的傾瀉,不可收覆、肆意延伸。不禁讓人感嘆:最熾熱而濃烈的母愛竟然是悄無聲息的;而最深沉且厚重的母愛,卻總是以合歡樹般曼妙而輕盈的姿態呈現,繁雜瑣碎的細小事情與質樸無華的涓涓深情相得益彰,字里行間所流露的深深母愛,使世人讀來久久難以平息,引起強烈的共鳴感。
三、美:歸于沉靜 生命永恒
我國當代美學家宗白華說:“文學的審美境界的實現,端賴藝術家平素的精神涵養。”因而讀者不難可知,《合歡樹》的審美意象不僅源于對母親的懷念以及對母愛的眷戀,而且亦來自時過境遷后對世事的淡然處之與淡泊明志。世人固然無法否認《合歡樹》是圍繞著母親這一主要人物形象來刻畫的,它也的確表現了最為深沉的母愛,但更多的應該是表達了一種歷經無盡滄桑與悲慘事件后的沉靜與淡然。正是由于這種沉靜,才促使史鐵生擁有了獨自面對生活的勇氣,也正是由于這種淡然,才幫助史鐵生逐步理解了母親先前的良苦用心。
換而言之,從根本層面而言,這其實是一種大徹大悟,是一種超凡脫俗,更是一種看似輕描淡寫,實則重過千鈞的不容輕視的人生力量。在二十歲患病初期,他的自暴自棄,他的妄自菲薄,令年輕貌美的母親雪花殘月,在歲月的摩挲下,迫使面龐習慣了蕭風的摧殘而變得粗糙不堪。文中借他人之口寫道:“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這一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語背后蘊含的是對生命與生活的嶄新思考,樹生長的茁壯程度亦象征著人類生命的永恒。史鐵生通過側面描寫的方式,著重展現出合歡樹的茂盛與堅定,促使合歡樹在無形之中給予了作者強烈而有力的生命導向作用,逐步激發起作者對于如何面對人生中難以預料的突發悲劇這一深奧問題的探索之心,不僅具有極高的哲學意義,而且其審美功用亦不容小覷。
四、結語
《合歡樹》的寫作開啟史鐵生對人生、生命、命運等問題的哲理性關照的探索過程,在他之后的散文創作中,這一系列問題得到了更為豐富的闡釋。《合歡樹》作為其經典之作,平淡中蘊含著深情,簡約卻又勝過繁文,語言平實質樸,感情真摯動人,讀來受益匪淺、難以忘懷。
參考文獻:
[1]范欣欣,石宏偉.真善美——文學藝術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J].名作欣賞,2007,(12):139-141.
[2]江足寧.文學藝術弘揚真善美對建設和諧文化的時代價值[J].軍隊政工理論研究,2007,(03):29-30.
[3]王海娜.真善美——文學的價值追求[J].商業文化,2010,(04):206.
[4]王繁.苦痛之后的沉靜——重讀《合歡樹》[J].中學語文,2020,(25):48-50.
[5]唐福玖.重讀《合歡樹》的幾處細節[J].語文教學與研究,2020,(09):102-104.
[6]錢虹,史鐵生.平淡蘊深情 簡約勝繁文——《合歡樹》課文導讀[J].名作欣賞,2003,(09):38-40.
[7]徐恩仙.只見淚滴,不聞哭聲——淺析《合歡樹》的語言藝術[J].課外語文,2015,(20):197.
[8]史鐵生.合歡樹[J].意林文匯,2020,(11):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