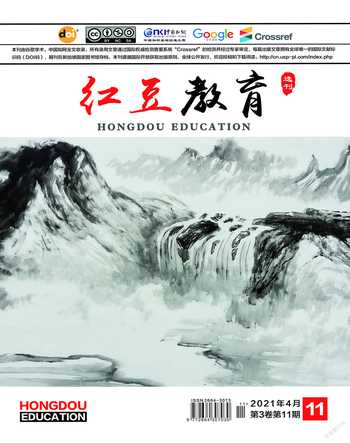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的創意傳播路徑
【摘要】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以及移動網絡技術的支持下,新媒體已然成為與紙媒、電視等傳統媒體相提并論的“第五媒體”,并且逐漸成為現代人信息發布、交流、獲取的主要途徑。在現代社會生活節奏日趨加快的背景下,新媒體以不可遏制的勢頭逐漸成為社會的主要媒體形式,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圖書館作為文化服務機構,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新媒體實現傳播層次和傳播效率的提高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圖書館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空間。因此,在新媒體背景下,探究圖書館的創意傳播路徑,在新時期實現圖書館文化傳播的轉型,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新媒體;圖書館;創意傳播;路徑
根據中國互聯網中心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網民規模已經達到9.89億,而且互聯網普及率高達70.4%。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到9.27億,在網民整體中占93.7%,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8.73億,在網民整體88.3%。從我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以及用戶規模的整體情況來看,無論是在線教育、在線醫療、在線政務,還是電商零售、娛樂消遣,網絡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們交流、互動、溝通、信息獲取的主要平臺。特別是艾媒資訊的統計報告顯示,中國數字閱讀行業用戶規模已經達到5.1億人次,尤其是年輕人在線閱讀的頻率已經明顯高于傳統紙媒閱讀的頻率,這就意味著傳統不借助互聯網的文化輸出模式已經不適用于新媒體時代,新媒體背景下,大眾文化素質提升以及個人能力發展都開始借助于現代網絡途徑。所以對于圖書館來講,如果圖書館在媒體形式改革與創新的新階段,不能有效地迎合時代發展的客觀需求,勢必會逐漸被時代和閱讀市場所淘汰。因此如何實現傳播路徑的創意化,滿足讀者日益多元的閱讀需求,是當代的圖書館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一、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掌上傳播路徑
(一)圖書館資源的“掌上化”
圖書館資源的“掌上化”顧名思義就是指將傳統圖書館的線下資源以數字化技術進行掃描、上傳,并通過線上移動網絡渠道,在移動網絡環境中,打造一個虛擬的線上圖書館,并以APP作為門戶,讓讀者可以足不出戶就能夠獲得圖書館內部的所有資源、信息。當然,想要實現圖書館資源的“掌上化”并不容易,一方面對于圖書館來講,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進行技術研發,尤其是APP設計,如何能夠凸顯出圖書館內在的文化底蘊以及圖書館的品牌文化標識是圖書館APP設計與應用的重中之重,而這對于大部分圖書館來講,在不能有效自負盈虧的情況下,想要維持圖書館APP的運營并非易事。而另一方面,對于圖書館來說,要將圖書館所有線下儲存文獻,尤其是地方志、地方文獻資源進行數字化處理,同樣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財力的支持,很多原始文獻本質上并不支持數字化處理,所以如何能夠在保存好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實現文獻資源的數字化,推動圖書館內部資源的高度優化也是目前圖書館資源“掌上化”發展的客觀阻礙。在這方面,解決這兩大難題可以充分參考國家圖書館的“掌上國圖”。
不可否認的是,國家圖書館相較于大部分圖書館來講都具有豐富的資源基礎和財力基礎,但是通過“掌上國圖”能夠看到的是,國家圖書館切實有效地利用圖書館的數字化發展將文化服務通過線上的方式進行了創意化的傳播,而且切實的將線上圖書館與線下圖書館有機結合并依托于自身資源向大眾提供了多元文化服務內容。從期刊、學術到書籍、數據庫等,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掌上國圖”為很多省市地區的大型圖書館提供了創意傳播的發展路徑,也為圖書館在新媒體背景下的轉型提供了可以參考和借鑒的模板。
(二)圖書館資源的“視聽化”
圖書館資源的“視聽化”是指將線下資源以播講、視頻演繹、課程講解等方式對外傳播和輸出。對于圖書館而言,在新媒體背景下,網絡資訊和信息不斷豐富且駁雜的情況下,圖書館本身具有的專業性以及權威性是其他網絡渠道和平臺不可替代的,這也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可以實現創意文化傳播的必要條件和核心競爭力。但是相較于以往的文字閱讀來講,在當前社會節奏持續加快,對文化傳播的感官認知需求呈現多元化的情況下,圖書館資源的“視聽化”可以說是參考網絡視聽資源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全新的文化輸出模式。
國家圖書館開發的“掌上國圖”APP除了將國家圖書館內部資源實現了數字化和掌上化以外,更突出的特點就在于其將部分文獻、書籍資源進行視聽化處理。在“掌上國圖”聽書功能中,從國學啟蒙、歐美經典,到中外小說、中外童話應有盡有,劉慈欣的《三體》、韓寒的《三重門》,可以說“掌上國圖”并沒有過度彰顯權威和嚴肅性,而是真正意義上從文學發展視角出發,將傳統文學、現代文學等多元文學形式都進行了“視聽化”處理,能夠有效地滿足線上讀者的閱讀需求和閱讀體驗。而且“掌上國圖”不同于其他圖書館傳統文化傳播的地方在于,其還將各種公開課也納入到了線上的APP中,例如趙豐的《絲綢之路與絲路之綢》、《錦程》等課程,而且這些課程在“掌上國圖”中是完全免費的,這無疑能夠充實國家圖書館的線上文化輸出內容,提高了“掌上國圖”的文化傳播層次和水平,也是國家圖書館創意傳播的集中體現。不過,結合“掌上國圖”的設計與應用,從圖書館掌上傳播路徑本質上來講,更適合于省市級大規模的圖書館,這些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而且具有一定的財力基礎,既能夠實現自負盈虧,同時也可以有效地利用掌上APP的開發實現圖書館文化輸出價值的落實,履行圖書館教化大眾的責任,在新時期發揮圖書館對全民素質提高的作用與價值。
二、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微”傳播路徑
“微”傳播路徑從新媒體發展層面來講雖然表面上表現出了一定的滯后性,但是從“微”傳播的主體平臺來看,對于圖書館新媒體背景下的創意傳播來講,“微”傳播并不過時。根據微博發布的《微博用戶發展報告》來看,微博2020年的月活躍用戶在5.11億,而微信的用戶已經達到5.49億,可以說,在我國網絡用戶中,有超過半數的用戶都在使用微博和微信,這就意味著對于圖書館的文化傳播來講,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微”傳播路徑,即便是在當前新媒體形式逐漸的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下,依舊是可以凸顯圖書館文化底蘊和內涵的創意傳播模式。
(一)微博傳播
微博作為當前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主要信息共享平臺,其不僅具有門檻低、傳播速度快、共享性強等特點,最主要的特點在于其互動性強且能夠精準定位,而這是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創意傳播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相較于網絡駁雜的信息資訊來講,圖書館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其信息具有權威性和專業性,所以微博能夠為圖書館提供文化傳播的可行平臺,幫助圖書館將各種活動和話題實現廣泛的傳播,并且帶動的用戶進行討論與交流,有助于圖書館吸引讀者、傳遞服務定位,并為圖書館的線下文化服務奠定堅實的基礎。例如,上海圖書館就曾通過微博平臺與圖書館閱讀量相對較大的讀者量身定做,具有個性化的閱讀賬單,并通過微博平臺進行發送,一時間,讓上海圖書館吸引了廣泛關注,并且奠定了上海圖書館文化服務的基本屬性。
與此同時,上海圖書館還利用新浪微博的線上活動,例如有獎征集、有獎轉發等活動,針對不同的閱讀群體,向微博用戶提供并共享了多元化的圖書閱讀、獎品服務,有效地實現上海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高度交流,樹立了上海圖書館的在線網絡形象,不僅有效地促進上海圖書館文化傳播責任的履行,更主要的是為上海圖書館自身品牌和網絡形象的塑造、傳播與發展提供了助力。此外,上海圖書館利用微博實現創意傳播的經驗還在于有效地實現了新媒體線上渠道與線下圖書館之間的有機對接,通過微博,直播圖書館的書展服務、直播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直播“專家講堂”講座,甚至是直播讀者在圖書館的求婚儀式,可以說上海圖書館真正有效地利用了新媒體,特別是微博打造了更加親民的圖書館形象,并且改善并優化了圖書館在民眾心中的形象,讓上海圖書館的影響范圍不僅局限在上海市內,甚至是很多其他省市地區的讀者都以上海圖書館為目的地參與到上海旅游活動中,凸顯了上海圖書館的文化傳播價值,同時也打造了上海圖書館的商業和經濟價值。
(二)微信傳播
對于大部分圖書館而言,想要效仿國家圖書館打造全新媒體模式的數字化圖書館并不容易,國家圖書館的“掌上國圖”也并不適用于所有圖書館,但是通過微信公眾號來打磨圖書館的傳播路徑,并且借助微信公眾號功能向大眾提供多元化的閱讀服務,對于大部分圖書館來講都可以有效適用,也是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創意傳播路徑的一種可行方式。
廣州圖書館的微信公眾號閱讀服務歷經多年打磨已經逐漸成為圖書館書目檢索、逾期支付、附近圖書館查詢等功能于一體的文化服務平臺。當然相較于功能齊全的APP媒體渠道來講,微信公眾號的閱讀服務平臺確實很難向所有讀者提供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閱讀服務,但是通過微信公眾號,圖書館可以打破傳統線下文化服務和文化傳播的模式,構建線上和線下并行的一種服務模式,通過將圖書館的信息、咨詢以及微刊等內容融入到微信公眾號中,切實有效的豐富用戶的圖書館線上應用體驗。而且不同于微博傳播的地方在于,微博更多地趨向于廣場化的交流、活動、溝通與互動,而微信公眾號能夠滿足用戶個人的特色化需求,實現讀者對圖書館的全面認知和了解,以便于為讀者通過圖書館獲得自我提升、自我發展創設必要的途徑和條件,提高讀者的體驗層次,以便于強化讀者對圖書館的用戶黏性。
對于大部分圖書館而言,在自身財力、物力、人力不支持圖書館大力開發APP,維護APP運營的情況下,雙微文化傳播是圖書館可以嘗試并且參考和借鑒的創意傳播方向,一方面能夠有效地實現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相互關聯,提高讀者與圖書館之間的交互頻率,而另一方面則是可以深層次地塑造圖書館的全新形象,打造線上線下的立體品牌,以此在新媒體背景下,煥發出圖書館的全新升級與活力。
三、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短視頻”傳播路徑
短視頻的快速發展,標志著新媒體進入到全新的發展階段,短視頻也逐漸成為新媒體背景下重要的傳播平臺。很多圖書館都有意識地通過短視頻平臺來搭建創意傳播的渠道,開辟全新的文化輸出路徑,例如江西省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
從江西省圖書館的短視頻內容來看,江西省圖書館通過短視頻平臺發布的視頻內容及包含了江西省圖書館的整體介紹,也包含了書籍推薦、讀者訪談、文化創意產品推薦等。而浙江圖書館的視頻內容則更多以文化輸出為核心,更多地滿足用戶的獵奇心理。綜合來看,短視頻平臺上的圖書館文化輸出效果可以看到,就目前來講,圖書館的短視頻傳播路徑開辟水平還是相對有限。一方面是短視頻制作內容的精致程度相對有限,雖然部分圖書館切實把握住圖書館所具有的文化屬性和文化傳播特點,將文化內容作為視頻內容的內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迎合用戶獵奇心理的特點,并沒有真正意義上挖掘出圖書館在短視頻平臺上文化輸出的潛在價值與作用。在這方面,圖書館要通過短視頻來開辟全新的創意傳播路徑,就需要契合短視頻平臺的特殊性,打造優質的短視頻內容。或是通過剪輯,將具有全民認可度的影視內容作為剪輯和文化內容傳播的“底色”,借助這些影視內容來實現更深層次的文化傳播,既可以做到引流的作用,同時也能夠進一步達到深化文化傳播層次的目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短視頻題材選擇偏失,短視頻平臺盡量來的發展,存在明顯的泛娛樂化現象,但是短視頻平臺作為新媒體背景下,擁有廣泛用戶的信息傳播渠道,圖書館在進行短視頻傳播的過程中應該秉持著圖書館應有的權威性,當然,這種權威性與圖書館內容制作的親民性本質上來講并不沖突。在娛樂化信息帶給用戶頻繁沖擊的背景下,優質的文化輸出其實更能夠獲得用戶,尤其是年輕用戶的青睞。所以,對于圖書館而言,在新媒體背景下開辟短視頻傳播路徑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結語
綜合上述研究內容來看,在新媒體背景下,圖書館創意傳播路徑其實已經開始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無論是國家圖書館的“掌上國圖”、還是浙江、江西省的短視頻文化傳播,亦或是上海圖書館的微博傳播和廣州圖書館的微信傳播,都給圖書館的新媒體創意傳播提供了一定的范式。
參考文獻:
[1]臺鈺瑩.多平臺環境下公共圖書館新媒體運營研究[J].新媒體研究,2020(07):80-82+87.
[2]胡瑋瑋.公共圖書館與新媒體資源整合策略[J].時代報告:學術版,2020(001):86-87.
作者簡介:王昌鴻(1970.03.29-),男,漢族,籍貫:遼寧沈陽人,沈陽大學圖書館,中級館員,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