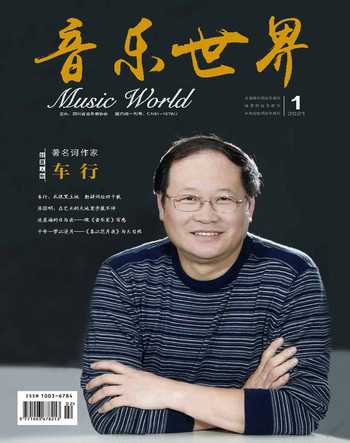古琴背后的故事

〔摘 要〕述說古琴背后的故事,“敷詠天淵”說“龍璈”。對“四唐琴”之一的“龍璈”琴的淵源一探究竟。
〔關鍵詞〕古琴;“龍璈”琴;背后的故事
一、因緣
2020年3月初,青年古琴演奏家鄭曉韻博士來電,告知她的系列古琴講座“曉韻談琴”即將在四川大學博物館設壇開講,作為前期準備工作的一部分,館方請她入庫探訪館藏古琴,她誠摯邀我一道赴四川大學博物館訪琴,對此因緣,我欣然隨喜。
近幾年,因為學琴,連帶對琴史、琴人及傳世古琴有所了解,寫過一些文章,特別是有關著名琴家裴鐵俠夫婦史事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引鳳”百衲琴及“雙雷”的玉碎》在琴界和學界產生反響,厘清了過去坊間一些不實的說法,被廣泛引用和轉載。
以前我對四川大學博物館館藏古琴的整體情況了解不多,因為寫裴鐵俠夫婦的緣故,只知道當年被裴先生目為“四唐琴”之一的“龍璈”琴,是川大博物館館藏八九張古琴中的佼佼者。能有機會一睹此琴,實在心向
往之。
二、身世迷離
關于“龍璈”琴,可以說它是一張命運多舛的古琴,也是一張身世撲朔迷離的古琴。它是如何入藏四川大學博物館的,學界及館方甚至裴鐵俠的后人皆語焉不詳,只籠統地說是上世紀“50年代征集”。不像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裴鐵俠的其他四張琴——“引鳳”“竹寒沙碧”“寒玉”“醉玉”——“這是由我父親裴墨痕(元翰)于1951年捐贈給省博的”(裴小秋(家滎)《我的祖父裴鐵俠》 )那樣流轉清楚,究竟它是如何入藏四川大學博物館的,到目前為止,仍然還是個謎。
蜀中著名琴學家唐中六老師在其大作《巴蜀琴藝考略》中,記述巴蜀傳世名琴甚詳,幾乎每張琴都“有圖有真相”,談到這張琴時,是這樣說的:
四川大學博物館今藏古琴一床,名“龍璈”(原文誤為嗷),仲尼式,紫紅色,十三徽全,為螺鈿質,琴體完好,琴身通體裂斷紋,附件齊全,保管甚佳。該琴在20世紀50年代前由裴鐵俠收藏,裴氏生前將“大雷”“小雷”“古龍吟”“龍璈”(原文誤為嗷)并稱為“四唐琴”。現考證“龍璈”(原文誤為嗷)為宋琴。此琴什么時期、在怎樣條件下被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無從知曉。
至于該琴銘款、形制的其他細節及照片等,唐老師的書卻付之闕如,令讀者諸君如我者,滿是遺憾和期待。
要知道,當年這張琴可是裴鐵俠最為看重的“四唐琴”之一,“四唐琴”中的“大雷”“小雷”已于1950年6月4日隨裴鐵俠夫婦慘烈“玉碎”,“同登仙界”(詳見裴小秋(家滎)《我的祖父裴鐵俠》及拙文《文物背后的故事——“引鳳”百衲琴及“雙雷”的玉碎》,裴氏夫婦和“雙雷”玉碎的具體日子,近日已被學者、書法家向黃先生精確考證為公歷6月4日),而“古龍吟”流落上海,具體琴況不詳。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成都琴人雅集,每于裴府和喻紹澤、喻紹唐故居舉行琴會。琴會中,除不能演奏的“大雷”外,就數“小雷”和這張“龍璈”最為有名了。請看古琴名家喻紹唐的一篇雅集記錄:
民國三十六年(1947)正月十一,社友等應裴君之約于裴宅首次琴集。午前十時,李燮和(璠)和伍洛書均已先到。日中馬瘦予、紹唐、紹澤聯袂而至。伍君攜有新斫仲尼式琴一張,色深赭,體甚修偉,為近年所見大琴恐未有出其右者。面青桐,底老杉。休息片時紹澤即用該琴奏《高山》一曲,音甚洪大,巍巍乎,子期之聽或亦類此大琴乎!夫元明之時斫琴者已多不合法,若近代更瞠乎其后矣。伍君考古證今悉心研究提倡造琴之興趣,良非斟也。裴君亦出其先年所斫仿大雷琴式一床,音亦洪松較之伍所斫有過之而無不及。裴君繼用所藏龍璈古琴奏《秋鴻》操。社友等久未聞裴君鼓此操,故皆悚耳靜聽,聆一室之中除琴音外不聞有一點其他聲音,一時覺鴻雁來賓,恍若置身于霄漢之間……
雅集中,裴鐵俠用“龍璈”古琴演奏《秋鴻》,竟讓喻紹唐等“久未聞裴君鼓此操”的社友們,“皆悚耳靜聽”,“一時覺鴻雁來賓,恍若置身于霄漢之間”,這則琴會記錄除了說明裴鐵俠的琴藝高妙外,“龍璈”古琴的音聲之美,自不在話下。
三、一睹芳容
3月9日,鄭曉韻博士來電,說已經和博物館約好,11日下午兩點整去訪以“龍璈”琴為首的四川大學博物館珍藏古琴。經過幾天漫長的等待,好不容易等到了11日。午后,和鄭曉韻博士及川大古琴社的王心嫄等三位小友按時趕往四川大學博物館,心里免不了還是有些激動,像是要去見一位心儀已久終于可以見面的朋友時的心情。
接待我們的是庫房管理部的達瓦扎西老師,他說,霍巍館長親筆批示,只允許鄭曉韻博士和我兩人可以進入藏品庫內親炙寶貝,琴社的三位小友則只能在庫房外面。對于這樣難得的機緣,我心中充滿感恩。
達瓦扎西老師非常專業,辦完嚴格的簽字手續,按照規定要求我們將所有背包存在庫外后,便帶領我們只攜上兩架相機進入了戒備森嚴的庫房。他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打開庫房藏品柜,取出珍藏的古琴,一張一張讓我們認真細看、拍照。除三四張琴做工較精致外,其余不足觀,甚至有一張充其量是道具琴,琴身輕而薄,琴首作夸張的雙髻狀,像個米老鼠的頭,做工粗俗,是行內俗稱“家具琴”者。在看過六七張明清各式琴后,扎西老師遺憾地說,為配合非遺系列講座,前兩天陳展部已經將“龍璈”琴陳列到一樓大廳的展柜中,我們今天只能隔著玻璃展柜一睹芳容了。
一樓展廳不太顯眼的位置,“龍璈”琴靜靜地立在展柜中,在冷光燈的烘托下,清晰可見殘存的三根絲弦稍顯松弛地掛在琴面上,七枚青玉軫歪歪斜斜地擠在軫池中,全靠著絨剅的牽扯才不至于掉落下來。十三徽不像螺鈿質的,而是金徽,只因年代久遠,間有修葺、蒙塵,金徽有些黯然甚至剝落。琴底琴面均有數處朱漆補髹的痕跡,青玉雁足也是精致的鏤雕花卉紋飾,透露出些許華貴、雍容。而整張琴就像一條飽經風霜、歷盡磨難的老龍,不聲不響地蜷曲一隅,默默注視著變幻莫測的人世,有幾分無奈,幾分落寞,更似有一聲“弦斷有誰聽”的沉重嘆息。然而畢竟是身世不凡的宋琴,那滿身的蛇腹斷紋和細密的牦牛斷紋,依然從經典的器形、精致的做工和斑駁的漆色中展現出少有的美麗風華。誠如網絡語言所形容的,“和你只隔一厘米遠,卻不能輕撫你的容顏”,此刻佇立在展柜外端詳這張名琴,正是這種感覺。
仔細分辨琴底板上的琴銘,頸處龍池上方是非常整飭、精致的陰刻篆書琴名“龍璈”兩字,龍池兩側齊肩處從右至左是兩行陰刻楷書銘款:“飛龍九五,敷詠天淵;大璈大夏,兮哉圣賢。”(標點為筆者所加),結體謹嚴,筆力精勁,頗具唐賢楷書的法度。
要讀懂這段銘文,就不得不說到《易經》。“飛龍九五”中的“九五”一詞源于《易經》的首卦——乾卦。乾者象征天,因此也就成了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條陽爻組成,是極陽、極盛之相。從下向上數,第五爻稱為九五,九代表此爻為陽爻,五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爻,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因此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最佳一爻了。這里的“九”本不是具體的數字,而是判別數字陰陽屬性的符號。九五固然是乾卦中最好的一爻,但九五代表至尊倒也不全是因為它最好。實際上每個爻位都有特定的代表意義,第五爻本來就是君位,這個位置代表的就是帝王,在乾卦中陽氣在這個位置達到最盛,代表的是廣施德行,慢慢積累,從初九到達這里,恰恰是最中正剛健的好位置,這個位置就是帝王之德的象征,別的身份不可能配得上這一爻。所以《易·乾·象》曰:“或躍在淵,進無咎也(九四)。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孔老夫子也解釋為:“圣人作,而萬物睹。”
再來看《辭海》 “九五”條,釋文如下:“ 《易經》中卦爻位名。九,陽爻;五,第五爻。《易·乾》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穎達疏:‘言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飛龍在天……猶若圣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后因以‘九五’指帝位。”(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2002年版縮印本第871頁)
我們可以這樣來推斷:“龍璈”琴的原主人定是身居帝王之位,琴上銘文既喻示了其九五之尊的地位,也是對圣人作(琴)器由衷的贊嘆。試譯成白話即:飛龍高居九五之尊,布施詠唱于天淵之上;偉大的樂器偉大的華夏,啊,偉大的圣賢!
正因“四唐琴”的地位尊崇,裴鐵俠才沒有像他收藏的其他琴那樣,再在琴底上鐫刻自己的名款、印章。因此,此琴如果斷為宋琴的話,其原主人當在宣和殿(北宋皇宮著名宮殿,前后經歷始建重建,后稱保和殿,用以藏書藏畫,北宋皇室三大藏書處所之一。著名的《宣和書譜》《宣和畫譜》都與此殿關系密切。北宋末年,宋徽宗在宣和內府設“萬琴堂”,廣羅天下古琴神品于其中)里求之。
拙見只是拋磚,究竟如何,仍有待學界、琴界的繼續挖掘和研究。
(本文照片由茍世建、鄭曉韻提供)
參考資料 :
①唐中六:《巴蜀琴藝考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②楊曉:《蜀中琴人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版。
③紹南文化:《易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