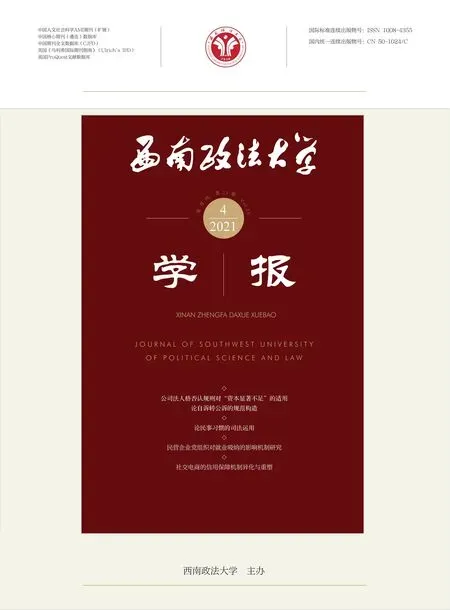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正當根據(jù)與司法適用
王登輝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法的立改廢釋,是為了解決和防范現(xiàn)實存在的、將來會發(fā)生的問題,應當符合天理人情、公共理性,既體現(xiàn)民意又避免情緒化、民粹化;立法一般會有理論依據(jù),但不等于必須以某個理論、學說為出發(fā)點,畢竟原則和例外并存乃是常態(tài)。刑事立法追求的是一個相對最優(yōu)的解決方案,而不是能夠“徹底解決問題(杜絕犯罪)”的完美方案——這是脫離實際的。如何劃定犯罪圈,將哪些主體、哪些行為納入犯罪圈,需要利益衡量、價值取舍,主要是刑事政策作用于立法的過程,而不是抽象演繹的過程。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到來,未成年人惡性違法犯罪行為因其自帶超強傳播力而被更多民眾所知,其中不滿14周歲的人實施弒親、弒師、殘殺同學和鄰居等惡行因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而不負刑事責任,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和巨大爭議。要不要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宜選擇哪種解決方案,利弊如何,眾說紛紜,值得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一)問題的由來
我國1997年《刑法》第17條對刑事責任年齡作了具體規(guī)定,即16周歲以上的人對一切犯罪均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以下簡稱“14~16周歲”)的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zhì)共八種罪行負刑事責任(1979年《刑法》第14條第2款規(guī)定的四種罪行“殺人、重傷、搶劫、放火”得以沿用);不滿14周歲的人對一切罪行均不負刑事責任。這一立法例屬于“三分法”,同意大利、瑞士、保加利亞、泰國等國的相關規(guī)定頗為接近。幾乎沒有人認為,14~16周歲的人對這八種嚴重罪行負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過于嚴酷而應當刪減罪行,或過于寬松而明確主張應當增加罪行。鑒于主張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大多數(shù)主張下調(diào)2歲,故本文主要從立法角度探討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以下簡稱“12~14周歲”)的人的刑事責任問題。
2020年10月21日,中國人大網(wǎng)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審議稿)》規(guī)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jié)惡劣的,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應當負刑事責任。”同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規(guī)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jié)惡劣,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說明:立法機關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采用的是“年齡+罪行+程序控制”模式,遠非“一降了之”;12~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以下簡稱“兩種嚴重暴力犯罪”),且符合“情節(jié)惡劣”“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條件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不涉及14~16周歲的人、16周歲以上的人這兩大群體,并不是“普降”;不滿12周歲的人不是任何犯罪的主體,其實施任何罪行,均不負刑事責任。有人認為,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擴大了犯罪圈”,違反了刑法謙抑主義的要求,過于苛刻、嚴酷,故欠缺正當性。但這種觀點犯了教條主義、“好人主義”和掩耳盜鈴的錯誤,以致泛道德化的說辭是蒼白無力的。鑒于質(zhì)疑者較多,從理論上闡明立法規(guī)定的正當性,頗有現(xiàn)實必要性。
(二)真正的問題是什么
找準問題,是分析問題的前提,但并非易事。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罪行是客觀存在的,同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不會因為不將其評價為犯罪而不存在或者可以忽視。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在全部犯罪中的比例、總體趨勢(1)例如,2018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人數(shù)為3.4萬人,與上年基本持平,比2010年減少3.4萬人,降幅達49.6%。未成年人犯罪人數(shù)占同期犯罪人數(shù)的比重為2.41%,比上年下降0.17個百分點,比2010年下降4.37個百分點。青少年作案人員占全部作案人員的比重為17.2%,比上年下降2.1個百分點,比2010年下降18.7個百分點。參見國家統(tǒng)計局:《2018年〈中國兒童發(fā)展綱要(2011—2020年)〉統(tǒng)計監(jiān)測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2/t20191206_1715751.html,2019年12月6日發(fā)布。2021年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顯示,2016年至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14~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5890人、5189人、4695人、5445人、5259人,占受理審查起訴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分別為9.97%、8.71%、8.05%、8.88%和9.57%。通過這些數(shù)據(jù),可以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概況有初步了解。當然,不滿14周歲的人實施了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不負刑事責任,并不會納入上述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如何,14~16周歲的人實施八種罪行的總數(shù)和趨勢如何,12~14周歲及不滿12周歲的人實施嚴重罪行的趨勢如何,對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應當產(chǎn)生影響,至少不是所需考慮的重要因素。不滿12周歲的人受體力、智力、閱歷等的制約,很少實施惡性犯罪行為,這些情形目前可以忽略不計;主流民意出于法治文明、人道主義等考慮而不欲使之負刑事責任,也是重要因素。12~14周歲的人實施嚴重罪行的絕對數(shù)量如何,是否很小以致可以無視,才是值得重視的方面。
現(xiàn)在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絕不表明以后也會下調(diào);今后是否再次下調(diào)(或者上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未來之事,自然由將來的民意決定,并非現(xiàn)在所要解決、所需考慮的問題。由現(xiàn)在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推導出以后會再次下調(diào),犯了“滑坡謬誤”的錯誤,不能作為反對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理由。
如何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身心特點和改造規(guī)律的行刑制度、幫助其回歸社會、防范其在服刑期間學到更多的犯罪方法,只是配套措施而已,與該不該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無關。被判刑的少年犯面臨“被未成年犯管教所這個大染缸染黑”的風險,不是否認其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理由。有趣的是,幾乎無人擔心其可能“把未成年犯管教所里的其他少年犯染得更黑”。可見,人們潛意識里把少年犯當作“罪惡輸出”的被動接受者,而忽視了其可能仍是“罪惡輸出”的主體。實際上,即使犯有嚴重罪行的少年未被定罪處罰、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仍可以掌握并傳授諸多犯罪方法。這樣說,并不是否認低齡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可塑性較強;嚴格地說,犯罪人的可塑性與定罪量刑無關,只是行刑階段會考慮的因素。
未成年人幾乎沒有自己的財產(chǎn)可供賠償,其監(jiān)護人往往不愿意賠償,或者遠不足以賠償。《行政處罰法》第30條規(guī)定:“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有違法行為的,不予行政處罰……”2012年修正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1條規(guī)定:“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或者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的,依照本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不執(zhí)行行政拘留處罰。”這決定了,對觸法未成年人很少行政處罰,即使處以行政拘留也很少執(zhí)行,對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更是毫無威懾力可言。民事經(jīng)濟手段、行政手段對低齡未成年人的嚴重罪行軟弱無力,幾乎沒有什么預防效果,還會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這體現(xiàn)了法律家長主義的事前缺位、刑法的預防性不彰,也傷害了人民群眾的正義感、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權威。如果明知“惡不能退,害不能除”仍無所作為,面對嚴重罪行堅持不作為,放棄社會防衛(wèi)、放任熵增,體現(xiàn)了異化的、病態(tài)的價值觀,很難說是明智的。審時度勢,作為二次法的刑法適時出場調(diào)整這些社會關系,很有必要性。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現(xiàn)實中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實施了嚴重罪行,何種處理方案是最合適的?申言之,如果12~14周歲的人實施了《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嚴重罪行,最優(yōu)或相對最優(yōu)的解決方案是什么?其實施的哪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宜作為犯罪制裁?如果囿于現(xiàn)行法律而不能實施該方案,可以考慮修改法律使之實現(xiàn)。
(三)問題的關鍵是什么
刑事責任年齡的關鍵在于物質(zhì)基礎:當今12~14周歲的人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是否達到了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或曰是否與1980年1月1日以后(或者1997年10月1日以后)已滿14周歲的人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相等或相當。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可以認為精神正常的行為人對部分嚴重罪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人們都承認當代少年營養(yǎng)好、發(fā)育早(甚至早熟)、知識多、見識廣,在身高、體重、腦容量、信息獲取等方面普遍超過了1980年代已滿14周歲的人,不過這些感性認識畢竟不同于現(xiàn)代犯罪生物學的實證研究;即使對此有充分、透徹的實證研究,也不等同于對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本身的研究。現(xiàn)實中,不少行為人公開聲稱“犯罪要趁早”“我是未成年人,殺人不負刑事責任/不能判死刑”,不乏撒謊成性、具有較強反偵查能力者,說明其并不是不懂事、不懂法,其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很正常,與14周歲以上的人幾乎無差異。如果分析12~14周歲的人“心智是否成熟或者完全成熟”,無異于將“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替換為“心智成熟”,暗中偷換了概念,未抓住問題的關鍵,也不客觀公允。畢竟很多年滿18周歲甚至70周歲的人也很難說“心智完全成熟”,例如有成年人為了買手機而賣腎,為了瘦身而切胃、抽脂、抽肋骨,為了增高而斷腿骨,因失戀而自殺或殺人,可以說是“心智不成熟”,幾乎沒有人認為這些成年人是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
《刑法》關于自然犯的規(guī)定,同樣是關于道德底線的規(guī)定,人們不難認識到其禁止性。一般而言,如果某個犯罪存在具體的被害人,則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大,行為人更容易認識到加害行為的違法性。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等常見的自然犯均存在具體的被害人,實施這些罪行的未成年人無一不是故意為之,不可能未認識到其違法性。縱然其實施犯罪時不計后果,也不是未考慮到后果,更不是無能力考慮后果。其認識到行為的違法性仍決意為之,說明其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從認識難度來看,可否殺人、傷害他人身體的認識難度小于認識一般民事法律行為(如用5000元買一部手機、用6000元買一件高檔服裝、用7000元打賞主播、捐8000元給喜愛的明星等)的社會意義的難度,后者小于認識性行為的社會意義的難度。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實際上規(guī)定了性同意年齡(Age of Consent)為14周歲,高于12周歲,實屬正常。刑事責任年齡與性同意年齡本質(zhì)不同、規(guī)定不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其實,如此復雜并無必要,不必舍簡求繁。可以設定一個“一般人標準”,(2)“一般人”不同于“均值人(average man)”,后者指達到平均水平的人,基本上可以認為達到者和未達到者總數(shù)相當。認為“一般人”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具有行為能力和受刑能力,具有相應的刑事責任能力。如果立法機關認為,除了精神不正常的、智力發(fā)育遲緩的極少數(shù)人以外,當今12~14周歲的人幾乎都達到了“一般人標準”,即立法時機成熟,便可依法定程序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其實,與我國其他部門法關于法律責任年齡的規(guī)定相比,與世界主要國家對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guī)定相比,規(guī)定年滿12周歲的人對個別嚴重罪行負刑事責任,是非常溫和的,與《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并不沖突。(3)王登輝:《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基本問題研究》,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第86頁。郭爍教授指出:“即便非要從比較法上找靈感,12歲是各國主流刑事責任年齡規(guī)定,才是真正的客觀描述。”(4)郭爍:《應當毫不猶豫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騰訊大家https://xw.qq.com/iphone/m/category/5e4d0656bb64e3eb891d872e4c705b57.html,2019年10月28日訪問。縱觀國內(nèi)外歷史發(fā)展,刑事責任年齡不會墨守成規(guī),適時地調(diào)整是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必然要求。(5)高雅楠:《未成年人能力發(fā)展理論中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載《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9期,第45頁。
二、兩種利益衡量
(一)必要性之利益衡量:被害人、少年整體更值得保護
犯罪是對罪刑規(guī)范的違反。行為人在自由意志下實施犯罪行為,等于宣布自己是反對法秩序的人,放棄了自己的部分權利,也不值得被法律充分保護。若犯罪不受法律制裁,就會鼓勵其他越軌者仿效作案,會增加被害人,不利于犯罪抑制。刑罰是必要的惡害,符合比例原則的刑罰是適當?shù)膽土P,因其必要性而具有善的一面,因其法定性而具有正當性,蘊含著正義的因素。誠然,關愛未成年人成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絕對正確的、不可動搖的,而“立法的仁慈最終演變?yōu)橐恍┤诉x擇作惡的機會和理由”。(6)李玫瑾:《從刑事責任年齡之爭反思刑事責任能力判斷根據(jù)——由大連少年惡性案件引發(fā)的思考》,載《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13頁。1980年至今的少年刑事司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的實踐,而震驚全國的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懲罰不足”的巨大副作用,可以說已經(jīng)異化成為“教育(指狹義的教育)感化有余、懲罰不足原則”。(7)其實,家庭、學校、社會的苦口婆心的說教和司法機關的定罪判刑都屬于“教育”和“挽救”。狹義的“教育”主要指前者,廣義的“教育”可以包括后者。為避免歧義,筆者不使用“教育挽救有余”的提法。“懲罰為輔”長期“口惠而實不至”,會造成立法產(chǎn)品闕如,有損法律權威。
對未成年人的侵害有相當部分來自未成年人——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未成年人甲侵害未成年人乙的情形下,乙當然是更值得保護的——不一定是直接給予乙某種利益,通過處罰甲從而撫慰乙也是一種利益。如果立法規(guī)定,此種情形下甲應當負刑事責任,那么在乙為成年人的情形下,甲仍應當負刑事責任,不能因被害人年齡的不同而區(qū)別對待。
對實施特定犯罪的低齡未成年人予以刑罰處罰,目的是糾偏糾錯,幫助行為人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體現(xiàn)了一種父愛式的特殊保護。表面上看,其收獲的是痛苦——永遠小于被害人死亡(或者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痛苦,從長遠看有利于其改造、回歸社會,可以安撫被害方、減少復仇,也不會向潛在的模仿者釋放錯誤信號,對全社會都是有益的。如果認為這不是保護的一種體現(xiàn),而認為是向其施加惡害、迫害,則說明論者未能完整理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如果無視被害人的不幸遭遇、一般預防效果以及社會公義,不提報應、淡化威懾,以為一味地善待優(yōu)待犯罪人便可取得較好的特殊預防效果,對加害人過度關愛,類似于用“社會溺愛”接續(xù)“家庭溺愛”,可能是把主觀臆想的特殊預防效果凌駕于一般預防效果之上所致——須知“皮格馬利翁效應”只是古希臘神話,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實為鄉(xiāng)愿。如果把可能的道德否定、輿論譴責當作適量的“處罰”,從而否認刑罰的必要性,可能是夸大了批評教育的威力,顯然是源于“圣化構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托馬斯·索維爾語)的過度樂觀。依法追究罪錯未成年人的法律責任,追究犯有嚴重罪行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是利益衡量的結(jié)果,是對“懲罰為輔”原則的落實,符合“雙向保護”“平等保護”原則,與泛刑主義、重刑主義無關。
不妨將未成年的行為人、被害人、知情人(主要是目擊者和其他知悉該罪行的人)視為“少年整體”。只考慮行為人在犯罪前對他人罪行的模仿(潛意識里把行為人當成“社會之惡”的被害人),而不考慮他人對行為人罪行的模仿,顯然欠妥。行為人的罪行對知情人的心理沖擊并不小,對知情人的示范效應不容小覷。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大體上可以將三者的關系簡化為三種模式:

模式未成年行為人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知情人簡評一因:未實施特定罪行果:不受刑事追訴未受害無模仿對象上策二因:實施特定罪行果:受到刑事追訴受害不模仿犯罪中策三因:實施特定罪行果:不受刑事追訴受害有人會模仿犯罪下策
很顯然,模式一是對少年整體、全社會最有利的,是最理想的、值得追求的,可謂“上策”。模式二主張自我答責、處罰罪錯行為人,會給行為人帶來限制權利的痛苦和“糾正”的利益(其自身往往不認為這是利益),對被害人相對有利,有一定的安撫作用,即使有知情的未成年人隨后實施相同的犯罪也不是因為行為人未受制裁而模仿犯罪,其功利價值介于模式一和模式三之間,可謂“中策”。模式三對被害人的保護弱于對行為人的保護,并未安撫被害方,會給被害人(及家屬)造成二次傷害,甚至引發(fā)血親復仇;未體現(xiàn)否定性評價,未體現(xiàn)“懲罰為輔”,是行為人最希望得到的結(jié)果,還可能因放縱犯罪而客觀上鼓勵他人模仿犯罪。這樣的激勵機制是錯位的,不會起到一般預防的效果——縱然有很多人未模仿犯罪,也是因為其原本不愿意犯罪,而不是不敢犯罪。模式三可謂“下策”。模式二與模式一的價值取向基本一致,結(jié)果會發(fā)生趨同;而模式三將行為人的利益置于優(yōu)于被害人的地位,與模式一存在重大矛盾。反對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人會認為,模式三優(yōu)于模式二。但這種觀點錯誤的根源在于對功利主義作了庸俗化的理解,不能接受“正義的實質(zhì)是各人得到其應得的”的法律思想。
有學者指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直面社會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有助于發(fā)揮刑罰的安撫功能。(8)王恩海:《應毫不猶豫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20年第2期,第66-69頁。可以肯定地說,嚴重罪錯未成年人與(嚴重)不良未成年人存在本質(zhì)不同,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從而追究嚴重罪錯低齡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并不違反“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并未違反“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反而有利于將這些方針、原則落到實處。(9)王登輝:《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基本問題研究》,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第87-88頁。這也是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正當性的重要方面。
(二)可行性之利益衡量:移植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不如“一刀切”
移植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與“一刀切”之爭,是在支持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共識下的路徑選擇之爭。若12~14周歲的、精神正常的人擬制為均達到了“一般人標準”,且不能用證據(jù)推翻,則屬于“一刀切”方案;若12~14周歲的、精神正常的人視為均達到了“一般人標準”,控方應當舉證證明、辯方可以用證據(jù)推翻這一推定,則屬于“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的方案;若12~14周歲的、精神正常的人視為均達到了“一般人標準”,控方無須舉證證明,但辯方可以用證據(jù)推翻這一推定,則采用的方案類似于“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不少人主張引進域外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相關文獻頗多,茲不贅述。因其只考慮正當性、忽略可行性,故筆者旗幟鮮明地反對,具體理由如下:
其一,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違反了刑法的明確性原則。明確性是美國法學家富勒提出的法治八原則之一。“刑法的明確性不僅可以使裁判規(guī)范明確,進而限制司法機關的權力,有利于保障國民的自由,而且可以使行為規(guī)范明確,從而使國民明確哪些行為被刑法所禁止,有利于保護法益。”(10)張明楷:《明確性原則在刑事司法中的貫徹》,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4期,第26頁。“惡意”系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存在不同認識本屬正常。從表面上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主觀上有惡意則會提起公訴、判決有罪,無惡意或不能證明存在惡意則會不起訴、宣告無罪,似乎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刑罰個別化原則,仿佛實現(xiàn)了實質(zhì)正義。實際上,這違反了刑法的明確性原則,也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不符合類型化思想和經(jīng)濟原則,會引發(fā)諸多無謂的爭議并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正如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立案追訴標準只能以靜脈血樣中乙醇含量為根據(jù),而不能以行為人的酒精耐受度、駕駛能力受損評估值為根據(jù),只有摒棄“繁瑣哲學”才會找到可行的路徑。
其二,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對刑事訴訟證明提出了新挑戰(zhàn)。行為人的“惡意”往往只有間接證據(jù)證明,是否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必然成為爭議的焦點,除非行為人承認且穩(wěn)定供述。(1)12~14周歲的人在實施“兩種嚴重暴力犯罪”之前一貫溫良恭儉讓、純真守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實施“兩種嚴重暴力犯罪”是從“小錯不斷,大錯不犯”階段發(fā)展到“犯大錯后”階段的里程碑。而這些“小錯”,可能被認為與“惡意”存在強關聯(lián),也可能被認為只存在弱關聯(lián)。行為人家境不佳、缺暖少愛,可能被認為值得同情,也可能被認為不利于改過自新;行為人家境富裕、溺愛無度,可能被認為不值得同情,也可能被認為有利于改過自新。如果通過證明其成長經(jīng)歷、一貫表現(xiàn)等罪前事實的證據(jù)來證明“惡意”,難免瑣碎且被辯方認為欠缺關聯(lián)性,缺乏說服力。當前城市居民鄰里之間往往長久互不認識、交往很少,司法人員通過偵查或社會調(diào)查可能只了解到行為人的部分“小錯”,畢竟其監(jiān)護人所知有限或不愿意告訴,所訪對象未必知情或出于“明哲保身,少得罪人”“多栽花少栽刺”的心理而避重就輕、有所保留。司法人員通過偵查或社會調(diào)查能獲悉多少有意義的個性化的真相,通過社會調(diào)查報告來判斷是否存在“惡意”,顯然是值得懷疑的。無論由偵查機關取證,還是由社會調(diào)查機構取證,煞有介事卻無甚意義。故不宜過分看重犯罪原因中的環(huán)境因素、案外次要因素而拋棄類型化思維。(2)惡意存在于犯罪前和犯罪中,很少存在于犯罪后。犯意表示方面的證據(jù),當然是證明“惡意”的重要證據(jù),如果能夠取得且在案,則會對量刑產(chǎn)生微弱影響;如果未取得,一般也不會對定罪量刑產(chǎn)生什么影響,幾乎不會影響對“惡意”的認定。如果通過證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認罪悔罪、賠償與諒解等罪后事實的證據(jù)來證明“惡意”,顯然是南轅北轍,還可能被偽裝、表象所迷惑。期待行為人自動投案、如實供述屬于不合理的期待,不能因其不投案、不如實供述而認為其有“惡意”;若其自動投案或/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即可,并不能抵消之前的“惡意”。很多行為人的悔罪,可能是表演,也可能是在精神壓力之下的應激反應,不一定說明其真心認識到自己殺傷他人行為的錯誤性質(zhì)。很多行為人是因自己面臨牢獄之災而流淚,不是因被害人的悲慘遭遇而流淚。因行為人說句“我錯了”“對不起”,就相信這是真誠悔罪,可能不符合事實。很多時候,賠償經(jīng)濟損失只能證明其家庭有代為賠償?shù)哪芰Γ⒉荒苷f明更多。很多被害人家屬的諒解是在行為人家屬的威逼利誘下作出的,甚至在司法人員、各路說客的強大壓力下違心作出的,一律把諒解作為“社會關系被恢復”的鐵證顯然是過于表面化了。這些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只是揭示“房間里的大象”罷了。(3)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jù)足以證明犯罪動機、目的、性質(zhì)、情節(jié)、后果和社會危害程度等,足以證明其具有“惡意”。事實上,行為人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手段幾乎都是殘忍的,情節(jié)幾乎都是惡劣的,也能反映其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極大,很難說誰沒有“惡意”;以特別殘忍手段傷害他人身體,無論后果如何,亦然。可以說,證明存在“惡意”的事實99%以上是罪中事實,證明存在“惡意”的證據(jù)99%以上和定罪量刑證據(jù)重合,只能證明“惡意”卻與定罪量刑無關的證據(jù)是不存在的。那么,證明“惡意”存在的證據(jù)是否達到證明標準的爭議就會淪為無意義的內(nèi)耗。
其三,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系彈性認定規(guī)則,賦予司法人員巨大的自由裁量權,會給少年刑事司法造成巨大沖擊,甚至危及司法人員正常履職。更大的自由裁量權意味著更大的司法責任,無異于將司法人員置于火山口,明智的司法人員未必希望享有這種自由裁量權。關于行為人有無惡意、是否“情節(jié)惡劣”、要不要移送審查起訴、要不要提起公訴、要不要判決有罪,各方均會認為“有一定的希望”;行為人家屬以為可以爭取一下,便會采用一切手段左右司法,使結(jié)局對己方有利。若司法人員忤逆其意愿,則會滿懷憤懣,懷疑存在司法黑幕,無理投訴、誣告陷害乃至殺傷司法人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根本沒有“活動空間”,很多妄念、痛苦、悲劇就不會產(chǎn)生。表面上,其弊端是司法人員自由裁量權過大、可能徇私舞弊,實際上其帶給司法人員的風險和痛苦遠多于現(xiàn)在,很可能成為司法人員的不可承受之重,制度成本極高。
任何對策建議都不能脫離我國國情,若所選方案欠妥會造成更多問題。簡單移植域外法可能產(chǎn)生南橘北枳的效果,若殊難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更是如此。當前,我國司法權威較之應然狀態(tài)存在較大差距,引進“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的初衷雖好,卻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新問題,弊遠遠大于利。為避免前述弊端現(xiàn)實化,立法機關明確規(guī)定,12~14周歲的人對特定罪行負刑事責任,這是“一刀切”的一種方案——其實是從“兩刀切”改為“三刀切”、由“三分法”改為“四分法”,并未采用“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根本不是什么“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的中國化、本土化。如此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體現(xiàn)了類型化、明確性的要求,公開公平公正又簡便易行,既有剛性又有溫度,可將各方不滿、疑慮化解于無形,還有利于保護司法人員正常履職——盡管會被批評為簡單粗暴,不符合個別化、精細化的要求、趨勢。假如立法機關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下調(diào)至13周歲,筆者也是支持的,因為刑法的精確性決定了這一問題的清晰答案比模糊答案要好得多。倘若探討為什么不調(diào)至13.5周歲、12.5周歲或11周歲,以此追問下調(diào)至12周歲的正當性,采用的方法是鉆牛角尖,實質(zhì)上是否認下調(diào)至12周歲的正當性,意義有限。
三、立法評估: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影響
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至12周歲,會產(chǎn)生什么社會影響,影響范圍有多大,利弊如何,是立法之前就要審慎考慮的問題。司法實踐亦將給予反饋,只是尚需時日檢驗。
(一)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影響范圍
1.直接影響的人數(shù)測評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國0~14歲人口為253383938人,占17.95%。(11)國家統(tǒng)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五號)——人口年齡構成情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2021年5月11日發(fā)布。原文用的是“歲”,不是“周歲”,不過我國法律用語中的歲一般表達周歲的意思,當然誤差也是難免的,因無實在根據(jù)故忽略之。截至2019年末,我國人口出生率只有1.048%,2019年人口死亡率為7.14‰,(12)國家統(tǒng)計局:《2019年國民經(jīng)濟運行總體平穩(wěn) 發(fā)展主要預期目標較好實現(xiàn)》,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1/ t20200117_1723383.html,2020年1月17日發(fā)布。故可以假設2021年后總?cè)丝跀?shù)、0~14周歲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變,并不會導致數(shù)據(jù)過度偏離真實。假設0~14歲各年齡段人口平均分布,則可以推算當前及今后較長時間內(nèi)12~14周歲人口總數(shù)為36197705人左右。而我國故意殺人犯罪率為十萬分之二,不等于但相當于每十萬人有二人被殺。(13)絕大多數(shù)故意殺人犯罪是一個行為人殺一個被害人,多人殺死一人、一人殺死多人的情況所占比例不大,故可以如此估算。世界主要國家每十萬人的故意殺人犯罪人數(shù)分別如下:洪都拉斯、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索馬里、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摩洛哥、伊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為87、67、53、36、27、25、22、17、15、12、12、11,俄羅斯、土耳其、塞爾維亞、印度、厄立特里亞、意大利、英國、希臘、荷蘭、美國、越南為9、8、7、7、7、4.6、4、4、3、3、3,中國、法國、德國、泰國、西班牙為2、2、1.7、1、0.6。可見,我國故意殺人犯罪率在全世界處于極低水平。經(jīng)與資深司法人員交談,筆者將12~14周歲的人故意殺人的概率估值為上述數(shù)值的1/20,即百萬分之一,可以推算全國每年約有36.19個12~14周歲的人實施故意殺人致死的行為。
通過類似“費米估算”的方法所得數(shù)值為36.19,基本可信,可以粗略估算出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后,全國每年約有36個12~14周歲的人因犯故意殺人罪既遂而受到直接影響。上述分析方法也適用于12~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未遂但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且情節(jié)惡劣的情形,全國范圍內(nèi)每年其數(shù)量應該不少于30人。同理,12~14周歲的人犯故意傷害罪且致人死亡、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又情節(jié)惡劣的情形,全國范圍內(nèi)每年其數(shù)量約為70人。鑒于前述故意殺人概率的統(tǒng)計口徑不一定統(tǒng)一,對故意殺人既遂和故意傷害致死可能未加區(qū)分,12~14周歲的人犯“兩種嚴重暴力犯罪”的數(shù)量之和不是136,而是100左右,也是有可能的。有人認為,這類惡性犯罪很少,即使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極少適用,故不必修法,顯然是過于樂觀了。如果實際發(fā)生的犯罪數(shù)量小于預估的數(shù)量,則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起到了較好的一般預防效果,實現(xiàn)了立法的價值導向和社會防衛(wèi)功能;如果其大于預估的數(shù)量,也可能是量刑普遍偏輕、威懾力小所致,或者歷史慣性所致,不能簡單化地認為未實現(xiàn)立法目的從而否認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意義。
2.關于司法機關的工作量的測評
在12~14周歲的人成為“兩種嚴重暴力犯罪”的犯罪主體之前,該行為屬于民事侵權行為,不必承受行政處罰、治安管理處罰,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律關系,公安機關不能立案偵查、刑事拘留,可以采用的措施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算公安機關的工作量。將該類型化的惡行入罪后,公安機關依法處置更加順暢,可以計入工作量,更有利于平等保護未成年人、維護法律權威。
2020年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披露,2014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4569人,批準逮捕194082人,不批準逮捕88953人;受理移送審查起訴383414人,提起公訴292988人,不起訴58739人,不捕率、不訴率分別為31.43%和16.70%。(14)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http://www.spp.gov.cn/xwfbh/wsfbt/202006/t20200601_ 463698.shtml,2020年6月1日發(fā)布。當然,其中沒有12~14周歲的人犯罪數(shù)據(jù),參考意義有限。不過,對于測評檢察機關辦理“未檢”案件工作量仍有一定現(xiàn)實意義。可以推算,全國檢察機關平均每年辦理未成年人犯罪審查起訴案件總數(shù)略低于63902件,共計有63902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5)2012年后,“未檢”工作已經(jīng)實行捕、訴、監(jiān)(法律監(jiān)督)、防(犯罪預防)一體化工作模式,2018年后全面推進捕訴合一改革對“未檢”工作的影響很小。盡管不同罪名、相同罪名的不同案件的工作量有所差異,但從整體視之這種差異可以忽略。每年再增加100~136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相當于“未檢”部門的工作量增加了1.565‰~2.128‰,明顯在可承受范圍內(nèi)。
2014~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披露,2013~2019年全國法院辦理一審刑事案件共910萬件、判決罪犯人數(shù)1068.6萬人。可以推算,近八年來全國法院每年平均辦理刑事案件約113.75萬件、判決罪犯約133.58萬人。一年新增的12~14周歲的人犯“兩種嚴重暴力犯罪”的案件數(shù)及相應的工作量只是當前每年辦理刑事案件的0.0879‰~0.1195‰,完全在法院可承受范圍內(nèi),不可能導致案件數(shù)激增以致法院不堪重負。
(二)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影響內(nèi)容
應當承認,絕大多數(shù)12~14周歲的人是守法的,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對其只有益處,沒有壞處。少數(shù)低齡未成年人被定罪(一般還會判刑),根本原因是其故意實施了嚴重惡行,而不是因為立法機關將該惡行規(guī)定為犯罪;其可能因此在人生道路上面臨一些不利益,根本原因是其故意實施了嚴重罪行,而不是法院判決其有罪。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個別下調(diào)2歲,意味著一些12~14周歲的人因?qū)嵤┝藘煞N嚴重暴力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責任,有的人會被核準追訴,有的人會因未核準而不起訴,大多數(shù)會被法院判決犯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不會有人被判處死刑。對手段殘忍、后果嚴重、動機卑劣的低齡犯罪人判處無期徒刑,并不違法,只是比較少見而已。理論上講,對其可以免除刑罰處罰,但現(xiàn)實中可能極少。對未成年人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認罪認罰從寬、犯罪記錄封存、不會構成累犯、社區(qū)矯正與幫教等規(guī)定當然可以適用這些犯罪人,不是“一判了之”。其服刑的地點是未成年犯管教所或者類似感化院之類的專門矯治教育機構。行為人應當以服從改造、遵紀守法、不再違法犯罪來證明“我改造好了”“我現(xiàn)在是守法公民”,重獲信任,不能因為社會排斥而怨恨社會。其可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也可能與狐朋狗友抱團重出江湖,還可能因諸事不順而變得仇恨社會,甚至報復證人、被害人家屬、公檢法辦案人員、無辜者。這究竟是反社會人格的再現(xiàn),抑或刑事處罰的副作用,其表面上的守法是否隱忍偽裝,均難以確定,不能因為其又犯罪而簡單地認為改造效果不好,更不能認為不該定罪處罰。
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間接影響對象涉及每一個家庭,對未成年人(特別是越軌少年)及其監(jiān)護人(基本等同于父母)會起到明顯的威懾作用,有利于取得較好的一般預防效果,預防性立法功能也得以體現(xiàn)。父母如果不想子女成為不良少年,不想其因犯罪被追訴、被處罰,不想其人生道路坎坷、被社會排斥甚至“社會性死亡”,就必須加強對問題子女的管教,很多頑劣難教、桀驁不馴的少年會有所忌憚、有所收斂、有所節(jié)制。如果加強了家庭教育,其仍犯重罪,則說明家庭教育基本失效和失敗,其家庭環(huán)境是改造難度大的重要原因;如果家庭依舊疏于管教,其犯了重罪,則說明全家法律意識淡漠、家庭教育缺位和失敗,其家庭環(huán)境也是改造難度大的重要原因。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已經(jīng)宣告了其家庭教育的徹底破產(chǎn),不能把有監(jiān)護人(相當于父或母健在)當作“有管教條件”而不予處理。“責令其家長或者監(jiān)護人加以管教”——不屬于負刑事責任,并不能使其脫離滋生犯罪的原生環(huán)境,任由其繼續(xù)處于此種境況顯然不利于改造和社會化。2021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婦聯(lián)、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發(fā)布《關于在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體現(xiàn)了中央國家機關對家庭教育的重視,填補了法律空白,對改善家庭教育、減少未成年人犯罪與被害將持續(xù)產(chǎn)生積極影響。
行為人被定罪判刑,通常還有服刑經(jīng)歷——只是受到了規(guī)范的否定性評價,并不表明國家拋棄了他。如果法律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等出臺歧視有違法犯罪劣跡的未成年人的規(guī)定,屬于制度性歧視,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其規(guī)定當然無效、應予改正。從現(xiàn)實來看,人們普遍對“一進宮”“二進宮”的犯罪人無甚好感,唯恐避之不及,對看守所、監(jiān)獄、少年犯管教所、少年感化院(少年教養(yǎng)所、少年拘留所)、矯治機構、工讀學校、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不包括專門招收聾啞人之類的特殊教育學校)、專門學校、專門矯治教育機構等敬而遠之,實際上體現(xiàn)了有罪判決的附隨效應,也體現(xiàn)了人們樸素的法規(guī)范意識、對劣跡人群的不信任。這些非規(guī)范性評價系私法自治范疇,并不違法,國家無權干涉,不能苛責人們“有偏見”“缺乏愛心”“亂貼標簽”“歧視犯罪的人”,更不能強制普通公民都關愛犯罪人、給予優(yōu)待。人們因為“進去的人不是好人”而對其無好感,并不是因為某個場所被污名化故而討厭其中的人。如果說污名化,也是因為“進去的人不是好人”導致場所被污名化,而不是相反,切不可顛倒因果關系。無論將矯治少年犯的機構冠以何種名稱,假以時日,皆會“污名化”。以為變更場所名稱可以“減少歧視”、有利于少年犯回歸社會的觀點,值得商榷。
四、關于罪行選擇
(一)“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之解釋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實際上還修改了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主體要件和客觀要件,值得研究。各種非典型的故意殺人或暴力致人死亡行為是否被規(guī)制,將是實務中爭議的焦點。12~14周歲的人非法拘禁且不給飲食致被拘禁人死亡的,非法拘禁他人并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綁架他人并殺害被綁架人的,搶劫(含轉(zhuǎn)化型搶劫)致人死亡的,聚眾斗毆且其行為致人死亡的,聚眾“打砸搶”且其行為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致人重傷又將傷員隱匿、遺棄致人死亡等轉(zhuǎn)化犯、結(jié)果加重犯、包容犯及其他非典型的殺人、暴力致人死亡,也應當被這里的“故意殺人”所涵攝。12~14周歲的人在實施綁架、搶劫等罪行的情形下,如果實施故意傷害行為致人死亡,又沒有證據(jù)證明其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仍屬于這里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強奸致人死亡或者自殺,強制猥褻致人死亡,侮辱、折磨或者恐嚇導致未成年人自殺等可否評價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行為,以及行為是否屬于“情節(jié)惡劣”,將會引起巨大爭議。筆者認為,前述情形均被這里的“犯故意傷害罪”所包含——盡管相關本罪的最高法定刑可能較低或者未將致人死亡規(guī)定為加重結(jié)果。
考慮到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實行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jié)果之間可能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可能有外部因素介入,認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有一定難度,又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加持及誤用,不少案件會成為爭議頗大的疑難案件,這無疑會影響到法律實施的效果。不妨假設一種極端情形:5~6個13周歲的男性按住并輪奸一名10周歲的女童,致其當場死亡或者事后自殺而死。很難將強奸行為評價為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辯方會提出“行為人對強奸行為不負刑事責任,強奸行為不是故意傷害行為,也不是故意殺人行為,普通毆打行為和被害人的死亡結(jié)果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幾個行為人無罪”的辯護意見。即使12~14周歲的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沒有違背女性意志、有沒有侵犯女性的性自主權、是否構成犯罪、會不會認定輪奸情節(jié)等欠缺正確認識,也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違反最低道德準則的嚴重惡行。依據(jù)《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后的《刑法》第17條第3款,追究這些12~14周歲的人構成強奸罪(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并無不妥。
從文義來看,“致人重傷”和“造成嚴重殘疾”是并列關系,不是選擇關系,是指故意殺人未遂或者故意傷害行為結(jié)束后,被害人的人體損傷程度已達到了重傷標準,傷愈后達到了嚴重殘疾的標準。關于“重傷”的認定,應當依據(jù)2013年《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關于“殘疾”的認定,應當依據(jù)2016年《人體損傷致殘程度分級》,不過認定“嚴重殘疾”的標準不夠明晰,參照《勞動能力鑒定職工工傷與職業(yè)病致殘等級》(GB/T 16180—2014)的相關規(guī)定,宜認為一級至七級殘疾為“嚴重殘疾”。如果12~14周歲的人以強酸損毀被害人容貌,可能只認定為重傷而不會認為屬于“嚴重殘疾”,依此條便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了。若將“致人重傷”和“造成嚴重殘疾”解釋為選擇關系,未超過文義射程,并非不可取。如果表述為“致人重傷或者造成嚴重殘疾”,則“致人重傷”與“造成嚴重殘疾”擇一即可,可能更佳。
(二)“情節(jié)惡劣”之解釋
該條中的“情節(jié)惡劣”修飾的僅是“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抑或加上“致人死亡”?易言之,如果發(fā)生了致人死亡后果,是否還要求情節(jié)惡劣?若“情節(jié)惡劣”僅修飾前者,則屬于情節(jié)犯;若修飾兩者,則在修飾“致人死亡”時屬于整體的評價要素——又有疊床架屋之嫌。從現(xiàn)實來看,“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但情節(jié)不惡劣,幾乎不可能;如果故意殺人既遂或者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卻由于某種原因認定為不屬于“情節(jié)惡劣”,難以令人信服。也即“致人死亡”的結(jié)果與“情節(jié)惡劣”往往是基本等價的,宜認為發(fā)生致人死亡后果的一律屬于“情節(jié)惡劣”。故筆者認為,“情節(jié)惡劣”僅修飾“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
該條中的“情節(jié)惡劣”與“以特別殘忍手段”之間是什么關系?人們很容易認為,“情節(jié)惡劣”是對“以特別殘忍手段”的重復評價,但如果通過刑法解釋得出其他合理結(jié)論,則不能認為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刑法》第234條第2款規(guī)定,“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再結(jié)合《刑法》第17條第2款可見,立法機關認為,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比一般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更惡劣,具有更大的可非難性,有的與故意殺人罪既遂相當,應當配置更重的法定刑,不排除死刑。從體系解釋來看,“情節(jié)惡劣”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刑法》第234條第2款中的“以特別殘忍手段”,可將這一表述視為“特別殘忍手段”的同位語。“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顯然包括了行為人以特別殘忍手段殘害他人的肢體的行為,例如刀砍、斧劈、匕首捅刺、鐵錘猛砸、從高處摔下等。而唆使狂犬咬人致人感染狂犬病毒而死,投放毒蛇咬人致人死亡(或者成為植物人),投放危險物質(zhì)使人中毒或患絕癥而死亡,用裝有艾滋病人血液的針頭扎人、用強酸強堿毀容等,是否屬于“以特別殘忍手段”,會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均屬于“以特別殘忍手段”。普通的拳打腳踢也足以將人活活打死,若以“手段不是特別殘忍”或者“手段不是特別殘忍,就不是情節(jié)惡劣”為由而不追究刑事責任,并不妥當。而“手段殘忍”與“手段特別殘忍”之爭,也是不可避免的。故宜舍棄“特別”這一修飾語,解釋為“殘忍手段”為佳,也不宜對動機、目的、程度做其他限制。
從實踐來看,司法機關一般會從動機目的是否卑劣、是否事出有因、有無被害人過錯、作案手段是否殘忍、后果是否嚴重、有無自首坦白、認罪悔罪態(tài)度、有無賠償被害方損失、有無刑事和解、行為人一貫表現(xiàn)及有無劣跡等綜合認定“情節(jié)惡劣”。但有的未成年人對生命缺乏基本的敬畏,因瑣事釀成命案的情形頗多,往往有較易偵破、認罪態(tài)度好等特點,這一司法經(jīng)驗未必可資依賴。另外,“情節(jié)惡劣”這一構成要件要素亦需要解釋和證明,對“情節(jié)惡劣”的證明同對“惡意”的證明類似,本來在案的罪中證據(jù)足以證明是否“情節(jié)惡劣”,卻會陷入無謂的爭執(zhí)。故“情節(jié)惡劣”之規(guī)定,沒有實質(zhì)意義,刪除為宜。
五、程序控制——“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亟待制定細則
《刑法修正案(十一)》規(guī)定“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是一種程序控制,使得“一刀切”有了一定的柔性,可以從標準上從嚴把握追訴的必要性和準確性。這樣的目的是從嚴統(tǒng)一標準、限制處罰范圍,從社會發(fā)展大局考慮,從國家層面去判斷,有利于法治統(tǒng)一。如前所述,可以預測全國每年約有100~136個12~14周歲的人因犯罪被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那么細化具體規(guī)定、構建完善程序勢在必行,即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發(fā)布相關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極具必要性。
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很明顯只在審查起訴階段,而不是審查批準逮捕階段;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并不需要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后,地方檢察院不提起公訴是不可能的。當前有三個重要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受理審查起訴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是基層檢察院,還是中級人民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筆者認為,應當是后者。基層人民檢察院對此無管轄權,如果受理則應當移送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理由如下:(1)司法實踐中,12~14周歲的人的罪名大多數(shù)將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基本犯對應的法定刑是“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對應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搶劫致人死亡、非法拘禁他人并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綁架他人并殺害被綁架人、故意傷害被綁架人致其死亡等,應當適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一般包括了死刑、無期徒刑。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條規(guī)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極其嚴重的,才可以適用無期徒刑。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可見,人民法院有權對12~14周歲的罪行極其嚴重的被告人判處無期徒刑,《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顯示,2020年全國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判處無期徒刑50人,認為對未成年人不能判處無期徒刑的觀點是不成立的。依據(jù)《刑事訴訟法》第21條,應當由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一審。相應地,公訴機關也應當是中級人民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即使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也不應例外;否則,可能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2)截至2020年2月,我國有965個市轄區(qū)、387個縣級市、1323個縣、117個自治縣、49個旗、3個自治旗、1個特區(qū)、1個林區(qū),共2846個縣級區(qū)劃。那么,每個縣級區(qū)劃平均有12718個12~14周歲的人,因其概率取百萬分之一,可以推算大體上每79個縣級區(qū)劃一年共發(fā)生1起12~14周歲的人故意殺人致死的犯罪,平均79個縣級區(qū)劃一年共發(fā)生約4起12~14周歲的人犯“兩種嚴重暴力犯罪”的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集中管轄,審查起訴、層報核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積累辦案經(jīng)驗、把握尺度。最高人民檢察院如果核準追訴,宜在《核準追訴決定書》上載明:本案應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指定同級的某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如此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爭議,節(jié)約司法成本。(3)從2020年《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來看,“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或決定)”的表述均有,意味著偵查終結(jié)后不一定都是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有可能是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
二是,核準決定權是否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專有?易言之,省級人民檢察院有無否決權?如果層報至省級人民檢察院后,其認為不應當追訴,核準程序就此停止,還是應該繼續(xù)層報至最高人民檢察院?“是否應當核準追訴”主要是實體方面的整體性判斷,而“是否符合層報核準追訴的條件”主要是程序方面的細節(jié)性判斷,這是兩個殊途同歸的問題。“不應當核準追訴”有可能異化成“不符合層報核準追訴的條件”,對此應當警惕。因?qū)Ψ缸锵右扇耸欠駥儆?2~14周歲的人有分歧、法外因素等原因,中級人民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對是否符合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核準的條件存在分歧的,宜請示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省級檢察院認為符合層報核準條件、應當核準追訴的,當然還應當上報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不應當核準追訴的(公開理由可能是不符合層報核準追訴的條件),基于檢察一體原則,一般應當以省級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為準,但對于這一問題未必仍舊適宜;若賦予下級檢察院的復議權,又有程序倒流、增加司法成本之嫌。筆者認為,核準追訴權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專有,省級人民檢察院沒有否決權;如果省級人民檢察院認為不符合層報核準追訴的條件或不應當核準追訴的,也應當報請最高檢察院核準追訴(可以一并提出本院的處理建議和理由),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最終決定。這也可以減少越級上報、申訴控告的發(fā)生。
三是,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核準,應當由受理審查起訴的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還是由偵查機關撤銷案件?在“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前提下,如果是前者,系微罪不起訴,還是絕對不起訴?第一種觀點認為,“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實際上是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序要件,并不給違法性、有責性提供依據(jù),與表面的構成要件要素有些類似,未核準追訴說明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具有可罰性,則應當作出微罪不起訴決定。第二種觀點認為,該規(guī)定給有責性提供依據(jù),未核準追訴說明最高人民檢察院認定犯罪嫌疑人不負刑事責任,則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應當絕對不起訴,或者由偵查機關撤銷案件。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依《不予核準追訴決定書》的理由不同而區(qū)別對待。鑒于最高人民檢察院不可能認定某個精神正常的12~14周歲的犯罪嫌疑人是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也不太可能是“不屬于重傷”或者“未造成嚴重殘疾”,其理由主要是“不屬于特別殘忍手段”或“不屬于情節(jié)惡劣”,相當于《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2款中“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情形,又考慮到司法機關收集的證據(jù)可能用于民事訴訟中,筆者傾向于第一種觀點。
對12~14周歲的人的特定犯罪核準追訴,與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差異頗大,與對已過二十年追訴期限的犯罪核準追訴頗為類似,即并未采取備案制或事后審批生效制,而是采用事前審批制。在層報的標準、所需材料、流程、辦案期限等具體規(guī)定方面,可以仿效后者的制度設計。參照201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核準追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茲擬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核準追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相關內(nèi)容如下:
第一條 辦理核準追訴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以下簡稱“核準追訴”)案件應當嚴格依法、從嚴控制。
第二條 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或者死亡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
未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不得對案件提起公訴。
2.2.1推進化肥減量增效 支持長江經(jīng)濟帶11省(市)實施化肥使用量負增長行動,選擇一批重點縣(市)開展化肥減量增效示范,加快技術集成創(chuàng)新,集中推廣一批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復和化肥減量增效技術模式,探索有效服務機制,在更高層次上推進化肥減量增效。
第三條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前,偵查機關可以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檢察機關應當及時介入,有權調(diào)查核實。
偵查機關提請追訴并提請逮捕犯罪時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嫌疑人,人民檢察院經(jīng)審查認為應當追訴而且符合法定逮捕條件的,可以依法批準逮捕,同時要求偵查機關在提請核準追訴期間不停止對案件的偵查。
第四條 報請核準追訴的案件應當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有證據(jù)證明存在犯罪事實,且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
(二)犯罪嫌疑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或者死亡的;
(三)犯罪嫌疑人能夠及時到案接受追訴的。
第五條 偵查機關提請追訴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受理并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
第六條 人民檢察院對偵查機關移送的提請追訴的案件,應當審查是否移送下列材料:
(一)報請核準追訴案件意見書;
(二)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jù)材料;
(三)關于發(fā)案、立案、偵查、采取強制措施等有關情況的書面說明及相關法律文書。(17)筆者認為,“被害方、案發(fā)地群眾、基層組織等的意見和反映”不應當保留。主要理由是,幾乎不用調(diào)查便可知被害方希望從嚴從重從快判處;案發(fā)地群眾、基層組織等未必比辦案人員更了解全部案情,其意見可能失真,且并不重要;若知者甚多,可能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具文。
材料齊備的,應當受理案件;材料不齊備的,應當要求偵查機關補充移送。
第七條 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偵查機關提請追訴的案件,應當及時進行審查并開展必要的調(diào)查,經(jīng)檢察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同意追訴的意見,在受理案件后十日之內(nèi)制作《報請核準追訴案件報告書》,連同案件材料一并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申請核準追訴程序的期間,不計入審查起訴期限。
第八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收到省級人民檢察院報送的《報請核準追訴案件報告書》及案件材料后,應當及時審查,必要時派人到案發(fā)地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應當在受理案件后一個月之內(nèi)作出是否核準追訴的決定,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十五日,并制作《核準追訴決定書》或者《不予核準追訴決定書》,逐級下達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送達提請追訴的偵查機關。
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不予核準追訴,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收到《不予核準追訴決定書》后十五個工作日內(nèi)決定不起訴。犯罪嫌疑人在押的,應當立即釋放。
第九條 對已經(jīng)批準逮捕的案件,偵查羈押期限屆滿不能做出是否核準追訴決定的,應當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變更強制措施或者延長偵查羈押期限。
第十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核準追訴的案件,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監(jiān)督偵查機關及時開展偵查取證。
需要強調(diào)的是,任何預設立場及指標化管理均會使該制度異化,不存在“以不核準為原則,以核準為例外”原則,也不存在“以核準為原則,以不核準為例外”原則。可以預測,12~14周歲的人犯罪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案件,大多數(shù)會得到核準,只有被害人有重大過錯、行為人長期遭受校園霸凌而還擊施害者、行為人有較嚴重智力障礙等情況不會得到核準。最高人民檢察院可能因被害人重大過錯、行為人主觀惡性不深等原因而不予核準追訴,在文書中以一兩句話闡述理由為宜,不必詳細說理。如果未核準追訴,當然不是因某個12~14周歲的行為人沒有惡意而不追究,也不是因行為人不具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而不追究,不能認為之前的批準逮捕決定是錯誤的。無論最終核準追訴與否,均應當計入偵查機關的工作量,以免其因擔心不被核準而怠于偵查取證。
六、結(jié)語
《刑法修正案(十一)》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至12周歲,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內(nèi)在規(guī)律和比例原則,是全方位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的必要舉措,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充分的正當性,根本不是情緒立法、民粹立法。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和“情節(jié)惡劣”的解釋與認定,很可能是爭議的焦點、適用的難點。當務之急是細化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條件與程序。個別下調(diào)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代表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還應當抓緊抓好相關配套措施和延伸工作,做好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如加強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做好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建立健全親情會見、強制親職教育、心理干預、臨界預防、強制辯護、“未檢”業(yè)務統(tǒng)一集中辦理、分案起訴、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體系、未檢公益訴訟、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體系、“政法一條龍”工作機制、“社會一條龍”工作機制等,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