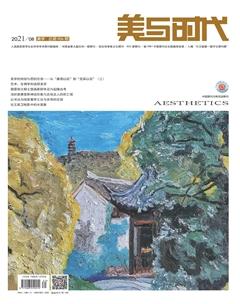美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
三、美學的終結:四個轉向
綜上所述,我講到的,其實是生命美學之所以出現的思想背景。概括言之,可以叫做:“以信仰代宗教”與“以審美促信仰”。簡而言之,在宗教退回教堂、革命退回殿堂之后,信仰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審美與藝術則成為了信仰建構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是“因審美,而信仰”,也是“因信仰,而審美”⑤。
不過,前面我所講的,還只是生命美學得以產生的外在原因。可是,外因畢竟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因此,下面我們還要來進而討論一下生命美學得以產生的內在原因。
而這就涉及到對于審美與藝術本身的討論。
然而,這也并不容易。本來,問題并不復雜,審美與藝術家所涉及的,其實就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困惑。叔本華曾經提示說:“關于美的形而上學,其真正的難題可以以這樣的發問相當簡單地表示出來:在某一事物與我們的意欲沒有任何關聯的情況下,這一事物為什么會引起我們的某種愉悅之情?”[35]在我看來,這段話是對“主觀的普遍必然性”這一康德的重大發現的一個深入淺出的說明。確實,情感愉悅早已是一個老問題,而且,諸如逐利的情感愉悅、求真的情感愉悅、向善的情感愉悅,也都已經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但是,引人矚目的是,審美的情感愉悅卻始終沒有能夠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畫餅”不是為了“充饑”,“望梅”不是為了“止渴”,那么,為什么還要“畫”?為什么還要“望”?其它的木頭都可以“焚”,“琴”何以就不能“焚”?雞鴨魚肉都可以“煮”,“鶴”何以就不能“煮”?或者,審美與藝術沒有用,但是為什么卻又須臾不可離開?平心而論,人類也并不是沒有意識到其中必定蘊涵著深刻的涵義,但是,長期以來,卻學派紛爭,各持一說,似乎誰都難以服眾。而且,當年曾經以為已經完美解釋了的,一旦時過境遷,似乎也就變得破綻百出,難以令人信服。例如,人們曾經將審美與藝術作為神性的附庸,或者將審美與藝術作為理性的附庸,并且由此而在輔助的、從屬的、娛樂的層面作出過解釋,可是一旦連上帝、理性都灰飛煙滅,這些解釋也就再也沒有了市場。然而,審美與藝術卻仍舊存在,而且,還一切如前所敘,不論是就“以審美促信仰”而言,還是就阻擊作為元問題的虛無主義而言,其影響都日益重大、日益顯赫。因此,對于審美與藝術的解釋又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
無疑,這一切都期待著一種全新的對于審美與藝術的解釋。而且,這也正是在“尼采以后”的生命美學的努力方向。
具體來說,生命美學亟待完成的是四大轉換。同時它也意味著:美學要走出四大誤區。具體來說,美學要走出“自然的人化”的誤區,走向“自然界向人生成”的轉換;美學要走出“適者生存”的誤區,走向“愛者優存”的轉換;美學要走出“我實踐故我在”的誤區,走向“我愛故我在”的轉換;美學還要走出審美活動是實踐活動的附屬品、奢侈品的誤區,走向審美活動是生命活動的必然與必須的轉換。
(一)美學要走出“自然的人化”的誤區,走向“自然界生成為人”的轉換
昔日的美學,無論具體的看法如何,都存在著一個外在的原因,卻是共同的,例如神性的推動、理性的推動,等等。實踐美學也是如此,無非是把推動力放在了外在的實踐活動身上,所謂“勞動創造了美”“自然的人化”,則是其中的關鍵詞。但是,我已經討論過,而今神性、理性作為外在的推動力已經完全沒有了說服力,第一推動力、救世主都沒有了,再用神性或者理性去解釋審美與藝術,也已經此路不通。應該說,這已經成為了人們的共識。
以中國的新時期以來的美學研究為例,表面看起來是“實踐”與“生命”的對立,但是實際上卻是一個不斷地“去實踐化”“弱實踐化”與“泛實踐化”的過程。生命美學、超越美學、存在美學就不用說了,因為它們都是走在“去實踐化”的道路之上,而新實踐美學也好,實踐存在論美學也好,包括李澤厚本人力主的實踐美學也好、其實也都是在不同程度的給實踐加括號,都是在懸置它。新實踐美學的“新”在哪里?實踐存在論美學何以要為“實踐”加上“存在”?他們當然都是解釋為“拓展”,但是,與其解釋為“拓展”,遠不如解釋為“弱實踐化”“泛實踐化”更為合乎實際情況。李澤厚的“情本體”是怎么回事?難道不也是在“弱實踐化”“泛實踐化”?顯然,從一般本體論的實踐本體論轉向了基礎本體論、主體間性的超越本體論,情本境界的生命本體論是其中的大趨勢。而在這背后的,則是“去本質化”“弱本質化”“泛本質化”,也就是不再幻想用神性或者理性的方法來界定審美與藝術。嚴羽說:“吾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其實,中國的新時期以來的美學研究所走過的,也同樣是“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的道路,這就是“去實踐化”“弱實踐化”與“泛實踐化”,也是“去本質化”“弱本質化”與“泛本質化”。
海森堡說:“在物理學發展的各個時期,凡是由于出現上述這種原因而對以實驗為基礎的事實不能提出一個邏輯無可指責的描述的時刻,推動事物前進的最富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往往把現在所發現的矛盾提升為原理。這也就是說,試圖把這個矛盾納入理論的基本假說之中而為科學知識開拓新的領域。”顯然,當美學發生了轉變,當上帝與理性退出了美學的中心之后,我們也亟待提出一個新的“假設”,以便把“現在所發現的矛盾提升為真理”并且“開拓新的領域”。當然,這個“假設”,就是“生命”。
我所強調的美學的第一個轉換,也就因此而呼之欲出了,這就是向“自然界生成為人”的轉換。
在中國,人們喜歡講“自然的人化”,甚至出現了“實踐拜物教”或者“勞動拜物教”(因此我經常建議年輕博士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去認真地反省一下當代中國美學的“實踐”話語或者“勞動”話語),但是后來卻遭遇了幾乎是所有人的迎頭痛擊。最煞風景的事,連被奉為神圣的馬克思的“勞動創造了美”也被改譯為“勞動生產了美”。何況,這樣一種把自然界與人蠻橫無情地用“實踐”去斷開的方法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其中,至少有四個沒有辦法解釋的困惑。第一,自然科學早就證明了動物也制造工具,而且已經制造了好多萬年,那么,為什么動物偏偏就沒有進化為人?第二,本來已經被制造工具的實踐積淀過的“狼孩”——就是被狼弄去養大的小孩,為什么無論如何無論怎么教育都再也無法成為人了呢?第三,地震災害降臨的時候,眾多動物中為什么最愚鈍無知的偏偏是已經被制造工具的實踐積淀過了的人類?第四,性審美肯定是出現在實踐活動之前的,這無可置疑,那么,又怎么解釋?
其實,物質實踐與審美活動都是生命的“所然”,只有生命本身,才是這一切的一切的“所以然”。人類無疑是先有生命然后才有實踐。我們知道,宇宙的年齡大約是150億年,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6億年,生物的年齡大約是33億年,而人類的年齡則大約是300萬年。試問,在這300萬年里,人類的生命無疑已經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可是,是否也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人類的物質實踐?如果有,無疑還需要科學論證;如果沒有,那么是否就是在斷言:那個時候的人還根本就不是人?而且,馬克思已經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那么,生命難道不也是物質實踐的“第一個前提”?更何況,人類是在沒有制造出石頭工具之前就已經進化出了手,進化出了足弓、骨盆、膝蓋骨、拇指,進化出了平衡、對稱、比例……光波的輻射波長全距在10的負四次方與10的八次方米之間,但是人類卻在物質實踐之前就進化出了與太陽光線能量最高部分的光波波長僅在400毫米—800毫米之間的內在和諧區域;同時,溫度是從零下幾百度到零上幾千度的都存在的,但是人類的卻在物質實踐之前就進化出了人體最為適宜的與20-30度左右的內在和諧區域。再如,與審美關系密切的語言也不是物質實踐的產物,而是緣于人類基因組的一個名叫FOXP2基因,它來自10-20萬年前的基因突變。
那么,何去何從?在我看來,只有轉向“自然界生成為人”。
這個問題,我在1991年出版《生命美學》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可惜,那個時候也許是太年輕了,根本沒有人理睬我。知音少,年輕有誰光顧?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但是,真理是不問年齡的,就像英雄不問出處一樣。至于原因,則已如前述,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作為第一推動力的上帝與理性根本就不存在。我們或者可以把廣義的自然可以稱之為宇宙世界,而把狹義的自然稱之為物質世界;前者涵蓋人,后者卻不涵蓋人。因此,宇宙世界不但是物質性的,而且還是超物質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它與人有其相近之處。不同的只是,我們把宇宙世界稱之為宇宙大生命(涵蓋了人類的生命,宇宙即一切,一切即宇宙)的創演,而把人類世界稱之為與人類小生命的創生。創演,是“生生之美”;創生,則是“生命之美”。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一致。“生生之美”要通過“生命之美”才能夠呈現出來,“生命之美”也必須依賴于“生生之美”的呈現。但是,也有一致之處,這就是:超生命,或者叫做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內在機制。所謂“天道”邏輯——“損有余而補不足”,奉行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基本原則,生物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則稱之為“生命的邏輯”。它類似一只神奇的看不見的手。只是,“生生之美”對于“生命的邏輯”是不自覺的,“生命之美”對于“生命的邏輯”則是自覺的。
而借助馬克思的思考,我們則可以把這樣一種生命的創演與創生,生命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稱之為“自然界生成為人”。
馬克思早已說過:“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36]可是我們卻一直未能深究,未能意識到亟待去以“自然界生成為人”去提升“自然的人化”。因此,我們忽視了“自然界生成為人”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而這也是美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自然的人化”只是馬克思的勞動哲學、實踐哲學。我們不能只注意到了其中的橫向的聯系,而且還不是全部——只是其中之一,卻忽視了其中的縱向的聯系。而其中一系列的區別是: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界生成為人”;不是“勞動創造了美”,而是“勞動與自然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也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而是“自我確證”“自由地實現自由”“生命的自由表現”。
具體來看,“自然的人化”只能涉及“自然界生成為人”的“現實部分”,也就是“人通過勞動生成”這一階段,但是“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非現實部分”卻無從涉及。例如,實踐美學從實踐活動看審美活動,主要思路就是美來自“自然的人化”,順理成章地,人類社會之前也就無美可言了,至于自然美,當然是“自然的人化”的結果。但是,自然的“天然”之美又何以解釋?例如月亮的美。因此,只看到“自然界生成為人”的“現實部分”,看不見“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非現實部分”,實踐也就被抽象化了,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陷入了“對人的自我產生的行動或自我對象化的行動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結果,實踐活動成為了世界的本體,成為人類存在的根源,也成為了審美和美的根源。至于人類實踐之前、人類實踐之外的一切,則完全被忽略不計。其實,為實踐美學所唯獨看重的所謂“人類歷史”應該只是自然史的一個特殊階段。因此,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界的自我意識”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我們都不能忽視。而且它們自身也本來就是互相依存的,后者還是前者得以存在的前提。這樣,離開自然去理解人、離開自然史去理解人類歷史,就無疑是荒謬的。換言之,人類歷史其實是“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它必須被放進整個自然史,作為自然史的“現實部分”,當然,是在“歷史”中人類才真正出現了的,但是,這并不排斥在“歷史”之前的“非現實部分”。彼時,人當然尚未出現,“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過程也沒有成為現實,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自然界也已經處在“生成為人”的過程中了。冒昧地將自然界最初的運動、將自然演化和生物進化的漫長過程完全與人剝離開來,并且不屑一顧,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是沒有根據的。而“自然界生成為人”則把歷史辯證法同自然辯證法統一了起來,也是對于包括人類歷史在內的整個自然史的發展規律的準確概括,更完全符合人類迄今所認識到的自然史運動過程的實際情況。
而且,從馬克思所告誡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出發,從“自然界的人的本質”的客觀存在出發,我們不難理解,那個“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其實是不存在的,如此這般的的自然界,對人來說只能是“無”。自然界往往被實踐原則去加以抽象理解,卻忽視了它始終都與人彼此相互關聯,無從分離。在人生成之前和生成之后,都如此。可是,在由無生命到有生命直至最高的生命的“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過程里,實踐活動卻主要是在“由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階段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也并非唯一),在前此的“無生命”和之后的“最高的生命”階段,卻并非如此。由此,實踐美學言必稱“實踐”,似乎是領到了尚方寶劍,誰都奈何它不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緣起于實踐也終結于實踐,實踐無所不能,實踐也萬能,然而,一旦如此,偏偏也就把“勞動”“實踐”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其實,實踐原則并不是萬能的。倘若從實踐原則發展到“唯實踐”“實踐烏托邦”,則也是不妥的。例如,認為只有實踐與人發生關系中的自然才是自然,這就難免落入實踐唯心主義、實踐拜物教。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已經領教了實踐唯心主義、實踐拜物教的危害。它將人與自然肆意分離,結果當然認為對待自然可以為所欲為,而且無論怎樣去對待自然,都不會反過來傷害自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這樣出籠的。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破壞自然界,當然也就是破壞“自然界的人的本質”、破壞人的本質。也就是把人變成“非人”。如此一來,美學也就無從立足了。
(二)美學要走出“適者生存”的誤區,走向“愛者優存”的轉換
這意味著,作為高級的生命現象,人類已經意識到:變化、差異以及對多樣性的追求,是對抗拒生命中熵流的瓦解和破壞的制勝法寶,而人類一旦從被動適應發展到主動適應,人類的自覺也就得以顯現。因此,人才可以自覺地與宇宙彼此協同,并且把宇宙生命的創演乃至互生、互惠、互存、互棲、互養的有機共生的根本之道發揚光大。這就是生命美學所立足的生命哲學:“萬物一體仁愛”“生之謂仁愛”。而當我們把生命看做一個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巨系統,當我們自由行善也自由行惡,從而最終得以由惡向善,愛,都是生命之為生命的忠實呵護者。愛守于自由而讓他人自由,是宇宙大生命與人類小生命自身的“生命向力”的自覺。
周輔成回憶,熊十力“覺得宇宙在‘變,但‘變決不會回頭、退步、向下,它只有向前,向上開展。宇宙如此,人生也如此,這種宇宙人生觀點,是樂觀的,向前看的。這個觀點,講出了幾千年中華民族得以愈來愈文明、愈進步的原因。具有這種健全的宇宙人生觀的民族,是所向無敵的,即使有失敗,但終必成功”[37]。其實,這也是人類生命的共同境界。“你要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別人”,這是用肯定性、勸令式的方式來表達西方文化的“愛的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則是以否定性、禁令式的方式表達中國的“愛的黃金法則”,而且比西方早提出了500多年。何況,中國有“仁愛”,西方有“博愛”,印度有“慈悲”……這一切告訴我們:愛,內在地靠近人類的根本價值,也內在地隸屬于人類的根本價值。愛,是人類根本價值中所蘊含的作為最大公約數與公理的共同價值
當然,這也就是所謂的“愛者優存”。或者,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非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是“適者生存”的黃金法則,因此,任何時候自己都不能輸,而只能是他者輸,就是其中的根本要求。但是,這恰恰不是生命之為生命的發展方向。生命史上最完美的故事一定應該是合作的故事、互助的故事。我活著,首先就要讓你活著;我不想做的,也首先不讓你做。莎士比亞提示我們:“在命運之書里,我們同在一行字之間。”“同在一行字之間“才是人類的共同命運,也才是人類的生命邏輯。因此,生命發展的推動力和最終趨向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關系,而是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即“非零和”。這正是柏格森所孜孜以求的“生命沖力”[38]6,正數的互利利他、正數的利益總和。它是可以改變一切的“宇宙酸”,也是共同進化的提升機。人類生命的演進,就是這樣地逐漸走向“非零和博弈”的時代。
在這方面,值得一讀的,是羅伯特·賴特的《非零和博弈——人類命運的邏輯》。他指出:早在康德那里,就已經認定人類歷史存在著“大自然隱秘計劃”,也就是“愛者優存”或“非零和博弈”的“大自然隱秘計劃”[38]22。“作出這種‘設計的并不是人類設計師,而是自然選擇。”[38]8它是人類生命存在的“非零和動力”。“地球上迄今為止的生命演變就是由這種驅動力塑造的。”[38]4因此,“唯有博弈論才能讓我們看清楚人類自己的歷史”[38]426。“地球上生命的歷史是一個好到難以書寫的故事。但是,無論你是否相信這個故事背后有一個天外的作者,有一點是相當清楚的:這就是我們的故事。作為它的主角,我們無法逃避它的意義。”[38]425
再比如,達爾文有兩本書,一本叫《物種起源》,還有一本叫《人類的由來》,《物種起源》是他前期的工作成果。那個時候,達爾文認為物種的進化是靠什么呢?“適者生存”,也就是“弱肉強食”,這當然是我們所非常熟悉的。但是,這并不是真正的達爾文。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是他后期的工作成果。在這本書里,出人意外的是,達爾文極少再用“適者生存”這個概念。有個學者做了個統計,說達爾文在他的這本書里一共只用過兩次。其中還有一次是因為要批評“適者生存”這一觀念。但是,有一個詞,達爾文卻用了九十多次,這就是“愛”。達爾文提示:事實上什么樣的動物種群才能夠進化呢?以“愛”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動物種群。這無疑是一場賭博——一場豪賭。因為沒有誰知道進化的最終結果,因此不同的動物種群實際上也就都是在豪賭:是自私自利?還是互相關愛?頗有意味的是:最終勝出的不是“適者生存”的動物種群,而是“愛者優存”的動物種群,是以“愛”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動物種群最終勝出。因此,哈佛大學的研究員愛德華·威爾遜稱之為的“親生命假設”。因為這個假設認為:生物間存在一種與其他生物親近的渴望,而人類更需要人與人之間親密的聯系。曾經有一個考古學家帶著學生挖出了一個人的尸體,考古學家發現:那個人的腿是斷了以后又接上的。于是,他對學生斷言:這應該已經是文明社會。因為所有的動物和人一樣,都怕受傷,一旦受傷,往往就失去了照顧,其結果就是因傷痛而死。但是這個人不一樣,盡管受了傷,但是卻能夠傷愈。這說明,他一定已經生活在一個互相關愛的社會。這正如舍勒所說:“只有當我們愛事物時,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事物。只有當我們相互熱愛,并共同愛某一事物時,我們才能相互認識。”[39]
總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信仰的覺醒一定就是自由的覺醒。現在我還要說,自由的覺醒也一定伴隨著愛的覺醒。愛是自由覺醒的必然結果,所以生命即愛,愛即生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再來看馬克思的話,就實在猶如醍醐灌頂:“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人的關系,那么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因此,提倡愛,其實強調的就是一種“獲得世界”的方式。正如西方《圣經》的《新約》說的“你們必通過真理獲得自由”,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馬長老說的“用愛去獲得世界”。或者,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愛故我在”。在這里,“愛”成為一種“覺”,但不是先天的(先知)先覺,而是后天的(先知)先覺,而且也先于實踐的“積淀”。懂得了這一點,也就懂得了王陽明的“龍場頓悟”,所謂“吾性自足”。換言之,其實在這里存在著一個西方積極心理學所提示的“洛薩達線”——一個消極情緒要以三個積極情緒來抵消。這是臨界點[40]。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向積極情緒移動的方式來改變自己。因為這樣的話,我們的作為創造力與可能性的心理杠桿就會變得更長,于是力量也就越大。最后,甚至可以撬動一切。這也就是人們往往會意外發現的所謂“愛能戰勝一切”。事實上,是積極情緒在不斷地創造和修正著我們的心理地圖,幫助我們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中快樂地生活。失敗不再被看做絆腳石,而被看做墊腳石。盡管“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也不再是“常念八九”,而是“常念一二”。猶如人之為人當然要首先滿足衣食住行的欲望,但是重要的是我如何去滿足衣食住行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李澤厚提出“吃飯哲學”,其實就是從康德向黑格爾的倒退。因為,在衣食住行的欲望的背后,還存在著孔子所謂的“安與不安”。什么叫“安與不安”?這個東西不是實踐“積淀”而來,而是人生而“覺”之的,是生命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巨系統的呈現。因此熊十力才說:只講生命活動不是真儒學,還要與“仁”結合。這就意味著:在“自然界生成為人”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個不可或缺的東西,那就是“愛”。對此,我們思考一下西方學者阿瑞提出的“內覺”,一種“無定形認識、一種非表現性的認識——也就是不能用形象、語詞、思維或任何動作表達出來的一種認識”[41],或許能夠有所啟迪?
我還要提示的是,同樣是在1991年,我已經提出要“帶著愛上路”:“生命因為稟賦了象征著終極關懷的絕對之愛才有價值,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真實場景”“學會愛,參與愛,帶著愛上路,是審美活動的最后抉擇,也是這個世界的最后選擇!”可惜,那個時候還是也許太年輕了,因也還是根本沒有人理睬我。不過,后來“帶著愛上路“的思路也在逐漸拓展,大大地拓展。我還提出了“萬物一體仁愛”的生命哲學。當然,北京大學的張世英先生曾經提出過“萬物一體”的哲學。但是,我認為還很不夠。正如熊十力先生所發現的的,只意識到了“萬物一體”還不是真儒學,還要意識到“愛”。何況,全部的宋明理學也都在做這件事情,都在超越萬物一體,也都已經推進到了“萬物一體之仁”,因此我們不應該只停留在“萬物一體”的初級階段。我所做的,則是再進一步,進而以“愛”釋“仁”,把傳統的“萬物一體之仁”的生命哲學提升為現代的“萬物一體仁愛”的生命哲學,愛即生命、生命即愛與因生而愛、因愛而生則是它的主題,而且,它并非西方的所謂“愛智慧”與智之愛,而是“愛的智慧”與愛之智。當然,順理成章的是,這一生命哲學也已經作為生命美學的哲學基礎,具體的論述,可以參看我的相關論著。
(三)美學還要走出“我實踐故我在”的誤區,走向“我審美故我在”的轉換
在實踐美學一統天下的時候,“實踐”成為了人之為人的標志,所謂“我實踐故我在”。今天的新實踐美學、實踐存在論美學也仍舊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走出“我實踐故我在”的藩籬(因此,它們的最大問題是解釋不了實踐活動之前的審美生成,也無法真正把實踐活動與審美活動區分開來)。可是,在生命美學看來,卻不但可以“我實踐故我在”,而且也可以“我審美故我在”。“審美”,同樣也是人之為人的標志。甚至,在生命美學看來,只有“我審美故我在”,才是人之為人的標志,“我實踐故我在”則不是。當然,如果我們不想過早引起爭論的話,那么起碼也可以說:人是直立的人、人是宗教的人、人是理性的人、人是實踐的人,人也是審美的人。
無疑,如果只強調人是實踐的,只強調“我實踐故我在”,其它的都是派生的,包括審美與藝術,無疑會產生很多問題。因為實踐活動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的一個問題,就是自由的覺醒的理想呈現。這本來是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呈現的,這就是馬克思所憧憬的“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也是馬克思所憧憬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42]。猶如我們說的,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同樣,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審美;只有當人審美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在這個意義上,因愛而美與因美而愛也就完全等值;生命即愛、愛即生命與生命即審美、審美即生命同樣完全等值;進而,“我愛故我在”與“我審美故我在”也完全等值。審美與藝術是自由的覺醒的“理想”實現,也是愛的“理想”實現。因此,如果我們今天在此岸世界就要看到美的實現,那就只能借助于審美與藝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我們無法從實踐活動中邏輯地推論出審美活動,實踐活動也不可能作為審美活動的根源。但是,在現實的層面無法實現的,出之于人類的超越本性,人類卻可以去理想地想象它,而且理想地去加以實現。因為,區別于實踐活動、認識活動,審美活動是以理想的象征性的實現為中介,體現了人對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這兩者的超越的需要。它既不服從內在“必需”也不服從“外在目的”,不實際地改造現實世界,也不冷靜地理解現實世界,而是從理想性出發,構筑一個虛擬的世界。這就是馬克思說的“真正物質生產的彼岸”。而且,這也正是只有審美與藝術才能在“理想”的層面“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也才能呈現“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的原因之所在。
在這里,十分重要的是形式的生命與生命的形式。“我審美故我在”建構的是一個形式的世界。1991年出版《生命美學》的時候,我在封面上題了一句話:“審美活動所建構的本體的生命世界”,其實正是對此的覺察⑥。也因此,審美與藝術都是形式對于內容的征服。并且,也因此而區別于內容的生命與生命的內容。人們發現,審美與藝術的世界往往與真的世界、善的世界無法重疊,例如曹禺的《雷雨》里的繁漪在現實生活里應該是個壞女人,可是在曹禺的作品里卻是個好人;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紅樓夢》里的賈政在現實生活里是個好干部、好父親。可是賈寶玉卻認為他不可愛。全世界的人寫回憶錄,大概很少有人說媽媽壞話的,“世上只有媽媽好”,壞的都是后媽,但是曹雪芹在回憶他的媽媽王夫人的時候,卻也說她不可愛。還有,健康活潑的東施何以就不如病懨懨的西施美?嚎啕大哭的情感抒發何以就不是藝術?這就是美和善之間、美和真之間的誤差。猶如我們在理解物質世界、動物世界的時候,往往是存在決定現象,可是我們在解釋人的精神世界的時候,卻是精神創造存在。例如,在求真向善的現實活動中,人類的生命、自由、情感往往要服從于本質、必然、理性,但在審美活動之中,這一切卻顛倒了過來,不再是從本質闡釋并選擇生命,而是從生命闡釋并選擇本質;不再是從必然闡釋并選擇自由,而是從自由闡釋并選擇必然;也不再是從理性闡釋并選擇情感,而是從情感闡釋并選擇理性……正如費爾巴哈所發現的,“心情厭惡自然之必然性,厭惡理性之必然性”。這當然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是形容決定形式,但是,在審美與藝術中,卻是形式決定內容。
因此,在形式中存在,存在于形式中,無疑也是一種人之為人的生存方式。審美的情感愉悅就是來自形式的愉悅。線條、色彩、明暗;節奏、旋律、和聲;跳躍、律動、旋轉;仰揚頓挫、起承轉合……那喀索斯看見了自己的水中倒影,從此就愛上了自己的倒影,這“水中倒影”不就是“我審美故我在”?皮格馬利翁(Pygmalion)是古代塞浦路斯的一位善于雕刻的國王,由于他把全部熱情和希望放在自己雕刻的少女雕像身上,后來竟使這座雕像活了起來。這座活了起來的雕像不也是“我審美故我在”?上帝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造了空氣;第三天造了地、海并地上的草木;第四天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造了水里的魚和空中的飛鳥;第六天造了地上的牲畜、昆蟲、野獸,并且照著自己的樣子造了人。可是,什么叫“照著自己的樣子”?由此我們不難受到啟發,我們也經常會說:人像“樣子”,或者不像“樣子”;人有“人味”,或沒有“人味”。可見,倘若我們能夠活得有“樣子”、有“人味”而且又能夠在形式中把它呈現出來,無疑也就正是“我審美故我在”。再聯想一下,人為什么要照鏡子?為什么要找對象?黑格爾也曾經好奇:人為什么喜歡看投石頭入河的漣漪?還有,兒童們為什么喜歡玩泥巴、堆沙子、捏面團?其實,也都是“我審美故我在”。至于真蝦不是藝術,齊白石的蝦卻是藝術,以及打仗不是藝術,京劇的武打卻是藝術,也只能從“我審美故我在”來加以解釋。因此,克羅齊才會說:“正是一種獨特的形式,使詩人成為詩人。”
進而,怎樣才能“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怎樣才能“獲得”“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馬克思剖析說,或者是“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那么,馬克思所謂的“獲得”又會如何?在我看來,這“獲得”可以是通過自我設計而完成的自我認識,也可以是通過自我調節而完成的自我完善,但是,也可以是自我欣賞而完成的自我表現。“我審美故我在”,就是自我欣賞,也是自我表現。它的前提是:自己的生命本身轉而成為對象(動物的機體反應——自我感覺與對象感覺——無法被當作自我、當做對象)。不是借助于神性,也不是借助于理性,而是借助于情感來建構世界、理解世界,讓自我被對象化,讓世界成為生命的象征。于是,世界,“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成為了“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成為“人的精神的無機界”[43]。而且,世界一旦成為人類的精神現象時,也就不再以現實的必然性制約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美是以“對象的方式現身的“人”;我們也可以說,美是“自我”在作品中的直接出場。
遺憾的是,我們過去對“我審美故我在”關注不夠,也始終未能敏捷意識到其中所蘊含的美學的全部秘密。以至于蘇珊·朗格要告誡我們說:“哲學家必須懂得藝術,也就是,‘內行地懂。”因為僅僅客觀地理解人的存在還是不夠的,還亟待“主觀地”理解、“內在地”理解。因此,歌德的一個提示就非常值得注意。前面已經說過,1985年的時候,歌德的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其實,后來歌德的另外一句話同樣也對我影響很大。他指出:“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夠發現詩的基本原則,它是太屬于精神世界了,太飄渺了。”[44]我們只要把“詩的基本原則”理解為美的基本原則,一切也就清楚了。歌德還提示過:“文藝作品的題材是人人可以看見的。內容意義經過一番努力才能把握,至于形式對大多數人是一個秘密。”[45]這其實都是對形式的生命與生命的形式的重要提示,也都是對于“我審美故我在”的重要提示。因此,正如同我經常說的那兩句話:重要的不是“美學的問題”,而是“美學問題”;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審美與藝術是精神對于世界的創造。如前所述,要解釋物理的世界、動物的世界,那無疑應該是存在決定現象,但是,要闡釋人類的世界,那就一定是意識“創造”存在。人之為人,一旦失去了這種精神的創造,也就失去了人的本性。這個本性,就是在形式中存在以及存在于形式中的本體存在,也是“我審美故我在”的本體存在。
(四)美學還要走出審美活動是實踐活動的附屬品、奢侈品的誤區,走向審美活動是生命活動的必然與必須的轉換
前面的三個轉換,最后必然走向新的轉換:審美活動是生命活動的必然和必須。
確實,一首詩、一部小說從來就沒有阻止過一次劫機或一次綁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仍然堅持說:“世界將由美拯救。”其實,他是有道理的。實踐美學喜歡說“勞動最光榮”,可是如果我通知你說,你一輩子都不用勞動了,那么,你還勞動不勞動?這個問題,只要憑良心回答,答案不難想見。當然,我沒有貶低“勞動”的意思,因為它也十分重要。但是,生命活動的最終完成,也確實是在勞動之外完成的。因為在未能到達“理想王國”之前,這個“完成”只能是在象征的意義上。因此,人類也就必然是為美而生,向美而在的。
這樣一來,實踐美學過于抬高實踐、過于貶低審美與藝術的缺憾就被暴露了出來。在實踐美學看來,審美與藝術只是實踐活動的奢侈品、附屬品,或者是神性的奢侈品、附屬品,或者是理性的奢侈品、附屬品,總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都是衍生性質的。當然,這并不正確。因為審美與藝術并不是實踐活動的奢侈品、附屬品,而是生命活動的必然與必須。因為審美活動并不在生命活動之外,生命即審美,審美即生命。它們彼此之間一而二、二而一,是一體的兩面。
具體來說,審美與藝術作為生命活動的必然與必須,一方面可以從“因生命,而審美”中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因審美,而生命”中看到。
“因生命,而審美”是指的人類的生命活動必然走向審美活動,審美活動是生命的理想本質的享受,可以簡稱為“生命的享受”。它是從生命活動的角度看審美活動,涉及的是人類的特定需要,所謂“人類為什么需要審美”,直面的困惑是:“人類為什么需要審美活動”“人類究竟是怎樣創造了審美活動”“審美活動從何處來”。
在人的生命活動中,存在著一種超越性的生命活動,它是最適合于人類天性的生命活動類型,也是生命的最高存在方式,然而又是一種理想性的生命活動方式,一種在現實中無法加以實現的生命活動方式。理想本性、第一需要是它的邏輯規定,也是對它的抽象理解,自由個性則是它的歷史形態,也是對它的具體闡釋。在理想社會,它是一種現實活動;而在現實社會,它卻是一種理想活動。審美活動,正是這樣一種人類現實社會中的理想活動,也即是一種超越性的生命活動。
這是因為,盡管實踐活動、理論活動和審美活動這三種基本的活動類型都同樣是著眼于自由的實現,但是又有所不同。實踐活動是人類生命活動的自由的基礎的實現。它以改造世界為中介,體現了人的合目的性(對于內在“必需”)的需求,是意志的自由的實現。它并非物質活動,而是實用活動,折射的是人的一種實用態度。而且,就實踐活動與工具的關系而言,是運用工具改造世界;就實踐活動與客體的關系而言,是主體對客體的占有;就實踐活動與世界的關系而言,是改造與被改造的可意向關系。不言而喻,在實踐活動的領域,人類最終所能實現的只能是一種人類能力的有限發展、一種有限的自由,至于全面的自由則根本無從談起,因為人類無法擺脫自然必然性的制約——也實在沒有必要擺脫,舊的自然必然性揚棄之日,即新的更為廣闊的自然必然性出現之時,人所需要做的只是使自己的活動在盡可能更合理的條件下進行。正如馬克思所說:“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46]
理論活動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手段的實現。它以把握世界為中介,體現了人的合規律性(對于“外在目的”)的需要,是認識自由的實現。它并非精神活動,而是理論活動,折射的是人的一種理論態度。而且,就理論活動與工具的關系而言,是運用工具反映世界;就理論活動與客體的關系而言,是主體對客體的抽象;就理論活動與世界的關系而言,是反映與被反映的可認知關系。不難看出,理論活動是對于實踐活動的一種超越。它超越了直接的內在“必需”,也超越了實踐活動的實用態度。理論家往往輕視實踐活動,也從反面說明了這一點。但實現的仍然是片面的自由。
而且,實踐活動是文明與自然的矛盾的實際解決,是基礎;理論活動是文明與自然的矛盾的理論解決,是手段,但是,由于它們都無法克服手段與目的的外在性、活動的有限性與人類理想的無限性的矛盾,因此矛盾就永遠無法解決,所以,就還要有一種生命活動的類型,去象征性地解決文明與自然的矛盾,這就是審美活動的出現。
審美活動是文明與自然的矛盾的象征解決。它以理想的象征性的實現為中介,體現了人對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這兩者的超越的需要,是情感自由的實現。它以實踐活動、理論活動為基礎但同時又是對它們的超越,它既不服從內在“必需”也不服從“外在目的”,既不實際地改造現實世界,也不冷靜地理解現實世界,而是從理想性出發,構筑一個虛擬的世界,以作為實踐世界與理論世界所無法實現的那些缺憾的彌補。假如實踐活動建構的是與現實世界的否定關系,是自由的基礎的實現;理論活動建構的是與現實世界的肯定關系,是自由的手段的實現;審美活動建構的則是與現實世界的否定之否定關系,是自由的理想的實現。換言之,由于主客體在審美活動中的矛盾是主客體矛盾的最后表現,故審美活動只能產生于理論活動與實踐活動的基礎之上。必須注意的是,三者既是并列的關系,也是遞進的關系,但絕不是包含關系。審美活動是對于人類最高目的的一種“理想”的實現。通過它,人類得以借助否定的方式彌補了實踐活動和科學活動的有限性。假如實踐活動與理論活動是“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審美活動則是“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假如實踐活動與理論活動是對無限的追求,審美活動則是無限的追求。在其中,人的現實性與理想性直接照面,有限性與無限性直接照面,自我分裂與自我救贖直接照面。由此,馬克思說的“真正物質生產的彼岸”或許就是審美活動之所在?而且,就審美活動與工具的關系而言,是運用工具想象世界;就審美活動與客體的關系而言,是主體對客體的超越⑦;就審美活動與世界的關系而言,是想象與被想象的可移情關系。因此,假如實踐活動與理論活動是一種現實活動,審美活動則是一種理想活動,在審美活動中折射的是人的一種終極關懷的理想態度。
事實也確實如此。假如從不“唯”實踐活動的人類生命活動原則出發,那么應當承認,審美活動無法等同于實踐活動(盡管它與實踐活動之間存在著彼此交融、滲透的一面),它是一種超越性的生命活動。具體來說,在人類形形色色的生命活動中,多數是以服膺于生命的有限性為特征的現實活動,例如,向善的實踐活動、求真的科學活動,它們都無法克服手段與目的的外在性、活動的有限性與人類理想的無限性的矛盾,只有審美活動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為特征的理想活動(當然,寬泛地說,還可以加上宗教活動)。審美活動以求真、向善等生命活動為基礎但同時又是對它們的超越。在人類的生命活動之中,只有審美活動成功地消除了生命活動中的有限性——當然只是象征性地消除。作為超越活動,審美活動是對于人類最高目的的一種“理想”實現。通過它,人類得以借助否定的方式彌補了實踐活動和科學活動的有限性,使自己在其他生命活動中未能得到發展的能力得到“理想”的發展,也使自己的生存活動有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一種完整性。
需要強調,在這里,審美活動的超越性質至關重要。審美活動之所以成為審美活動,并不是因為它成功地把人類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對象身上,而是因為它“理想”地實現了人類的自由本性。阿·尼·阿昂捷夫指出:最初,人類的生命活動“無疑是開始于人為了滿足自己在最基本的活體的需要而有所行動,但是往后這種關系就倒過來了,人為了有所行動而滿足自己的活體的需要”[47]。這就是說,只有人能夠、也只有人必須以理想本性的對象性運用——活動作為第一需要。人在什么層次上超出了物質需要(有限性),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實現了真正的需要;超出的層次越高,真正的需要的實現程度也就越高。一旦人的活動本身成為目的,人的真正需要也就最終得到了全面實現。這一點,在理想的社會(事實上不可能出現,只是一種虛擬的價值參照),可以現實地實現;在現實的社會,則只能“理想”地實現。而審美活動作為理想社會的現實活動和現實社會的“理想”活動,也就必然成為人類“最高”的生命方式。當然,這也就是說,“因生命,而審美”,生命之為生命,從生命活動走向審美活動,因此也就是必然的歸宿。這就正如安簡·查特吉所發現的,“將藝術看作本能或演化副產品的觀點都不能令人滿意”[48]6。也正如維戈茨基所發現的,“藝術是在生活最緊張、最重要的關頭使人和世界保持平衡的一種方法。這從根本上駁斥了藝術是點綴的觀點”[49]346。至于結論,則無疑應當是:“人類經過演化,對美的對象產生反應,因為這些反應對生存有用”“我們覺得美的地方正是能夠提高人類祖先生存機會的地方。”[48]71
“因審美,而生命”,指的則是審美活動必然走向生命活動,審美活動是生命的理想本質的生成。可以簡稱為:生命的生成。它是從審美活動的角度看生命活動,涉及的是人類的特定功能,所謂“審美活動為什么滿足人類生命活動的需要”,直面的困惑是:“審美活動向何處去”“審美活動為什么能夠滿足人類”“審美活動如何創造了人類自己”。
在這方面,實踐美學的“悅心悅意”之類的闡釋,實在是很膚淺、很蒼白,“以美啟真、以美儲善”之類,更是毫無道理。審美不是工具,藝術也不是婢女。如此來加以貶低排斥,卻根本無視它在推動、調控人類自身行為方面的獨立作用,是根本說不過去的。畢竟,審美活動并非實踐活動的副產品,也并非無關宏旨。在生命的存在中,審美活動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是完全理直氣壯的,無需像實踐美學宣揚的那樣像小媳婦一樣地委身依附于物質實踐。因此,重要的是要看到它在推動、調控人類自身行為方面的獨立作用。人類是“因審美,而生命”,在審美活動中自己把握自己、自己成為自己、自己生成自己。
換言之,猶如直立的人、宗教的人、理性的人、實踐的人都是人類生命進化的必然,審美的人,也是人類生命進化的必然。審美活動,不僅僅來自文化生命的塑造,也來自動物生命的“生物的”的或“自然的”進化,是被進化出來的人類生命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審美的人,在生命的進化之樹上至關重要。因為,生命的進化,首先當然是自然選擇,但是同時還不可或缺的則是審美選擇。審美被進化出來,就代表著人類生命的優化;倘若沒有被進化出來,則意味著人類生命的“劣化”。因而,猶如自然選擇的“用進廢退”,在人類生命的審美選擇中,同樣也是“美進劣退”,美者的生命優存,不美者的生命也就相應喪失了存在的機遇,并且會逐漸自我泯滅。因此,審美的人不但代表著“進化”的人,而且還更代表著“優化”的人。
當然,審美活動也就因此而不可能只是我們過去所膚淺理解的“無功利性”的問題,而應該是生命進化中的某種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它意味著:生命之為生命必然會是一種目的行為,也必然存在著目的取向。然而,這“目的”是如此難以把握,尤其是有諸多的選擇都對于個體而言還有害無益,但是對于全體而言卻是有益無害;或者,有諸多的選擇都對于個體而言盡管有利無害,但是對于全體而言卻是有害無益,置身其中,即便是借助于理性甚至是高度發展的理性也仍舊是無法予以取舍。于是,作為某種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它的必然導向目的的反饋調節就尤為重要。因為,具有意識能力的人類可以把目的主觀化,更善于驅動著目的轉而成為隨后的行為,并且使之不致溢出必然導向的目的。
由此,不難聯想,何以詩性思維要早出于抽象思維?我們如果不是從機械工業社會中所形成的類似電機、齒輪、轉軸、驅動輪,傳送帶之間嚙合傳遞的單向因果聯系的舊式思維切入,應該就不難意識到:在詩性思維的背后,一定存在著一種逐漸形成著的重大的生命反饋調節機制。從動物祖先到早期人類,自然界的偉大創造一定在尋覓著潛在的生命機制指向未來的運行方向的校正方式。“自然界生成為人”,就是要“生成”出這一生命反饋調節機制。而所謂的脫離動物界,也無非是指的這一生命反饋調節機制的從完全不自覺到較為自覺再到基本自覺。而且,這一點在人類的身上又體現得最為突出。這就正如普列漢諾夫所指出的,“需要是母親”。客觀的需要,迅即就會變為人類的主觀努力。這是因為,就人類的生命機制而言,倘若沒有內在的調節機制推動著他遙遙趨向于目的,那么在行為上也就很難出現相應的堅定追求,然而世界本身卻不會主動趨近于人、服務于人,長此以往,生命難免就會頹廢、衰竭乃至一蹶不振,甚至退出歷史舞臺。因此,隨著意識能力的覺醒,在把客觀目的變成主觀意識、把生命發展的客觀目的變成人類自我的主觀追求的變客觀需要為主觀反映的過程中,人類無疑是最善于敏捷地將生命進化中的必然性掌控于自己的手中的。
因此,馬克思說:“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其實也就是在提示我們:人類稟賦著把客觀目的主觀化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因此而可以去主動地確證著生命、也完滿著生命,享受著生命、更豐富著生命……倘若不存在潛在地指向某一目的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難道生命的進化是可以想象的嗎?在進化過程中大自然對于所有的動物的要求竟然是何等苛刻的——甚至苛刻到精確到小數點后面的很多很多位的地步。在這方面,不要說人類這樣一種高級的生命系統了,即便是最簡單的有機生命,也一定會進化出一種生命機制,一定存在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而且也一定是指向一定的目的的。不過,這“目的”不是一個主觀范疇,也未必一定要被意識到。它是一個客觀范疇,是生命進化在置身殘酷無情的自然選擇之時借助反饋調節而必然導向的目的。而且,這種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其實也并不神秘,借助今天的思想水準,也已經不難予以解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但是,卻并沒有“上帝”預先為我們謀劃,也并非自身在冥冥中自我謀劃,人類只是在盲目、隨機中借助自我鼓勵、自我協調的生命機制為生命導航。否則,或者并非真實的生命,或者是已經被淘汰了的生命。至于這是一個有意識能力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還是一個無意識能力的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卻并不重要,因為,它仍舊已經是生命。
這也許正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深意之所在。縱觀東西南北,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至今也都沒有發現一個不追求美、不愛藝術的民族,盡管其意識覺醒程度存在高低不同,這意味著:審美活動猶如陽光、空氣和水,不但并非偶然產生,也并非可有可無,而是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而且,它也不是實踐活動的副產品,不是實踐活動的消極結果。在把客觀目的主觀化的過程中,在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生命機制里,它起著最為重要而且也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而且,因為它是無法完全意識到的,因此才是“非功利性”的;因為它又是把人類生命中的客觀目的轉換為主觀的情感追求的,因此,才又稟賦著“主觀的普遍性”。
由此,只要我們不要象實踐美學那樣從人類的角度忽視了“自然界生成為人”、從個人的角度忽視了審美是生命的必然,只要我們去毅然直面這個“生成”與“必然”,就不難揭開審美之謎。如同歷史上頻繁出現的那些實體中心主義者一樣,如果死死抓住“實踐”要素不放,那就像盲人摸象的時候死死抓住的一條大象腿一樣,其實,這充其量也只是審美活動作為生命機制的系統中的一端,但是卻被錯誤地始終固執認定這就是全部,并且由此出發去解釋審美之謎。然而,在簡單的、直線的、單向的因果關系里,審美之謎卻悄然而逝。
其實,審美活動關乎“自然界生成為人”中的“生成”。因此,生命誠可貴,審美價更高。這審美活動作為一種特定的生命自鼓勵、自反饋、自組織、自協同的機制,它的存在就是為生命導航。人類在用審美活動肯定著某些東西,也在用審美活動否定著某些東西。從而,激勵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去冒險、創新、犧牲、奉獻,去追求在人類生活里從根本而言有益于進化的東西。因此,關于審美活動,我們可以用一個最為簡單的表述來把它講清楚:凡是為人類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所樂于接受的、樂于接近的、樂于欣賞的,就是人類的審美活動所肯定的;凡是為人類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所不樂于接受的、不樂于接近的、不樂于欣賞的,就是人類的審美活動所否定的。伴隨著生命機制的誕生而誕生的審美活動的內在根據在這里,在生命機制的巨系統里審美活動得以存身而且永不泯滅的巨大價值也在這里。
維戈茨基說:“沒有新藝術便沒有新人。”“藝術在重新鑄造人的過程中”“將會說出很有分量的和決定性的話來”[49]346。尼采說:“沒有詩,人就什么都不是,有了詩,人就幾乎成了上帝。”[49]327不能不說,他們說得很有道理。
四、思的任務:生命美學作為未來哲學
由上所述,還回到一開始就在討論的從“康德以后”到“尼采以后”,還回到“美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現在應該已經不難發現:美學其實確實并不如人們所想象的,作為美學學科的美學,作為美學教研室的教授們所教的美學,其實也根本不在現代社會的視野之內,康德、謝林、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馬爾庫塞……這些思想大家、哲學大師們眼中的美學,儼然也更多的只是一個問題、一條道路。這一點,在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中其實已經有所提示:“美學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形式提出了異常強有力的挑戰,并提供了新的選擇。”[9]導言3“本書倒是試圖在美學范疇內找到一條通向現代歐洲思想某些中心問題的道路,以便從那個特定的角度出發,弄清更大范圍內的社會、政治、倫理問題。”[9]導言1而且,佩爾尼奧拉在《當代美學》中也同樣已經有所提示:西方當代美學“將美學的根基扎在了四個具有本質意義的概念領域中,即生命、形式、知識和行為”。前兩個是康德美學的發展,后兩個是黑格爾美學的發展。而其中的“生命美學獲得了政治性意義”,并且,“已悄然出現并活躍于生命政治學”之中。
也因此,福柯當年的感嘆無疑是十分深刻的:“假如我能早一點了解法蘭克福學派,或者及時了解的話,我就能省卻許多工作,不說許多傻話,在我穩步前進時會少走許多彎路,因為道路已經被法蘭克福學派打開了。”何謂“道路已經被法蘭克福學派打開了”?顯然正是指的從“康德以后”到“尼采以后”的西方美學的成功探索。它昭示著康德、謝林、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馬爾庫塞等眾多真正震撼了世界的大哲們的目光究竟在關注什么。遺憾的是,當下的美學研究大多都沒有延續這一思想線索。當然,這些美學研究者都是一些美學教研室的教授,在他們看來,也許根本就毋需延續。
然而,在生命美學看來,如何延續他們思路,卻正是“美學終結”之后的“思的任務”。
因此,生命美學不應該是美學,而應該是“思”。它應該是“美學的終結”⑧,也應該是“思的任務”的開啟。
原來,美學的意義在美學之外。“形而上學的任務既不是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中加入某些思考的東西,也不是用各種概念來構成現實,而是試圖在自身中把握、顯示和激發現實對我們而言所包含的最深刻的生命力。”[50]因此,美學家應該關心那些能夠被稱之為美學的東西,而不是那些只是被聲稱為美學的東西;應該關心怎樣去正確地說一句話而不僅僅是怎樣說十句正確的話,因為好的美學與壞的美學之間的區別恰恰在于能否正確地說話,美學與非美學之間、美學與偽美學之間的區別恰恰也在于能否正確地說話。我在1991年的時候說過:美學,應該是“以探索生命的存在與超越為旨歸的美學”,它“追問的是審美活動與人類生存方式即生命的存在與超越如何可能這一根本問題”[51]。遺憾的是,這些苦口良言至今也很少為人們所理解。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要說的就是:傳統的美學學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審美與藝術問題。在被置身于“以審美促信仰”以及阻擊作為元問題的虛無主義這樣一個舞臺中心之后,審美與藝術,也就成為了一個問題。
在這里,重要的是“思索它們”,而不是“研究它們”[52];是“談論它們”,而不是“言說它們”[53]。這當然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學。后者,按照巴赫金的界定,“關注的是審美客體是用什么形式什么材料創造出來的”[54]。或者,按照雅格布森的總結:“目的首先就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使包含信息的字句變成了一件藝術品的?”[55]對此,海德格爾早就挑明,“這絕不是說對藝術家的活動應該從手工技藝方面來了解”[56]。波普爾更是警示說:“那些偉大的哲學家并不肩負著美學追求,他們并不想當構筑體系的建筑師。”[57]
因此,我們倒不妨傾聽一下埃克伯特·法阿斯的告誡:“藝術本身最終已經被一種非自然化的藝術理論毒害了,那種理論是由柏拉圖、經過奧古斯丁、康德和黑格爾直到今天的哲學家們提出來的。”[58]25幸而,“只有尼采作為一種仍然有待闡述的新美學提供了一個總體的框架,事實上這個總體框架正通過當代科學家以及像我自己一樣得益于他們的發現的批評家們的努力而出現”[58]34。
在歷史上,美學從未屬于過自己,它曾經屬于詩學、屬于藝術哲學、屬于科學、屬于神學……而今,借助于尼采的提示,我們終于發現:對于美學的關注,不應該是出之于對于審美奧秘的興趣,而應該是出之于對于人類解放的興趣,對于人文關懷的興趣。借助于審美的思考去進而啟蒙人性,是美學責無旁貸的使命,也是美學的理所應當的價值承諾。
結論就是這樣:美學要以“人的尊嚴”去解構“上帝的尊嚴”“理性的尊嚴”。過去是以“神性”的名義為人性啟蒙開路,或者是以“理性”的名義為人性啟蒙開路,現在,卻是要以“美”的名義為人性啟蒙開路。這樣,關于審美、關于藝術的思考就一定要轉型為關于人的思考。美學只能是借美思人,借船出海,借題發揮。美學其實是一個通向人的世界、洞悉人性奧秘、澄清生命困惑、尋覓生命意義的最佳通道。
這意味著,一方面,只有“具有充分的存在力量而向前進的人”“保持自己完整性的人”“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不滿的人”“能夠把存在的一切去方面都推向前進”的人,才會有完整的力量。因此,知識分子只信仰基督教等宗教,卻不去信仰“信仰”,是失敗的[59]。也因此,無疑就必然走向“以審美促信仰”,走向美學;另一方面,虛無主義已經不但是“訪客”,而且還已經是“常客”。“人類正在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60]這樣,要阻擊作為元問題的虛無主義,就還亟待走向美學,薩義德說:“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這里,無論是“向”(to)還是“為”(for),都標明了知識分子的及物性,或者說對于現世進行反思與批判的能力。顯然,因此也就還亟待走向美學。因為美學具備了“向”或“為”公眾說話的能力和愿望,可以成功地避免及物性的喪失、避免直面并進而解剖現世的能力的喪失。美學,因此而進入了當代思想的最前線。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美學也已經成為未來的哲學⑨。
利奧塔說得不錯:“戀愛中的人沒有一個參加哲學家的宴會。”“可是,誰又敢說,對生命做出理論性的思考不也是生活,或許還是更豐盛的生活?”[61]
還是尼采最富有先見之明:“即使人們閑置所有美(哲)學教席,我也不認為人類會停止美(哲)學的思考。”
當然不會,因為,人類恰恰因此才真正開始了“美(哲)學的思考”⑩。
注釋:
⑤具體的論述,可參見筆者的《信仰建構中的審美救贖》一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⑥我們的美學研究對此有所忽略,是沒有注意到美學研究亟待從“大道至簡”開始。例如,對于音樂首先要做“減法”,要把音樂中的美術化的視覺形象、文學化的思想概念減掉,視覺化、概念化或者美術性、文學性,或者造型性、語義性,以及形象化的內容、概念化的哲理,都不屬于音樂的美。應該去關注的只能是音的高低強弱以及節奏、速度。但是,誰又能說這樣的音樂里就沒有哲學?“德國是高度追求純音樂與絕對音樂性質的東西,而把音樂當成一種哲學式的東西來掌握的。”(野村良雄.音樂美學[M].金文達,張前,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90.)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里甚至說,“壞人”“靈魂里沒有音樂,或是聽了甜蜜和諧的樂聲而不會感動”。在音樂里,人就是存在于節奏之中的。人是節奏的存在物。節奏也是音樂的靈魂。柏拉圖認為,節奏和曲調會滲透到靈魂里面去,并在那里深深扎根,使靈魂變得優美。席勒認為,節奏中可以達到某種普遍的東西,也就是純人性的東西。節奏使得審美者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判斷力,叔本華則說,節奏“在未做任何判斷之前,就產生一種盲目的共鳴”以及“一種加強了的、不依賴于一切理由的說服力”。因此,尼采總結說,思想不會步行,要借助韻律的車輪。廣而言之,中國詩歌的“四聲八病”,其實也是節奏,它是生命的節奏,也是節奏的生命。詩歌的魅力就來自這里。那么,這是否就是“我節奏故我在”?
⑦假如再作一下比較,則可以說:實踐活動是實際地面對客體、改造客體,理論活動是邏輯地面對客體、再現客體,審美活動是象征地面對客體、超越客體。值得注意的是,范登堡指出:有三個領域能夠把人類文化的自我投射推向極端,達到文化上的超越,它們是場景、內在的自我、他人的一瞥。不難看出,這三者正是審美活動的內容。
⑧因此,我們才看到,在新時期的中國美學中,不但存在從“去實踐化”“弱實踐化”與“泛實踐化”到“去本質化”“弱本質化”與“泛本質化”的過程,而且還存在“去本質化”“弱本質化”與“泛本質化”到“去美學化”“弱美學化”與“泛美學化”的過程。這意味著:美學的終結。
⑨因此,生命美學涉及的當然不是啟蒙現代性,但是卻是審美現代性。現代性其實就是文明的教化。康德把它概括為“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魯迅說得更好:“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索要的是人。”其中,啟蒙現代性側重的是現代性的建構,關注的是現代性的現實層面以及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審美現代性側重的是現代性的反省,關注的是現代性的超越層面,是對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的反思,對理性的批判。所以,審美現代性一定是走向生命的。因此,關注審美現代性的美學也就一定是生命美學。
⑩而且,這道路海德格爾早就已經闡明:“惟憑借對尼采當作偉大風格來思考和要求的東西的展望,我們才達到了他的‘美學的頂峰,而在那里,他的‘美學根本就不再是一種美學了。”(海德格爾.尼采(上)[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163.)然而,尼采無疑做得還十分不夠:“尼采美學的問題提法推進到了自身的極端邊界處,從而已經沖破了自己。但美學決沒有得到克服,因為要克服美學,就需要我們的此在和認識的一種更為原始的轉變,而尼采只是間接地通過他的整個形而上學思想為這種轉變做了準備。”(同上書,155)在他那里,“最艱難的思想只是變得更為艱難了,觀察的頂峰也還沒有被登上過,也許說到底還根本未被發現呢”(同上書,22),“只是達到了這個問題的門檻邊緣,尚未進入問題本身中”(同上書,22)。
參考文獻:
[35]叔本華.叔本華思想隨筆[M].韋啟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
[3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4.
[37]周輔成.熊先生的人格和哲學體系不朽[C]//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黃岡縣委員會編.回憶熊十力.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35.
[38]賴特.非零和博弈——人類命運的邏輯[M].賴博,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9.
[39]舍勒.愛的秩序[M].林克,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120.
[40]塞利格曼.持續的幸福[M].趙昱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61.
[41]阿瑞提.創造的秘密[M].錢崗南,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70.
[4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4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44]歌德.詩與真[M].劉思慕,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445.
[45]宗白華.藝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339.
[4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
[47]阿昂捷夫.活動·意識·個性[M].李沂,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144.
[48]查特吉.審美的腦[M].林旭文,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49]維戈茨基.藝術心理學[M].周新,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346.
[50]奧伊肯.新人生哲學要義[M].張源,賈安倫,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160.
[51]潘知常.生命美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3.
[52]格魯秀斯.帕斯卡爾[M].江緒林,譯.北京:中華書局,2003:31.
[53]維特根斯坦.戰時筆記(1914-1917)[M].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4.
[54]塔馬爾欽科,金元浦.關于“俄羅斯當代文藝理論與中國文論研究”的對話[N].中華讀書報,2004-10-27(19).
[55]方丹.詩學:文學形式通論[M].陳靜,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
[56]海德格爾.林中路(修訂本)[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47.
[57]波普爾.通過知識獲得解放[M].范景中,李本正,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395.
[58]法阿斯.美學譜系學[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59]蒂利希.政治期望[M].徐鈞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36-137.
[60]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31.
[61]加塞爾.什么是哲學[M].商梓書,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