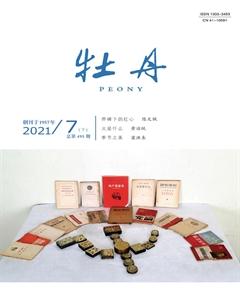從心所欲,不逾矩
武莎莎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朱光潛在美學著作《談美》中認為這是道德家的人生極境,也是藝術家的極境。通常“從心所欲”者往往“逾矩”,“不逾矩”者又往往不能“從心所欲”,凡是藝術家都要能打破這個矛盾。孔夫子到懸車之年時才做到這種境界,可見循格律而能脫化格律,大非易事。筆者在多年的藝術工作過程中,愈發體會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為創作箴言的辯證性與適用性。在藝術表現手法越來越多樣化的戲劇創作中,藝術家要能夠“循格律而又能脫化格律”,對經典藝術和前輩藝術的經驗積累要“循格律”,又需要“脫化格律”去創新,再作新時代的經典藝術,創作與時俱進的優秀藝術作品。“脫化格律”是一直努力于跋山涉水,辟蹊徑為坦途,做堅持不懈探索的一種追求。
舞臺美術是戲劇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物造型是舞臺美術藝術元素的一部分,其細致而精妙,可與演員的表情和肢體動作融為一體,因此,戲劇人物的造型可豐富戲劇表演內容。在中國傳統戲曲京劇表演中的化妝造型可以淋漓盡致地體現出化妝造型對于表演展現的重要作用。
京劇中的人物造型尤為別具一格,其鮮明特色造就了許多經典的戲曲人物形象,在觀眾心中有著深刻的認知。目前,將經典再編,以新時代的解讀方式去展現經典劇目,統稱為現代新編戲曲。新編戲曲在人物造型創作時,既要適應新編戲曲的新形式,又要保留中國戲曲的特色韻味,在多變的有形中,始終保留著中國傳統戲曲的無形本色,這是本文探討的核心所在。當今,設計師紛紛“從心所欲”,大展身手,使舞臺形象、風格呈現百花齊放的盛景。在這些經典再現、創新的作品中,如何創作出具有新時代、新感覺的優秀作品,從而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藝術極境,值得所有設計師思考。
一、推陳出新的經典造型
雖然新編京劇中的人物造型設計手法很寬泛,但還是要體現傳統京劇人物造型的藝術特色。人物造型形象如果完全改變,會與觀眾心中的角色形象相差甚遠,這意味著人物造型沒有展現京劇形象原有的鮮明信息,失去了京劇人物造型的特點,這會減弱京劇藝術本身的造型韻味,這樣的創作就“逾矩”了。
傳統京劇的人物造型經眾多名家推敲并完善,其經典的舞臺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進行再創作時,創作者要進行恰當的調整,不能使觀眾茫然不知所措,不能失去創造美的意義。因此,新編京劇在人物創作時要保留戲曲造型中民族審美的“魂”。
中國戲曲同其他傳統藝術一樣,崇尚寫意之美。新編京劇人物造型如果可以做到有選擇地突破“寫意”,則可有機地延展其藝術表現形式。京劇的藝術特征是舉世無雙的,但程式化的形式美又趨于雷同,缺了幾分生動和互動,使得觀演分離,所以創作時拓寬展現藝術表現形式以吸引觀眾產生共鳴可以作為創作思路的一個出發點,使創新后的傳統京劇人物造型不僅保留其藝術高度,又繼承大眾廣泛接受的普遍度,繼而獲得更多觀眾的廣泛關注,將傳統藝術發揚光大。
經典京劇《霸王別姬》中的人物造型形象深入人心,項羽是武功蓋世的西楚霸王,通常是勾花臉的凈角,具有不一樣的氣勢,而項羽的人生結局又是悲劇的,所以下垂眼、哭鼻的臉譜暗喻了他的宿命,這種方法是京劇人物造型常見的設計思路。
在設計新編京劇《霸王別姬》中的項羽時,筆者決定不再沿用傳統京劇的臉譜造型,這是因為一方面整個舞臺設計采用寫實風格,若沿用臉譜會顯得視覺突兀,另一方面是想賦予項羽新的形象特征。因此,項羽的造型沒有采用以形式圖案暗喻人物命運的方式,且舍棄了亂眉、下垂眼、哭鼻子的造型設計,而使演員的面部神情清晰化,更接近生活中的人物,表演者生動的面部表情更能恰如其分地演繹出人物英雄神武的一面,而非一味采用統一的臉譜。項羽的面部造型除了客觀體現其五官外,還要著重表現眉眼神氣,通過夸張的眉眼來增強表現力。
此外,由于男演員身形不高,其發型直接采用現代男子的短發造型,將豎起的頭發頂端染紅加以修飾,配合臉部的“揉紅”妝面,這樣既可以從視覺上彌補身高的不足,又融入了現代造型元素,帥氣中不失威猛。同時,針對項羽新設計的服裝,緊跟時代潮流,使多年來舞臺上濃墨重彩的項羽形象融入新的戲劇情景,符合當今時代的審美。
傳統京劇中,虞姬的扮相不同于其他的旦角。虞姬是隨軍妃子,屬花衫,但若是虞姬廣袖飄飄、云衣輕搖、百褶裙拖地,就不是劇本要展現的虞姬了。所以,戲曲中虞姬為如意冠、斗篷魚鱗甲造型,這個造型符合劇中的情境,仿佛歷史上的虞姬就是這個裝扮。在設計新編京劇《霸王別姬》中虞姬的發型時,筆者借鑒了傳統京劇中虞姬的造型,頭部保留了如意冠。但是,這個如意冠不是由發飾來體現,而是用發型體現,不僅保留了傳統京劇中虞姬的扮相,又給虞姬的頭飾設計提供了無限可能。這樣既讓觀眾看到了“老戲不長談”的新意,又沒有破壞觀眾心中的經典造型形象。
經典藝術是歷史的沉淀,設計師在設計京劇人物造型時,要對傳統京劇造型的精髓加以保留,在不影響觀眾認知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做到“不逾矩”。
二、寫實與寫意之間的“逾矩”創作
寫意是中國傳統戲曲人物造型的主要藝術風格,其呈現的神似超越了形似。傳神就是要傳人物之精神,體現人物的性格、品德、氣質等。戲曲人物造型的傳神美不僅對人物形象本身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也表現了人物性情并突出人物個性特征。
現代戲劇藝術形式多樣、現代物質材料豐富、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越來越高,這些促使現代造型設計重視形式多樣,有直截了當的視覺刺激。而形神兼備是中國古典美學理論一貫重視的藝術傳統,外露中更多的是內斂,注重的是精神層面的回味性。中國古典繪畫有六法之說,分別是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其中,應物象形、隨類賦彩是基礎,進一步則是骨法用筆,最高原則是氣韻生動。想要創作現代的經典形象藝術,筆者認為應吸取中國傳統美學的精華,體現傳神之美,在寫實與寫意間恰當地“逾矩”,相互融會貫通。
熒屏視覺藝術是現代藝術,大多采用的是寫實的表現手法,在廣大觀眾熟知的現代影視劇《包青天》中,包拯這一熒幕形象的創作靈感就來自傳統戲曲臉譜。包拯這個家喻戶曉的傳奇歷史人物,在不同的藝術形式中有著不同的體現,明代的戲曲臉譜中,包拯勾畫了兩道直的白眉,強調了他的剛正不阿;清代的戲曲臉譜中,包拯勾畫了一對緊縮的白眉,著重體現他的憂國憂民;清咸豐時期的戲曲臉譜中,包拯的眉毛上揚,額頭上出現月牙,著重體現他的神明公正。包拯的臉譜以黑色為主,用來表現他的鐵面無私。這些面部的勾勒就是以形的形式來傳神。影視劇的造型往往大都是寫實主義,在經典的戲曲妝容中恰到好處的提取出月亮與色彩的造型元素,在寫實的現代人物造型中能夠起到傳神的效果。戲曲造型能夠突出傳神效果的這種創作思路,被戲劇影視造型創作借鑒的成功范例很多。再例如,熟悉戲曲的人都知道“赤面綠蟒”是關羽的戲曲造型。在京劇臉譜中,忠貞之人多采用揉紅臉,而關羽的戲曲臉譜全臉抹紅,加上眉毛上揚、鳳目長髯,將他的英武神氣體現得淋漓盡致。影視劇中,寫實主義的造型手法提取了關羽戲曲臉譜的精華,在守矩和逾矩之間,塑造了被電視觀眾熟知的熒屏中的關羽形象:微紅的臉頰,上揚的眉毛,堅毅的眼神等。讓更多的觀眾對經典人物有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更廣的傳播作用。所以對傳統經典人物的現代再創作,化妝體現手法的逾矩就顯得更有意義了。
除了“傳神”,“形”的彰顯也是傳統戲曲化妝造型的特色,中國傳統美學中對于“形”的裝飾性和夸張性的偏愛是獨樹一幟的,以京劇人物造型為例,旦角化妝中濃郁的色彩,夸張的修正面容的技法理念;如程式化的行當盔頭、臉譜的圖案元素等都是在形式上具有很強
信號的“形”。
遼寧省歌舞團原創芭蕾舞劇《梅蘭芳》在設計舞蹈演員的造型時就巧妙地將芭蕾舞的“氣質”與京劇的“形式美”相結合,形成了獨特新穎的“芭蕾式”京劇人物。舞劇中要展現梅蘭芳先生藝術生涯中所扮演的一些著名京劇人物角色,設計師巧妙地將這些經典京劇人物造型做減法,保留了京劇人物造型的特征精華,也不干擾芭蕾舞演員在演出時的舞蹈動作,既能體現出芭蕾舞所具有的流暢線條美,又能把梅蘭芳所飾演過的經典京劇角色清晰、精確地展現給觀眾,設計師就是抓住京劇造型中的形式美,才成功地詮釋了芭蕾舞劇人物。舞者面部兩側的“片子”和后腦勺裝飾的“水簾子”是造型元素的關鍵,沒有完全照搬京劇旦角大頭的梳妝,而是運用旦角最具特征的修飾臉型的戲曲貼片和胭脂,配合帶有現代感簡潔、飄逸的改良服裝,踮著腳尖飛舞的“旦角”便躍然舞臺。刀馬旦佩戴的盔頭和翎子的藝術處理,恰到好處地點出了“京韻”,配合旋轉的舞姿,人物的心理,命運體現得更加生動。芭蕾舞的“氣質”與京劇的“形式美”都是創作中的“隨心所欲”和“矩”,在不同形式風格的演出中,兩者不斷切換,相互融合,相互借鑒,猶如太極般,為了藝術的創作呈現最終的“圓滿”。
三、相對變化中的永恒之美
每一個時代的藝術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創作語言,也有許多不可預知的新事物出現。不同的時代會賦予傳統美濃厚現代感。藝術創作者并不是讓創新取代傳統或是徹底消滅傳統,而使傳統與創新呈現一種相互影響、與時共進的狀態。
時尚感和現代性不是永恒不變的。藝術創作者要挖掘那些可以成為永恒的優良特質來充實傳統,這才是具有持久價值的藝術之道。
按波德萊爾的理解,現代性就意味著“從流行的東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有詩意的東西,從過渡中抽出永恒”,因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波德萊爾認為,現代性的變化只發生于藝術的一半,藝術的另一半是“永恒不變的”。現代性代表了藝術中變化的那部分,而不變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經典的藝術。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雖非畫家,但其《白香山集》卷十二《畫竹歌》中言:“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筆者認為其中的“似”與“真”,可作為藝術創作中的有形之“矩”,廣為發展,但大可不必固守“似”為“界”,“真”為“框”。戲劇人物造型創作形象的種子來源于生活,生活有其本來的面目,其既是創作的靈感來源,一定程度也是限制創作的具象存在,同理于人們對于戲曲經典人物造型的革新一般,現代藝術的創新要尊重傳統,挖掘經典,又不拘泥與傳統。對傳統藝術深入研究與理解,才能更好地發展傳統,為現代藝術創作所用。以“矩”為出發點,才能在無限的藝術領域開疆拓土,努力前行。
(中央戲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