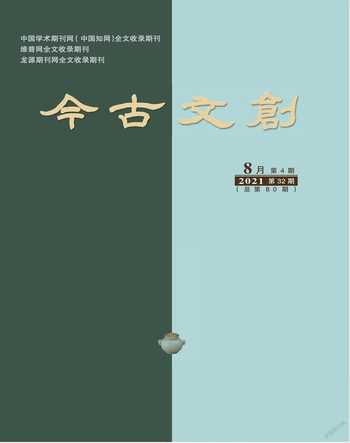論曹丕與曹植詩歌的異同
【摘要】 建安之初,“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詩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曹丕與曹植也多有此類詩作。時移世易,子建之詩著凄婉之調,子桓之詩則增悲涼之氣。藝術特征上,二人之詩都具有抒情性與現實關懷,模擬樂府并突破創新。他們的詩歌也各具特色:曹丕抒情,婉約細膩,多以女子口吻代人言情,曹植抒情,筆力遒勁,或豪情萬丈,或不平而鳴;丕詩簡明流暢,植詩辭采華茂;丕詩形式多樣,植詩句勢非常。
【關鍵詞】 曹丕;曹植;詩歌異同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2-0032-02
俊才云蒸的建安時代,文人名士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共同創造了垂范后世的建安文學。作為鄴下文人集團中最負盛名的二位公子,曹丕與曹植的文學作品極具研究價值。本文主要通過比較曹丕與曹植的詩歌,探析其中的相通與相異之處。
一、建安二公子
(一)主流題材的創作
《文心雕龍·明詩》有言:“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①
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詩,是建安詩歌的主流,曹氏兄弟也多有此類詩歌創作,如曹丕《于玄武陂作詩》寫兄弟同游、容與忘憂,《芙蓉池作》繪西園夜色、游園逍遙;曹植《箜篌引》抒游宴之喜悲,《公宴》述宴享之欣榮。
(二)詩歌風格的轉變
曹丕與曹植在詩歌創作上都存在一定的轉變,詩風可大致分為前后兩期。曹丕的詩歌創作以建安二十二年為界。是年,疾疫肆虐,與曹丕感情甚篤的王粲、徐幹、陳琳、應玚、劉楨相繼病逝,煊赫一時的鄴下文人集團陷入人才凋敝的窘境。這對曹丕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難免會陷入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前期,他的詩歌主要圍繞宴游酬贈的主題,如“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善哉行》),抑或抒寫戰爭之苦、罹亂之憂,如“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飲馬長城窟行》)。后期則多有“月盈則沖,華不再繁”(《丹霞蔽日行》)的傷逝之感以及“人生居天地間,忽如飛鳥棲枯枝”(《大墻上蒿行》)的人生慨嘆。曹植的詩歌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為界。是年,曹操逝世,曹丕繼任為王,曹植遭到貶謫,與之共事的文人謀士也慘遭殺戮。前期,曹子建以八斗之才、富艷之文,酣宴恩榮盡享,名士勝友相隨,詩歌創作主要以樂觀、浪漫的情調高唱理想抱負,揮灑少年意氣,對前途充滿信心,展現出如“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白馬篇》)的瀟灑與豪情。后期,由于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壓迫,詩歌逐漸喪失早期的豪邁自信,而多深沉悲涼之氣,發出“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吁嗟篇》)的哀嘆。
(三)藝術特征的相似
1.抒情性。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 ②的時代背景下,兩漢官方宗教神學的統治走向末路,人本意識覺醒,個性思想高揚,給抒情文學提供了發展空間。曹氏兄弟的詩歌也展現出抒情為主的傾向。曹丕朝游夕宴,欣慨交集,則道“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行軍艱苦,郁結于心,則感“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善哉行》)。悲欣苦樂,皆入詩中。曹植一朝勢落,兄弟鬩墻,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詩》);《七哀》詩中以“宕子妻”自況,哀吟“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情感溫柔敦厚、怨而不怒。這些詩歌都是緣感而發,情文相生,真摯動人。
2.平民化的現實關懷。他們的生母卞氏是身份低下的倡優出身,加上他們少年時都曾隨父出征,不乏接觸下層文化的機會,見過兵荒馬亂、白骨露野的哀景,感受過亂世中民不聊生之苦,這無疑為他們創作平民化的詩歌提供了素材。且受到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精神的影響,他們關注下層百姓的生活,詩歌帶有平民化的現實關懷,反映現實的功能增強,政治宣傳的功能削弱。如曹丕《上留田行》揭露貧富懸殊的現象,曹植《送應氏》描繪洛陽遭董卓之亂后的破敗荒涼。
3.模擬樂府。曹丕和曹植都有因聲作歌、模擬樂府的作品,同時對樂府進行了突破創新,不拘于樂府古辭的體裁,而多以五言代之,且突破原辭的本事,在詩歌的思想內容上有了發展和提升。如《善哉行》樂府古辭“來日大難”原是四言,旨在勸人及時行樂,曹丕“朝游高臺觀”篇則是五言,意在書寫宴飲奏樂,樂極悲生。《薤露》古辭原是雜言,作挽歌,曹植“天地無窮極”篇則是五言,寫人生短暫而當乘時立千古功名。曹丕的詩歌汲取了民歌明白曉暢的優點,形成了自然清麗的語言風格。《艷歌何嘗行》中“上殘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化用樂府古辭《東門行》的同時,將語言打磨得更為精致凝練,但模仿的跡象仍較明顯。曹植則創作《白馬篇》《名都篇》等樂府新題抒情言志。《美女篇》雖在形式上模擬樂府《陌上桑》,辭藻卻更華美,畫面也更細致靈動,賦予詩歌更高的意旨,造就了一種隱而不露、化為己用的境界。
二、詩性各自得
(一)抒情之異
曹氏兄弟的詩歌同具抒情性,但細品之,在抒情方式與抒情內容上又各具特色。曹丕之詩在抒情方式上有代人言情的特點,常以女子的口吻傳情達意。如《寡婦詩》乃傷阮瑀之妻孤寡所作,《清河作》代思婦言久盼征人的憂傷。曹丕個性敏感細膩,詩歌精思逸韻,善于捕捉人性中真摯動人的部分,多選取明月星辰、長路浮云的意象,在《燕歌行》二首、《永思篇》《雜詩》等篇中多有體現,如“仰看星月觀云間”“哀遐路之漫漫”“愿托乘于浮云”,往往借助這些意象抒發纏綿悱惻的凄婉之情。白天無法言說的情感積蓄到夜晚,夜不能寐,披衣出戶,仰觀月明云淡、星辰耀目,聊寄人生惆悵,訴說內心哀傷。相較于曹丕的婉約式抒情,曹植緣事而發,筆力遒勁,情感表達較為強烈。曹植任性而行,個性張揚,因而能直抒“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的自信豪邁之情。即便是建安25年后飽受壓抑,慘遭親人疏棄,他也有不平則鳴的骨氣,借詩歌抒發內心憤懣與悲哀。他常用“悲風”的意象,如“悲風鳴我側”(《贈丁儀王粲》),“弦急悲風發”(《雜詩》)。他高唱“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實際上卻空有志士報國之心,而無戎馬關山之命,于是將哀怨苦悶之感、壯志難酬之嘆揮灑于詩篇。
(二)語言之異
鐘嶸評曹丕之詩“百余篇率皆鄙質如偶語” ③,可見其詩歌有民歌的質樸,整體上的語言特征是通俗流暢。以《上留田》《艷歌何嘗行》為代表,語言如白話,簡明易曉。
曹植辭藻華麗,講究對仗煉字。如“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白馬篇》)在空間上對舉,俯仰之間充滿張力,有造勢之妙,“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侍太子坐》)則采用“白日”對“青春”、“時雨”對“飛塵”的句中對形式,語句工整而不失靈動。《公宴》詩“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一句,對仗嚴密,且巧用“被”“冒”二字,極具畫面感和動態美。
(三)特色之異
曹丕注重詩歌形式的建構,“形式的多樣性是曹丕詩的一個特色。” ④他的現存詩歌數量雖半于曹植,卻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兼備。《燕歌行》被認為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 ⑤,在七言詩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藝術表達上,曹丕常用疊詞增強表達效果,如《燕歌行》中“慊慊”“煢煢”極言孤獨之深與思念之切,《雜詩》中“漫漫”“烈烈”極言環境之凄涼,“郁郁”“綿綿”道出心境苦悶、思鄉之悲情。
曹植注重對詩歌句勢的創造。他極工起調,長于造勢。起句如“高樹多悲風”“飛觀百余尺”等,境界開闊,將全篇視野縱向展開,倍增詩歌之氣。《贈白馬王彪》一篇更是采用頂真格,首尾相接,氣勢暢達,將詩人在困頓中的掙扎和苦惱逐步推進。此外,他的詩歌多比興寄托,言近旨遠。《吁嗟篇》自比轉蓬,哀十年三徙,寄漂泊流離之感;《種葛篇》自方棄婦,嘆往昔不復,抒兄弟疏離之苦。
三、小結
無論是主流題材的創作、詩歌風格的轉變,還是模擬樂府、平民化、抒情化的藝術特征,都是曹丕與曹植詩歌的相通之處。而從詩歌的流傳、抒情方式與內容、詩歌語言和藝術特色的角度看,他們的詩歌又各有其特性。總言之,二人之詩合則氣象俊逸,分則各有千秋。子桓“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 ⑥,其詩便娟婉約,精思逸韻;子建“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 ⑦,其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不必執著于將二者一較高下,而應摒棄偏見,客觀理性地品味他們的詩歌,發掘他們詩歌的精華部分。
注釋:
①②⑥⑦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頁,第478頁,第476頁,第476頁。
③鐘嶸著、陳延杰注:《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
④余冠英:《三曹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頁。
⑤袁行霈:《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古代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3]曹道衡,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編年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4]余冠英.三曹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5]曹明升.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與魏晉文學批評的確立[J].古典文學知識,2020,(5):47-51.
[6]孫明君.建安氣象[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13(4):74-80.
[7]繆鉞.詩詞散論(增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作者簡介:
馮伊恬,女,漢族,江蘇蘇州人,揚州大學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2019級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