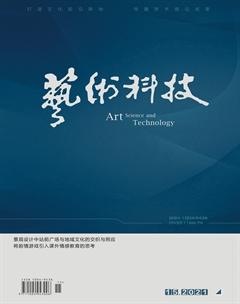動因與應對:新媒體語境下的群體焦慮
摘要:焦慮本是個體情緒,但在新媒體語境的渲染下,個體情感通過信息傳播擴大成為群體心態乃至社會問題。本文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探析新媒體時代群體焦慮的傳播機制,并試圖運用議程設置理論和意見領袖的功能為解決群體焦慮提供思路。
關鍵詞:傳播學;新媒體;焦慮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5-00-02
焦慮在心理學上表現為對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事情產生的緊張、抑郁、不安等煩躁情緒,是現代社會快節奏生活的產物,是一種現代性體驗和快速變遷背景下的時代癥候[1]。焦慮雖然是個體情緒,但是它可以依附于技術和情境進行情緒傳播,進而轉變成群體焦慮。新媒體的介入與主導信息的流動,影響著社會文化的建構[2]。它加速了情緒的傳遞,使焦慮通過信息的傳播無孔不入地滲透進各階層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容貌焦慮”“職場焦慮”“教育焦慮”,這些不同領域焦慮情緒的新名詞層出不窮。焦慮已經成為當下必須重視并且亟待解決的一類社會心態問題。
1 群體焦慮的特性
1.1 誘因的突發性
群體焦慮的誘發情境具有突發性、負面性和不確定性[3]。首先,它的產生難以預料,沒有規律可循。其次,群體焦慮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它帶來的負面情緒危害性極大,在短時間內傳播范圍廣。最后,導致焦慮的誘發情境來源并不明確,增加了解決群體焦慮問題的難度。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疫情的發生難以預料,即使多項舉措共同發力避免群體焦慮產生,但是仍然難以完全阻止恐慌情緒的蔓延。
1.2 情緒構成復雜
焦慮并不是一種單一的情緒,而是摻雜著緊張、恐懼、不安、抑郁的負面情緒綜合體。這些負面情緒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有一種負面情緒的存在,另一種負面情緒就會被喚醒,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負面情緒交織在一起,會對人產生不好的影響。
1.3 病毒式傳播
焦慮的傳播本質上是情緒的訴求和分享。根據病毒營銷研究,驚奇、愉悅、悲傷、憤怒、恐懼及厭惡六種訴求可以直接推動一個事件在虛擬人際網絡中的擴散[4]。當含有情感的事件被討論后,分享者和被分享者的思維處在同一層面,通過語言的描述可以快速構建一個情境,在此情境中當事人的情感很容易附著在語言上被他人捕捉,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共情。因此含有焦慮情感的事件極易引起病毒式傳播。情緒的易傳播性和易感染性決定了它不是短暫存在的,它可以被貯存在大腦的某個角落。當人們陷入相似情境時,上次被貯存的情緒會被喚醒。這種原本只是少數個體的焦慮,在短時間內能一傳十、十傳百,最后成為絕大多數人共有的消極情緒。
2 販賣焦慮:誰在背后推波助瀾
2.1 社會環境因素滋生焦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質的飛躍。但是精神文明發展的速度跟不上物質文明的發展速度,加上多元文化的涌入,人們的生活充斥著迷茫和不確定性。許多人逐漸在誘惑中迷失了自我,盲目跟風丟失了最初的信仰。研究表明,許多焦慮都是由社會外界壓力造成的。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環境、社會結構和經濟利益分配的急劇變化是焦慮出現的根本原因。
很多時候社會資源的分配沒辦法做到絕對公平,在教育、住房、就業等方面體現得尤其明顯。家長焦慮孩子需要更好的教育資源,即使背負房貸也要買學區房。應屆畢業生焦慮就業競爭激烈,僅憑本科學歷找不到高薪工作,只能選擇繼續考研或考公務員,考編考研人數逐年增長。類似的焦慮層出不窮,比比皆是,歸根結底源于社會上的種種競爭。
2.2 同輩比較導致焦慮升級
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作為社會動物,常常通過與相似個體比較的方法來評估自己的能力和價值。社會比較又分為向上比較和向下比較兩種方式。現代社會人們通常會選擇向上的社會比較來評判自己。多數人選擇同輩作為自己的比較對象,因為他們覺得同輩與自己從同一起跑線出發,這種比較得到的結論相對客觀。但是事實上每個個體的能力不同、背景不同、經歷不同,盲目對比后一旦發現自己與同輩在能力、榮譽等方面差距較大時,焦慮就會產生。更嚴重者會喪失自我效能,對生活失去信心,心理上的焦慮甚至會發展成生理上的病癥。
同輩比較發生在任何行業和任何年齡段,病態的競爭和比較導致內卷現象愈發嚴重。“內卷”一詞近來火遍全網,它原是由文化人類學家亞歷山大·戈登威澤提出,用于描述社會文化模式的變遷規律,主要指文化模式的固化從而不能進一步發展,無法轉化成新的文化形態[5]。現代網絡語境下的內卷指人在激烈病態的內部競爭中被迫投入更多的精力,只在有限的范圍內施展,不去向外擴張,作出一番努力之后卻得不到相對應的回報。寬泛來說,任何無實際意義的精益求精都是內卷行為。內卷的產生與同輩比較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難發現,內卷現象多發于學校和職場這兩個場所。首先是因為這兩個地方有大量的同輩人,其次是因為這兩個場所發生的競爭都和最終的個人成就掛鉤。成就不僅僅是自身努力的結果,也是經同輩襯托從而體現出的。在學校中,成績要比別人好、排名要比別人高才有機會被好學校錄取;在職場上,工作要比別人努力,考核績效比別人好才能獲得更多獎金。在這樣的高壓下,人會追求更高的排名。為了取得更高的排名,多數人選擇付出更多的努力。遺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意義,能夠取得好的結果。另一部分人發現其他人正在努力,擔憂自己不努力就會落后從而被淘汰,因此被迫加入競爭。根據社會比較效應的邏輯,同輩的成就越高,個體的比較優勢和對自身能力的評價就會越低,從而導致個人效能越低[6]。對于成績處在下層的人來說,比較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大。同輩比較之后發現個人能力不如他人會產生焦慮,為了擺脫焦慮盲目內向演化努力,被迫參與內卷。但是由于內卷更多是無效努力和無意義的競爭,實際的成果不盡如人意,會使自身更加焦慮。
2.3 受眾的認知障礙
新媒體技術建構的認識場域發生在屏幕上,受眾的認知對象不是現實中具體的人、事、物,而是屏幕中呈現的各種數字符碼[3]。因此受眾接收的信息不是立體的,而是被數字符碼簡化后的平面化內容。認知本身是具體的,它發生在由人類構建的真實社會情境中,同時人的認知思維依賴于情境。發達的新媒體技術將真實發生的情境濃縮進扁平化的文字符號里,在一定程度上剝離了受眾的真實感受和理性認知能力,使受眾產生一種虛擬現實感,與信息之間隔著一層膜。因此當人們在新媒體上獲得信息時,大腦沒有辦法準確判斷信息的真實性和價值,這就是受眾認知失調。例如,有的人看到媒體報道了有人被閃電劈中的消息就擔心自己也被閃電擊中,一到打雷下雨天就會害怕。其實人被閃電劈中這件事是在極端概率下才會發生的事情,但是由于認知失調,受眾的恐懼情緒被放大了,才會擔心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信息在新媒體上的傳播速度極快,每分鐘都有成千上萬的信息在微博等信息聚合平臺上發布。受眾在信息轟炸下大腦過濾、篩選和識別信息的速度會變慢,負荷過重之后會逐漸產生認知疲勞,漸漸對信息感到麻木。認知疲勞狀態下人們接收信息會受到阻礙,僅靠文字或視頻的視聽方式會使受眾對“真實”的體驗消失。明明是未曾經歷過的危險、恐怖事件,卻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大腦會不由自主地產生焦慮、緊張、害怕等情緒。
2.4 自媒體的推波助瀾
焦慮的傳播離不開自媒體在幕后的推波助瀾。自媒體是指運用移動互聯技術,創建屬于自己的獨立媒體賬號的新媒體的總稱。技術的變革使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逐步成熟,移動端的用戶數量不斷增加,快節奏的生活讓人們無法忍受冗長的視頻,對簡潔短小的視頻需求不斷增加。順應時代的潮流,自媒體如雨后春筍般興起。融媒體時代,自媒體被賦予了話語權,他們不僅是新聞制造者,也是信息傳播者。與傳統主流媒體不同的是,自媒體的傳播手段偏向私人化、自主化和平民化,傳播內容碎片化。令人眼花繚亂的信息,其源頭和真實性在還未證實的情況下就已經被廣泛傳播,影響人們對事情的判斷,加重了人們的焦慮。部分自媒體和營銷號追求流量利益,缺乏社會責任感,完全不考慮信息發布之后是否會引起網民的恐慌和焦慮。比如在疫情期間,許多媒體在未經醫學專家證實的情況下,將雙黃連有抑制新冠病毒的信息發到網上,引起民眾大規模搶購雙黃連,民眾的焦慮情緒再次升級。
3 應對焦慮:引導受眾正確釋放焦慮情緒
3.1 意見領袖的引導作用
意見領袖是指在兩極傳播中,具有傳播信息功能且具有支配和引導地位的角色,是信息發布和產生影響的中間過濾環節,對信息傳播有重要的影響。意見領袖對信息的傳播有協調和干擾的作用。如果意見領袖提出的觀點是符合其團隊成員主張的,那么意見領袖的觀點會取得多數人的認可,雙方協調操作,能給大眾傳播提供長久的動力。
互聯網時代,意見領袖往往是一些自媒體和有獨特見解的網紅,他們觀點新穎,有一定的影響力,受到許多人的追捧。面對群體焦慮,意見領袖應該清楚地意識到個人言行對受眾的影響,理應具備社會責任感,引導受眾正視焦慮。因此意見領袖應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不傳播謠言,不發布虛假信息,拒絕道德綁架,避免發布引起受眾“身材焦慮”“容貌焦慮”“學業焦慮”等負面情緒的信息,多傳播具有正能量的、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積極信息。
3.2 強化議程設置,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
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大眾傳媒對某些命題的強調程度,和這些命題在受眾中受重視程度成正比關系。議程設置包括“媒體議程的設定”“公眾議程的設定”“政策議程的設定”三個環節[7]。如今各種風格的新媒體層出不窮,受眾的興趣轉移十分快速,單純傳播信息的議程似乎無法滿足受眾的新鮮感。為了吸引受眾,一些議程設置迎合低俗需求,靠做“標題黨”博得受眾的關注。因此,大眾傳媒作為大部分受眾接觸信息的第一傳播主體,首先要對信息進行篩選過濾,確保承載核心價值觀的議程傳播渠道[8],杜絕虛假不實的信息在網絡上傳播。其次大眾傳媒要把握傳播主動權,有的放矢,圍繞群眾關注的熱點事件及時發聲,同時注意輿論的引導,避免引起人們矛盾和焦慮情緒,要倡導積極的理想信念。
3.3 加強心理健康教育
目前我國患焦慮癥的人數在逐年增長,社會對焦慮癥患者的關注還不夠,心理健康教育還有待加強。對焦慮癥等心理疾病的科普工作不足,導致許多人將焦慮視為洪水猛獸,對于焦慮閉口不談,有焦慮的癥狀后不愿去醫院尋求幫助,焦慮癥狀不僅不會緩解,還會嚴重惡化,妨礙正常生活。對此,國家要推進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向人們科普什么是焦慮,分析焦慮的來源,探尋焦慮傳播的原因。讓人們正視焦慮,了解焦慮,并且不要對焦慮的存在感到恐慌。學校、單位和社區都可以設置心理咨詢室,呼吁大眾對已有焦慮癥狀的民眾給予理解,鼓勵他們積極就醫。
4 結語
群體焦慮是一個無法被避免的社會問題,但絕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誠然,焦慮可以化為奮斗的壓力,從而提升自我,但是現在豐富的社交媒體生活不僅不利于個人焦慮情緒的釋放,還容易通過轉發、分享、點贊的互動形式形成矩陣式傳播。越來越多的人喜歡用表情包的形式來調侃焦慮,于是這種戲謔焦慮的方法逐漸成為一種喪文化的表達方式,面對焦慮不想辦法緩解、治愈,而是以“躺平”的形式任其蹂躪。群體焦慮會產生一種不健康的信息環境,在這個視域下,個人積極性遭受嚴重打擊,甚至會引發社會矛盾。因此社會要加強對焦慮的關注,人們也應該用平常心對待群體焦慮,從多角度出發剖析其產生的原因,對癥下藥,尋求化解焦慮的方法。
參考文獻:
[1] 劉洋.群體焦慮的傳播動因:媒介可供性視角下基于微信育兒群的研究[J].新聞界,2020(10):40-59.
[2] 劉丹凌.新傳播革命與主體焦慮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06):93-128.
[3] 俞國良.群體焦慮抑或社會焦慮:特點、成因和應對[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3(06):406-411.
[4] 欒心怡.“販賣焦慮”現象流行背后的傳播機制[J].青年記者,2018(06):7-8.
[5] 方慧.探析內卷視域之下年輕群體的焦慮傳播[J].視聽,2021(07):196-197.
[6] 曹蕊,吳愈曉.班級同輩群體與青少年教育期望:社會遵從與社會比較效應[J].青年研究,2019(05):25-33,94-95.
[7] 馬馭.網絡時代新媒體新聞評論的引領與創新[J].視聽界,2021(03):91-93.
[8] 薛一飛.新媒體傳播的議程設置實踐創新研究[J].傳媒論壇,2020,3(23):30-31.
作者簡介:徐彥青(2000—),女,江蘇蘇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
指導老師:馮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