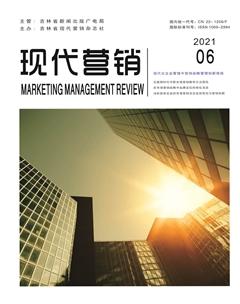探究新茶飲店中的消費儀式
黃斌
摘要:文章借用“儀式”的定義來闡釋消費社會中人們購買以奶茶為主的新茶飲行為,并以時下奶茶市場中的頭部品牌——喜茶為例,來探究該品牌是如何借助廣告符號完成消費儀式,進一步歸納出廣告符號令產品演化為象征物,激發消費者前往店鋪進行“媒介朝圣”并對于某類角色有所期待與主動扮演,設置儀式腳本,及觀看表演的他者。儀式的進行中令消費者參與到商品意義的生產,并衍生出新的意義。
關鍵詞:消費儀式;喜茶;商品意義;符號
新式茶飲“是采用不同萃取方式提取上等茶葉的濃縮液作為茶底,加入新鮮牛奶、進口奶油或各類水果調制而成的飲料,市面上的新式茶飲多以奶蓋茶和鮮果茶為代表”[1]。在眾多品牌中,喜茶脫穎而出,榮獲2020年上半年最受歡迎的茶飲稱號。新茶飲店抓住年輕人特立獨行、標榜自我的心態,讓飲茶這件事不再框定在一隅茶室間,而是與逛街、看電影等情景相聯系,向年輕人傳達出“喝茶,也可以很酷”的消費理念。這背后離不開廣告符號的助推,并形成了獨有的一套消費儀式。本文旨在探析消費儀式如何令喜茶出圈,又是怎樣構筑該品牌并豐富商品的意義。
一、儀式的由來
“儀式”這一概念起源于19世紀,被視作是人類經驗的一個分類范疇上的概念[2]。 人類學研究中基本將“儀式”界定為人類的社會行為,把儀式視作文化的原初形態,與神話間存在互文關系,雖然人類學家對于儀式的仍有差別,但均把儀式研究與神話相勾連。例如古典進化論學派的Edward Taylor把儀式納入“神話”的范疇,提倡“物質形態神話”這一說法。弗洛伊德追隨者將“俄狄浦斯情結”視為某個儀式的言說[3],認為是神話與儀式的聯袂展演。后期儀式研究開始與各個學科交叉融合,例如文化儀式、社會儀式、傳播儀式、儀式音樂等,學者們更為注意探索儀式同社會實踐二者的關系。例如李明華考察了中日兩國中元節的異同,比較二者間節日形式及相應儀式流程所體現的不同國別人民文化中帶有的延續性與習俗[4]。有人在傳播儀式觀的視角下,以春節聯歡晚會與北京奧運會兩大媒介奇觀為例,探索了傳媒是如何形塑文化認同[5]。總之,現在儀式的研究領域更加廣闊,被許多學科所納用進行分析,學術界目前尚未對“儀式”達成統一的定義,且多為描述性質,普遍將儀式看作是以某種固定方式,有序并重復出現的連續性的象征性行為。
二、消費儀式的界定
目前學術界對于“消費儀式”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較為零散,實證研究較少。孫乃娟等在論文中運用社會聯結理論、社會身份理論、調節聚焦理論對消費儀式的內涵、情境、演化進行了評述與回望[6]。費顯政等通過回顧文獻與二手數據開發出信效度較好的消費儀式感量表,測量消費儀式感“非功能性、禮儀性、獨特性、付出性、”四維度[7]。另外,在此對另一相似概念“儀式消費”進行區分,通過文獻梳理,筆者發現“儀式消費”的談論對象多在群體層面,且與民俗習慣、傳統節日,民間信仰相關。例如鐘鳴在博士論文中分析了馬達加斯加昂巴村降生、割禮、婚禮、翻尸、喪禮等人生儀式中各項大額消費與當地居民貧困的關系[8]。薛海波選取中國人最具儀式感的家庭聚餐“年夜飯”,從主體、時間、相關活動、情境四方面來解構該消費儀式,探討年夜飯是如何影響自我認同與建構家庭認同[9]。本文所討論的“消費儀式”則是在盧克“儀式四要件”理論基礎上,加入“媒介朝覲”這一環節,聚焦在被學者忽視的日常生活中,個人層面的消費行為。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物的符號體系》《幻象與仿真》等書中多次提到后現代社會中“物化價值體系”的流行, “人們周圍存在著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的現象,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10]在此借用儀式的四個部分來考究消費行為,將消費儀式視作個人在媒介所打造的特定空間內,通過某種象征物,遵照儀式腳本,在觀眾的凝視中,扮演內心所期待認可的角色的具有規律性的消費行為。通過儀式,商品本身的意義傳至消費者,令消費行為本身也具有符號意義。
三、消費儀式影響下的商品意義
商家試圖通過廣告令消費者在無形中在消費某種商品時養成固定的習慣,否則便不認為自己真正體驗,使用了該商品,即投身于消費儀式中。例如奧利奧的“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已經深入人心,該品牌已經有108年的歷史,#奧利奧粉了#獲得2020年最佳電商營銷創新獎金獎,其電商總監談到,好吃只是基礎,好玩很重要,這里的“玩”可以理解為消費儀式的腳本運作,培養了消費者的習慣,作出儀式化行為,將商品與日常生活相聯系,間接影響了消費者的情感偏好,一次完整的喜茶消費過程可視作是一套消費儀式,后文將結合象征物、腳本、角色塑造、觀眾、朝圣空間五部分來進一步論述。
(一)消費儀式的中介——象征物
象征物出現在整個消費儀式中,是儀式進行的基礎,消費者開展消費儀式的先啟,沒有了象征物,儀式也就無從做起,具體到本文則是一款喜茶產品。喜茶的創始人聶云辰從最初 者青睞。2020年間上線的天貓旗艦店,發售果汁、餅干等新產品,線上形式更能展現產品的顏值。另外,各類聯名也讓喜茶打破“一杯奶茶”的固有認知,2020年,喜茶與14個品牌進行聯名,例如與茶顏悅色聯名推出限量款禮盒立即被搶購一空,與“回力”聯名推出特別款球鞋,與wonderlab推出聯名款代餐,以此創造稀缺,增加關注度。
(二)消費儀式的底稿——腳本
本文的儀式腳本主要指菜單,菜單可以看做是消費者主動權的體現。喜茶產品的名稱并不是拘泥于“XX茶”,例如茗茶中的紅玉、綠妍、青霧、金鳳茶王,混合茶里的青玫、靜岡抹茶,當日限定的芝士芒等八大類。除了大小杯的區分外,消費者可以自行選擇底茶、甜度、加料等,以自己的喜好進行定制。值得一提的是喜茶的隱藏菜單,即“商家和高級用戶之間的專屬定制,并不會直接地放在菜單上,通過重新組合現有菜品來打造出口味獨特的爆款”。起初隱藏菜單是店家與常客間的對接暗號,象征著身份的尊貴,而社交媒體的發展令暗號也逐步推廣開來。隱藏菜單走紅的背后有以下兩點,一是提高了消費者的參與度,在點單中,消費者易形成一種親身制作的感受。二是提高消費的趣味性與游戲感,自由組合來調制自己喜愛的口味能提供新鮮感,三是增加了可分享的迷因,“隱藏”二字讓人有種發現神秘寶藏,向他人夸示的感覺,這種炫耀消費已經脫離了原有使用目的,為了彰顯聲名與地位[11]。
(三)消費儀式的祈愿——塑造角色
儀式可被視作是一種流程化的表演,消費者參與力度大,借表演來打造某種形象的功用更為突出。當消費者有了共同的目標時,會就商品的符號內涵開展磋商,形成共識,這本身也是在厘清群體邊界,構建社會認同[12]。消費者借用某類商品來定義本群體的地位階層,品味特征,與其它人群加以區分,將該群體內認可的符號予以形成通約,融入日常生活中。所涵括的產品體系之中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中提到“前臺”與“后臺”,前臺是個體以較為固定一般的方式為觀看者定制的某個特定的角度來看到某一情境,即學者董晨宇所概括的:給予強化、流露弱化,喜茶一杯價格在二三十元不等,屬于奶茶中的“高定品”,盡管一些學生或白領收入并不能完全匹配這個價位,但為了加入喜茶所營造的消費泡沫中,也選擇購買來強化自己時尚、酷炫的形象。商品符號崇拜不僅能滿足個體的表現欲,更在于符號使用者的群體規訓效用:即自我的消費源于他人,消費行為在他者的認可與肯定中轉換為自我的心理慰藉。在此背景下,消費更突出社會文化意義,劃分著不同的社會群體,消費者被商家的符碼全套所宰制,爭相用更多符號打造一個更好的形象。
(四)消費儀式的展演——觀眾共在
如果儀式僅由消費者在場的話,便失去了它的意義,需要有他者在場的觀看才更為完整。廣告符號通過增強象征物的知名度,讓更多人加以知曉,縮短了商品與消費者之間的鏈路距離。社交媒體就像是個人自我陳列的展館,來增加個人的曝光度,獲取更多關注度。許多人在購買喜茶后,或者在喜茶店中,會對其進行拍照,上傳至社交媒體,來賺取更多社交貨幣。除開茶飲的包裝,喜茶所提供的休閑空間,禪意、潮流的設計讓“喝茶”這項古老的儀式煥發新的活力,也增加了消費者分享的欲望。例如喜茶在12月份舉辦的INNERAECT2020潮流展會上發起了一項創意活動,將非遺文化與流行元素相結合,攜手中華老字號榮寶齋和著名藝術家DIgiway,并借微博來激發消費者參與圍觀,從而加強消費者與喜茶之間的情感關聯與提升消費者忠誠度。對于消費者而言,拍照上傳到個人平臺,能獲得布爾迪厄口中的“社交貨幣”,激發個人的表達欲望,增加與他人的談資,獲得更多的群體認同感。
(五)消費儀式的神壇——空間朝覲
朝覲行為在社交媒體與商業資本互相助推的當下實現祛魅,轉為自拍、擺拍、定位等儀式行為。庫爾德里將當代游客去到媒介敘事語境的實際地點的旅游行為稱作“媒介朝圣,不僅是跨越空間的真實游歷,也是在‘媒體世界與‘現實世界當中的距離所產生空間的實際行動[13]”,即去到媒體所描繪的世界,在朝圣中打通媒體的“里”和“外”。在此把去喜茶店鋪打卡消費視為一種旅行,先設條件即消費者認可了喜茶各個媒體平臺對于店鋪的宣傳。庫爾德里把媒體敘事間的地點視為對現實空間的擬像、仿真、再現,借由社交媒體在消費者內心創設某種想象,個人在商家推出的信息中進行甄別思量,預估是否要前往該地進行消費。喜茶別致的裝修風格和一些特殊主題的店鋪、展覽讓它成為消費者心中的“網紅目的地”,即打破消費者對同類景觀空間的既有認知,在單調生活外產生“震驚感[14]”,這種震驚感會讓人暫時性擺脫日常生活所滋生的麻木感,獲取興奮與愉悅,“沖動”地想前往該店鋪朝圣。
(六)結語
本文在“儀式”概念基礎上,選擇盧克所的“儀式四要件”概念(象征物、儀式腳本、扮演角色和觀看者)對當前年輕人在購買新茶飲產品中存在的儀式行為進行分析,并認為除了上述四部分外,“消費空間”也可以納入儀式分析中。具體而言,在喜茶特定的店鋪或者活動地址中,茶飲及各類周邊、聯名產品是消費儀式中的象征物,菜單及推薦喝法是儀式腳本,借助飲茶來塑造某種理想角色是儀式的第三部分,最后獲得觀眾的觀看支持。系列消費儀式讓人們奶茶等商品更具象征意義,不僅要好喝,也要讓人覺得“這奶茶看起來好有格調,我喝它會看起來有品味”,追求視覺快感的心理機制下,人們從“商品拜物教”中跳入“形象拜物教[15]”。值得注意的是,個人需警惕消費儀式帶來的快感而忘卻對現實生活的感知,應合理地消費喜茶等商品,在符號打造出來的景象前持有理性精神。
參考文獻:
[1]何群仙.淺談新中式茶飲之茶概念創新與質量控制[J].中國茶葉,2019,35( 2) : 43 -46.
[2]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研究評述[J]. 民族研究,2002年02期.
[3] Crossman,R.H.S.Plato Today,London:Unwin Books,1963
[4]李明華. 中日中元節民俗儀式比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5]邵培仁,范紅霞.傳播儀式與中國文化認同的重塑[J].當代傳播,2010年第3期.
[6]孫乃娟,范秀成,張琦詩.消費儀式觀研究述評與展望[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