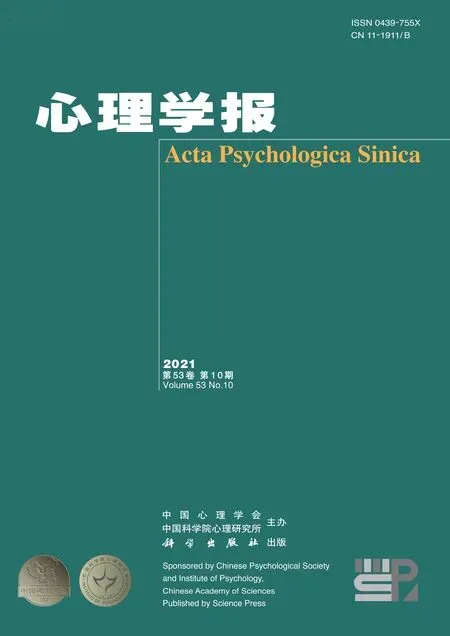職場排斥對員工家庭的溢出效應:歸屬需求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作用*
鄧昕才 何 山 呂 萍 周 星 葉一嬌 孟洪林 孔雨柔
(1 貴州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貴陽 550001)
(2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 廈門 361005)
(3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深圳 518060)
(4 上海大學管理學院,上海 200444)
1 問題提出
隨著組織多元化結構的快速演變和職場競爭的愈發激烈,組織內部的利益沖突和人際摩擦難以避免,職場“冷”暴力問題呈現出上升趨勢(Liu et al.,2013)。中國組織情景中的差序氛圍和“圈子文化”較為濃厚,使得職場排斥呈現出普遍性高和危害周期長等特點(Zhu et al.,2017;陳晨 等,2017)。同時,中國人普遍存在的“隱忍”特質以及傳統文化倡導的“以德報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等價值觀,也使得被排斥者受到的傷害相比于其他“冷”暴力更加隱蔽和持久(Wu et al.,2012;Zhu et al.,2017)。既有研究主要從心理、態度、行為和績效四個方面揭示了職場排斥在組織內部的危害和影響機制,但對于職場排斥向組織外部的溢出效應卻鮮有涉及(陳晨 等,2017;姜平,張麗華,2021)。相較于西方社會,中國員工的工作與家庭邊界相對模糊(Au &Kwan,2009),員工在職場的不良遭遇更容易通過員工的心理和情緒狀態溢出到家庭領域,從而影響員工的家庭生活和后續工作(Ashforth et al.,2000;Edwards &Rothbard,2000;Ten Brummelhuis &Bakker,2012)。
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s)強調的是工作和家庭兩個領域中的相互影響和跨領域轉移過程:員工的家庭貶損是工作-家庭負向溢出中典型的低強度偏差行為傾向,會對家庭和諧產生破壞性影響(Hoobler &Brass,2006;Restubog et al.,2011);員工的家庭滿意度是正向溢出的重要衡量指標,同時也是良好家庭績效和家庭整體幸福感的基礎(Liu et al.,2013;Ten Brummelhuis &Bakker,2012)。既有研究表明組織內部因素會溢出組織邊界對家庭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倫理型領導和LMX 等因素正向增益家庭滿意度(Liao et al.,2015;Liao et al.,2016),而辱虐管理和職場性騷擾等行為則給會員工的家庭生活帶來困擾(Hoobler &Brass,2006;Xin et al.,2018)。本研究首先要探討的問題就是職場排斥的危害是否會溢出到家庭領域,一方面是否會讓員工產生家庭貶損,另一方面是否會降低員工的家庭滿意度。其次,資源保存理論從資源消耗與獲取的視角為職場排斥的具體溢出機制提供了理論框架,職場排斥所帶來的被排擠忽視的痛苦、關鍵資源阻斷以及社會關系破壞無不損耗著員工的心理資源。資源損耗以及后續的連鎖反應會對員工產生持續性壓力困擾,有可能會溢出到家庭領域(Liu et al.,2013;嚴瑜,王軼鳴,2016;Howard et al.,2020)。因此,職場排斥的不良影響如何溢出到家庭領域,工作壓力是否在溢出效應中充當了關鍵性的穿透因素,這是本研究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此外,資源保存理論還指出不同個體對受損資源的價值評價存在差異,從而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壓力認知和反應,更在乎集體歸屬、他人認可的個體對于排斥更為敏感,職場排斥對于其資源損耗會更大(O’Fallon &Butterfield,2011)。因此,本研究探討的第三個問題是不同歸屬需求水平的個體是否會對職場排斥的壓力感受和行為反應有所不同,進而影響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的溢出效應。最后,個體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是決定工作-家庭邊界滲透性和區隔性的重要因素,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較低的被排斥個體傾向于將工作-家庭邊界模糊化和一體化,使得排斥引起的壓力反應更多能溢出到家庭領域(賈西子,蘇勇,2020;Kreiner,2006;Nippert-Eng,2008;Howard et al.,2020)。因此,在不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水平下,工作壓力對家庭領域的傳導是否存在著差異,進而影響職場排斥到家庭領域的溢出效應?這是本研究探討的第四個問題。本研究的整體研究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1.1 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
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認為個體具有努力保持、保護、培養和獲取資源的傾向,這些資源既包括物資資源、條件資源和社會資源,也包括心理資源、控制資源和能量資源等,個體的資源損失遠比資源獲得的影響更大更持久,在資源損失過程中和其后一段時間會引發一系列的身心后果(Hobfoll,1989,2001;Hobfoll et al.,2018)。
職場排斥是指員工在工作場所中對于來自領導、同事等多個方面的忽視排擠和孤立冷漠的主觀感受(Ferris et al.,2008)。遭受職場排斥的員工極易產生焦慮、沮喪、抑郁等一系列消極情緒,他們需要耗費額外時間和精力去評估、抑制和調整消極情緒和心理壓力,這些都會損耗大量的心理資源(吳隆增 等,2010;Hagger et al.,2010;Lee et al.,2016);同時,資源保存理論指出遭受資源損失的個體會針對性地投資新資源來試圖脫離損失狀態(Hobfoll,2002;Halbesleben et al.,2014;Hobfoll et al.,2018)。為了打破人際互動障礙,被排斥員工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去揣測他人意圖、評估人際環境和尋求被冷落原因,有意識地做出親社會行為或逢迎行為來竭力擺脫被孤立的困境,從而引發能量資源和控制資源的進一步損失,最終進入“資源損失螺旋”(康勇軍,彭堅,2018;Zhu et al.,2017)。
一方面,長期的消極情緒控制和人際關系修復嘗試會使員工身陷資源損失螺旋,較大資源損失或瀕臨資源耗盡的個體容易產生一些非理性、缺乏自我控制、低未來取向的行為傾向(Ito &Brotheridge,2003;Halbesleben &Buckley,2004;Baumeister et al.,2007)。這種傾向在職場內表現為職場不文明行為、反生產行為等(Lee et al.,2016;Zhao et al.,2013),而當資源匱乏狀態溢出到家庭生活時,處于資源損失螺旋的員工會在家庭生活中出現低強度的不良行為和傾向,例如針對家庭的負面發泄傾向,產生言語或者態度上對家庭的厭倦和貶損,甚至對家人的言語侮辱等(Ten Brummelhuis &Bakker,2012;Liu et al.,2015)。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資源保存理論,個體在特定領域資源損耗需要從其他領域獲取資源來替代和補充,資源損失的被排斥者會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家庭領域的各類資源,致使個體無暇顧及和體驗家庭生活幸福(Halbesleben,2006;Ten Brummelhuis &Bakker,2012)。資源保存理論還指出處在資源損失狀態下的個體,其資源評價的尺度會發生較大變化,對于周邊資源補給的期望和要求會有所強化(Hobfoll,1989;Hobfoll,2001;Hobfoll,2002;Hobfoll et al.,2018)。家庭滿意度是個體依據自身設定的標準和期望對家庭生活質量的主觀評估(Carlson et al.,2010),遭受排斥的員工長期處于資源缺乏、損耗甚至于瀕臨耗盡的狀態,這類員工對家庭領域資源補給會抱以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在家庭環境客觀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被排斥員工會因相對變高的期望未能滿足而導致較低的家庭滿意度(Halbesleben &Buckley,2004;Hobfoll et al.,2018)。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職場排斥對家庭滿意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1.2 工作壓力的中介作用
工作壓力是指員工在工作環境中感知到的對工作資源和行為造成威脅、損耗的心理反應(House&Rizzo,1972)。根據資源保存理論,作為職場內不良的人際互動體驗和困擾,職場排斥是一種典型的阻斷性壓力源:一方面,感受到來自領導或者同事忽視的員工難以掌控職場環境,從而需要消耗額外的資源去重新獲取對環境的控制,這一過程會使得員工產生心理壓力;另一方面,職場排斥阻斷了員工的組織關系和社會關系,員工難以從組織成員那獲得提升工作技能、解決工作問題所需要的支持性信息和關鍵性資源,以致于無法應對工作要求和任務,最終導致員工出現高焦慮、高壓力的狀態(Halbesleben,2006)。
職場排斥阻斷了工作-家庭增益的情感型和工具型路徑,從而觸發兩種壓力應變反應溢出到家庭領域,干擾員工的心態和行為傾向(Greenhaus &Powell,2006;Lim et al.,2008):一種是基于情感的壓力應變反應。被排斥員工累積在心中不良情緒和壓力受組織規范所限難以在工作場所內得到排解和釋放,通過對家庭成員的宣泄或貶損來釋放壓力是被排斥員工最直接的方式(Liu et al.,2013;Nohe et al.,2015;嚴瑜,王軼鳴,2016)。在這種情況下,員工對家庭領域的沖突感知更加敏感,也使其更容易對家庭產生厭倦感(Wu et al.,2012);另一種是基于行為的壓力應變反應。不良人際關系給員工帶來的職場內自我否定和自我挫敗感也會通過壓力反應溢出到家庭中,員工的家庭角色履職效能感會顯著下降(嚴瑜,王軼鳴,2016),甚至可能采取一些非暴力但富有破壞性的行為來緩解壓力,比如家庭溝通中表現出富有攻擊性或者貶損行為傾向等壓力應變反應(Swimberghe et al.,2014)。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工作壓力在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之間起著中介的作用。
職場排斥所帶來資源枯竭導致了員工內心壓力劇增,持續的阻斷性壓力源容易使員工陷入負面情緒漩渦中難以抽離,當轉換到家庭角色中時員工也容易在負面陰影的籠罩下以消極情緒和態度對待家庭生活(Hobfoll,2001;Hobfoll,2002;Nohe et al.,2015)。同時,心理壓力會刺激和誘導被排斥者更關注工作家庭中的消極因素并對周圍環境信息進行負面加工識別(Forgas &George,2001);另一方面,被排斥者傾向于在家庭領域來釋放和化解負面情緒和工作壓力,會在一定程度上無意識的提高對家庭成員和環境的主觀要求和預期(Halbesleben &Buckley,2004;Hobfoll et al.,2018)。負面信息加工的強化以及主觀要求和預期的提高降低了員工對家庭的主觀滿意度(Liu et al.,2013),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工作壓力在職場排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起著中介的作用。
1.3 員工歸屬需求的調節作用
資源保存理論指出個體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對資源損失的感知、保護和獲取資源的傾向程度,不同個體對于損失資源的主觀價值判斷差異決定了其壓力反應強度和持續時間(Hobfoll,1989;Hobfoll,2001)。歸屬需求是指個人對于建立、維系與他人社會聯結的內在需要(Baumeister &Leary,1995),具有不同歸屬需求特征的個體感受到的職場排斥對資源損耗的程度存在差異。具體而言,高歸屬需求的員工傾向于與他人保持親密關系,同時具有較強人際關系敏感性,對來自他人的排斥、拒絕和孤立更為敏感和在意(Pickett et al.,2004;O’Fallon &Butterfield,2011)。此外,當高歸屬需求個體感受到排斥時,會更傾向于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彌補與他人的聯結(如親社會行為、逢迎行為),這些反應會消耗大量心理資源,進一步加劇了工作壓力(Zhu et al.,2017)。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歸屬需求調節了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之間的關系,即員工的歸屬需求越強烈,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之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強。
進一步地,歸屬需求偏高的個體更在乎集體歸屬、他人認可,對排斥所帶來的相關資源損失更加敏感,因而會觸發更深的工作壓力和更持久的后續壓力反應,進而對家庭領域產生影響,導致家庭貶損傾向的增加和家庭滿意度的下降(Hobfoll,1989;Hobfoll,2001;Pickett et al.,2004)。當員工歸屬需求低時,員工感知到的職場排斥帶來的資源剝奪感較弱,繼而工作壓力較低,從而緩解了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的溢出效應。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歸屬需求調節了職場排斥和家庭貶損之間通過工作壓力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員工的歸屬需求越強烈,這一間接關系越強。
H:歸屬需求調節了職場排斥和家庭滿意度之間通過工作壓力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員工的歸屬需求越強烈,這一間接關系越強。
1.4 員工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調節作用
個體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是決定工作-家庭邊界滲透性和區隔性的重要因素(Kreiner,2006;Nippert-Eng,2008)。資源保存理論認為個體在出現資源損失時會用其他領域的資源來替代和補充,而個體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的替代領域指向家庭領域的具體程度,進而決定了壓力反應向家庭領域的溢出程度(Hobfoll,2001)。高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個體的工作-家庭邊界具有較嚴格分割界限和低滲透性(Liu et al.,2013;王桃林,2019;Xin et al.,2018),這類員工更多地將資源損耗影響控制在工作領域之內,或者利用友情領域等非家庭領域來進行來資源替代和補充(Ito &Brotheridge,2003;Halbesleben et al.,2014)。而低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個體則傾向于把家庭當做是資源枯竭的“避風港”,更多地通過對家庭的宣泄或貶損來釋放壓力,進一步加劇家庭預期與實際感知之間的差距(Xin et al.,2018)。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調節了工作壓力與家庭貶損之間的關系,即員工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越強烈,工作壓力與家庭貶損之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弱。
H: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調節了工作壓力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關系,即員工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越強烈,工作壓力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負向關系就越弱。
進一步地,具有較高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員工,即使遭受了他人的冷漠忽視和孤立排擠,他們也傾向于將工作壓力控制在工作領域之內,避免釋放壓力的宣泄和貶損行為溢出到家庭生活中(Xin et al.,2018);同時,當員工轉換到家庭角色中時,高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員工能夠快速地從高壓力和負面情緒旋渦中抽離,從而削弱了職場排斥對家庭滿意度的壓力溢出(Kreiner,2006)。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調節了職場排斥和家庭貶損之間通過工作壓力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員工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越強烈,這一間接關系越弱。
H: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調節了職場排斥和家庭滿意度之間通過工作壓力的間接關系,具體而言,員工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越強烈,這一間接關系越弱。
2 研究方法
2.1 樣本及程序
為了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增強結果的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本研究通過兩次調研來檢驗研究假設。樣本1 和樣本2 皆采取多時點問卷數據收集方式,分別開展3 輪調研,樣本1 每輪間隔一個月,樣本2 每輪間隔一周。在樣本1 中將員工初始的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狀態(T1 階段采集)作為控制變量進行檢驗,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分隔開其他干擾因素對員工家庭貶損以及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更好地凸顯職場排斥溢出到員工家庭態度和行為的凈效應。在樣本2 中將職場排斥影響機制中可能會對工作-家庭邊界產生影響的消極情緒和情緒耗竭作為控制變量(Jiang et al.,2020;Howard et al.,2020),以排除個體情緒相關因素對工作壓力溢出機制的干擾。
樣本1:對16 家旅游服務企業的一線服務員工開展了3 輪調研,從與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的員工中隨機挑選了444 名并對其逐一編號。第一輪問卷(T1)涉及的信息包括員工的社會人口信息、職場排斥、歸屬需求、工作家庭區隔偏好以及初始狀態的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第二輪問卷(T2)填答工作壓力;第三輪問卷(T3)中填答員工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共發出444 份員工問卷,經3 輪次調研剔除離職或調崗人員答卷和無效問卷后,本研究共得到264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59.46%。在這264 名員工中,男性占20.45%,樣本的平均年齡為30.32 歲(SD
=8.89),擁有小孩個數平均為0.60 (SD
=0.62)。樣本2:對5 家酒店和旅游服務企業的一線服務員工進行3 輪調研,調研對象需與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第一輪問卷(T1)調研信息包括員工的社會人口信息、職場排斥、歸屬需求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第二輪問卷(T2)信息包括員工工作壓力、情緒耗竭和消極情緒;第三輪問卷(T3)填答員工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共發出300 份員工問卷,回收239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79.67%。其中男性占42.3%,樣本的平均年齡為31.70 歲(SD
=10.65),擁有小孩個數平均為0.79 (SD
=0.85)。2.2 測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量表均為在國內外研究廣泛使用且信效度良好的權威量表,為了保證翻譯過后的英文量表與其原始量表的一致性,我們嚴格遵循了雙譯程序原則。同時,在大規模調研之前,我們聯系了4 家酒店120 名一線員工進行了小規模的預測試,通過預測試的反饋信息對問卷的措辭進行了微調。預測試和兩次調研變量測量皆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法。
職場排斥(T1):采用了Ferris 等人(2008)的10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組織中的同事/領導常避免與我接觸”、“組織中的同事/領導常對我視而不見”。樣本1 和樣本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7 和0.97。
歸屬需求(T1):采用 O’Fallon 和 Butterfield(2011)的4 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我樂意作為一個組織的成員工作而非單干”、“我喜歡歸屬于某一個組織”。樣本1 和樣本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1 和0.82。
工作壓力(T2):采用House 和Rizzo (1972)的7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我常因為工作而焦躁不安”、“公司相關的事常使我晚上睡不著覺”。樣本1和樣本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0 和0.86。
工作家庭區隔偏好(T1):采用Kreiner (2006)的4 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當我在家時,我不喜歡想工作的事”、“我不喜歡工作的事情侵擾我的家庭生活”。樣本1 和樣本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4 和0.93。
家庭貶損(T1、T3):采用Hoobler 和Brass (2006)的3 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我常將怒火和怨氣發泄在家人身上”、“我常有對我的家人們表現出厭倦”。樣本1 的T1 和T3 階段家庭貶損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9 和0.91,樣本2 家庭貶損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2。
家庭滿意度(T1、T3):采用Carlson 等人(2010)的3 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總體而言,我對我的家庭很滿意”、“總體而言,我非常喜歡我的家庭”。樣本1 中T1 和T3 階段家庭滿意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68 和0.85,樣本2 中家庭滿意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
情緒耗竭(T2):采用Maslach 等人(1986)的5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我的工作讓我感覺精神耗盡”、“我的工作讓我有快要崩潰的感覺”。樣本2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0.88。
消極情緒(T2):采用Watson 等人(1988)的10題項量表,示例問題如:“在過去的一周,我經常感到心煩意亂”、“在過去的一周,我經常感到沮喪”。樣本2 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7。
控制變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員工的年齡、性別和擁有18 歲以下小孩個數會影響員工的家庭態度和行為(Wu et al.,2012;楊自偉 等,2014;Zhou et al.,2019),因此在兩次調研中都將這些員工背景因素作為控制變量處理。同時,兩次調研都將員工所屬企業作為控制變量,創造虛擬變量放入回歸方程以控制來自企業層次的方差影響。
3 研究結果
3.1 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AMOS 24.0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結果如表1 所示。樣本1 中的六因子模型擬合程度(χ(419)=746.42,RMSEA=0.055,CFI=0.95,TLI=0.94)顯著優于競爭模型,樣本2 中的八因子模型擬合程度(χ(961)=1711.77,RMSEA=0.057,CFI=0.93,TLI=0.92)顯著優于競爭模型,這表明兩個樣本中各變量間的區分效度良好。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3.2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而設計的填答方式均為自我報告形式,雖然采用的多時點研究設計(timelagged research design)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Podsakoff et al.,2003),但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嚴謹性,本研究按照 Podsakoff 等(2003)、周浩和龍立榮(2004)的建議利用控制未測單一方法潛因子法來評估共同方法偏差,在驗證性因子分析中引入共同方法因子(CMV)。檢驗結果如表1 所示,樣本1 中六因子模型+CMV 模型(χ(388)=693.11,RMSEA=0.055,CFI=0.95,TLI=0.94)與六因子模型擬合程度相比,樣本2 中八因子模型+CMV 模型(χ(915)=1548.71,RMSEA=0.054,CFI=0.94,TLI=0.93)與八因子模型擬合程度相比,擬合指標RMSEA、CFI 和TFI 的變化幅度都不明顯,可知樣本1 和樣本2 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影響在允許范圍內(溫忠麟 等,2018)。
3.3 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2 給出的結果看,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T3)呈現(樣本1:r
=0.26,p
< 0.01) (樣本2:r
=0.24,p
< 0.01)正向相關,與家庭滿意度(T3) (樣本1:r
=-0.24,p
< 0.01) (樣本2:r
=-0.22,p
< 0.01)呈現負向相關。此外,在樣本1 中,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分別在T1 和T3 階段的數值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r
家庭貶損=0.17,p
< 0.01;r
家庭滿意度=0.29,p
< 0.01),相關系數并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個體主觀的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在中短期內影響因素比較多,如一些偶發性職場侵犯行為(Xin et al.,2018;Zhu et al.,2017)和在旅游服務業中特有的顧客粗暴行為(Chi et al.,2018)等因素都會溢出到家庭領域,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將初始階段的員工個體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作為控制變量的必要性。在樣本2中,工作壓力、消極情緒和情緒耗竭皆與職場排斥呈現出正相關,與家庭貶損呈現出正相關,與家庭滿意度呈現負相關。
表2 主要研究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3.4 假設驗證
(1)主效應檢驗。為了驗證假設H和假設H這兩個主效應假設,首先將員工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依次設為因變量,從表3 和表4 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引入控制變量(性別、年齡和18 歲以下小孩個數)的基礎上,職場排斥正向影響家庭貶損(樣本1:M2,β=0.22,p
< 0.01;樣本2:M10,β=0.25,p
<0.01),負向影響家庭滿意度(樣本1:M6,β=-0.17p
< 0.05;樣本2:M15,β=-0.23,p
< 0.01)。因此,假設H和假設H得到了數據的支持。(2)中介效應檢驗。本研究綜合運用逐步法(Baron &Kenny,1986)和bootstrapping 法(Edwards&Lambert,2007)來驗證工作壓力的中介效應。在樣本1 中,從表3 和表5 可見,職場排斥對工作壓力(M20,β=0.36,p
< 0.01)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壓力對家庭貶損(M3,β=0.32,p
< 0.01)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家庭滿意度(M7,β=-0.20,p
< 0.01)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當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同時放入回歸方程中分析時發現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的影響變為不顯著,而工作壓力對家庭貶損的影響顯著(M4,β=0.29,p
< 0.01),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顯著(M8,β=-0.17,
p
< 0.01)。在樣本2 中,從表4 和表6 可知,職場排斥對工作壓力(M32,β=0.28,p
< 0.01)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控制了消極情緒和情緒耗竭影響的基礎上,工作壓力對家庭貶損(M12,β=0.25,p
< 0.01)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家庭滿意度(M17,β=-0.22,p
< 0.01)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時當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同時放入回歸方程中分析時發現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的影響變為不顯著,而工作壓力對家庭貶損的影響顯著(M13,β=0.23,p
< 0.01),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顯著(M18,β=-0.20,p
<0.01)。由此,結合前文假設H和假設H,可以得出工作壓力在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之間都起到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設H和假設H。此外,Bootstrapping 重復抽樣5000 次分析結果表明,樣本1 中工作壓力在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之間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為[0.06,0.18],在職場排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為[-0.10,-0.02],兩個區間內都不包括零;樣本2 中同時放入消極情緒、情緒耗竭和工作壓力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發現情緒耗竭、工作壓力在職場排斥與家庭貶損之間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為[0.02,0.12],在職場排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為[-0.13,-0.02],兩個區間內都不包括零。因此,假設H和假設H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與支持。
表3 中介效應檢驗(樣本1)

表4 中介效應檢驗(樣本2)

表5 調節效應檢驗(樣本1)

表6 調節效應檢驗(樣本2)
(3)調節效應檢驗。本研究采用 Cohen 等人(2013)推薦的交互項構建來檢驗調節效應。為了降低多重共線性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在計算交互項前對各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從表5 和表6可以看出職場排斥與員工歸屬需求之間的交互項會對工作壓力產生正向影響(樣本1:M22,β=0.14,
p
< 0.05;樣本2:M34,β=0.20,p
< 0.01)。這表明,員工的歸屬需求越強烈,職場排斥與員工工作壓力之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強,支持了假設H。工作壓力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交互項對家庭貶損會產生負向影響(樣本1:M26,β=-0.20,
p
< 0.01;樣本2:M38,β=-0.19,p
< 0.01),對家庭滿意度會產生正向影響(樣本1:M30,β=0.16,
p
< 0.01;樣本2:M42,β=0.23,p
< 0.01)。這表明員工的工作家庭區隔偏好越強烈,員工工作壓力與家庭貶損的正向關系就越弱,和家庭滿意度之間的負向關系也越弱,假設H和假設H得到了支持。為了具體展示交互作用的影響效果,根據Cohen 等人(2013)的建議,本研究用調節變量的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進行了調節示意圖的繪制。員工不同歸屬需求水平下職場排斥對工作壓力的影響見圖2 和圖3;在不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水平下,工作壓力對家庭貶損的影響見圖4 和圖5,工作壓力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見圖6 和圖7。

圖2 歸屬需求對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的調節(樣本1)

圖3 歸屬需求對職場排斥與工作壓力的調節(樣本2)

圖4 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對工作壓力與家庭貶損的調節(樣本1)

圖5 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對工作壓力與家庭貶損的調節(樣本2)

圖6 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對工作壓力與家庭滿意度的調節(樣本1)

圖7 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對工作壓力與家庭滿意度的調節(樣本2)
(4)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本研究遵循Edwards 和Lambert (2007)推薦的方法來檢驗歸屬需求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兩個變量所發揮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從表7 結果中可以看出,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的間接效應在員工不同水平下歸屬需求的間接效應差異顯著(樣本1:Δβ=
0.09,p
< 0.05;樣本2:Δβ=
0.10,p
< 0.01),95%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假設H得到了數據的支持;職場排斥對家庭滿意度的間接效應在員工不同水平下歸屬需求的間接效應差異亦顯著(樣本1:Δβ=
-0.04,p
< 0.05;樣本2:Δβ=
-0.12,p
< 0.01),95%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假設H得到支持。
表7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此外,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的間接效應在員工不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水平上差異是顯著的(樣本1:Δβ=
-0.20,p
< 0.01;樣本2:Δβ=
-0.24,p
<0.01),95%置信區間都沒有包含0,因此假設H得到了數據的支持;職場排斥對家庭滿意度的間接影響在員工不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水平上差異是顯著的(樣本1:Δβ=
0.11,p
< 0.01;樣本2:Δβ=
0.30,p
< 0.01),95%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假設H得到實證數據的支持。4 討論
4.1 結果討論與理論意義
第一,以往關于職場排斥后果研究大多聚焦于探討職場排斥對員工組織內部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及其機制,而職場排斥這一職場“冷”暴力對于員工家庭生活的溢出效應卻鮮有研究(陳晨 等,2017;Howard et al.,2020)。本研究在資源保存理論框架下將研究視角從工作場所延伸到家庭領域,一方面探討了職場排斥使員工身陷資源損失螺旋,進而產生非理性、缺乏自我控制、低未來取向的行為傾向,從而出現家庭貶損傾向和行為;另一方面論證了被排斥者帶來的資源損耗不僅會占用家庭領域各類資源,還會提高對家庭領域資源補給的要求標準和期待,最終導致對于家庭滿意度的主觀評估也相應降低。此項研究揭示了職場排斥對家庭領域的溢出效應,同時也將家庭貶損和家庭滿意度的前因變量研究延伸到了職場領域(Hobfoll,1989,2001,2002;Hobfoll et al.,2018)。
第二,以往研究主要基于工作家庭增益理論和工作家庭沖突理論的視角來解釋職場因素對家庭生活的影響(Chen et al.,2009;李愛梅 等,2015),本研究基于資源保存理論考察了職場排斥對家庭貶損、家庭滿意度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一方面剖析了個體工作壓力在職場“冷”暴力與家庭領域的溢出傳導作用,進一步補充了職場“冷”暴力相關壓力源的研究(Wu et al.,2012;Xin et al.,2018);另一方面研究在控制來自于消極情緒和情緒耗竭的影響基礎上,發現工作壓力是職場排斥穿透工作-家庭邊界對家庭領域產生負向溢出效應的重要傳導機制,回應了既有研究對于創新原有視角來考察工作與家庭領域溢出“黑箱”的呼吁(Greenhaus &Powell,2006;Lim et al.,2008;Restubog et al.,2011;Swimberghe et al.,2014),同時拓展了資源保存理論的應用范圍。
第三,本研究從個人特質這一重要視角出發,對職場排斥溢出效應的邊界條件進行了有益探討,既有研究主要從資源補充的角度探究了個人資源和心理資源對職場排斥負面影響的緩沖作用(Wu et al.,2012;程豹 等,2019),忽視了個體特質對于職場排斥帶來資源損失的價值感知程度以及后續壓力反應溢出程度。本研究將歸屬需求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兩種重要的個人特質變量納入到模型中,擴展了職場排斥對其結果變量增強(歸屬需求)或阻隔(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的邊界條件,也為資源保存理論的應用提供了有效證據。同時,本研究構建了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厘清不同水平(歸屬需求和工作家庭區隔偏好)特征下遭受職場排斥的員工通過工作壓力這一中介路徑對其家庭生活影響差異。通過明晰歸屬需求和家庭區隔偏好兩個調節變量的具體效用,有助于更深入了解職場排斥的溢出效應,從而有針對性的提出職場排斥負面溢出效應的應對策略。
4.2 實踐啟示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提供了以下實踐啟示:第一,管理者需要及時監控發覺組織內部的職場排斥行為,重視職場“冷”暴力的壓力源作用和對家庭領域的溢出效應。管理者可以建設和諧、寬容、友好的組織文化氛圍,從源頭上減少職場內不良人際關系所帶來的壓力源;第二,管理者應該引導員工進行有效的壓力管理,及時對被排斥員工采取心理壓力干預和疏導,提高員工的情緒管理能力和壓力復原力,削弱阻斷性壓力不良影響,防止其溢出到家庭領域對家庭生活產生負面影響;第三,具有高歸屬需求的員工對職場排斥十分敏感,容易形成壓力源和溢出誘因。管理者應該關注員工個人特質,針對具有強烈歸屬需求同時又遭受到職場排斥的員工進行正面的引導,放大歸屬需求的積極效應并抑制消極效應的產生;第四,工作家庭區隔偏好是有效緩解工作壓力對員工家庭負面影響的“防火墻”,管理者需要了解員工的工作家庭區偏好,建立權變和個性化的組織邊界管理機制。
4.3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著不足和局限,亟待后續研究中進一步完善。第一,本研究雖然采用多時點研究設計,并且通過多種統計檢驗證實了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并不嚴重,但自陳式問卷調查的方式仍然可能給研究帶來共同方法偏差。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優化研究設計,通過日記分析法或者員工與主要家庭成員匹配的方式來采集數據,進一步保證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同時也在關注溢出效應基礎上將家庭不同成員之間交叉效應納入研究框架。第二,本研究中雖然將因變量的初始狀態作為重要的控制變量,但依然無法完全排除影響結果變量的其他因素。未來可以考慮采用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等動態跟蹤研究該溢出效應,在明晰具體動態溢出效應的同時也探究家庭領域后果變量之間的關系。第三,本研究的樣本集中于酒店和旅游服務業,雖然能夠有效地控制行業屬性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但是同時忽略了其他行業內職場排斥行為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差異性,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有待進一步提升。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調研范圍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第四,本研究僅關注于職場排斥的溢出效應,未來可以繼續研究其他職場“冷”暴力(職場負面八卦、工作場所無禮行為等)對家庭領域的影響(嚴瑜,王軼鳴,2016),從而更全面的分析工作領域負面行為對家庭領域的溢出效應。
5 結論
本研究基于資源保存理論,從一正一反兩個角度探討了職場排斥對員工家庭領域的溢出效應,同時還發現工作壓力是溢出過程中重要的傳導因素。研究進一步檢驗了個體歸屬需求、工作家庭區隔偏好分別在溢出效應的前端和后端所起的邊界作用,前者決定了個體對于遭受職場排斥而損失的資源價值高低評價以及后續的壓力反應程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替代資源的獲取是否指向家庭領域以及指向的具體程度。這一研究為職場“冷”暴力對家庭領域溢出效應提供了新證據,同時也揭示了職場排斥對員工家庭的具體溢出機制。
致謝:
感謝編委專家和匿名評審專家的建設性意見,感謝貴州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潘運教授團隊在本文修繕過程中給予的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