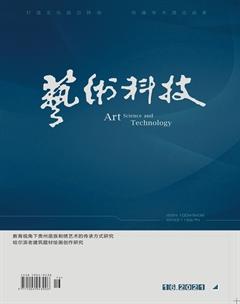符號論美學視域下亨利·盧梭叢林畫中的動物形象研究
李承寅 於玲玲
摘要:亨利·盧梭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樸素派代表藝術家,其筆下充滿著茂密的叢林、看不見腳又有些許稚拙的人物以及具有拉美原始藝術風格的動物。樸素派誕生的原因眾說紛紜,或許是因為“歐洲中心論”的日漸式微,又或許是因為工業時代藝術家回歸自然田園尋求精神寄托。在符號論美學的指導下,盧梭作品中的動物形象與其整體形式的有機關系能得到解釋,盧梭作品背后的藝術意味也能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關鍵詞:亨利·盧梭;動物形象;符號論美學;生命形式
中圖分類號:J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6-0-02
0 引言
亨利·盧梭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星期天”畫家,他曾是一名銀行稅員,未曾接受過學院派系統的美術教育,而是從自己獨特的眼光和視角出發,繪制如夢如幻的內心世界。國內外關于亨利·盧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區別于同時代印象派畫家的獨特手法上,其筆下波譎云詭波云詭的叢林夢境與有意無意的趣味形象也是研究熱點,而針對其動物形象的研究還有待補充。本文以蘇珊·朗格符號論美學為理論指導,深入探尋盧梭動物形象的美學含義。
1 和睦與危機——亨利·盧梭作品中動物形象的力
藝術作品之中的力,并不是指生理機能上肌肉所發出的力量,而是專門為知覺創造的,也是為知覺存在的力[1]。這種力,是可以被觀者感知的,包含了作品中各部分的節奏關系與情感表達。
筆者通過對現有資料調查統計得知,亨利·盧梭共有24幅叢林動物畫傳世。畫中的叢林植物大多充滿想象,層疊在一起,對空間營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盧梭每一幅叢林畫中幾乎都有動物或人物形象存在,這些獨具原始藝術特色的動物形象包含著不同的矛盾關系。
亨利·盧梭最熱衷于表現的便是靜謐雨林中暗藏的殺機。盧梭在1891年的作品《驚奇!》中描繪了一只在叢林中蓄勢待發準備捕獵的老虎。老虎的形象頗具印第安圖騰柱的特色,它眼睛瞪得巨大,齜牙咧嘴,匍匐前進,身上的虎紋具有裝飾韻味,像印第安人圖騰柱上那些夸張且神秘的動物。畫面未曾出現除老虎之外的任何動物,背景中只有劃過天空的閃電和被狂風吹斷或倒伏的雨林植物,但觀者仍能感知到老虎正在捕獵,且捕獵的緊張之感也呈現了出來。這種能被觀者所感知的緊張感便是該作品中的力,這樣的力是以老虎的動態形象為載體呈現出來的。老虎即將捕獵的動態及其緊盯獵物的視線、背景中植物倒伏的趨向無一不指向畫面外的右下角。繪畫表現的是一種空間的虛像[2],作品中的力是畫家創造出來且只能為知覺所感受的虛的力,并不由真實的肌肉表達出來。動物、植物的符號形象與環境刻畫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即整幅畫面。在這樣的整體之中,部分與部分之間的形象產生各種聯結,增強了作品情感的豐富性、情節性、強烈性。
此外,和諧安寧的景象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現在盧梭的筆下。《夏娃》與《弄蛇女》皆表現了女人與蛇共處的場景,流暢的線條表達使蛇的形象少了主流大眾心中邪惡與冰冷的色彩,反倒增添了一絲溫馴與柔美。《弄蛇女》中的女子在黃昏中吹著長笛,蛇柔軟的身體環繞在她的身體上,似乎要跟笛聲一同舞動一般,旁邊還有一只匙嘴鷺安靜相伴,整幅畫呈現出安靜祥和的氛圍。相對于盧梭表現動物野性的殺機的力,這般和諧景象中的力顯然要溫和許多。
亨利·盧梭作品中呈現出的三種不同強度的力,構建了其作品情感輕重緩急的節奏。正如詩中的平仄和抑揚頓挫,皆因作品中符號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盧梭把幻想的植物置于嚴謹的構圖之中,如幕布般的植物構成了舞臺背景,而位于注意力中心的動物形象就像是舞臺上的舞蹈演員,它們彼此之間動態形象的微妙關系形成了輕重不同的力。這些只能為知覺所感知的力,與舞臺中的環境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客體,即畫面的表現性形式,這種表現形式能讓觀者感受到作品中不同的情感變化。
蘇珊·朗格所討論的“虛幻的力”,便是藝術作品中各部分之間的關系。這樣的關系之于造型藝術,是各個領域藝術家都稱之為“緊張”的一種相互作用。畫面意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塊面的關系、色彩的明暗冷暖偏向、線條的流動方向等一系列作品構成因素,在虛幻的空間之中持續對比并構成了空間緊張[3]。
2 想象與拷貝——動物形象符號在亨利·盧梭作品中的建構
符號論美學奠基人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一切以某種形式或在其他方面能為知覺揭示出意義的現象,都是符號。”符號既具有某種形式,又能為知覺揭示某種意義。符號其實就是藝術家能夠進行抽象的某種方法。
2.1 藝術符號與藝術中的符號
藝術符號區別于藝術中的符號,藝術符號是藝術家構建的有意味的形式,即作品整體,而藝術中的符號則是畫面整體中各部分的繪畫形象。例如,亨利·盧梭叢林畫中的動物形象就是藝術中的符號,此種符號在畫面的構成中有不同的作用及貢獻,且各自的意義不盡相同。不過,那些野性的、神秘的動物形象作為作品的組成部分參與了盧梭作品的形式構建,卻不是整個藝術品所要傳達的意味[4]。
藝術家在藝術創造中對符號的運用,要遵循一種構造法則,即一種設計方法。畫面意象之間多變的組合建構能使作品產生不同的情感呈現。亨利·盧梭從未離開法國真正前往密林之中觀察動植物的狀態,大多數動物形象都源自巴黎當地博物館中的標本或教科書和雜志上的圖片[5]。盧梭很喜歡用一個可以調整尺寸大小的畫圖器,復刻他在書中看到的圖片,但經過畫家的主觀安排之后,這些拷貝而來的動物形象又獲得了全新的生命[6]。
盧梭作品中的動物形象往往是通過對具體形象的抽離和重組得到的。分析盧梭《日落森林的風光》與其參考的攝影集《野獸》中的照片可以發現,盧梭雖然熱衷于拷貝雜志上的具體形象,但對其進行了藝術抽象轉換,并得到了具有新的情感且適宜放置在叢林環境中的動物形象[7]。照片中的豹子與人拍攝于一家動物園之中,豹子立起身子玩鬧似的環抱著一名白人男子,與其說他們之間是獵物與獵手的矛盾關系,不如說展現了飼養員與飼養物之間打鬧的和諧景象。奇怪的是,雖然能從兩者的對比中發現盧梭作品中印第安人與豹子的動態、造型皆為借鑒,但畫中人與動物之間的斗爭關系卻顯得尤為明顯。盧梭把原本照片中的白人男子替換成了印第安人。豹子臉部的刻畫頗有些立體主義的味道,盧梭并沒有完全遵循透視的法則,而是以一種相對稱的視角把豹子的頭部平攤開了,標志性的空洞大眼分布在“劈開”的豹子頭上。不知是這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藝術家的無意之舉還是有意識的加工重組,盧梭把觀察豹子的兩個不同視角統一了起來。類似的搏斗的動物形象,多次出現在盧梭的叢林畫之中,象征著動物與動物、人與人之間激烈的矛盾沖突[8]。在《獅子的饗宴》中,畫家刻畫了一只正在吞噬獵物的獅子,而被吞噬的對象與《日落森林的風光》中的豹子極其相似。肉食動物之間相互吞噬在大自然中很難見到,但盧梭為了表達叢林之中動物的激烈矛盾,把兩種肉食動物的形象拼接在一起,產生了有悖于現實自然食物鏈的殺戮之感。
亨利·盧梭把現實與想象相結合,將具體的感性內容抽象為一種可感的形式,這種形式便是通過如同舞臺布景般的叢林畫呈現出來的。藝術家經由頭腦中想象的加工,從具體的形象中提煉概括出相似的形體,并有意識地與其他形象進行組合,以形成一種可辨的創造性形象,而動物符號在其作品中的建構,便是通過這種想象與重組參與的。
2.2 亨利·盧梭動物形象的隱喻
不容忽視的是,亨利·盧梭的動物形象具有一定的隱喻意義。在盧梭的叢林畫中,反復出現的動物形象有獅子、老虎、猴子、蛇等。最讓人疑惑的莫過于其筆下的猴子了,盧梭的諸多作品都對猴子進行了描繪,且其作品中的靈長類動物幾乎都有擬人化的面孔。《快樂的小丑》是一個謎,畫面下方類似山魈的動物緊緊擠在一起,臉上流露出驚恐的神情。很顯然,盧梭在畫猴子的時候,并沒有遵循猴子的生理結構,微張的“一”字形嘴巴與人類的嘴巴極其相似,這不得不讓觀者聯想到畫面之外超越猴子本身的意義。猴子的前方有一個倒置漂浮的奶瓶,兩旁還各有一只動物,奶瓶中的液體汨汨流出。擬人化的形象加上如舞臺幕布的植物背景,整幅畫仿佛是一臺正在上演的幽默、詭異、難以預料的啞劇[9]。
亨利·盧梭樂于描繪工業化的產物,在他一些風景畫和肖像畫中,能看到飛機、輪船、飛艇、熱氣球、大炮之類的物件,這也許能解釋《快樂的小丑》中出現工廠流水線生產的玻璃奶瓶和諸多人類物件的原因。盧梭生活的年代正是歐洲工業革命的頂峰時期,因此其叢林畫中拷貝的工業化物件或許代表著工業生產和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被動物們倒掉的牛奶也隱喻著盧梭對工業時代惡果的思考與抗爭[10]。
3 節奏與成長——從亨利·盧梭作品看生命的形式
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是直接作用于知覺的個別形式,這是一種極其特殊的形式,因為其不僅僅是一種視覺形象,看上去似乎還具有某種生命的活力。生命的形式是藝術符號學的基本概念,而好的藝術品也是一種生命的形式。藝術品不可以呼吸、運動,但是其仍然具有有機體的結構特征,即具有一定的節奏性,且各個部分之間緊密相關,具備一定的“動能形式”。
亨利·盧梭叢林畫的生命形式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動植物形象的存在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動態形式,即變化式樣的節奏性;二是具有裝飾意味的線條創造出了一定的空間,且構成了表現持久性和變化性之間辯證關系的形象。
觀者可以從盧梭的作品中觀察到許多動態形式,以作品《叢林中老虎的埋伏偷襲》為例,畫面中有一組具有強烈動感的形象。一只老虎從密林中竄出,撲倒了一位穿著白色衣物的印第安人,老虎的爪子、牙齒鋒利無比,仿佛馬上就要痛下殺手。左邊有一個騎著馬的印第安人,他的馬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壞了,前腿高高抬起,嘴巴大張作驚恐狀。馬背上的印第安人艱難地把握著平衡,一手舉著長矛,朝著老虎刺去,用盡全身力氣保護已被老虎嚇得癱軟在地的同伴。畫的前景是盧梭筆下極具特色的劍狀植物,雜亂但有規律地倒伏著。背景中的樹林在夕陽下顯得格外昏暗靜謐,與前景中極具動態的形象產生了強烈對比。
另外,有裝飾意味的線條使畫面的流動感更為強烈。線條本身是有趨向的,而這種趨向更像是一種不斷成長的動能。在盧梭的《睡夢中的吉卜賽人》中,線條的運用十分巧妙。遠景中重巒疊嶂的山、機警獅子身上的鬃毛、吉卜賽女孩衣服上的線條都呈現出或靜或動的趨勢。在藝術家創造的虛空之中,線條既可以表示運動,也可以表示靜止。它們時而運動時而穩定,使作品呈現出有機性的生命特征。
4 結語
亨利·盧梭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藝術具有深遠影響,畢加索曾經認真研究過盧梭的肖像畫,康定斯基也對盧梭贊賞有加。但在當時,盧梭并不為主流畫家、畫展所接納,飽受諷刺、批評與挖苦。符號論美學作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風靡的美學理論,由于過于唯心主義,一直為人詬病。無論如何,一位畫家、一門學說都不會是完美的,但也并非一無是處。找到契合的方法論,并利用其對老生常談的畫家進行新的解讀,亦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參考文獻:
[1] [美]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1-16.
[2]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23-127.
[3] 何政廣.盧梭[M].河北:河北美術教育出版社,1998:87-88.
[4] 侯田田. 享利·盧梭繪畫中動物形象的解析[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9.
[5] 張偉.生命的隱喻和象征[D].西安:西安美術學院,2015.
[6] 沙凱.抽象與構形——蘇珊·朗格符號論美學思想探析[J].俄羅斯文藝,2011(2):71-75.
[7] 陳春雨.淺談亨利·盧梭繪畫藝術中的樸素之美[J].美術教育研究,2016(22):13.
[8] 劉藝孛.符號論美學視域下弗里達繪畫的建構[D].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18.
[9] 徐雪娜. “稚拙趣味”——淺談畫家亨利·盧梭[D].日照:曲阜師范大學,2019.
[10] 張薇.符號論美學在吳冠中油畫創作中的運用[D].無錫:江南大學,2015.
作者簡介:李承寅(1998—),男,江蘇南京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油畫創作。
於玲玲(1977—),女,江蘇如東人,碩士,教授,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西畫創作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