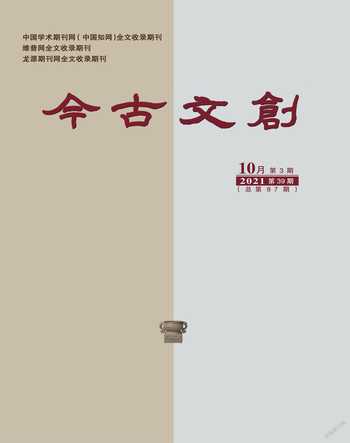失落群體的苦難人生
【摘要】黃春明作為“小人物的代言人”,著重描寫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底層人民的命運及其與臺灣三十年來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對黃春明小說中一系列的邊緣人物分析,可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與傳統鄉村文化的激烈碰撞給人帶來的影響,從而辯證看待本民族傳統的鄉土文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關鍵詞】黃春明;鄉土文學;邊緣人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9-0015-04
“邊緣人”最早起源于社會學研究,明確提出邊緣人概念的是美國社會學家帕克。他從移民角度出發,將邊緣人定義為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對兩個世界都陌生的人。在文學作品中可以將邊緣人群體理解為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特殊轉型時期下生活的以小人物為代表的失落群體。邊緣人往往無所適從,處在生存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之下,從而內心也是充滿了矛盾。導致了身份的不確定性,迫于無奈或是主動選擇成為背負社會轉型陣痛的犧牲者。“邊緣的性質,從政治上看,就是弱勢的,無權勢的;從經濟上看,就是落后的,不發達的;從文化上看,就是少數的,可以忽略的。”[1]在黃春明描繪的臺灣社會轉型時期底層民眾邊緣生存狀態的小說中,有進城務工的油漆工,有自小被養父賣給娼寮的妓女,有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還有受西方工業文明侵入影響而異化的人……他將這些被邊緣化的貧民階層、女性和中產階級群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突出地展示了這些被邊緣化的個體所陷入的困境和不同的人生選擇。
一、黃春明邊緣人形象的創作語境
(一)社會變革下的時代呼喚
由于戰后特殊的地緣政治境遇,使得20世紀60年代的臺灣不可避免地完全地陷入了西方意識形態當中。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臺灣文學青年普遍追求西方現代派文學“沉郁破碎”的寫作風格,“他們視虛無縹緲為偉大的題材,視蒼白無根為高貴的情操”[2],此時的臺灣文壇進入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模仿時期。
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性質及其演變是息息相關的。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臺灣社會正處于經濟急速變化,政治思想禁錮極為嚴格的社會轉型時期。尉天驄認為:“目前臺灣的現代文學與現實生活脫了節,我們多么需要一種健康的寫實藝術和文學。”[3]面對這些弊端,臺灣文學界展開了一場影響極其深遠的“鄉土文學論爭”,人們開始反省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帶來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上的貧困,并且開始尋求民族文化傳統之根。這場論爭重新肯定了臺灣本土文學中蘊含的民族精神的傳統,促使了西方現代派文學在重新認識傳統和關懷現實中進行審視和調整。
黃春明注意到臺灣社會的變革給鄉村帶來的沖擊,以社會底層人民的遭遇為視角,刻畫了各式各樣被時代變革潮流裹挾而前的小人物。在他看來臺灣“經濟奇跡”的背后,其實是新舊之間痛苦的“決裂”。他善于通過傾聽小人物的心聲,用自然的筆調,具體真實地描繪小人物的生活,來表達對物質文明入侵古老鄉土的抗拒與隱憂。
(二)湘西邊城對宜蘭小鎮的構建
除去臺灣鄉土文學思潮對黃春明創作的產生的影響,中學時期,國文老師向他推薦的沈從文短篇小說集,也對黃春明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沈從文在小說世界中構筑了一個名為“邊城”的烏托邦。在《湘行散記》中有兩類群體是出現頻次最高的人物形象,即以水手、妓女為代表的邊緣人形象,他們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最平凡的小人物,卻又閃現出不平凡的人性之美。《柏子》中的妓女與水手并不是簡單的金錢與肉體的交易關系,在日復一日的艱苦生活中,吊腳樓上的妓女給予了水手柏子精神上的撫慰與生活的盼望。柏子與妓女間的情感是相互的,在這樣的境地下迸發出了純真的愛意。河岸吊腳樓上的妓女與“河下人”水手,因恩情所結,組合成了奇異的情感關系。她們雖然為了生活屈身做著卑賤的職業,但并沒有辱沒她們純真的心靈。她們重情守信、率真善良,讓本無生命歡樂的地方,擁有了生命的歡歌。
這類書寫小人物的人性之美的作品給后來黃春明創作鄉村與城鎮的邊緣人形象帶來了許多啟示。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作品中出現了許多與之類似的邊緣人形象,大多地位低下、職業卑賤,在社會上沒有話語權。如《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處在同樣悲慘的生活境遇中,卻能保有一顆善良的赤子之心,為了同伴挺身而出,堅強而又有韌性。黃春明筆下的人物與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精神內核是一致的,她們對生活都有著同樣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逆境中保持著難能可貴的人性之美。
“文學生命力的源泉來源于藝術的地方色彩。”[4]沈從文的“邊城”滲透著原始的道德美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受其影響,黃春明也將自己的故鄉宜蘭作為創作的精神故土。他們在小說中上都表達了對故鄉鄉土的熱愛與眷戀。《邊城》中充斥著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描寫,“那條河便是歷史上的知名的酉水,新名叫白河……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常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 [5]而宜蘭的“濁水溪”也頻頻出現在《青番公的故事》里,“從海口那邊吹皺了蘭陽濁水溪水的東風,翻過堤岸把稻穗搖得沙沙響。”[6]
景與人往往是相互映襯的,一如沈從文的“湘西”。他樂于描寫人性美、風俗美。構成了極具繪畫意境美的風俗畫面,美的人性與美的景致相互融合使得作品充滿神韻。黃春明出身貧苦,大自然無所不包的美麗風光,廣闊天地里辛勤耕種的勞動人民,古老村落里口耳相傳的鄉野傳說都構成了黃春明筆下的瑰麗夢幻的鄉土畫卷。他將宜蘭的鄉野風俗用具體化的生活內容來融入現代化的小說情節當中。如《青番公的故事》里青番公哄睡孫子時哼的閩語歌謠與《兩個油漆工》中油漆工在機械化工作的間隙嘴里無意識地哼唱來自家鄉的歌謠。《憨欽仔》中也運用了大量極具閩南語特色的方言。平淡的表述方式,使小說富有生活氣息,扎根臺灣地區的鄉土天地。依托宜蘭平原的自然風貌,回歸鄉土,用鄉土的興衰來反映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從湘西邊城到宜蘭小鎮,黃春明的小說承繼了沈從文在鄉土社會中追尋傳統精神家園的特點。
(三)俄國邊緣人書寫風格的延續
沈從文曾坦言自己“較多地讀過契訶夫、屠格涅夫的作品,覺得方法上可取之處太多。”[7]作為黃春明鄉土創作道路的引路人,這些俄國作家同樣也對黃春明的創作產生了沉潛而持久的影響。“契訶夫不以情節取勝,只是描繪日常的瑣事,在平凡中透視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本質”[8],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農民、仆從還是馬車夫、流放者,都過著壓抑悲慘的生活,他們痛苦掙扎卻又無力掙脫,人的尊嚴與快樂被生活的重壓無情剝奪。這在黃春明的小說創作中也有相同的體現,《兩個油漆工》中的阿力與猴子,原本只是登上樓頂說話散心,被人誤以為是想要跳樓自殺,在與市長、記者的交談過程中,猴子一躍而下,以死亡收場。
另一位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人物塑造以及敘述方面則與契訶夫略有不同,他在《獵人筆記》中更為注重對理想化人格的塑造。同樣是對俄國黑暗的農奴制度展開強烈的批判,屠格涅夫還樂于去挖掘底層人民身上所蘊含的積極向上,樂觀健康的因素。《看海的日子》中妓女白梅,想借一個孩子重新被世界接納,回歸鄉土的故事,也體現了黃春明在面對“被殖民”的臺灣社會時,希望通過主人公重獲“認可”獲得救贖的遭遇來呼喚夢中“理想的鄉土世界”,寄托了他對“邊緣人”的同情與關愛。
契訶夫在小說中常借人物之口來發表具有抒情色彩的議論,屠格涅夫的用筆更為沉靜,在小說中少見議論。他常常躲在文本背后,用冷靜、克制的筆調通過對事件發生的場景、故事的講述重點含蓄的透露出來。黃春明的敘述風格與屠格涅夫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善于使用臺灣地區方言進行對話寫作,他仔細描述在日常生活的中所看到的細節。用平易質樸的語言來描述發生在鄉村與都市的不同職業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故事,空間在田野、小鎮、高樓間變幻,所要表達的故事內核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俄國作家的創作風格極大地啟發了黃春明描寫底層大眾生活的創作方向。黃春明筆下的“邊緣人”有的雖然社會地位卑微,受盡侮辱與損害,卻從不向命運妥協。他肯定了底層人民在面對命運不公時不懈的抗爭精神,體現了他特有的人文關懷理念以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
二、黃春明小說中邊緣人的類型
(一)都市與鄉鎮的邊緣人
從鄉村走向城市的蛻變道路中,必然要經歷時代的“陣痛”。作為在底層社會生活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被夾雜在“鄉村”與“城市”的邊緣地帶。在黃春明的小說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空間對于人物的作用是無法低估的,他根據小說的整體情節與所有人物之間的關系來敘述空間,描寫了城鄉文化的沖突中人性的軟弱和局限。
臺灣光復后,經濟狀況一直在惡化。從鄉村到城市的遷移過程中,人們被迫或是主動開始選擇不依靠土地謀生。《兒子的大玩偶》中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傳統農業耕作為生計的農民。鄉鎮貧民坤樹,為了能夠養家糊口,向老板毛遂自薦,自請充當最下層地位的“三明治人”,身體前后都掛著電影廣告的牌子,臉上涂滿色彩艷麗極其夸張的粉墨,頭上戴著一頂帶羽毛的圓通高帽,被大伯稱作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9]小說中充斥著大量以坤樹為主視角的心理描寫,可是他的想法在腦海里兜兜轉轉,最后也只是對自我精神的自虐,顯露小人物心聲被壓抑的痛苦。家庭的責任驅使著坤樹不得不做戴上“面具”失去自我的大玩偶,他掙扎在謀生的困苦與精神上尊嚴的缺失中,成了徘徊在人格尊嚴邊緣的弱勢群體。
不同于坤樹對家庭的歸屬與眷戀,《兩個油漆匠》中的阿力和猴子都不愿意再回到東部的山間生活。阿力進城務工后,對母親謊稱每月工資有兩千塊,在每月給家里寄錢時都要向同伴猴子借錢補足,不敢向母親坦白事實,生怕被召回去種地。即使,這份油漆工的工作叫他糊涂,令他苦惱。猴子告訴阿力,其他為了這個工程被招過來的工人一天能有一百塊的工資,阿力發出困惑,“那真沒意思,把我們當什么呢?”猴子干脆地回答,“你才知道!”[10]進城兩年多,一成不變的工作與微薄的報酬,讓他們生出對理想的幻滅。
阿力與猴子看似偶然的悲劇中一定程度上蘊藏著這些外來務工的異鄉人悲劇命運的必然性。當阿力和猴子攀上高樓在北愛河的上空往下望時,發現在城市地下生活的人們就像手表里的機器,來來往往。此時,主人公所處的空間其實暗示著這個迥異于故鄉村鎮的大型城市從未真正接納過他們。
土地流失,驅使著大量農村人口為了擺脫貧困涌入城市,進城務工。然而,“無論是選擇固守在鄉村還是選擇走向城市,高速發展現代化的城鎮難以融入,而曾經封閉的鄉村已經回不去。這些小人物不可避免地淪為雙重邊緣人”[11]。一切唯利是圖的嘴臉將社會原本溫情樸實的一面掩蓋,人們想到城市追求幸福,卻不幸被城市所吞噬。
(二)備受屈辱和摧殘的女性
“女性群體的人格失落與殘酷的社會環境、嚴苛的家庭氛圍之間有著深層次聯系。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女性就幾乎沒有肯定自我存在的意識,也沒有表達自己意愿的勇氣。”[12]《看海的日子》中的主人公白梅,是在時代大背景下社會灰色角落邊緣人的生存寫照,也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社會角落的現實。然而,在這樣悲慘的人生境遇下,她的自我救贖依然閃爍著人性的光輝,重獲新生的經歷充滿著“女性覺醒”的意味。
沈從文的小說中一些女性形象與白梅擁有相同的特質。典型環境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她們都繼承了鄉土中傳統的難能可貴的堅韌品質,雖然身處殘缺的生活環境,仍具有堅強的意志和原始的生命力,敢于去追求人性的尊嚴與愛欲。如《旅店》中失去丈夫的寡婦黑貓,獨自經營旅店,應對來往的客商,并沒有被悲慘的命運所打敗而自怨自艾。她坦然面對內心“不端方的愿望”,沖擊封建倫理的束縛,聽從內心的欲望,積極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白梅的前半生就如那首“雨夜花”中唱的,“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顧,冥日怨嗟。”[13]她在娼寮里用善良的態度去對待與她處于同一處境下的其他女性,在同伴鶯鶯面對熱烈的愛情追求時,白梅用近乎冷淡的態度告誡鶯鶯,“這種場合你千萬別動感情”。自小被賣入火坑的白梅到二十多歲仍然輾轉在靠海碼頭的娼寮中。于她而言,鶯鶯的愛情幻想是虛妄的不切實際的。而在火車上與鶯鶯的重聚,出乎意料的點燃了她冰封已久的心。她開始盼望著生育一個只屬于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嫁給他人做妻子,而是成為一個孩子的母親。白梅精心挑選了一個年輕壯實的討海人,在一夜溫存過后,她帶著腹中孕育的生活新希望回到了家鄉。在經歷生育的艱難后,白梅如愿得到了一個孩子。作者在結尾與前文相呼應,“魚群來了!”當白梅抱著孩子回到漁港時,她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暢快。一直以來橫亙在她與外部世界廣大人群間的鴻溝都染被磨平,消失不見。她看見的世界不再是透過令她窒息的牢籠的格窗了,她成了世界中的一員。
《看海的日子》迫切地表達了黃春明對于現代文明的反感以及對鄉土世界的無限眷戀,白梅作為一個備受屈辱和摧殘的邊緣人形象,最終在回歸鄉土中得到救贖,重建了人的尊嚴,孕育生活的新希望。作者期望借助這種人物回歸“鄉土”的經歷,來表達內心對鄉土世界的依戀。
(三)固執堅守傳統鄉土的老人
20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之間的矛盾沖突下,面對來勢洶洶的外來力量,鄉村的農民幾乎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幾乎沒有受過教育,也不了解這股反對他們的力量。因此,他們缺乏有效抵抗資本主義勢力侵占他們土地、使他們陷入失業和貧困的力量。而當這些處于弱勢群體地位的鄉村農民運用以往傳承下來的經驗去適應新的社會規則時,很明顯失去作用了。
在《溺死一只老貓》中,新老之間的沖突貫穿整篇小說。故事的起因是清泉村計劃開始建設游泳池,卻遭到阿盛伯一群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將破壞當地的風水。當傳統的風水信仰影響了公民們現代化公共政策的正當權利,就將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一種尷尬和對現代化的一種障礙。故事的結尾以阿盛伯溺死在游泳池里的悲劇告終,而阿盛伯的犧牲對于村民來說,就如題目所說的溺死一只老貓一般微不足道,外界并不會因為他的死而停止前進的腳步。
“對于阿盛伯的保守和迷信,作者是有所批判的,但出于對這些小人物的同情,有意的淡化了批判的鋒芒。”[14]因此,在小說標題《溺死一只老貓》中我們可以窺見作者對于阻礙社會文明正當進步,以阿盛伯為代表的邊緣人的嘲弄。而對于滲透進鄉土的工業文明,從《青番公的故事》中也表達了他隱含的擔憂。青番公篤信自然帶給人類的訊息能夠使人們在土地上收獲豐厚的報酬,也能在災難來臨之前,給予人們真誠的警報。一方面,黃春明對于那些淳樸直率的傳統感到深深的眷戀,另一方面,他又意識到城市化進程給人們帶來的種種好處。所以,他是帶著懷舊卻又樂觀的心態去敘述這些令人感傷的鄉鎮小人物的故事。
(四)被資本異化的人
20世紀70年代在黃春明的小說創作時期中,有一個極為明顯的轉變。即是在他移居臺北后,深感西方工業文明的入侵給普通民眾帶來思想上的“異化”。所以,他逐漸將從以宜蘭平原為主要寫作視角的“鄉土”轉向了被西方工業經濟體系入侵的城市“鄉土”。這在黃春明的鄉土小說創作上是一個極大的突破與創新,他開拓了全新的視野去觀照被資本異化的邊緣人。這些被資本異化的人,包括了《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和《莎呦娜啦·再見》的黃君,這些新殖民主的社會買辦小資產階級精英在面對代表強勢一派的“西方”資本與弱勢的傳統一派“東方”傳統農業對弈時所做出的不同選擇。他們也屬于邊緣人中的“失落群體”,是脫離了原始鄉土后的城市人群。在這個大環境下,他們對于自我的身份認同是矛盾的、無實感的。
《莎呦娜啦·再見》的寫作視角,以“我”為第一人稱寫作,可以看到“我”在困惑中掙扎時也伴有間隔性的醒悟。黃君在作者的筆下能夠熟練運用多國語言,而且能機智應變。他利用語言上的優勢,一方面激烈的批判日本人侵華的暴行,另一方面叫徐崇洋媚外的大學青年。使人們不得不產生這樣的聯想,作者是在借“黃君”之口,來發出對帝國主義暴行的憎惡與對被資本異化喪失自我民族意識青年的嘆息。
在臺灣大量引進外來資本的同時,外來價值觀念滲透極大程度地扭曲了人們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念,消解了原本穩固的民族認同感。黃春明在《我愛瑪莉》里,刻畫了“里外不是人”的主人公陳順德。陳順德一心想要取悅他的洋上司,自愿照顧上司一家遺留下來的狗“瑪莉”,甚至不惜為此失去自己的家庭。他沉醉在自己營造的“美國幻夢”當中。不但不以此為恥,反倒引以為傲,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等同于美國上流社會的人的常態。但其實,陳順德的心理及行為已經成為一種變相的“病態”。瑪莉的到來徹底激化了陳順德與妻子的矛盾,等到了妻子不得不將自己與狗等同的婚姻絕境時,她向陳順德發問,“你愛我?還是愛狗?”陳順德瘋了一般地大叫“愛狗!”[15]黃春明通過愛“洋狗”甚于愛妻的陳順德,深刻地剖析了這股崇洋媚外的社會風氣是如何侵蝕人們的心靈,讓他們不惜失去自我,拋棄家庭,最終丟掉了民族尊嚴,表達了強烈的現實意識和民族意識。
三、黃春明鄉土創作的悲憫情懷
黃春明塑造的小人物,往往蘊涵著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對邊緣人物的人生選擇,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有批判也有理解與同情。這些邊緣人形象大致可分為四大類:漂泊不定的城鎮務工人員、灰色地帶的邊緣女性、固執堅守傳統鄉土的老人、被資本異化的都市人。他們的哭與笑,痛和淚反映了臺灣現代化進程對社會底層人民造成的價值觀念、生活環境乃至人生命運的巨大變化,同時也映射了臺灣社會在轉型時期出現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從《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貓》中對鄉村遭遇西方文明侵入產生巨大變化的深切反思,到講述《蘋果的滋味》《兩個油漆工》里對城鎮底層人民困窘生活、艱難命運的同情,以及寫《莎呦娜啦·再見》《我愛瑪莉》對造成崇洋媚外的人以及背后的資本主義的無情批判。黃春明開創了文學與臺灣現實結合的道路,展現了別具一格的創作特色,邊緣人物面臨的困境,對現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一是揭示,揭示了人性的復雜、揭示了生存的困境,在揭示中顯現直面現實的勇氣;由小人物的悲歡擴展到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他用關心人、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文學態度進行創作。二是批判,一方面批判資本主義文明和外國經濟的侵入對臺灣鄉土社會造成的惡果,另一方面批判封建傳統對邊緣人思想的禁錮與戕害;面對復雜多變的局勢,他理智上并沒有全盤排斥城市化進程帶來的文明與進步,情感上對鄉土文明被侵蝕感到憂慮與惋惜。三是頌揚,頌揚苦難中的人性之美。透過黃春明筆下的邊緣人,可以感受到生命帶給人心靈的震撼,坤樹、白梅、阿盛伯們是樸實而又純真的,他們以真摯赤誠的心去面對生活,尋求失落的人性尊嚴。
參考文獻:
[1]張書群.價值的缺失和追問——黃春明小說中的邊緣人物論[J].語文學刊,2016,(17).
[2][3]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美)赫姆林·加蘭.破碎的偶像//美國作家論文學[M].劉保端譯.北京:北京三聯書店,1984.
[5]沈從文.邊城·長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6][9][10][15]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7]凌宇.沈從文談自己的創作——對一些有關問題的回答[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04).
[8]錢少武.契訶夫、屠格涅夫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J].甘肅社會科學,2001,(06).
[11]宋媛媛.淺析黃春明臺灣轉型期小說中的悲劇[J].文學教育,2014,(03).
[12]龔潤枝.蕭紅作品與女性群體的人格失落——以《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為例[J].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5,37(02).
[13]黃春明.看海的日子[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
[14]王士瓊.論黃春明小說的鄉土世界[D].汕頭大學,2006.
作者簡介:謝淑瑤,女,漢族,江西瑞金人,塔里木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學科教學(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