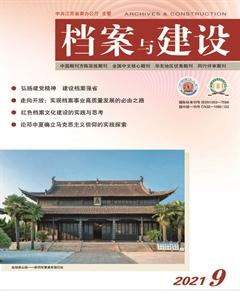從滄浪亭旁的蘇工到看花宮的陜北公學分校
劉丹 施建平
摘 要:1938年,身在國統區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顧稀為了抗日救國、追求進步,拋棄穩定的技術工作,歷經艱難曲折,遠赴陜北投奔共產黨、參加抗戰,頗有時代典型意義。
關鍵詞:蘇工; 陜北公學;顧稀;中國共產黨;抗日
顧稀(1919—2012),原名顧乾熙,江蘇崇明(今屬上海市)人。1938年9月參加革命,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任北方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代院長,1951年任院長,1952年任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院長。顧稀作為生在江南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為了抗日救國、追求進步,于抗戰前期遠赴陜北投奔共產黨、參加抗戰的人生經歷,在當時頗為典型。
一、就讀于滄浪亭旁的蘇工
1934年6月,生活在崇明縣橋鎮的顧乾熙剛年滿15周歲,得知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學校(簡稱“蘇工”)招生消息,便加入了備考大軍。他從上千的考生中脫穎而出,被錄取為蘇工土木科的學生。當時三元坊的蘇工校舍容納不了眾多的學生,一年級的新生只能先在蘇州平門外的分校上課。蘇工管理學生非常嚴格,平時不準學生出校門,僅周日可以出門辦點事。嚴謹治學的環境使顧乾熙可以在校安靜地博覽群書,思考人生和社會。
當時正值東北淪陷、長城抗戰之后,全國抗戰呼聲高漲,大多數學生受時局影響,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感。《蘇工土木科民二六級大事記》對蘇工當時的學習、軍訓、實習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因為時局的緣故,加上學制變動——五年制的課基本要在三年內學完,同學們學習都非常緊張,周日上午都排有四節課,有時寒假也不放。此外,還有注重個人衛生的“清潔運動”、強健體魄的“課外運動”。而軍訓則新生入校即開始,每年三個月,軍訓中學生稍不注意,就要吃教官的“槍柄”。1936年4月中旬,同學們的學習更加緊張了——“每日增加軍訓二小時,于下午三時至五時教授。功課仍不變……上午七時半上課,每課三刻鐘,上午五課,下午二課,及軍訓二小時。”參加軍訓的同學經常要步行十幾里路,到蘇州古城外的獅子山(今獅山公園)下打靶,最后進行實彈射擊;還要到虎丘山下的公路邊進行爆破,炸彈威力巨大,使同學們終生難忘。在高強度的學習和軍訓中,有的同學累到生病退學——1934年入學時有40人,而1937年畢業時僅有30多人。1936年冬,同學們為了支援傅作義將軍在百靈廟抗擊日軍,積極響應“援綏運動”,食菜飯一周,佐菜全靠醬油湯,每人節約捐出四角二分,此外爐子也不生了,把冬季的取暖費也捐贈了出來。[1]
自1935年起,顧乾熙便來到位于北宋古典園林滄浪亭旁的蘇工本部學習,學校豐富的圖書、報刊擴大了他的視野。當時的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也在學校隔壁。自1934年起設立的“民眾學校”,讓他接觸到了社會,使他更加深刻地思考民族、抗戰等問題。他喜歡閱讀鄒韜奮編輯的《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進步圖書,漸漸在心中埋下了思想進步的種子。[2]
二、在福建就業筑路
蘇工的土木科主任兼教務主任沈慕曾,字賓顏,浙江紹興人,為1908年浙江省首批官派考選赴歐美的留學生,與錢寶琮、翁文灝是同學。沈賓顏深受嚴復實業救國理念之熏陶,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科,是地道的“海歸”。沈賓顏既能教書,也偶爾從事翻譯工作,譯有英國羅蕊著的流行小說《里城案》問世。沈賓顏人格高尚、生活簡樸、治學嚴謹、很有學問,深受學生喜歡,對同學們影響很大。老師長輩的教誨也與顧乾熙閱讀的《大眾生活》周刊等進步刊物倡導的人生之意義基本一致:生活之目的,一是為自己謀生,二是為社會盡職,三是為民族爭光,等等。
20世紀30年代,老師、長輩、校友推薦是畢業生就業的主要渠道。沈賓顏曾在交通部工作過,在土木工程界有較為廣泛的人脈,他對各個學生的情況也十分了解。顧乾熙當時在學校并不活躍,沉默寡言,平時不喜歡運動,體育場上找不到他的身影,但他學習成績不錯,在《蘇工民二六級畢業紀念刊》中,他和錢家榮等同學撰寫的具有論文性質的《南通軍山氣象臺實習記》,排在所有同學文章匯編之首。因此,1937年7月底,顧乾熙從蘇工畢業后,由沈賓顏介紹去隴海鐵路工作。顧乾熙家在崇明,就業之前他返鄉與親人告別。但因為有同學不愿意去較為偏遠的福建工作,而當時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沈賓顏只得將顧乾熙換到福建省公路工程處去工作。
1937年秋,顧乾熙開始在福州的福田路工程處工作。他作為筑路工程技術人員,不僅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技術,還要關心氣候和地理。由于工作駐地在福州西北的白沙鎮,交通方便、消息靈通,顧乾熙他們每天都能接收到抗戰的相關訊息,隨即用廣播等形式傳播給當地民眾。他一直閱讀鄒韜奮編輯的《抗戰》三日刊、后來的《全民抗戰》三日刊。怎樣才能切實為民族作一點事情呢?這個想法一直縈繞在這個18歲的年輕人的腦海。
1938年春,顧乾熙被調到福建寧化的寧石路工程處工作。這里原屬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由于從事公路勘測工作,顧乾熙有機會深入到深山老林、窮鄉僻壤,看到中央蘇區時代留下的標語傳單。從《全民抗戰》三日刊上又看到對中共辦的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的介紹。他提高了對中共的認識,對陜甘寧邊區有所向往。耳濡目染加上1938年七八月間福建抗戰形勢動蕩,顧乾熙決心遠赴陜北投奔共產黨,參加抗日,他在等待機會。[3]
三、從閩西輾轉至陜西關中
1938年夏天,日軍逼近武漢。作為工程技術人員的顧乾熙當然明白,一旦武漢失守,中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就此切斷。當時工程處剛好有一批人員想在武漢失守前離開福建到湘黔鐵路工作,顧乾熙趁此機會,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938年8月,他們辭職離開了閩西山區。當時北上之路十分曲折,要從寧化步行到長汀,而后乘車去江西瑞金,再從瑞金搭船到贛州,再乘長途汽車去廣東韶關,轉乘火車沿粵漢路北上。
1938年9月中旬顧乾熙到達武漢,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要他去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接洽。9月17日他到達西安,在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陜甘寧邊區學習。填表時顧乾熙“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自認為是“稀有之人”,把名字改為顧稀。次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分配顧稀前往陜北公學栒邑分校學習。
陜北公學是中共培養抗日軍政干部的學校,栒邑分校位于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栒邑縣(今陜西省旬邑縣)看花宮村。看花宮村的名字由來有趣。相傳以前村里出過探花,所以曾改名為“探花谷”,后來有人在此種過花,又改為“看花谷”,后來以訛傳訛就稱作“看花宮”了。還有一種說法是唐明皇和楊貴妃曾來此賞牡丹、修行宮,故得此名。[4]
顧稀在福建辭職前,每月能有三十幾元的積余,到西安時他在一路上花費之后,身上還有些錢。他打算先乘長途汽車到邠縣(今陜西省彬州市),再步行去栒邑分校,而不是從西安開始步行。9月20日,顧稀在西安汽車站排隊買車票時,有個軍人要他代買一張同程的汽車票。他們一起上了車,坐在一起,穿過一大片平原和丘陵之后到達了邠縣。此人自我介紹姓柴,也要去陜北公學。他說在邠縣要住一夜,第二天走一天就可到達。顧稀憑自己的直覺,感覺晚上肯定有事情要發生,不免心里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他的直覺是完全正確的,有一批和他一起從西安出發去看花宮的有志青年,因為是步行就被國民黨的人攔截住,押送到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顧稀在回憶此事時寫道:
我們二人走進了一家旅館,住在一個房間里。他說:“半夜里會有人來查夜,你就說你叫×××。”這天夜里,我們睡到半夜時,有人急促敲門,柴同志把門打開,走進來兩個便衣警察,他拿出護照給他們看。這兩人在房間里查看了一下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們起身,他說:“我們合雇一個毛驢,把行李馱上,我們空身走。”我說:“好。”我們二人從邠縣縣城岀發,向栒邑縣(即現在的旬邑縣)看花宮村走去。路上我們吃了點大餅,我又拿出一些餅干來一起吃。柴同志說:“這餅干你留著,帶到陜北公學,就成為珍貴的禮品了。”下午三點來鐘,我們二人走到了一個村邊,迎面走來兩個兒童,手執紅纓槍,向我們要“路條”,柴同志拿出護照,我們就通過了。[5]
柴同志告訴顧稀:我們已進入到陜甘寧邊區了。這時顧稀興奮極了,終于從福建來到原來的陜北革命根據地,實現了自己人生的愿望。顧稀三個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尤其是交通行業高等院校的領導工作。
四、久別重逢,志同道合
畢業后分別已久的蘇工老同學們并不知道顧稀到西安后已改名,1947年印刷的《蘇工校友錄》上,土木工程科1937屆學生中仍寫“顧乾熙”的名字,其通信地址欄一片空白。從這冊《蘇工校友錄》可知,同屆同科的學生里接替顧乾熙在隴海鐵路工作的是老家在無錫顧山的張嗣香,通信地址為“陜西寶雞隴海鐵路工程第三總段轉七分段”。抗戰勝利后,張嗣香供職于國民政府交通部鐵路測量總處,辦公地點在南京市珠江路728號。
老同學們在尋找顧乾熙,顧稀則一直在尋找那位讓自己順利到達看花宮的“引路人”柴同志。1985年離休后,顧稀終于有時間來搞清這個問題了。陜北公學老校長成仿吾的夫人張琳告訴他:可以問一下柴樹藩。顧稀回憶:“1986年春,我冒失地給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柴樹藩同志發了一信,詢問他我1938年去陜北的上述情景。1986年6月中旬他來信說‘您1938年9月從西安經邠縣到旬邑路遇的那個人就是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四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終于找到了。”在上海錦江飯店,兩人暢談了近五十年前的共同革命經歷,感慨萬千。[6]
其實柴樹藩也是在抗戰前期遠赴陜北投奔共產黨、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當顧乾熙還在閩西尋找救國之路時,在他的家鄉崇明附近的上海讀了兩年稅務、只比他大一歲的柴樹藩,已經先其半年奔赴延安。
1933年,柴樹藩懷揣母親烙的山東煎餅,赴清華、燕京大學趕考,結果在兩所大學都金榜題名,卻交不起學費而忍痛棄學。失望之余,他馬上南下報考了“不收學費,食宿全包”的上海稅務專門學校——其學生畢業后直接成為海關職員,捧上“金飯碗”。1935年柴樹藩從稅校畢業后,被分配到天津海關入職。當時的天津海關由英國人把持,中國人只能干低級職務,受盡了氣。日本侵占東北,威逼華北,日本人也明目張膽地在海上走私日貨,中國海關人員在緝私時只能忍氣吞聲。1937年七七事變后,天津海關為日本人控制。1938年 3 月,柴樹藩與同事袁成隆結伴而行,投奔共產黨。他們南下廣州,繞道武漢,最終到達延安,考入培養抗日軍政干部的陜北公學。同年5月,柴樹藩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全國各地成百上千的愛國青年奔赴延安,這給當地的后勤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加上愛國青年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往往還被國民黨攔截、逮捕,因此急需在離西安和隴海鐵路較近的地方找到一個合適的辦學點。同年7 月,陜北公學栒邑分校成立,柴樹藩先后擔任分校政治部秘書、校務部副部長、部長,從西安把愛國青年帶到栒邑分校便成了他的重要工作。[7] 柴樹藩這就與顧稀有了交集。后來柴樹藩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在改革開放初期擔任第六機械工業部(主業是船舶制造)部長,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首任董事長、黨組書記,為中國造船工業做出卓越貢獻。
*本文系蘇州市職業大學“校史·校友研究”重點課題“蘇工專紅色基因與革命歷程研究”階段性成果,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建設基地吳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項目(項目編號:2018ZDJDB01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與參考文獻
[1]畢業紀念刊籌備委員會編:《蘇工民二六級畢業紀念刊》,1937年,第1-5頁。
[2][6]顧稀:《我和共和國同成長》,《滄浪》1999年9月20日,第1-3版。
[3][5]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編寫組編:《血與火的洗禮——從陜北公學到華北大學回憶錄》第一卷,1997年,第92-95頁。
[4]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時期校史讀物編委會編:《中國不會亡 因為有陜公——陜北公學(1937-193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5頁。
[7]王宗光主編:《懷念柴樹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