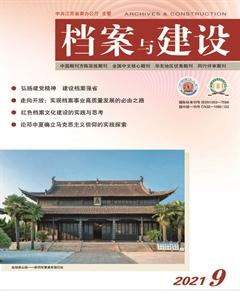清末民初生活方式、社會意識、消費觀念的變遷
王志強
摘 要: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習俗傳入中國。不論是百姓日用中呈現的崇洋媚物,還是突破倫理約束下的僭越趨新,消費觀念下尚奢去儉的風尚,都除舊布新,出現了不少新事物、新氣象,引領民眾的社會生活面貌發生巨大變化。
關鍵詞:生活方式;社會意識;消費觀念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雜糅了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近代等對立因素,國民的思想與意識處在一個躁動的時期、敏感的時代,呈現出崇洋媚物、僭越趨新、尚奢去儉的時代特色,并充分體現在這一時期的設計之中。
一、崇洋媚物,日用器物變化下生活方式的變革
清末民初,大量的外來商品涌入,外形新奇、功能優越的各類“洋貨”受到大眾的青睞和追捧。“一種文化對于異質文化的吸收,往往首先開始于最表層的生活習尚層次……隨著近代文明的滲入,中國人看到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模式,激發了追求、模仿人類進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無意地用這種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實自己的生活,從而使傳統的生活方式出現了巨大的變革。由于受到西俗的強烈影響,這些變革顯現出的一大特色就是趨新與洋化。”[1]毋庸置疑,最先吹響沖鋒號角的是西方的日常器物即洋貨。“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鐵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與紙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備之;光緒乙未、丙申之際,改用火柴,俗稱‘自來火,為歐洲之輸入品。夜間取光,農家用篝(俗稱油盞),城鎮用陶制燈檠,家稍裕者,則用瓷制或銅錫制者,有婚喪事者,則燃燭;光緒中葉后,多燃煤油燈,而燈檠遂歸淘汰。洗面擦身之布,舊時多用土布,有用高麗布者已為特殊,其布仿于高麗,質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農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產之皂莢,自歐美肥皂行銷中國后,遂無有用皂莢者。計時之器,僅有日晷儀,用者亦不多,購買外洋鐘表者尤為稀少;自輪船、火車通行,往來有一大時刻,鐘表始盛行。箱篋之類,鄉間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則用皮制者,嫁妝內所備多用朱漆;光(光緒)、宣(宣統)之間,西式提箱仿造于滬地,于是旅客多購用之。”[2]由西方傳入的日常器物被民眾所接受,洋貨占有了中國廣闊的市場并持續擴大,進而推動了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
《馬關條約》簽訂后,列強陸續得以在中國直接投資設廠,雇傭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在中國本土生產銷售各類洋貨或仿制洋貨,價格進一步降低。“上而縉紳之家,下而蓬戶甕牖,莫不樂用洋燈,而舊式之油盞燈淘汰盡矣”。[3]隨著通商口岸的逐漸增多,洋貨的生產與銷售逐漸深入內地,洋貨使用日益普及,“飲食日用曰洋貨者,殆不啻十之五矣”。[4]無疑,器物的傳入影響了大眾的消費觀念,進而改變著大眾的日常生活方式。這種崇洋媚物的生活態度首先出現于少數通商口岸與官僚富裕之家,隨后逐漸傳入內地和農村。“凡物之及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衣有洋縐,帽曰洋筒,掛燈曰洋燈,火鍋名為洋鍋,細而至于醬油之佳者名洋醬油,顏料之鮮明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5]
眾所周知,“在對洋貨的選擇上,盡管人們有著復雜的心理,也經歷了一個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長過程,然而洋貨最終以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占據了城市人的生活,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這之中,沒有恥辱,沒有自尊,有的只是對西方文明的無比羨慕。在沒有其他參照系的前提下,洋貨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國對英、美等國先進文明的學習與渴望。”[6] 正如西餐館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上海市民對于飲食種類的認知,也接受了一種新的公共空間類型與文娛生活方式,咖啡館、酒吧、臺球吧、社交俱樂部等。中國社會依托西方的器物文化,呈現出一種靠近西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價值觀。隨著洋貨被大眾接受,學習、模仿、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成為必然的文化現象,傳統生活方式才隨之改變,進而加速著傳統社會禮儀、習俗等諸多方面的變革。
二、僭越趨新,等級觀念約束下社會意識的覺醒
傳統文化對大眾的服飾、日用、居所有著森嚴的等級規定。以貴族為代表的上層社會既有享用奢華器物的權利,又有消費、使用的實力,還有享用奢華器物文明的組織生產條件,有完善、成體系的特權服務人員和機構。如在我國專制等級制度時期,存在著官府與民用兩大制造體系。官造體系有專門的設計機構、生產作坊,工藝精湛,物不外流。官民制造,等級嚴明,不可僭越。傳統習俗也受等級觀念約束,在器物層面體現出尊卑有別,如官服中紋樣和色彩的差異、民服中質料和工藝的區別,乃至相應的花飾、配件不能有絲毫僭越。普通百姓如果貿然使用某些高檔或特殊的器物必然被上層階級所譴責,甚至處罰,也不被廣大社會所認可。“商賈不衣錦,中產家婦女無金珠羅綺”。[7]不可僭越成為一種社會無意識的文化存在現象,被投射在傳統手工藝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南京、上海等地城市化幾乎與全球資本主義社會同步,城市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念主導著近代中國設計思想的走向。“近代以來,隨著清朝中央集權的逐漸衰落,等級制受到嚴重挑戰。城市中的知識階層和工商業階層最先脫去長衫,穿上西服,成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驅。辛亥以后,帝制被推翻,清代的官服隨之被拋棄,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服飾消費成了流行與時尚的標志,最終失去了區分等級的功能。”[8]傳統等級與秩序被刻意突破,在影像、廣告以及商業形式的促動下,妓女可以打扮成千金、名媛,癟三亦可以著西裝、戴禮帽,產生與其身份不相稱的影響力。傳統設計是在等級、地位的嚴格限制下,在經濟能力的約束下,各階層的人分享設計的不公平原則;而隨著等級、地位等因素被打破,金錢成為制約大眾選擇設計、享用設計的唯一因素。就設計對象而言,在消費能力的制約下,不同的階層站在各自的社會、經濟平臺,享受設計的公正與平等,破除、消解等級觀念,僭越趨新成為社會意識的常態。“張愛玲曾敏銳察覺到洋貨在中國社會制造出的文化誘惑,當人們意識到眼鏡是現代性的符號時,社會上的女孩與職場女性也都紛紛戴上了眼鏡作為裝飾。新職業、新著裝、新發型、新媒體、新的公共空間等,這種女性形象逐漸轉變為一種資本主義的商業力量呈現出迷人的、時尚的、欲望的、觸手可及的印象。”[9]歷史證明設計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具有的無限潛力,設計可以滿足消費者愿望,可以激發某種價值渴求,從而鼓勵消費者接受物質文化來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在注重實用功能和追求享樂的生活倫理的支配下,傳統等級貴賤讓位于金錢,以金錢來衡量一切的觀念被逐步接受,金錢成為消費中重要的制約因素,崇尚金錢在大眾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這在否定傳統等級觀念、義利觀念的同時,客觀地推動了近代消費觀的重構,對人們的社會生活、交往方式、人際關系、價值觀念及倫理觀念等諸多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趨新與洋化是消費習俗走向近代過程中自然而突出的文化現象,其背后則是顛覆等級權貴、僭越趨新的社會意識日益風靡。可見,等級制度通過物化形態來體現統治階級的特權地位,借助倫理規范嚴禁僭越,與經濟、實用功能無關,其背后是“禮制”的彰顯,“人倫”的凸顯。奢華與僭越的社會表征加之近代消費觀念的突破,是對傳統消費習俗和社會意識的挑戰與顛覆,是等級觀念約束下近代社會意識的覺醒。
三、尚奢去儉,消費理念影響下風俗習慣的轉向
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自然經濟,遵守孔孟儒學“尚儉去奢”的思想,講求“儉不違禮,用不傷義”的價值取向,要求大眾的日常生活“知足常樂、安之若素”,并以道德、倫理為理論支撐。在中國漫長的文化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約定俗成的消費習慣,無論是器物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中華民族都崇尚克勤克儉、樸素節約,勤儉節約是傳統消費習俗中最為突出的特點。
消費觀念和消費習俗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由傳統進入近代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和影響。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刺激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復存在,傳統消費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開埠后,消費風習漸趨華靡。”[10]隨著近代新經濟因素的出現,經濟體量的增長,經濟觀念的變遷,傳統的農業社會消費觀受到“尚奢去儉”消費觀念的沖擊,自近代上海開埠以來,奢侈消費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尚奢之風由大都市擴散到城鎮及農村。
奢華能夠擴大大眾對商品的需求,促進生產,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促進社會財富的流動,奢華的商業價值被當時很多學者認識到并極力倡導。如譚嗣同認為:“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為之名,又為之教曰黜奢崇儉,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資,憑借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并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11]甚至梁啟超也撰文反駁傳統儒家的節儉觀念,認為“崇儉”是“上古不得已之陋習”,是自然經濟生產力低下的結果,必將被先進的近代生產力所取代。[12]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于1904年初夏作歐洲十一國游,后作《歐洲十一國游記》,其中《意大利游記》描寫了奈波里建國的歷史及其人口、地理環境,描寫了它的城市商業環境、市容風貌,還寫出了與北京對比而生的感想。”[13]他認為:“舊國整頓極難,以屋難拆毀故也,整頓道路,治宮室,非別辟新埠不可。”[14]尚奢去儉思想的提倡和宣揚,使奢侈消費觀逐漸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為近代消費的一大特征。
新文化運動以來對人權、人文、個性的提倡,推動物質消費觀念和資本主義文化消費觀念不再受到傳統倫理的束縛,大眾化的審美需求得到設計的迎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現出趨時逐新、尚奢去儉的現象。如市民對西裝洋服的崇尚與效仿,甚至達到了只識衣裳不認人的狀況,魯迅就因為著裝問題而遭到南京路豪華飯店“華懋飯店”服務人員的奚落和冷遇。中國人重視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重視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見諸日常生活中的體面、身份、時尚等行為特征不僅僅體現生存性,還體現出強烈的社會性。人們購買新奇、時尚的器物,多是出于交際、夸耀、消遣、享樂的心理需求,而不單單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它沒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卻比思想更廣泛的走人每一個人的生活里去。但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之后,它同時成為人們生活的一個部分了。”[15]近代中國大眾的消費觀受西方影響非常明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體現了一般百姓對近代化的接受程度,趨新、逐尚、求異一直是大眾消費風俗的重要特征,是追求個性消費觀念的體現形式之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 項目“藝術設計倫理概論研究”(項目編號:17YJA760055),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專項課題“大學生藝術教育通識課程群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與參考文獻
[1]嚴昌洪.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演變[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152.
[2]陳傳德修,黃世祚,王燾曾,等纂.嘉定縣續志·卷五.見黃葦,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3]嚴偉修,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十八. 見黃葦,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M].上海:中華書局,1962:1106.
[5]陳作霖.秉燭里談.見嚴昌洪.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演變[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43.
[6]譙珊.近代城市消費生活變遷的原因及其特點[J].中華文化論壇,2001(2).
[7]黃葦,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6.
[8]耿光連.社會習俗變遷與近代中國[M].濟南:濟南出版社,2009:105.
[9] Eileen Chang,“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Twentieth Centuye,1943,4(1):p59.
[10]樊衛國.近代中國的奢侈消費[J] .探索與爭鳴,1994(12).
[11]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M].北京:中華書局,1981:322.
[1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9:37-44.
[13]薛娟.中國近現代設計藝術史論[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9:53.
[14]馮光廉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287.
[15]陳旭麓.陳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