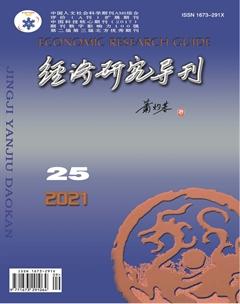志愿文化助推鄉風文明建設研究
羅曼妮
摘 要:志愿文化嵌入是推進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路徑之一。志愿文化的基本內涵包括人道主義、慈善理念、責任意識、互助精神等方面。弘揚志愿文化對于提升農民道德素質,培育鄉村支持網絡,重構鄉村人際關系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應通過傳統文化挖掘、現代文化注入以及文化服務落地等路徑,進一步推進志愿文化對鄉風文明的引領,促進鄉村文化振興。
關鍵詞:志愿文化;鄉風文明;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1)25-0031-03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內容,也是新時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范疇。但是鄉村文化建設中的陣地缺乏、設施簡陋、經費匱乏、活動貧乏等問題客觀存在,鄉村文化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1]。在新時代文明實踐背景下,倡導公益理念、慈善精神與助人服務的“志愿文化”理應逐漸滲透至鄉村文化中,成為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層面。開展志愿服務、弘揚志愿文化對于弘揚人道主義精神、宣揚優良道德理念、重振鄉村精神[2]、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具有積極效用[3]。
一、志愿文化的基本內涵
志愿文化是指志愿參與過程中產生的所有物質和精神的產出總和。志愿者的思想意識、志愿服務的方式方法、志愿組織的宣傳標語與設施、志愿服務的規章制度、志愿服務的社會宣傳等都屬于廣義的志愿文化范疇。志愿文化的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人道主義。志愿服務的產生與針對社會弱勢者的人道主義幫扶息息相關。一戰后,部分公民志愿參與城市重建,修復受損的家園,一些志愿者通過心理援助等人道主義救助方式幫助人們修復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當代志愿服務范圍廣泛,貧困者、疾病者、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是志愿服務的重要對象。志愿者則通過多種途徑滿足貧困者、殘疾人等受助者的需要,不求回報,無私奉獻,保障受助者的生存權利與生命尊嚴。志愿文化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是最樸素的人道主義呈現。
第二,慈善理念。志愿精神的源起與慈善理念一脈相承。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公益慈善觀念、基督教中的“愛人如己”“施愛于人”等教義都主張與人為善,幫助他人。早期慈善觀念對西方國家志愿精神的興起與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現代志愿文化同樣強調“無償”“公益”等元素,志愿者不將志愿服務作為有償工作以及賺取利益的途徑,而將其視為社會互助、踐行社會責任、獲得自我實現的方式。志愿文化可以看作是慈善文化的一個方面,是善意的傳遞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路徑。
第三,責任意識。志愿文化強調一種責任意識。投身志愿服務不是法定義務,這種行動是由個人所自我認同的社會責任所驅動的[4],個人基于公民的道德觀念與公共意識,將幫助解決社會問題、積極參與社會建設、推動社會發展視為個體的社會責任,并經由責任意識驅使,積極投身志愿活動實踐與志愿文化宣傳。由此,志愿文化的本質是利他的,志愿者是以社會責任而非個人得失為出發點的,志愿文化強調將個人幸福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系,是對個人對公平正義等社會責任的深刻認識,是強調公民與社會的責任聯結的先進文化。
第四,互助精神。志愿實踐并非僅是單向幫助,更多表現為志愿者個體與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助關系。志愿文化產生于社會互動與互助中,鼓勵志愿者和受助者相互傳遞互助精神,具體表現為志愿者與受助者之間、志愿者之間以及受助者之間的三個維度。首先,志愿者和受助者之間通過志愿服務實現物質幫扶和精神支持,受助者從志愿者處獲得一定的物質或精神資源,另一方面,志愿者在助人的同時也獲得了心理認同與精神升華。其次,志愿者之間在工作過程中必然會產生關系的聯結,幫助對方處理一些問題也是互助精神的具體體現。此外,受助者受到了幫助,也可能進行善意傳遞,主動關懷幫助與自己相似境遇的個體,將互助精神內化于心并向社會傳遞。
二、志愿文化對鄉風文明建設的積極影響
第一,提升農民道德素質。志愿文化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內源性動力。中國傳統“小農思想”在部分農村仍有殘余,表現為小富即安、裙帶思想、自私自利等觀念,這些歷史遺留顯然有悖于現代鄉風文明建設。培育孵化“公益書屋”“老年互助小組”等鄉村志愿組織,營造鄉村志愿文化氛圍,讓農民感受到志愿服務的社會效益,轉變農民傳統封閉的思想觀念,幫助農民形成開放的為人處事態度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志愿文化引導村民積極參與志愿服務,讓農民在實踐中加深對鄉風文明的理解,在活動與服務中感受志愿文化,以行動帶動認知提升,普及開放互助的志愿文化理念,有助于提升農民道德素質與人文素養。
第二,培育鄉村支持網絡。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帶來鄉村社會的轉型[5],鄉村人口大量外流,鄉村空心化問題突出,農村青年鄉土文化認同感缺失,“孝”文化等傳統文化淡化[6],鄉村留守老人養老問題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突出[7]。除了動員社會組織或企業供給專業化服務以外[8],弘揚志愿文化,倡導志愿服務,構建鄉村社區內部幫扶體系,培育鄉村支持網絡,發展鄉村“自服務”能力,是滿足農村老年人、殘疾人、留守兒童等特殊群體的需求的重要途徑之一[9]。志愿文化強調公平互惠以及互幫互助,弘揚志愿文化,號召農民自發參與社區事務或社區建設是現代鄉村社會的必然選擇,宣傳推廣志愿文化,鼓勵社區參與,提升農民集體意識,培育社區歸屬感,實現共治共建共享[10],實現鄉村文化振興與自我回歸發展[11]。
第三,重構鄉村人際關系。相較于傳統鄉村,現代農村社區的居住、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譬如,居住方式上,從傳統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式居住逐漸轉型為現代化集中式樓房居住;生產方式上,從傳統的個體勞動逐步轉型為規模化、機械化的農業生產;社會結構上,從傳統的“熟人社會”轉型為當代農村的“半熟人社會”。農民生活的私人化傾向突出,“家本位”觀念濃厚,自我主體意識強烈,并逐漸呈現“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化趨向。自我化、封閉化、冷漠化導致鄉村社區人際關系“原子化”,社會交往表面化。志愿文化強調互幫互助,倡導社群互動,志愿文化引領下的志愿服務可提升村民之間的交往頻率,深化村民之間的了解程度。守望相助的文化內涵有利于打破逐漸加高的“心理圍墻”,帶來互相信任、彼此依賴的心理體驗,并構建良性運轉的人際關系網絡,形成文明和諧的鄉村文化氛圍。
三、志愿文化助推鄉風文明建設的實踐路徑
第一,傳統文化挖掘。守望互助是志愿文化的基本內涵之一,中國自古就有深遠的互助文化傳統。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了諸多助人、仁愛、慈善等“志愿文化”元素。比如,孔子指出,“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論語·顏淵》);孟子主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孫中山先生提出,“進化之動力在互助而不在競爭。”這些觀念均折射出我國深厚的志愿文化歷史底蘊,表明志愿文化是中國文化遺產的有機組成[12]。志愿服務將團結、奉獻作為其核心精神的重要組成方面,中國鄉村社區互助的優良傳統與志愿文化的精神內核一脈相承。志愿文化嵌入鄉村文明建設首先應挖掘傳統文化的力量,比如組織傳統文化宣講隊,開展諸如端午節包粽子、重陽節登山等群體性的傳統文化活動,挖掘守望相助的傳統精神,喚醒鄰里親睦的傳統慣習,營造參與式的鄉里鄰里氛圍[13],以此為依托,積極傳播志愿文化,助推鄉風文明建設。
第二,現代文化注入。志愿文化與慈善觀念密切相關,現代的慈善不僅是直接的捐錢捐物,更重要的是通過服務供給實現助人自助的目的。傳統的西方志愿服務具有的慈善性質,常表現為上層人士對底層人士在物質上的幫助,標示出鮮明的社會等級,帶有施舍性質。此類“志愿文化”忽視了人的尊嚴與價值,具有狹隘性。在當代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志愿文化亦需本土化與現代化,在鄉村振興與鄉風文明中,注入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現代文化與價值元素[14],形成平等、共享、參與等理念,使農民在志愿參與中加深對公民社會道德與主流價值觀的理解。在新時代背景下,尤其要關注將黨建文化注入到志愿文化培育當中,加強黨組織與志愿組織、社區組織之間的關聯[15],堅持黨建文化引領志愿文化建設,提升志愿文化的活力、生命力與影響力。
第三,文化服務落地。志愿文化不能脫離志愿實踐而存在,否則會導致“重送輕種”的懸浮化傾向[16]。志愿文化需轉化為志愿服務與志愿活動,才能得以宣傳推廣并使農民領悟其文化內涵,形成新型的鄉村文化傳播結構[17],以志愿服務實踐助推鄉風文明建設與鄉村治理轉型[18]。我國鄉村社區異質性程度高,由此,農村社區需要綜合考察人口、地域、組織、設施等要素,精準評估社區需求,依據當地文化特點、文化資源以及農民需求,精準孵化或鏈接志愿服務項目方案[19]。一方面,動員農村留守婦女、低齡老人、退休村干部等,挖掘鄉村內部的志愿者“資源稟賦”[20];另一方面,鏈接外部資源[21],導入運作較為成熟的志愿組織以及社區服務設施[22],提升志愿服務的效果。同時,規范志愿管理,以“共享平臺”[23]等工具建設完善鄉村志愿隊伍管理機制,形成較為完備的志愿者隊伍管理體系與志愿服務組織體系,保障志愿服務的質量與效果。此外,優化鄉村志愿者培訓制度,提升志愿服務的獲得感,建立志愿者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
參考文獻:
[1]? 蘇鎏一.教育振興背景下鄉村中小學藝術教育路徑優化研究[J].漢字文化,2020,(8):185-186.
[2]? 張嘉煒.網絡短視頻傳播中的鄉土文化發展研究[J].漢字文化,2020,(14):46-47.
[3]? 韓鵬云.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踐檢視與理論反思[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102-110.
[4]? 張祖沖.我國志愿文化構建的維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5):132-134.
[5]? 易艷陽,周沛.危機與重構:AGIL框架下的農村殘障老人家庭支持系統[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86-95+157.
[6]? 劉熙雨,潘承亞.“孝”文化變遷與城市家庭養老重構[J].漢字文化,2020,(19):130-131.
[7]? 陳晶晶.父母教養方式對留守兒童未來取向的影響:心理控制源的中介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0,(9).
[8]? 陳睿玲.養老企業供給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8,(34):36-37+41.
[9]? 張娜.從《海洋天堂》看殘疾人的家庭支持[J].戲劇之家,2019,(24):99-100.
[10]? 易艷陽,周沛.“共享養老”:社區居家養老產業創新發展路徑[J].理論月刊,2020,(3):88-95.
[11]? 韓鵬云.鄉村文化的歷史轉型與振興路徑[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1-9.
[12]? 王泗通,張繼焦.文化融合視域下老字號品牌現代轉型的路徑選擇[J].貴州民族研究,2020,(7):126-131.
[13]? 王泗通.垃圾分類何以能在單位社區持續推行——以“單位人”為研究視角[J].求索,2020,(4):158-163.
[14]? 易艷陽,周沛.文化資本與助殘社會組織文化建設[J].寧夏社會科學,2020,(1):120-126.
[15]? 馬超峰,薛美琴.組織資源稟賦與社會組織黨建嵌入類型——基于南京市社會組織的案例分析[J].學習與實踐,2020,(6):70-78.
[16]? 韓鵬云.鄉村公共文化的實踐邏輯及其治理[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3):103-111.
[17]? 馮廣圣.互嵌與協同:社會結構變遷語境下鄉村傳播結構演變及其影響[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2):91-101.
[18]? 韓鵬云.鄉村治理轉型的實踐邏輯與反思[J].人文雜志,2020,(8):114-121.
[19]? 易艷陽.殘障社會工作循證實踐模式本土化探究[J].社會工作,2019,(5):88-95+111.
[20]? 易艷陽.資源稟賦、可行能力與殘障青年創業支持——基于Z市典型案例的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20,(2):87-94.
[21]? 易艷陽.助殘社會組織內源發展動因與策略研究[J].江淮論壇,2019,(2):137-142.
[22]? 錢瑜.社區養老設施建設中的鄰避沖突成因及治理[J].戲劇之家,2019,(20):224-225.
[23]? 易天媛.共享型養老平臺構建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8,(36):46-47+58.[責任編輯 毛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