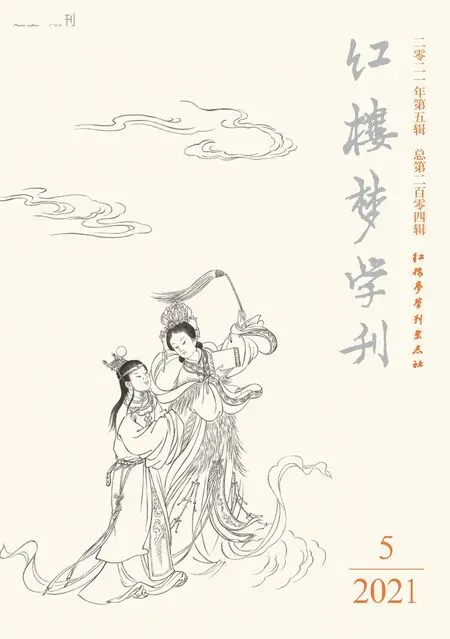楊憲益-戴乃迭《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翻譯研究?
王金波 王 燕
內容提要: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始于《中國小說史略》翻譯,該譯本的修訂再版與《紅樓夢》翻譯出版密切相關,可以視作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120回英文全譯本的前奏,是全譯本誕生過程的重要環節。本文利用第一手資料從描寫譯學的視角探討《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描寫譯文特點、評價譯文質量、解釋譯文成因并概述其流傳與影響。本文認為,盡管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章節譯文屬于特定歷史時期與個人境遇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但翻譯質量總體相當出色,隨《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在英語世界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120回英文全譯本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隨后成為國內外《紅樓夢》翻譯研究熱點。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實際歷時逾二十載,存在多種形態與載體,先后經歷片斷翻譯、完整章節選譯、120回全譯、節譯、雙語對照等。依照各階段首版時間,主要包括1958年《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雜志《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1959年《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翻譯、《中國文學》1964、1974、1977年章節選譯、1978-1980年一百二十回三卷全譯本、1986年節譯本、1999年漢英對照本(大中華文庫一百二十回全本、雙語節選本)、2003年漢英經典文庫本等。楊憲益鐘愛并大量譯介魯迅作品,對魯迅作品翻譯與傳播居功至偉,其貢獻不在翻譯《紅樓夢》之下。楊憲益很認可個人對魯迅作品翻譯與流傳的貢獻,認為1950年代自己的扛鼎譯作可能是四卷本《魯迅選集》。饒有趣味的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是中國第一部小說史專著,而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正是發端于《中國小說史略》翻譯。
李晶概述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歷史并對《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進行了初步介紹與研究。榮立宇、蕭輝(2019)則從微觀層面粗略比較《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與1978-1980年一百二十回三卷全譯本相應文字差異。總體而言,對這一章節譯文的現有研究要么在考證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全譯本底本時順便提及,要么直接比對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進程的首尾譯文。雖然現有研究有助于深入透視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但其不足十分明顯。一言以蔽之,現有研究均或多或少忽視原文底本、譯本版本變化,幾乎無視《中國文學》章節選譯這一重要中間環節,總體研究深度不足且在史實、細節方面存留舛誤與紕漏,對于譯文的評價比較粗淺而且有失公允,留有很大的進一步探討空間。
描寫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把現實生活中業已存在的譯文作為研究對象,描述譯文特點,探尋促使譯文產生的因素以及譯文對目的語文化的影響等問題,因此堪當研究片斷譯文的理想理論框架。本文從描寫譯學的視角探討楊憲益-戴乃迭《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紅樓夢》章節,描寫并評價譯文特點、解釋譯文成因并揭示譯文流傳情況,旨在豐富與深化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研究。
一、基本史實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由初創到最終定型,經過多次增補修訂,歷時近20年;1923、1924年北大新潮社初版上下冊的問世使得全書篇幅固定為28篇。《中國小說史略》在魯迅生前共印行11版次,其中1935年6月北新書局第十版再次修訂本是作者生前最后修訂本,以后各版均與此版相同,最終確定了此后流傳至今的《中國小說史略》總體面貌。就版本而言,新中國成立之后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形態多樣,既包括各個時期印行并修訂的單行本,又包括收錄于《魯迅全集》多卷本分冊之選文。
《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說”專論《紅樓夢》,而通常作為附錄收錄其中的魯迅演講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也涉及《紅樓夢》。李晶認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譯文連載于《中國文學》1958年第5、6期,1959年成書出版。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楊憲益、戴乃迭于《中國文學》1958年第5、6期發表的只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而非整個《中國小說史略》28篇全部內容的譯文,這篇譯文作為附錄收入楊憲益-戴乃迭《中國小說史略》1959年英譯本。與期刊譯文相比,單行本書中收錄的相應譯文只是刪除了腳注與提及的著作中文原名,改譯部分書名,內容幾乎全同。此外,《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雖然概述《紅樓夢》情節與相關研究,但除了書名、人名等并未引用小說原文任何內容。因此,嚴格說來,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雖然始于《中國文學》1958年譯文,但實際發軔于1959年《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章節翻譯。
1959年英譯本布面精裝,配有木刻插圖與古本書影,列入外文出版社“中國知識叢書”(China Knowledge Series)。根據英譯本出版說明,《中國小說史略》原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八卷。在魯迅著作出版史上,這里的《魯迅全集》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版本,即1958年版《魯迅全集》(十卷本),出版時間為1956年至1958年。《魯迅全集》第八卷實際出版于1957年12月,內容包括《中國小說史略》與《漢文學史綱要》,附錄為此前版本從未收入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需要注意的是,1959年英譯本除了翻譯《魯迅全集》第八卷所錄《中國小說史略》全部內容,還翻譯了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與《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序,其中日譯本序出自《魯迅全集》第六卷收錄之《且介亭雜文二集》。這種選擇背后的原因不難理解。首先,魯迅1935年6月9日所寫日譯本序提及《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后新史料與新觀點的出現,表明自己修訂原作的態度,具有重要的史料與學術價值。其次,增田涉翻譯的日譯本是《中國小說史略》第一個外文譯本,楊憲益-戴乃迭英譯本則是第二個譯本,增譯日譯本序言可以豐富英語世界中國文學研究者的視野,有利于譯本流播。這一做法可能顧及西方漢學界不成文的傳統:治漢學者必通日文,治日本學者必通中文。
然而,《魯迅全集》“第八卷說明”也含有明顯的史實錯誤,即以為魯迅1930年修訂后的版本是最終版本,決定了后來版本的面貌。令人遺憾的是,1959年英譯本出版說明按照中文版說明翻譯,并未加以改正或注釋說明,而此后的英譯再版本如法炮制,始終沒有發現這個問題。此外,1959年英譯本出版說明不知何故,竟然把新潮社《中國小說史略》上冊的出版時間“1923年12月”誤譯為January 1923,1964年版依然如故,直到1976年版才予以改正。下文探討則以1957年12月《魯迅全集》第八卷中《中國小說史略》原文與1959年英譯本為主,兼及1964、1976年版英譯本等再版重印本與《中國文學》1958年《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
二、譯文描寫與評價
依照筆者自建的1957年12月《魯迅全集》第八卷《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章節原文與1959年英譯本之譯文漢英對照段落對齊生語料庫,原文共計5542字(包括標題“清之人情小說”),譯文共計5386詞(包括標題、腳注詞語)。一般而言,由于文言文簡潔凝煉,將中國文言文作品翻譯為現代英文,結果總是原文字數較少而譯文用詞較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主要為文言文寫就,即便考慮到譯文對原文極少量內容(書名等)進行了簡略刪削處理,原文與譯文字數比為1.03∶1,近乎1∶1,楊戴譯文一貫簡練明快的風格由此可見一斑。
《紅樓夢》章節直接引用原文第1、2、5、57、75、78、105、120回部分文字,總計2361字(不包括標點符號),引用程偉元序與高鶚敘共166字,其余部分為魯迅概述小說情節、介紹作者家世、評價小說成就的文字,共計3015字。從紅學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楊戴120回全譯本“出版說明”(Publisher's Note)主要從階級斗爭觀點介紹小說歷史背景與紅學史等,對曹雪芹、高鶚家世及小說藝術成就著墨極少,對于楊戴紅樓譯本的接受很不利,而《紅樓夢》章節符合英語讀者閱讀習慣,正好可以補充楊戴紅樓全譯本輔文本(paratexts)不足之缺點,具有獨特學術價值。就細節而言,譯文還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一)書名《石頭記》與《紅樓夢》翻譯幾經變動
在《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說”中,書名《石頭記》與《紅樓夢》多次出現,譯文并非始終如一,而是不斷修改,數度變動。為了直觀與準確起見,依照原文中《石頭記》與《紅樓夢》出現次序與對應譯文列表如下:

原文 1959、1964年譯本 1976年及以后譯本有小說曰《石頭記》者 the Tale of a Rock the Tale of the Rock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the Tale of a Rock the Tale of a Rock改名《紅樓夢》the name of the novel was changed to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ung Lou Meng)Hung Lou Me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The Hung Lou Meng deals with the family of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Ming Chu Hung Lou Meng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This theory that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s autobiographical Hung Lou Meng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His son Tsao Haueh-chin wrote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ng Lou Meng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he wrote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ng Lou Meng艷情人自說《紅樓》 All speak of the romance of the Red Chamber the red mansions
在原文中,《紅樓夢》作為單獨書名共出現10次,除了上表所列具有對應譯名的例子,其他語境下譯文都用代詞指代或不予翻譯。《石頭記》作為單獨書名共出現9次,除了上表所列具有對應譯名的例子,其他語境下譯文都用代詞指代。此外,盡管《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原文并未配備《紅樓夢》插圖,1959、1964、1976、2009年譯本等卻配有1791年程甲本插圖兩幅。對于插圖中的書名《紅樓夢》與正文譯法保持一致,1959、1964年譯本插圖文字選擇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而1976年等譯本則用音譯Hung Lou Meng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書名翻譯幾經變動,而英文版《中國文學》相應譯文堪稱風向標與晴雨表。《中國文學》1958年第6期《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中,《紅樓夢》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石頭記》為The Story of the Rock,在1959年英譯本第24篇正文以及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中,前者譯名相同,后者改為The Tale of a Rock。《中國文學》1964年第6、7、8期刊登的《紅樓夢》介紹文章與譯文都用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翻譯《紅樓夢》,1964年《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的選擇與此一致,《中國文學》1974年第5期譯文依然如此。
1976年英譯本把音譯Hung Lou Meng作為正式書名,意譯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作為補充說明放在括號中,“紅樓”也順勢譯為red mansions。此后《中國文學》1977年第11期譯文直接把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作為正式譯名,1977年第12期譯文同樣如此,并且在第四十回前所加按語(Editor’s Note)中把Hung Lou Meng與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作為音譯與意譯書名放在括號中作為補充說明,預示并標志A Dream of Red Mansions成為最終選擇。1978-1980年百二十回全譯本果不其然,但《石頭記》譯文卻前后不一:在第一卷為The Tale of the Stone,而在第三卷卻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需要注意的是,1959年英譯本“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中的書名《石頭記》譯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未必是誤譯,很可能為了照應上文“改名《紅樓夢》”與“其子雪芹撰《紅樓夢》”等文字。
(二)人名翻譯反復變化,最終音譯為主
《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篇幅不大,涉及《紅樓夢》部分主要人物。總體而言,1959年英譯本音譯男性人物而意譯女性人物,1964年及以后譯本幾乎全部音譯人名,無論男女:

1959年譯本 1964與 1976及以后譯本1929年王際真譯本/1958年王際真譯本[15] 1958年麥克休姐妹譯本(庫恩德譯本之轉譯本)[16]寶玉 Pao-yu(Precious Jade)Pao-yu(Precious Jade)Pao Yu(Precious Jade) Pao Yu黛玉 Black Jade Tai-yu Black Jade Black Jade寶釵 Precious Clasp Pao-chai Precious Virtue Precious Clasp元春 Primal Spring Yuan-chun Cardinal Spring Beginning of Spring鳳姐 Madame Phoenix Hsi-feng Phoenix Madame Phoenix湘云 River Mist Hsiang-yun Hsiang-Yun/River Mist Little Cloud妙玉 Mystic Jade Miao-yu Exquisite Jade Miao Yu晴雯 Bright Cloud Ching-wen Bright Design Bright Cloud襲人 Fragrant Flower Hsi-jen Pervading Fragrance Pearl平兒 Little Ping Ping-erh Patience Little Ping紫鵑 Cuckoo Tzu-chuan Purple Cuckoo Cuckoo雪雁 Snow Swan Hsueh-yen Snow Duck Snowgoose金釧 Gold Bangle Chin-chuan Golden Bracelet Gold Ring尤二姐 Second Sister Yu Second Sister Yu Yew Erh-chieh Second Sister Yu
上表清楚無誤地表明,《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篇人名譯法并非一成不變。第一,《中國文學》1958年第6期《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譯文中,凡《紅樓夢》概述部分提到的人名無論男女全部音譯。在《中國小說史略》1959年英譯本正文中男性人物中只有寶玉在第一次出現時括注意譯,其余都用音譯,女性人物全部意譯,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與此保持一致。這一人名翻譯策略明顯受到王際真1929年英文節譯本影響,但1964年及以后英譯本中人名翻譯又改為音譯為主,但所用拼法仍然以威妥瑪式(Wade-Gile system)為主,并未使用漢語拼音。第二,1959年英譯本的人名翻譯受到庫恩德譯本之1958年英文轉譯本以及王際真1929、1958年譯本影響,上表14個人名中同前者的譯名7個,同后者的譯名4個,其余名字譯法也受到二者啟發。耐人尋味的是,王際真1929英譯本序中認為“湘云”無法翻譯,1958年譯本則譯為River Mist,這一譯法顯然深得楊戴贊許并直接借用。第三,在1959年英譯本所附折疊式大張賈府人物表中,女性人物先音譯,然后括注意譯,二者并用,但1964、1976年等譯本只留音譯,刪除意譯。
(三)所選原本底本有誤,譯文亦有個別誤譯
1957年12月《魯迅全集》第八卷《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章節原文有三處錯誤,譯文因照譯而出現兩處錯誤。第一處在原文開頭部分“東魯孔海溪則題曰《風月寶鑒》”,此處“孔海溪”即“孔梅溪”之誤,但1959年及以后譯本均照此譯為Kung Hai-hsi。第二處在中間引述程本高鶚敘末尾“乾隆辛亥冬至后一日”,此處“一日”系“五日”之誤。1959年及以后譯本全部依此譯為the day 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of 1791。筆者追溯《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史并親自翻檢原文,發現第一處文字1924年版無誤,而1936年10月第11版、1938年版《魯迅全集》第九卷反而印錯;第二處文字以上三個重要版本均為“乾隆辛酉冬至后一日”,包含“辛酉”與“一日”兩處錯誤。按照概率推算,這很可能是魯迅筆誤或所引原書錯誤。盡管如此,這種原文本身的錯誤譯者當時即使發現也可能無權擅自改動,惟有照譯。第三處涉及介紹曹寅生平的文字“清世祖南巡時”,此處1957年版腳注說明應該為“清圣祖”,譯文直接用名詞emperor及代詞his指代,并無問題。
在原文本身無誤之處,譯文尚存誤譯:(1)人名。“林海”(即黛玉之父林如海)在1959年譯本錯譯為Lin Han,除了1973年美國重印本后來的版本均改為Lin Hai;在賈府人物表中,“李紈”在1959年譯本中譯為Li Wan,本來正確無誤,但在1964年譯本中竟然錯譯為Li Huan,此后版本又都為Li Wan。令人蹊蹺的是,《中國文學》1964年譯文同樣錯譯為Li Huan,而此前王際真1929、1958年英譯本也誤譯為Li Huan,不知是巧合還是真有某種關聯。不過,《中國文學》1977年譯文已經改為Li Wan,1978-1980年全譯本亦復如是。此外,所有版本譯文都將“王夢阮”誤譯為Wang Meng-yuan,“孟森”誤譯為Meng Sheng。(2)地名。1959年譯本“金陵十二釵”徑直譯為Twelve Fair Women of Nanking,“青州”譯為Shantung。雖然“金陵”是南京舊稱,“青州”屬于古代九州,轄地主要在山東境內,但此舉多少有損于地名蘊含的歷史意味與小說時空設置。此外,“金陵十二釵”中巧姐是少女,Women無法囊括。盡管如此,1964、1976等各個版本卻一直保留原譯,直到1978-1980年全譯本方才改為Twelve Beauties of Chinling。“青州”則從1964年譯本開始就改為Chingchou。(3)粗疏。1959年譯本“次年應鄉試”錯譯為The following day he take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可惜以后各個版本從未改動。原文評價袁枚《隨園詩話》曹雪芹為曹寅之子關系錯誤的文字“以孫為子”,1959年譯本竟然誤譯為Tsao Hsueh-chin was not his grandson but his son,不但與前文矛盾,而且正好顛倒!所幸1964年譯本改正為Tsao Hsueh-chin was not his son but his grandson。
(四)譯文考慮英語讀者知識,酌情淡化原文文化
原文有不少文化意味濃厚的詞語,1959年譯本都酌情淡化。第一,介紹索隱派紅學主要觀點、曹雪芹家世與后四十回續書時魯迅逐一用括號列出了許多觀點的出處,這些著作如《譚瀛室筆記》《寄蝸殘贅》《金玉緣》《燕下鄉脞錄》《詩人征略》《心史叢刊》《隨園詩話》《續閱微草堂筆記》等大多刪除不譯,而將容易翻譯的書名巧妙融入文字。例如,“俞樾(《小浮梅閑話》)亦謂其”譯成Yu Yueh in his anecdotes comments that,用anecdotes替代《小浮梅閑話》,下接所援引文字,構成自然完整的句子;“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譯文為Hu Shih in his researches on this novel has pointed out many such discrepancies,不但刪除《胡適文存》,而且用researches on this novel替代《紅樓夢考證》,與前例如出一轍,堪稱妙筆。
第二,關于《紅樓夢》原文中的部分專有名詞,譯文要么不譯,要么用普通名詞替代。例如,“一日,寶玉倦臥秦可卿室,遽夢入太虛境,遇警幻仙,閱《金陵十二釵正冊》及《副冊》”,譯文為One day Pao-yu,taking a nap in the room of his nephew's wife,dreams that he is in fairyland where he meets a goddess and reads theTwelve Fair Women of Nanking
。此處“太虛幻境”與“警幻仙子”只用普通名詞替代,“《正冊》”與《副冊》”也未譯,“秦可卿”雖然未譯,但突出其乃寶玉nephew's wife。值得注意的是,在所附賈府人物表中,“秦可卿”音譯為Chin Ko-ching。這種翻譯手法雖然欠佳,但弱化此句蘊含的神話與夢幻色彩有助于英語世界讀者理解小說情節,無可厚非。不過,在后來的全譯本中,相應地方都有妥貼譯名,恕不贅述。第三,譯文盡可能泛化原文中文化意味詞語,甚至不惜修改本來正確的譯文。例如,“正白旗漢軍”與“鑲黃旗漢軍”涉及滿洲八旗制度,譯文只留“漢軍”,不涉細節。此外,批駁袁枚《隨園詩話》錯寫曹寅號的文字“以楝為練”譯文有所修改。1959年譯本文字Tsao’s name was Lien-Ting with a“wood”radical,not Lien-ting with a“silk”radical(楝亭是“木”字旁,而非“絞絲”旁),可謂精準無誤,一絲不茍,但需要英語世界讀者懂得漢字基本常識才有意義。在1964年譯本中,這一句譯為Tsao Yin’s name was wrongly written,實則化繁為簡,一語中的。
(五)詩歌翻譯白璧微瑕,但精煉傳神,韻味獨特
原文引用第一、一百二十回詩歌,譯文雖然稍欠準確,但不乏韻味: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Pages of fantasy,
/Tears of despair,
An author mocked as mad,
/None lays his meaning bare.說到酸辛事,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癡。
Thís is a tale of sorrow/And of fantasy(
1959)【
fantastic but sad(
1964)】
Our life is but a dream,
/Laugh not at mortals’
folly.第一回詩歌前接小說書名來歷,說明是曹雪芹書成后所題,具有自我解嘲意味。譯文前兩句各有三個單詞,分別為5、4個音節,后兩句各用五個單詞,均為6個音節,偶數行押韻,后兩句mocked/mad/meaning構成頭韻,前后各自工整,視覺上形成強烈反差,成功烘托作者最后兩句蘊含的欲言又止、滿腔怨憤又擔心遭人誤解的苦衷。然而,“辛酸”譯為Despair(絕望)顯然不夠準確。第一百二十回詩歌是結書偈語,又照應第一回詩歌。1959年譯本用fantasy只譯出了“荒唐”之意,遺漏“可悲”,榮立宇、蕭輝完全忽視了這個版本。1964年譯本改變句式,補足所缺意義。總體而言,1964年譯文含有sorrow/sad、fantastic/folly兩組頭韻,意思準確,節奏明快,自成一體。
三、譯文成因解釋
翻譯活動總是處于特定的時空,并非處于真空與理想狀態,譯文的面貌受制于諸多因素。關于此書翻譯的時代背景與具體情況,楊憲益本人在英文自傳及他人采訪中多次提及:
1958年大躍進時期,
我們瘋狂譯書,
不分白晝大量炮制,
出書速度很快。
譯作的質量自然受到影響。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是一本杰作,
十天之內就譯完了。
我們當時沒有充足的時間譯得更好,
對此我一直感到遺憾。
(
筆者自譯)
問:
您覺得有必要改進您的譯作嗎?
答:
是的,
我認為有必要改正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譯本。
我們在大躍進時期翻譯了這本書。
按照要求我們每天要完成一定字數。
我來不及打字,
因此不得不口授譯文,
由戴乃迭打字,
因為她打得比我快。
于是,
我們十天之內就翻完了,
隨后出版。
這太匆忙了。
我覺得譯文改進余地很大。
翻譯之前必須非常仔細地研究原著。……
問:
在您之前別人已經翻譯了《
聊齋志異》
與《
紅樓夢》。
您在翻譯這些小說時看過并參考前人的譯文嗎?
答:
我看過別人的譯文,
但只是好玩而已。
很久以后我才決定翻譯這些著作。
(
筆者自譯)
楊憲益1990年開始撰寫并完成英文自傳,但書稿正式出版卻在2002年。作者鄭重其事地將譯書經歷寫入自傳告知世人,在相隔二十年后的采訪當中,仍然表達遺憾之情并追述更多細節,這一切足見楊憲益對魯迅作品之摯愛與個人赤誠之心。從其中透露的具體個人境遇不難理解為何譯本呈現上節總結的特點。首先,由于翻譯任務限定了每日工作量,譯者無暇細究原文的諸多細節與難點,提到的諸多著作名稱,只能大多刪除不譯,原文的文化背景盡量淡化,人名直接借鑒前人的譯法。第二,翻譯方式為楊憲益口授譯文,戴乃迭打字,二人商議定稿。這種方式對于漢語非母語的戴乃迭而言,很容易匆忙之中聽錯打錯,導致譯文出現人名、地名、粗疏硬傷。第三,在2001年的采訪中,譯者所說的翻譯《紅樓夢》實指始于1960年代初的《紅樓夢》全譯工作。這證明譯者很久以前讀過王際真1929年譯本等,而1958年下半年翻譯《中國小說史略》時又閱讀參考了當年出版的王際真新譯本與庫恩英文轉譯本,這與前文中人名翻譯的分析結果不謀而合。
在大躍進期間,整個國家與社會處于混亂失序狀態,譯者自然無法置身度外,譯本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與顯眼舛誤。曾于1994年9月6日采訪楊憲益的作家秦穎忠實記錄了譯者對大躍進的看法:
不知怎么我們談到了“
大躍進”,
他說當時,
上面要求他們的翻譯也要上一個臺階。
總在一旁靜靜聽談話的戴乃迭女士忽然插話進來:“
我們每天都得翻一番(
翻)。”
雙關用語頗為形象,
逗得我們笑了起來。
就這么一句話,
英式的詼諧幽默展露無余,
那些不堪的往事都付笑談了。
盡管如此,《紅樓夢》章節譯文簡潔流暢,文辭優美,足以傳達魯迅原文風格。除極個別簡單錯誤,所有關鍵文字并無問題,整體屬于上乘之作。從1959年初譯到1964、1976年改譯,譯者所做的修改工作只僅限于調整人名、地名、書名、微小局部細節翻譯等,對于《紅樓夢》原文引文的翻譯卻幾乎未改。筆者推測,修改潤飾耗時費力,譯者任務素來繁重,可能無暇顧及。最大的可能是楊憲益信念堅定,對先前的譯文整體頗為自信,寧意保留時代特色。
筆者認為,1959年譯本中的紅樓文字與1978-1980年全譯本的文字屬于兩種時空背景下的作品,各有千秋,相得益彰,雖然后者總體更為細膩精巧,未必處處優于前者。第一,以棋類比賽為喻,前者就像快棋與超快棋比賽,選手無暇長考,全憑棋感飛速落子,偶爾難免失誤,比賽質量稍遜一籌;后者類似慢棋與番棋比賽,選手絞盡腦汁,頻頻長考,力求妙手,比賽質量更勝一籌,但二者都可以體現出棋手的真實水平。
其次,從翻譯工作量的角度來看,楊戴承受了數倍壓力,非常人可比。例如,聯合國系統規定,筆譯員每人每日工作量為1650個英文單詞(5個英文標準頁,每頁330詞),審校員為4950詞(筆譯員的3倍),打字員為1650個英文單詞或3300個原文單詞。依據這個標準推算漢英翻譯,設定每人每日翻譯3300個漢字;楊戴二人融筆譯、打字、審校三種職責為一體,并且處于非常時刻,就按6600個漢字當作最大工作量。以純漢字為準,《中國小說史略》題記228字,序言210字,后記304字,日本譯本序550字,正文28篇共102485字,總計103777字,則每日平均實際翻譯10377字,近乎設定值兩倍,與戴乃迭的趣談完全吻合。聯合國系統所翻譯的文件套話很多,總體難度一般;楊戴翻譯的是文學作品且系文言文,難度更大。即便如此,楊戴翻譯質量依然很高,其翻譯藝術堪稱登峰造極。
四、譯文流傳與影響
筆者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為題名檢索OCLC Worldcat專題數據庫,逐一整理譯本信息如下:

國家 出版地 出版社 年代 全球館藏 重要特征中國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330 第一版中國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146 第二版美國 Westport,Connecticut Hyperion Press 1973 160 1959年版重印本中國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290 第三版中國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8 1976年版重印本美國 Westport,Connecticut Hyperion Press 1990 2 1982年版重印本美國 Honolulu, Hawaii of the Pacific 2000 6 1982年版重印本,無插圖University Press中國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9 29新版,前三版中的插圖全部移到正文前美國 San Francisco Sinomedia International Group 2014 7 最新版,無插圖
從以數據可以發現如下幾個明顯的特點:(1)購買收藏這些譯本的圖書館絕大多數來自主流英語國家(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愛爾蘭),其中美國占據大多數。值得注意的是,美國Hyperion出版社兩度接洽與外文出版社推出重印本,此后還由美國其他出版社重印。(2)譯本所在收藏館不限于具有中文專業與漢學傳統的大學與機構,眾多英語世界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不少著名大學圖書館均藏有譯本,在所有譯本的978條收藏記錄中,共有603條數據來自各大大學圖書館收藏記錄,占比61.7%。這些英語國家的圖書館不但包括眾多著名大學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蘇格蘭國立圖書館等代表主流精英文化與國家典藏的權威機構,還涵蓋公立圖書館、縣區與社區圖書館等基層機構,尤其是1959和1976年兩個版本的譯本的公共圖書館收藏記錄相對更多。這一切說明,譯本在英語世界分布與傳播廣泛,深入學術界與普通民眾。
毋庸置疑,隨著《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的廣泛傳播,楊憲益-戴乃迭譯文直接或間接影響許多西方漢學家理解、闡釋、講述乃至翻譯中國小說。筆者推斷,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譯文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鵝經典版《紅樓夢》英譯者霍克思、閔福德,理由如下:
第一,威爾士國家圖書館的霍克思文庫(David Hawkes Collection)包含其約4400冊各類藏書,其中編號為HAWKES-1042的圖書卡片對應《中國小說史略》1959年英譯本。雖然不清楚霍克思到底何時獲得此書,但一定不會很晚。此外,西方許多大學都訂購《中國文學》雜志,牛津大學也在其中,身為漢學教授的霍克思一生研究重點就是中國文學,很可能也讀過1964年《紅樓夢》譯文。這意味著早在霍克思1970年與企鵝圖書簽訂《紅樓夢》翻譯出版合同之前,他或許已經仔細閱讀了楊戴《紅樓夢》譯文,獲得某種啟發與靈感。這對于他講述紅學、翻譯紅樓均大有裨益。
第二,閔福德于1980年完成的關于《紅樓夢》后四十回研究的博士論文參考文獻含有《中國小說史略》原本與1976年英譯本、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本前兩卷。楊憲益-戴乃迭《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譯文包含程偉元序與高鶚敘部分文字,這可能助力閔福德理解并翻譯程乙本中程偉元序、高鶚敘與程高引言。此外,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本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同年楊憲益與吳世昌擔任閔福德博士論文答辯委員。閔福德在1982年出版的企鵝經典版《紅樓夢》英譯本第四卷前言中鄭重致謝楊憲益與吳世昌。種種跡象表明,閔福德肯定閱讀過《中國小說史略》與《紅樓夢》的楊戴譯本并吸收借鑒了某些譯法。
結語
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英譯始于《中國文學》1958年《中國小說史略》之附錄翻譯,《中國小說史略》英譯本1959年首次問世,后來多次再版重印。就《紅樓夢》章節而言,除了人名、地名、書名、部分內容翻譯略有改動外,總體幾乎未變。楊戴譯文忠實流暢、文采飛揚,近乎完美傳達了魯迅原作的內容與精神;另一方面,譯文存在微小瑕疵,但譯者不斷盡量修正以往紕漏。從翻譯活動的具體時空來看,由于特定歷史境遇的限制,楊憲益-戴乃迭用于《中國小說史略》英譯的時間明顯不夠,導致譯文存在刪削與少量錯誤,而譯者多次表達遺憾之情,彰顯譯者的敬業精神與專業素養。譯者在翻譯與修訂《中國小說史略》之《紅樓夢》章節時借鑒了王際真、庫恩譯本部分文字,而譯文也很可能對霍克思-閔福德《紅樓夢》英譯產生了某種微妙的影響。楊憲益-戴乃迭《中國小說史略》的翻譯與出版歷程印證了描寫譯學所倡導的翻譯產品(product)、過程(process)、功能(function)之間交織互動、錯綜復雜的關系,只有三管齊下才能客觀公正評價譯者與譯本。
注釋
① 本文初稿部分內容始撰于2017年12月,
后因《
中國小說史略》
原本與英譯本第一手資料不足及其他事務擱筆。
第一作者此前已在國內多次學術會議上講述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史并介紹《
中國小說史略》
英譯本之《
紅樓夢》
章節、《
中國文學》
章節選譯等。
參見王金波《
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文流傳與接受研究(
1958-2014)》,
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第十二次全國學術研討會暨2016英漢語比較與翻譯研討會,
2016年10月21-23日,
上海交通大學;
王金波《
中國文學外譯作品副文本中的中國形象——
以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為例》,
第二屆中國形象研究高端論壇,
2017年12月8-10日,
上海交通大學;
王金波《
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英譯與國家形象構建》,“
文化的轉碼與譯者的立場:《
紅樓夢》
與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翻譯”
國際學術工作坊,
2019年4月6-7日,
復旦大學。
② 黃喬生《
楊憲益與魯迅著作英譯》,《
海內與海外》
2010年第1期。
③[20] Yang Xianyi.White Tiger: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8、
204。
④ 李晶《
楊憲益-戴乃迭的〈
紅樓夢〉
英譯本底本研究初探》,《
紅樓夢學刊》
2012年第1輯;
李晶《
外部環境對楊譯〈
紅樓夢〉
底本選擇的影響》,《
紅樓夢學刊》
2012年第6輯;
李晶《〈
紅樓夢〉
三種英文全譯本底本差異性管窺》,《
紅樓夢學刊》
2017年第6輯。
⑤ 榮立宇、
蕭輝《
楊憲益兩種〈
紅樓夢〉
譯筆對比研究》,《
語言教育》
2019年第4期。
此文不知何故無視此前李晶的著述,
導致其文獻綜述較為空泛。
更為嚴重的是,
此文忽視《
中國小說史略》
譯本版本變化,
所引2009年版不能反映譯本文字演變,
不少觀點值得商榷。
⑥ 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p.23-31。
⑦ 鮑國華《
論〈
中國小說史略〉
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改的學術史意義》,《
魯迅研究月刊》
2007年第1期。
⑧ 劉運峰《
1958年版〈
魯迅全集〉
的編輯和出版》,《
中國出版史研究》
2017年第3期。
⑨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全集》
第八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A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1964、
1976;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ction.Chinese Literature,
1958年第5、
6期。
⑩ 許多文本分析軟件把漢語標點符號也作為漢字予以統計,
而英語文本標點符號不計入字數統計。
關于這一重要區別,
參見馮慶華《
思維模式下的譯文句式:〈
紅樓夢〉
英語譯本研究》,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第22頁。
筆者通過文本編輯手段手工刪除原文全部標點符號,
只統計純漢字與英文(
包括表達意思的阿拉伯數字),
所用軟件為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原文與譯文字數統計均不含賈府主要人物關系表。
[11] 許多學者誤以為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章節選譯僅限《
中國文學》
雜志1964年第6、
7、
8期,
只含第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七回譯文,
完全忽視了此后1974、
1977年刊登的第四、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
四十一回譯文。
例如,
持此觀點的學者包括范圣宇、
黃福海、
馮全功等。
參見范圣宇《
紅樓夢管窺——
英譯、
語言與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頁);
黃福海《
楊憲益英譯〈
紅樓夢〉
的再認識》(《
外國文藝》
2017年第4期);
馮全功《
楊憲益、
戴乃迭〈
紅樓夢〉
改譯研究》(
載于馮全功《〈
紅樓夢〉
翻譯研究散論》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第178—
195頁)。
黃福海誤以為楊憲益-戴乃迭《
紅樓夢》
章節選譯還包括第七十六回譯文,
馮全功的研究雖然更進一步,
但其參考文獻及分析論述因缺乏版本與歷史意識問題不少。
實際上,《
中國文學》
雜志上刊登的楊戴紅樓譯文上承《
中國小說史略》
篇章譯文,
下啟一百二十回全譯本,
不但本身篇幅浩大,
而且涉及楊戴紅樓英譯歷史進程中許多因素,
特點與成因極其復雜,
筆者擬專門深入研究。
[12]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Dream of the Red Chamber.Chinese Literature,
1964年第6、
7、
8期;
1974年第5期。
[13]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A Dream of Red Mansions.Chinese Literature,
1977年第11、
12期。
[14]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A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ume I.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第5-6、
251頁;A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ume III.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第585頁。
需要指出的是,
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譯法早在王際真1929年英譯本中就已出現,
并非霍克思首創。
霍克思1973年《
紅樓夢》
英譯本第一卷導言中《
紅樓夢》
前后有A Dream of Red Mansions與Dream of Golden Days兩種譯法。
楊戴全譯本最終選定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可能受其影響,
也可能是長期斟酌并與吳世昌等商議的結果。
外文出版社要推出大陸官方全譯本,
勢必不會采用最流行的譯法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吳世昌《
紅樓夢探源》
的英文標題采用The Red Chamber Dream,
雖然更為準確,
其實并未擺脫前譯影響。
這樣一來,
除了Red與Dream作為書名要素必須保留外,
留給譯者翻譯“
樓”
的選擇微乎其微,
Mansion必然成為考慮的對象。
雖然1964年底楊戴已經翻譯了大約100回,
1964年《
中國文學》
所刊登的譯文沒有第一、
五回,
無法直接觀察正文中《
紅樓夢》
譯名的變化。
令人遺憾的是,
1968年入獄前的紅樓譯稿與1972年出獄后重新翻譯并經吳世昌修改后的譯稿及校樣均不知所終,
許多問題將因第一手史料不足而成為懸案。
[15] Chi-chen Wang.trans.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Company,
1929;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58.[16] Florence McHugh and Isabel McHugh,
trans.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8.[17] 曹雪芹、
高鶚《
程甲本紅樓夢》,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曹雪芹、
高鶚《
紅樓夢:
乾隆間程乙本》,
中國書店2017年版。
據原書影印的這兩個版本高鶚敘均為“
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
[18]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北大第一院新潮社1924年版,
第255、
264頁;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北新書局1936年版,
第283、
292頁;
魯迅《
魯迅全集:
第九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1938年版,
第374、
382頁。
[19] 楊憲益是詩人,
擅長寫古體詩,
所寫打油詩幽默風趣,
具備譯詩的一切條件,
翻譯此類詩歌駕輕就熟。
此外,
榮立宇、
蕭輝援引前人研究,
提及楊戴全譯本第1首詩譯文與霍克思譯文極為相似。
筆者認為,
此前研究忽視了霍克思譯文其實受到前人譯文啟發的事實,
更未從翻譯史的角度審視楊戴全譯本問世過程,
兩種譯文此處的高度相似并不意味著楊戴必然參考了霍克思譯文。
由于涉及的史料與因素太多,
筆者擬撰文專門探討這一議題。
[21] Qian,
Duoxiu and E.S-P Almberg.Interview with Yang Xianyi.Translation Review,
2001(
2):
17-25。
[22] 秦穎《
秦穎攝影手記15:
楊憲益先生》,
發表于《
百道秦穎專欄》,
2013年7月1日。
參見網址https:
//www.bookdao.com/article/65172/,
訪問日期2019年5月5日。
[23] 盡管楊憲益一生歷盡曲折,
文革期間無端入獄,
后來痛失愛子,
但對譯事總是傾情投入,
無怨無悔。
楊憲益在自傳末尾的話可資參考:“
假如我還能重新活一遍,
我還會像以前那樣生活。”
參見楊憲益著,
薛鴻時譯《
漏船載酒憶當年》(
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第256頁)。
[24]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譯員黃文新在2014年的一次講座中介紹聯合國筆譯工作量,
參見https:
//sits.gdufs.edu.cn/info/1060/6369.htm,
訪問日期為2019年2月8日。
此外,
筆者從網上搜索獲得一份名為A/35/7/Add.7,
1980年11月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文件,
其中詳細規定了工作量。
參見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25] http:
//www.worldcat.org,
訪問日期為2018年12月18日。
[26] Wu Jianzhong.comp.David Hawkes Collection(
霍克思文庫)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1990,
p.109。
訪問威爾士國家圖書館(
https:
//www.library.wales/collections/featured/ethnic-collections)
可以下載霍克思文庫卡片目錄。
吳建中于從1989年起為威爾士國家圖書館對霍克思捐贈的圖書進行編目,
親自手寫完成全部圖書卡片,
歷時一年。
吳建中后來任上海圖書館館長。
[27] John Minford.The Last Forty Chapter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p.285、
274.[28] 2019年4月7日,
本文第一作者在復旦大學舉行的論壇主題發言完畢后,
閔福德在問答環節親口告知博士論文答辯情況,
但卻否認師徒二人受到楊戴紅樓英譯影響。
[29] John Minford.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4.London:
Penguin,
1982,
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