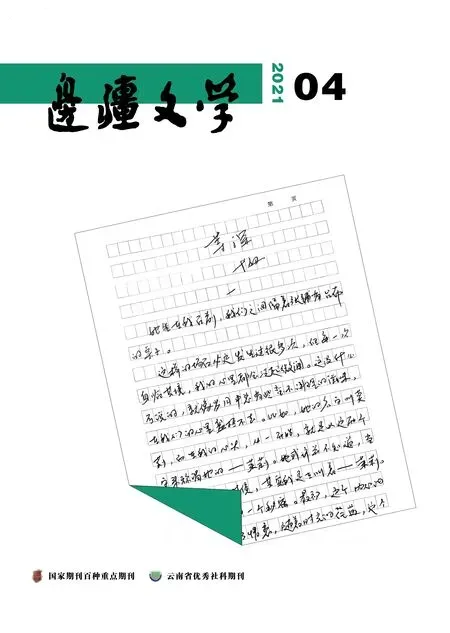雨天書 短篇小說
田興家(苗族)
我一醒來就下著雨,實在讓人難以忍受。但我還是起床開了門,興許曉默就在今天到達。院子里的泥土完全濕透,一腳絕對踩出一個深腳印。糖梨樹下有幾條螻蛄挖的通道,我想象著那玩意如何肥嫩。一條通道的盡頭,微凸起的泥土動了動,一只半大的螻蛄冒出頭。那只黑色母雞從樹上飛下來,啄住螻蛄又飛回樹上,一群小雞嘰嘰喳喳地搶著吃。
昨晚上我夢到一群飛翔的螻蛄,它們氣勢洶洶地攻擊我的房子。夢中的我驚慌失措。就在我打算要出逃時,村主任提著網袋跑過來,那模樣跟他年幼時一樣。村主任吹著口哨,右手在空中畫著曲線,螻蛄沿著曲線飛進左手的網袋里。最后他突然瞪我一眼,用那種開會講話的語氣說:“油炸透后,用來下酒,絕對美味。”我吞了吞口水,他驕傲地笑著走了。
假如曉默今天傍晚到達,雨肯定已經停了一會,那我就把這個夢講給她聽。曉默聽完后應該要唱一首歌,然后我們會相擁著哭泣很久。想到這些我鼻子發酸,抬眼看向糖梨樹,那群小雞依舊嘰嘰喳喳。黑色母雞從茂盛的葉子里探出頭來看我,怪叫兩聲后縮回頭,小雞全部安靜下來。我瞬間有點生氣。
肚子里一陣攪動。我想我的肚子里有兩條金魚,它們時不時就甩動尾巴,把我攪得難受。我懷疑是那天在河溝喝水所導致的。那是一條神奇的河溝,年幼時我目睹過一群長翅膀的金魚從水里飛向天空,它們興高采烈地叫著,有兩條追逐著繞圈子,似乎是故意繞給我們看的。當時阿丑滿臉鼻涕,提著網袋站在我旁邊,待金魚飛遠后,他說:“有一天我要學會本領。”我感到很吃驚,問他學什么本領,他說:“指揮這些會飛的生物。”我回家把阿丑的話告訴父親,父親說:“他是個有正能量的孩子。”果然,多年以后,阿丑就當上了村主任。
有人喊我一聲,我看到西村的阿婆翻到石墻上,對我做了個鬼臉,然后跳下墻來。別看這個阿婆已經年老,走路顫巍巍的,她可是翻墻的能手。阿婆年輕時曾開過一個“翻墻班”,招三個強壯的小男孩當作學生(包括我在內),整天講解翻墻心得以及翻墻技巧。聽了阿婆的課后,其他兩個小男孩都翻墻摔死了,唯有膽小不敢嘗試的我還活到今天。此刻阿婆像是在淤泥里,一腳深一腳淺地向我走來。
“我是來跟你談判的。”阿婆說著接過我遞過去的板凳,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下去,似乎感覺很累。屋檐的雨水不緊不慢地掉在阿婆腳邊,我這才發現她已全身濕透,正冒著若有若無的白氣。我知道阿婆正在心里發功。“我總懷疑,我養的那條毒蛇半夜溜出來,被你的黑母雞吃掉了。”阿婆又說道。
聽說阿婆二十歲時,丈夫去世,她每天去墳前哭一回。有一天,一條筷子般的毒蛇從墳里鉆出來,阿婆認為是他丈夫變的,于是就帶回家養,每天給它講一個故事。一年又一年,毒蛇長大了,有大腿那么粗,阿婆每天晚上都摟著毒蛇睡覺,有傳言說她還和毒蛇做那種事情,半夜里發出奇怪的聲音。可一個下雨的清晨,醒來的阿婆發現毒蛇不見了,找遍整個村莊都不見。阿婆斷定毒蛇是趁她半夜睡著時悄悄溜走的,因為那天晚上睡覺時她沒有摟緊毒蛇。
“你打算怎么辦吧?”阿婆盯著我,咳嗽兩聲,繼續說:“這幾天你一直躲著我,所以我只能親自來到家里找你。”
“你的毒蛇肯定長翅膀飛走了。”我沒好氣地說:“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個村什么事都有可能發生。”
“那你為什么老是躲著我?”
“我不想看到你哭泣的樣子。”我蹲下身來,換一種語氣說:“阿婆,你要試著理解我,別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樣。”
“我這么老了,還能哭什么,我只不過想讓你把那只黑母雞賠給我。”
提到這我就來氣。那只黑色母雞原本是在地上生活的,我總是撿它下的蛋吃,它就飛到樹上去生活了。這個村似乎什么生物都可以飛,唯獨我們人類不可以。我曾向村主任抱怨,我說:“阿丑,我也想要飛,你指揮我一下吧。”村主任笑瞇瞇地說:“不要急,等我忙完工作了,帶你去美國安裝一對翅膀。”我知道他只是說說而已,自從他當上村主任,就當面一套背地一套,這讓我極其不適應,要不是一直在等待曉默,我早就離開這個村了。這些阿婆是不理解的,我也無法向她解釋。
“你看看這些雨,一點停歇的意思都沒有,似乎要下到世界末日。”我轉移話題。
“可憐呀,你是我看著長大的,怎么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阿婆說:“你呀,簡直跟你爸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世界末日估計就要到了,我總覺得這段時間的夜晚比較長,那些螻蛄趁我不注意就鉆進我的左耳,吱吱地吵個不停。”
“你媽失蹤后不久,你爸總在半夜提著鐮刀來敲我的門,想殘害我養的那條毒蛇,我只能裝睡著,用呼嚕聲把他嚇走。”
“你真的無法想象,那些螻蛄吵累了,就會斷成兩半,頭部從我的右耳爬出來,尾部留在我左耳里腐爛,這些跡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即將到來。”最后幾個字,我故意加重語氣說,我想嚇嚇阿婆。
“其實你媽沒有跟那個賣米粉的小商販走,她是失蹤的。一個人失蹤就是突然不見了,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世界末日一到,我們就會無法動彈,永遠生活在黑暗中,連話都不能說,但我們的思維是清晰的,我們可以虛構一個人,然后想象他的一生。”
“你以為你爸真的是因為上山尋找野蜂蜜摔死的?不,你錯了。你爸故意用遍體鱗傷的尸體迷惑我們,其實他變成了一只野蜂。有一年我帶我的毒蛇去山里,看到一只野蜂在采花蜜,它的臉跟你爸一模一樣。”
一只螻蛄又從通道里冒出頭來,黑色母雞忽地飛到地上啄住,自己吞掉了。它看了我和阿婆一眼,又飛回樹上。雨仍在淅淅瀝瀝地下著,整個天空陰沉沉的。我聽到村主任在他家房頂上故意咳嗽,仿佛村里要發生什么大事。我突然感到心煩意亂,那兩條金魚又攪動了一陣。
“阿婆,你從院子里出去吧,鐵門沒有鎖。”停了片刻,我又說:“我不想看到你在墻上對我做鬼臉。”
“好吧,可憐呀,我們越來越沒有共同語言了。”
阿婆站起身來,抖動一下身體,掉了一攤水,她顫顫巍巍走出院子。伸手拉開鐵門時,一道閃電劈過來,阿婆的頭發瞬間變成一堆熊熊烈火,但她沒有任何反應,一腳深一腳淺地走遠。她的背影越來越小,頭上的火越燃越旺。
這令我想到了張三,他說我曾經教過他的初中語文。他第一次來看我時確實是這樣說的,但是我什么時候有過學生,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估計是上輩子的事吧,人們都說我是死而復生的人。有時候我真想爆粗口罵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太沒有邏輯了,那些醒著的人其實是在昏昏欲睡。我把我的觀點告訴村里的人,他們吹蘆笙跳著舞來侮辱我,那奇怪的舞姿像是在夢中一樣。唯有張三把我的觀點記錄在筆記本上。
“一個人的背影才是他最真實的內心寫照,因為面部表情可以偽裝,而背影不可以偽裝。”這句話是張三說的。我再看阿婆的背影,已經不見了,只看到一堆火在空中晃動著。張三曾經帶幾個年輕人來到我家里,為我拍了很多張背影照。張三說要挑一張最好的打印出來給我掛在墻上,但是一直沒有實現承諾,我也懶得問他,因為那幾個年輕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讓我感到害怕。
我似乎又看到一群光頭,他們穿著同樣的衣服,一齊打我、踢我、罵我。“你這模樣也能當老師?”“你怎么能對一個女同事下狠手?”“你還算個男人嗎?”他們的聲音亂成一片。有人把我拉起來,用力將我砸在地上,我感覺背上有一根骨頭斷了,馬上一只腳猛踩在我雙腿間,接下來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醒過來,我像狗那樣趴著,那些穿同樣衣服的光頭排隊在我屁股后撞擊。
我們可以假設這只是一個編造的故事,曉默,你不要過于替我難過。你侄兒已經長大,你哥和你嫂離婚了,你哥的生活過得一塌糊涂,沒有精力管教你侄兒,于是你侄兒學會了抽煙,那天我在路上碰見他,他還把煙頭朝我扔過來。你爸去年過世了,他臨終前說要去找你,你媽哭了一天一夜,聲音都啞了,從那以后就變成了啞巴。曉默,我不會再和你討論孤獨,我早就戰勝孤獨了。這讓那些石頭不高興,但它們拿我沒辦法,最多也只能在背地說風涼話。
又有人喊我一聲,我回過神來,又是西村的阿婆。她又翻到了石墻上,對我做著鬼臉。我知道今晚又要失眠了,一天中只要看到阿婆的兩次鬼臉,晚上就會害怕得睡不著覺。我狠狠地瞪著她,她頭上的那堆火依舊燃著,隔著老遠熱氣不斷向我襲來。那只黑色母雞飛過去,欲撲滅阿婆頭上的火,阿婆迅速頭一歪,用手指比作槍對準母雞,母雞立即吐血倒地身亡。整個過程一氣呵成,阿婆的動作竟如此敏捷。那群小雞嘰嘰喳喳的,它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這讓我感到很舒服。”阿婆笑著說。她晃動著頭,摸了摸頭上的火,像是摸頭發一樣,那表情有些得意。
“真是晦氣的一天。”我不高興地說道,歪過臉去。我覺得不解氣,隨即又補充道:“那些螻蛄怎么不鉆進她的耳朵里,讓她受耳鳴的困擾而死。”
阿婆一定能聽出我是在罵她,在這一點上她是很聰明的。我偷偷斜著眼睛看阿婆,她在石墻上調整一下坐姿,并沒有生氣的跡象。我這才注意到,阿婆身體的范圍內沒有下雨,也許是她頭上那堆火的緣故。她身體以外的地方仍在淅淅瀝瀝的,那只黑色母雞的血已經被沖干凈。
“我想想還是回來一趟。回來是想找你合作。”阿婆抬起右手做了一下手勢,繼續說:“你想想吧,在這個小村里,只有我們可以相依為命了。”
相依為命?我差點就笑出聲來,我才不會上阿婆的當。其實只有曉默可以和我相依為命,但我不忍心告訴阿婆,我怕她頭上的火會突然熄滅,然后她去向村主任告狀,那我是負不起責任的。自從阿婆的毒蛇失蹤后,我知道村主任在想方設法尋找我的缺點,想在會議上公布出來,讓村民們一齊放聲大笑三分鐘,把我置于死地。我還是小心一點為好。
“你不知道嗎?戰爭就要開始了。”見我沒回應,阿婆又說道:“他們都在隱瞞你,但我想還是對你說實話吧。村里前兩天已經組織了一支軍隊,那些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蠢蠢欲動,就等著村主任下令了。”
阿婆的話讓我嚇了一跳,不知道她說的這些是否屬實。我調整一下情緒保持鎮定,裝作無所謂地說:“打仗能有什么用,也阻止不了世界末日的到來。”
“你不要故作清高,到時候戰爭一開始,你還得來找我。”阿婆清了一下嗓子,繼續說:“別忘了當年你爸是怎樣求著我教你翻墻的,只可惜你爛泥扶不上墻。算了,我說這些舊事做什么。我只想告訴你,除了翻墻,我還有很多本領沒露出來。”
“誰去找誰,還說不定。戰爭真要發生,大家都自身難保,特別是像你這種年紀的。”我蔑視一般地說道,我想我不能在阿婆的面前表現得太懦弱。
“那就等著瞧吧。”阿婆嘴角笑了笑,接著說:“我的猜測肯定沒錯,你現在已經感到害怕了,可憐呀。”阿婆說著往墻外跳去。
石墻有兩個成年人那么高,原計劃砌成一個正方形,可只砌了三條邊,是父親未完成的夢想,但我無力幫他完成了。我看不到阿婆的背影,只看到那堆高高燃起的火,火越來越遠。我覺得阿婆的行為不符合常理,也許她是某個世界的人虛構出來的。那個世界的末日到了,某個人便躺在黑暗中虛構出阿婆這樣一個人物。從阿婆的身上可以看出,虛構她的這個人一定有些怪異。
我再向遠處望去,估計阿婆已經到家了。我想我得去找村支書,問他是否聽說了村里建立軍隊的事情。我找了一把傘撐開,過去撿起死去的黑色母雞,我打算送給村支書。據我所知,村支書臥病在床已有半年,村里的一切工作都由村主任主持。村主任那種敢用“阿丑”作為名字的人,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來。
我提著黑色母雞的尸體走出院子,估計那群小雞通過樹葉的縫隙看到了,它們齊聲大哭起來。我能有什么辦法呢?我只能懶得理會,快步往村支書家走去。肚子里的那兩條金魚又開始攪動,這一次攪得很厲害,也許它們已經餓了,我從前天下午起就沒有吃任何東西,因為我不想看到小鳳那肥胖的身體。
一進村支書家院子,難聞的藥味立即撲鼻而來,他家那條躺在屋檐下的狗突然睜開眼睛,搖著尾巴朝我跑過來,想咬我手中的黑色母雞尸體。我踢了狗一腳,它慘叫一聲又回屋檐下躺下了。村支書的妻子正在屋里搗藥,村支書在臥室里痛苦地呻吟著,他的兒子和兒媳在樓上吵架,但聽不清吵些什么。
“你來得正好,他這幾天一直叨嘮,說想見你一面,估計是有重要事情要和你商量。”村支書的妻子說。
我心里一驚,莫非是村里建立軍隊的事情,難道村支書已經聽說了?看來這些大事村主任都沒有跟他商量,要不他不會說想見我一面。村主任真是個心比天高的人呀。我替村支書感到憤憤不平,趕緊往臥室走去。
“我知道你會過來的。”村支書停止呻吟,試著坐起來,看著很費力。我擺擺手止住了他,讓他躺著說就行。
“沒什么禮物,就把這只黑母雞送給你吧。”我把黑色母雞的尸體放在村支書的枕頭邊。
村支書努力歪著眼睛看了一眼,長嘆一口氣,囁嚅著什么。樓上傳來砸東西的聲音,好像是砸了一個花瓶。村支書痛苦地呻吟幾聲,然后對我說:“你是個了不起的后生,只是你讀的書太多了,那些書籍讓你憂郁,所以你才走到今天這一步。”
村支書又呻吟了幾聲,繼續說:“并不是每個人都合適學習知識的。”停了片刻,他又說:“你現在正一步步走入毀滅之中,不知道你自己領會到了沒有。”
這幾句沒頭沒尾的話讓我摸不著頭腦。難道村支書想見我只是為了跟我說這幾句話?這讓我一時還不知道怎樣回答。我想跟他談談村里建立軍隊的事,但思慮一番決定等他先開口,因為我怕我先開口了會傷他的心。
“我一直都打算要幫助你,但我現在無能為力了。”村支書說,他的表情似乎有些難過。“這樣吧,給你一個機會,你把這只雞拿到龍鳳餐館,叫小鳳燉了給我送過來。”聽村支書的聲音,我知道他一時是死不了的,且有可能會好轉起來,重新掌權。
我拿起黑色母雞的尸體走出臥室。村支書的妻子不見了,地上放著搗好一半的藥,我注意聽樓上,什么動靜也沒有。但我沒對這一切進行想象,匆匆跨出了大門,屋檐下臥著的狗連眼睛都沒睜一下。
途中我摔了一跤,肚子里的兩條金魚終于安靜下來,我想它們一定是餓昏了。一只螻蛄在地上爬行著,它那慢吞吞的模樣似在挑釁我手中死去的黑色母雞。我替母雞感到憤怒,便把螻蛄撿起來,看它那肥嫩的肚子和嶄新的翅膀,然后丟進嘴里吃掉了。
到達龍鳳餐館時,小鳳正坐在門口剪腳指甲,看到我提著黑色母雞的尸體,她笑瞇瞇地站起來說:“今天自己帶材料來了?”小鳳笑起來跟村主任很像,她是村主任的侄女。小鳳的丈夫叫阿龍,是個開大貨車的。餐館用他們夫妻倆的名字命名,特色菜就是龍鳳湯,經常有人開車過來嘗。
我把黑色母雞的尸體朝小鳳扔過去,她那肥胖的身體一偏,伸手抓住雞腳。我把傘放在飲水機處,大聲說:“先給我煮一碗面,再把這只雞燉了。”
“是給別人燉的吧?”小鳳問。
“是的。”我怕她不認真對待,于是欺騙她:“給村主任燉的,燉好了我給他送過去。”
“咦,還挺會來事的,不錯不錯。”接著她又說:“村委一天只給我兩頓飯的錢,所以你一天只能在我這里吃兩頓飯。現在還沒到中午,你確定要吃?”
我說:“確定。”
看著小鳳斤斤計較的樣子,我心里有點不舒服。我想問問她,昨天我一天都沒吃飯,她是不是應該把兩頓飯的錢給我,但我想想覺得算了。小鳳把黑色母雞的尸體放進盆里,打開煤氣灶忙碌起來。為了對她的斤斤計較表示抗議,我一口氣喝了兩杯水。
面條很快就上桌了,我剝兩瓣蒜放進去,攪拌一下吃起來。小鳳倒熱水燙雞、拔毛、破肚,有條不紊地忙著,我看到她把內臟收起來了。龍鳳餐館似乎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這里面燉的雞都沒有內臟。聽說小鳳要把內臟留給阿龍吃,好讓開貨車的他起得像雞一樣早。
小鳳正把雞剁成塊,一輛疾馳的小車一個急剎,停在餐館門口,下來兩個男人。小鳳放下刀,把他們迎進門。他們點了一道龍鳳湯,說是開路路過,特意停下來嘗的。小鳳笑瞇瞇地說:“先坐著等一會,我家的龍鳳湯是現燉的,比較鮮。”接著她指墻上的電話號碼,建議那兩個男人存下,以后來之前可以打電話預定。那兩個男人存下電話號碼后,四處看了看,到靠窗那桌坐下,輕聲地談起了什么事,不時放聲大笑。
小鳳把剁好的雞肉放進高壓鍋里燉,我看到她留下了三分之一。我知道她留著為那兩個男人燉龍鳳湯,我起身想要過去質問,但無意間注意到那兩個男人穿著同樣的衣服(還打著領帶),我一陣懼怕,又坐了下來。我仔細聽他們談話,其中一個說:“這回戰爭真的要開始了。”另一個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他們都沉默下來。
小鳳從冰箱里拿出一截蛇肉,有大腿那么粗,她砍下一小點,把剩下的放回去。我驚訝得半張嘴巴,那一定是阿婆養的那條毒蛇,原來被龍鳳餐館一點一點地端上餐桌了。我再次起身又坐下,那兩個穿同樣衣服的男人直盯著我。
“這是你們村的那個瘋子吧?”一個男人輕聲問小鳳。
“有時候瘋,有時候好。”小鳳把留下的雞肉和切好的蛇肉放進另一個高壓鍋里。
“聽說以前是老師,后來犯事坐牢,就變瘋了。”那個男人好像顯得很興奮。
小鳳噓了一聲,用眼神示意他,他就沒再往下說了。我抬起碗,把剩下的湯全部喝掉。那兩個男人不再關注我,繼續談起事情,比剛才壓低了聲音,我聽出似乎還是關于戰爭的。我怕他們談著談著又盯著我看,便蒙住耳朵躲到桌子底下。
過了二十來分鐘,有人踢我一腳,我松開蒙耳朵的雙手,聽到小鳳說:“雞肉燉好了,你快點送去。”我站起身來,那兩個男人突然大笑,其中一個說:“像這樣的人,在戰爭中肯定要死。”我向他們看去,但他們沒有看我。
我的傘不見了,怎么也找不著。我懷疑是我躲在桌子底下時,被那兩個男人悄悄拿走的,但我不敢問他們。我只能冒著雨,提著小鳳打包好的雞肉,往村支書家走去。
路上我看到曉默的侄兒,他和一個小伙子騎著摩托車迎面駛來。到我旁邊時,他們一齊朝我吐口水,幸好我反應快,及時躲開了。雨似乎比剛才還大,我全身很快就濕透了。我突然想:這樣的雨天,沒有母雞了,那群小雞怎么活呢?我似乎看到它們哭泣的畫面,它們哭得死去活來的,我心里不由得一陣發緊。
走到村支書家院子,看到他家大門緊鎖,我這才注意到先前那難聞的藥味沒有了。我感到莫名其妙,走過去敲門,一點回應都沒有,我喊了幾聲,還是一點回應都沒有。那條狗突然憤怒地爬起來,朝我狂吠幾聲,跳起來想要咬我。情急之下我把雞肉朝它扔過去,它三下五除二把包裝咬碎,大口地吃著雞肉,還對我笑了笑。
我心里亂糟糟的。我想大哭一場,但曉默還沒有來,沒有人會擁抱我。肚子里的兩條金魚攪動幾下,我想我只能回家。我特意繞從村委會大樓走,我要看看那幫人在準備什么行動。我從窗戶看到會議室,村主任正在對一群小伙子訓話,那群小伙子穿著同樣的衣服,曉默的侄兒也在里面。我一陣驚恐,趕緊走開了。
村主任的兒子在路坎下的地里抓螻蛄,他把抓到的螻蛄穿成一串,那串螻蛄動著腳掙扎著,不時還扇動翅膀。村主任的這個兒子十三四歲就輟學了,整天在村里游手好閑的。我想向他打聽有關戰爭和軍隊的事情,便笑著打招呼道:“抓去給你爹下酒嗎?”他說:“是抓給你爹下酒。”說完他大笑起來。我覺得沒趣,繼續往家走去。
我濕淋淋地回到院子里,那群小雞突然從樹葉里飛出來,有二十只左右,顯然是剛學著飛,有些晃來晃去的。我意識到了什么,用手指比作槍,朝小雞射擊,但一點用處都沒有。它們朝我撲過來,我扒開一只,另一只又補上,不停地啄我的臉。我蒙著臉蹲在地上,它們又啄我后腦勺和已掉光頭發的頭頂。我驚叫著說:“你們的母親逝世,只是一個意外,并不是我干的……”但小雞們根本不聽解釋,我感覺我的頭頂已經冒血了。我只得站起來沖出院子,還好那群小雞沒跟上來,又飛回了樹葉中。
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得選擇去阿婆家。阿婆正在屋里立筷子,她頭上的那堆火好像沒有先前旺了。阿婆手一松,三根筷子就立在了半碗清水中,接著她微閉眼睛念念有詞。我在一邊耐心地等待,我想阿婆應該是在向死去多年的丈夫詢問毒蛇的下落吧。有那么一秒鐘,我沖動得張開嘴,想告訴阿婆她的毒蛇死在龍鳳餐館里,但最終還是沒有說出來。
過了一會,筷子往一邊倒去,阿婆趕緊伸手扶住。阿婆拿起筷子,舀半瓢剩飯放進碗中,搖了搖碗,最終把“水飯”倒出門外。然后她似笑非笑地對我說:“看,我說的沒錯吧,你會來找我的。”
我說:“我能有什么辦法?你把我的黑色母雞打死,那群小雞找我報仇,我現在連家都回不了。”
“可憐呀,要是你早的時候把那只黑母雞賠給我就好了。”阿婆把碗和筷子洗凈,放回碗柜里,搖了搖頭上的火,接著說:“說說吧,你現在打算怎么辦?”
“我想請你過去把那群小雞也了結了。”
“可以,但你得告訴我一個秘密。”
我說:“好的,我正好有秘密要告訴你。”
我和阿婆很快回到我家。阿婆所站之處沒下雨,我就站在她旁邊,卻淋著雨。我朝著糖梨樹挑釁地叫一聲,那群小雞又飛出來了。阿婆用手指比作槍,對準飛過來的小雞,一只接一只地射擊。很快那二十來只小雞全掉在地上,村支書家的狗不知從哪冒出來,看到那么多死去的小雞,哈哈大笑地沖過去吃。
“你要告訴我的秘密是什么?”阿婆笑了笑,把耳朵湊過來。
我在內心里糾結一番,還是打算把毒蛇的下落告訴阿婆,我說:“你養的那條毒蛇在龍鳳餐館里,現在還剩這么一截。”我用手比畫了一下。
阿婆突然一跺腳,面部扭曲成一團,想不到她憤怒的表情這么嚇人。她頭上的那堆火瞬間熄滅,但頭發完好無損,只是所站之處又下雨了。阿婆做了一次深呼吸,轉身走出院子。我在鐵門處看,她是朝著龍鳳餐館走去的。
在轉角處,那群穿同樣衣服的小伙子四處搜尋著什么,雨依舊淅瀝地下著,但他們毫不在意。兩輛小車一前一后往村口駛去,我認出前面一輛是村支書家的,后面一輛是剛才在龍鳳餐館吃飯的。小伙子們大叫一聲,朝著小車追去,曉默的侄兒沖在最前頭。村主任披著雨衣,提著什么東西,不慌不忙地向我走來。
待村主任走近后,我發現他手里拿著的是一個大信封。他把信封遞給我,和藹地說:“這是你的學生寄給你的,前兩天就到了,你一直不過去拿。”我接過信封,看到上面有“張三”兩個字,心里一陣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拆開,是一幅照片——我的背影照。我想,等曉默到了,我們就一起把照片貼在墻上。
村主任已經轉身走了,我朝他喊道:“戰爭就要開始了嗎?”
他頭也不回地說:“是呀,你最好不要出門。”
照片已經淋了雨,我趕緊回到屋里,把照片鎖進箱子。我脫掉濕透的衣服褲子,在床上躺下來。雨好像更大了,嘩嘩地打在窗外。肚子里的兩條金魚攪動了幾下,我捂著肚子翻身側著。村支書家的狗估計已經把小雞吃完,它來到我床邊,我懶得理會它。它猛地抖動身體,甩下一攤水,朝我笑了笑,轉身出去了。
曉默,下雨天合適談論什么,世界末日,還是感冒?可惜很多事情我都忘記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感冒過沒有。那就談論即將發生的戰爭吧,等到黑夜來臨人們就會穿上苗族服裝吹著蘆笙跳起舞,在戰爭中等待死亡或者重生。曉默,你侄兒也加入了村里的軍隊,他那神氣的模樣也許會讓人羨慕。如果他在半夜三更戰死沙場,你一定要托夢給你母親,讓她不要再哭泣。
曉默假如我躲在窗前遠眺看到一個矮個子姑娘從田里回來手舉一片荷葉那個姑娘一定就是你曉默你跟路上遇到的人打招呼天色漸漸變暗有很多話還沒說出口戰爭就要開始曉默你快一點吧我在為你感到心急如焚屋檐越來越低我們像是回到遙遠的童年暗黃的電燈下簡單的晚餐一如往常可是戰爭就要開始槍聲突然響起你丟開荷葉朝我跑來驚慌失措的樣子瞬間讓我流下眼淚……
我似乎聽到什么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來。那聲音越來越真切,不一會就變得密密麻麻的了。我爬起來向窗外看去,一群壯大的螻蛄隊伍飛過來,很快就到達了院子。眨眼之間,已經有螻蛄從那扇破窗飛進來,我趕緊下床跑出臥室。屋里的大門沒關,螻蛄已經飛進屋里,一齊朝我撲來。我想跑出門外,但螻蛄越來越多,形成一道門把門框堵住,我根本擠不出去。
我大聲地叫喊著求助,但我的聲音卡在聲帶里傳不出來,連我自己都聽不到。我想到了村主任,他會不會提著網袋跑過來呢?螻蛄已經沾滿我的全身,我想扒開眼前的螻蛄,可連手都抬不起來。我知道還有很多螻蛄繼續朝我撲來,我的整個身體越來越重,最后失去了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