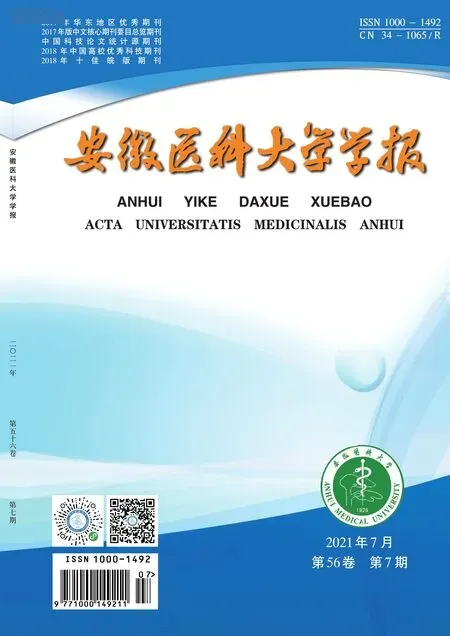多西他賽血液學毒性人群間差異研究進展
傅昌芳,儲宣寧,張 蕾,陳昭琳,韓興華 綜述 潘躍銀 審校
多西他賽是20世紀80年代合成紫杉醇時意外發現的半合成產物,活性測試表現出比紫杉醇更強的結合微管蛋白的能力,最早被批準用于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腺癌,劑量為60~100 mg/m。目前多西他賽已在多種實體瘤中廣泛應用,是最具活性的單藥。
血液學毒性是多西他賽的劑量限制性毒性反應。臨床研究表明,多西他賽嚴重的血液學毒性在亞裔人群(60 mg/m)比在西方人群(75~100 mg/m)發生更頻繁,即使降低給藥劑量,亞裔人群發生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的風險仍高于西方人群。多西他賽在亞裔人群和非亞裔人群之間血液學毒性差異的原因尚不清楚,探索多西他賽血液學毒性差異的機制,為中國腫瘤患者使用多西他賽選擇一個最佳劑量是臨床治療中急需解決的問題。現從臨床研究、藥代動力學、藥物基因組學角度對多西他賽的血液學毒性在亞裔和非亞裔人群間出現差異的機制進行綜述,為多西他賽的安全使用和個體化治療提供參考,為探索多西他賽的精準治療提供方向。
1 臨床研究
Ⅲ期臨床研究考察了多西他賽60、75、100 mg/m3個劑量用于晚期轉移性乳腺癌的療效和安全性。結果表明,隨著多西他賽劑量的增加,腫瘤的緩解率增加分別為22.1%、23.3%和36.0%,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發生率分別為76.4%、83.7%和93.4%,中性粒細胞減少性發熱發生率分別為4.7%、7.4%和14.1%,證明多西他賽的臨床療效與給藥劑量之間存在一定的量效關系,但隨劑量增加血液學毒性發生率也增加。
上述研究是在西方白種人中進行的,為了解亞裔人群用藥資料,日本學者統計了全球以英文和日文發表的128項Ⅱ期和Ⅲ期乳腺癌和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使用多西他賽單藥治療的研究,多西他賽的用藥劑量包括60、66、70、75、100 mg/m,結果顯示多西他賽誘導的中性粒細胞減少在亞裔和非亞裔人群間存在顯著差異,亞裔人群嚴重的血液學毒性風險是非亞裔人群的19倍,多西他賽的劑量是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發生的獨立變量。但統計的亞洲的28項研究1 609例患者均來自日本,多西他賽劑量為70 mg/m或更低,尤其在Ⅲ期研究中多西他賽的劑量多為60 mg/m。
以上研究沒有涉及中國患者的用藥資料。一項針對亞裔人群的研究,入組32例患者分別來自中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其中24例接受多西他賽75 mg/m,8例接受多西他賽100 mg/m,前者17/23發生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后者5/8發生中性粒細胞減少,粒缺伴發熱分別發生在6/23和4/8患者,其中75 mg/m中出現4例死亡。
2 藥代動力學
2
.1 藥時曲線下面積和血漿清除率
研究顯示,多西他賽藥動學差異是導致其療效和毒副反應存在個體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多西他賽主要在肝臟經細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 proteins, CYP)3A4、3A5代謝,其血藥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和血漿清除率(plasma clearance, CL)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相同的給藥劑量下,不同患者體內多西他賽AUC個體差異可達到 3~4倍。白人中多西他賽的平均清除率約為22 L/(h·m),但針對亞裔人群的研究中,多西他賽的平均清除率為(15.3 ± 4.0)L/(h·m),明顯低于白人。在CYP3A4抑制劑酮康唑模擬的多西他賽模型中,中國人比馬來西亞人和印第安人的多西他賽清除率更低,AUC更高。多西他賽藥動學差異與其療效和毒性反應密切相關。文獻報道多西他賽的AUC 有隨化療周期增加而升高的趨勢,測定患者第一周期的AUC即可為后續化療提供重要參考。有學者將多西他賽的AUC劃分為高AUC、常規AUC和低AUC組,發現高AUC組發生中性粒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及貧血的概率大于常規AUC組。根據患者AUC不同來調整個體的給藥劑量,有望達到期望的療效并降低藥物毒副反應。有學者建立多西他賽群體藥動學模型(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PPK),設定多西他賽目標AUC范圍為(2.5~3.7)mg·h/L,基于AUC指導多西他賽個體化用藥劑量比基于體表面積的劑量偏差更小,毒性反應發生風險更低。
2
.2 轉運與分布
血漿中游離多西他賽的比例為4%~10%。多西他賽藥動學研究顯示,血漿中游離多西他賽而不是總的多西他賽的Cmax和AUC,與多西他賽3/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密切相關。多西他賽在血漿中的載體主要是α-1酸性糖蛋白(alpha-1-acid glycoprotein,AAG)、白蛋白和脂蛋白。多西他賽血漿蛋白結合率超過98%,主要是與AAG結合。AAG是一種急性期蛋白,與藥物的結合存在個體差異。血漿AAG對多西他賽清除率有顯著影響,多西他賽與AAG結合率越高,游離多西他賽濃度越低。有報道說明AAG水平是多西他賽血漿蛋白結合出現個體差異的主要決定因素。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乳腺癌患者多西他賽單藥化療后AAG血漿水平,發現不同種族乳腺癌患者血漿AAG水平存在差異,中國人為(182±85)mg/dl,馬來西亞人為(237±94)mg/dl,印度人為(240±83)mg/dl,且低血漿AAG水平與多西他賽的口腔黏膜炎和皮疹顯著發生相關,血漿AAG可作為多西他賽致口腔黏膜炎和皮疹的一個潛在預測生物標志物。基線AAG的水平可以對多西他賽3/4級血液毒性進行初步預測。3 藥物基因組學
多西他賽經腸道轉運體轉運吸收,在肝臟中經肝藥酶代謝消除,而與之相關的腸道轉運體和代謝酶存在較多的基因突變位點,且突變頻率較高,突變導致表達產物的功能發生改變,在不同人群中表現出不同的代謝能力。代謝酶和轉運體的基因多態性也可能是亞裔和非亞裔人群多西他賽血液學毒性差異的機制之一。
3.1 ATP結合轉運蛋白亞家族B1(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 member-1, ABCB1)
ABC轉運蛋白家族包括P-糖蛋白(P-glycoprotein, P-gp)、乳腺癌耐藥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BCRP)等,其是參與多西他賽轉運的主要轉運體。ABCB1存在于腸道和分泌膽汁中,編碼P-gp,影響藥物轉運。ABCB1的基因多態性可能是導致多西他賽血液學毒性差異的原因之一。ABCB1的基因多態性在不同種族發生率不同,其中C1236T CC/CT/TT在亞裔和黑人的發生率分別為13%、46%、41%和76%、22%、2%,與多西他賽的血漿清除率降低顯著相關,C1236T位點發生改變可降低多西他賽的清除率達25%。此外,有報道說明ABCB1 C3435T CC/CT/TT在亞裔和黑人的發生率分別為31%、51%、18%和62%、34%、4%,不同基因型乳腺癌患者在絕經前和絕經后多西他賽AUC有顯著差異,CC型患者多西他賽的AUC低于CT型和TT型;ABCB1 C3435T的TT型患者P-gp表達更低,可降低消除率,維持更高的血藥濃度,2級以上神經毒性的發生率更高。
ABCB1 2677G野生型比突變型患者的神經毒性更低,ABCB1 2677T和T3435T純合突變患者更易發生白細胞減少。ABCC2(MRP2)、SLCO1B3也在多西他賽肝臟轉運中發揮協同作用。ABCC2的rs12762549(P
=0.000 22)和SLCO1B3的 rs11045585(P
=0.000 17)與多西他賽誘導的白細胞減少和中性粒細胞減少有關。3.2 CYP3A基因
CYP3A是肝臟中最豐富的酶系,多數藥物在體內的代謝都通過該酶。CYP3A4和CYP 3A5是多西他賽的主要代謝酶。研究表明CYP3A4和3A5存在明顯的人群間差異,肝藥酶的誘導劑和抑制劑可明顯影響多西他賽的抗腫瘤效果。當多西他賽與CYP3A4抑制劑酮康唑聯用時,多西他賽的清除率會降低49%,通常攜帶CYP3A4活性最低的患者毒性最大。Lepper研究表明,多西他賽在攜帶CYP3A5基因的患者體內的血漿清除率較其他患者高。在報道的多種CYP3A5基因當中,CYP3A5×3是最具功能意義的突變位點,可影響mRNA的剪切,引起蛋白質截斷,導致蛋白質合成的減少,使得個體酶性降低或消失。同時存在CYP3A4×1B和CYP3A5×1A等位基因可致多西他賽清除率下降64%(P
=0.001 5)。CYP39A1的rs7761731被認為是28個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中唯一的與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相關的SNP。多西他賽的藥物基因組學還未完全闡明,還需開展大規模的臨床研究。研究顯示,亞裔人群發生CYP3A4×1B的突變頻率為1%,低于白種人4%~9%;亞裔人群CYP3A5×3C發生突變的頻率為65%~73%,低于白種人86%~95%。CYP3A4×1B和CYP3A5×3C等位基因同時存在,可顯著提高白種人的清除率。
4 總結與展望
多西他賽已經使用近二十年,目前是抗腫瘤治療最重要的一類細胞毒藥物。全球大多數多西他賽的臨床研究都是在西方人群和日本人群中進行,在中國人群進行的多西他賽的藥動學、耐受性和安全性的研究較少。臨床實踐中,盡管大多數亞裔人群采用的都是較低劑量,但嚴重毒性反應的發生率比歐美人群使用標準劑量更高。
臨床研究顯示,藥代動力學參數如AUC、CL,血漿AAG水平,藥物代謝酶和轉運體的基因多態性等均是導致多西他賽血液學毒性出現人群間差異的可能機制。目前已有報道采用AUC、血漿AAG水平對多西他賽3/4級血液毒性進行初步預測,對降低其治療風險具有重要意義,但在中國人群的研究較少。探索多西他賽在中國人群血液學毒性差異的機制,研究中國乳腺癌患者多西他賽的精準治療,遴選多西他賽治療優勢人群,提高療效,減少毒副反應,降低患者經濟負擔,對乳腺癌的防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