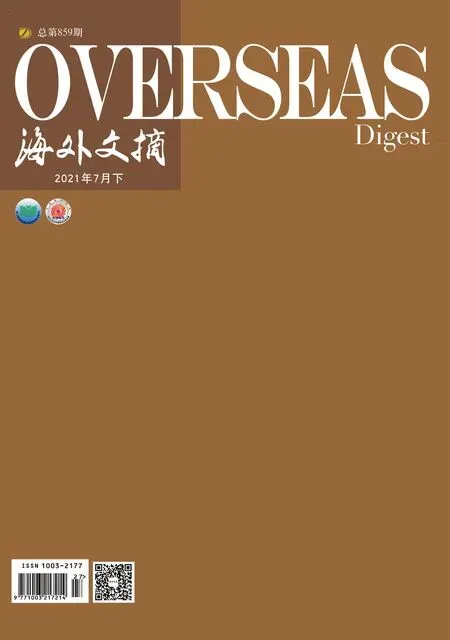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困境與對策
李驍洋
(江蘇省司法警官高等職業學校,江蘇鎮江 212000)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會發展中客觀存在的現象,也是我國無法忽視的問題。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與成年人都存在明顯差異,國際和國內觀點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方面已達成共識,在司法實踐中需要給予未成年人特殊保護。雖然我國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未成年人實體保護、特殊程序等方面有所探索,但尚未跳出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框架,距現代意義上的少年司法仍有距離。因此,審視當前我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困境,積極尋求中國特殊未成年人司法體系建設的出路,成為我國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議題。
1 我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情況
2017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犯罪人數呈現出明顯的變動曲線,先是快速增長,而后逐漸減少。自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我國未成年犯罪人數持續上升,隨著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2007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犯罪人數逐年下降,2016年已降至2.9%,明顯體現出近年來我國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所作工作的成效。
1.1 建立健全未成年司法保護法律法規
我國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中,借鑒外國實踐經驗,參照國際公約,不斷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教育改造的法律法規,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工作提供法律依據。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通過。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過。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施行。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訂,設置未成年人訴訟程序。此外,《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等規定頒布,都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撐。
1.2 探索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實踐工作
第一,刑事審判中確立了多項維護未成年人司法權益的保護機制。就少年法庭這一特殊未成年審判組織來看,少年法庭采用“圓桌式”的審判方式減輕未成年人對審判的恐懼感,提升庭審效果。未成年人刑事審判中也明確了社會調查制度,使法庭審判工作更具客觀性和科學性。
第二,未成年犯處遇措施多元化和輕緩化。我國目前對未成年犯通常使用的矯正模式有監管矯正模式、社區矯正模式、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模式等。未成年人司法強調對未成年犯教育為主的原則,以從輕減輕思想為指導,體現了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人文關懷。
2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困境
2.1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立法工作滯后于現實需求
第一,法律法規碎片化,缺乏系統性。目前,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司法規定主要體現于《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部專門法和刑法第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百條中,除此之外,未成年人犯罪的罪行確定和刑事處罰與成年人處置一致。我國缺乏針對未成年人司法活動的獨立法律體系,囊括實體法、程序法、執行法及其配套規章的法律體系尚未形成。由于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體系不夠完善,未成年犯刑事保護的各項規定和法條也存在缺乏連貫性、系統性、操作性等問題,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實踐受到諸多約束。
第二,法律法規模糊,缺乏確定性。總體來看,我國當前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于未成年犯“從輕減輕”的處罰規定表述模糊,實踐過程中司法人員主觀性較強、自由裁量權較大,造成司法差異性明顯的問題。同時,未成年人保護法主要以原則性和政策性的條文呈現,而缺乏具體性措施的引導,造成當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中“有法難依”等困境。
2.2 未成年人保護處遇機制不健全
第一,強調刑事處罰,罪錯處分缺乏多元性。與我國對未成年犯采用“從輕減輕”的處罰原則。然而,我國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犯罪行為性質都較為惡劣,比如強奸、搶劫、故意殺人等,法定刑較重,幾乎不可能達到緩刑適用標準。因此,雖然我國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中包括責令具結悔過、賠償損失等處理方法,但未成年人非刑罰適用范圍并不寬泛,監管矯正仍然占據核心地位。
第二,非刑罰處置方式不足。近年來,雖然未成年人總體犯罪率降低,但犯罪類型增加,犯罪手段多樣,當前適用未成年人的非刑罰處理方式內容單一,難以應對司法實踐中的客觀需求。對于未成年虞犯的處理方式也較為單調,主要是依靠學校和家庭進行教育,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流于表面,難以真正落實。
2.3 司法機關與社會組織合力不足
第一,司法機關與社會力量間銜接不暢。司法實踐中往往面臨兩難問題,如對于犯罪后受到刑事處罰的未成年學生,即使判處的是非監禁刑,學校也會根據《高等學校管理條例》,對涉罪學生采取開除學籍處分,且拒絕復學。從法理角度,高等學校的管理規定的效力低于未成年人保護法,然而在實踐中,缺少司法部門與社會組織間的協調體系,各部門責任并未在法律框架下明確劃分,不僅未能發揮整體優勢,還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不能達到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預期效果。
第二,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隊伍專業人才不足。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主要力量為司法機關和政府部門,而社會公益組織,如共青團、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對司法實踐參與度并不高,未成年人保護缺乏專業力量。
3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對策
3.1 加強立法工作,系統建立未成年司法保護法律體系
第一,結合我國當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適用的相關法律法規,形成系統的少年法。一方面,明確適用于未成年人的常用罪名和定罪標準。另一方面,也要依據未成年人特殊性,以立法的方式確立符合未成年人保護需求的少年司法訴訟程序。比如,批捕階段采用非羈押考察和心理評估,起訴階段推廣分案審理,執行過程完善輕罪封存等。
第二,對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進行補充完善。深化細化未成年司法保護法規條款,完善法律解釋,根據實踐需求,將家庭、學校和社會組織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實踐中的職責進一步細化,明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具體措施等。此外,針對現實社會中新出現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困境,去除或修改不適用的條文,根據現實需求完善和增添條文,保證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保護中有法可依。
3.2 健全未成年人保護處遇機制
第一,建立健全未成年犯緩刑制度。適當降低緩刑適用條件,不但能夠增加未成年人適用緩刑的可能,也有利于避免未成年犯因監管矯治而出現的犯罪“交叉感染”。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犯教育矯正是一項系統工作,未成年犯的教育矯正并非只取用緩刑就可以一勞永逸,還應設置專門的未成年人緩刑執行機構,為處于緩刑觀察期的未成年人提供思想教育、心理疏導等方面的幫助;同時,加強對處于緩刑期青少年的監管,保障未成年犯的矯正成效。
第二,豐富完善未成年人非刑罰處理方法。我國的未成年人非刑罰處理方法種類單一,探索完善非刑罰處理方法是當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重要舉措,具體可以包括暫緩判決宣告、管教協助、社區服務等。
3.3 探索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力量支持體系
第一,建立司法機關和社會組織合作平臺。通過信息交流平臺,司法機關可以將服務需求公布,社會組織能夠通過平臺主動掌握信息,與司法機關對接,提升司法服務效率和效果;社會組織也可以主動在平臺中標注團隊專業和特長,司法機關在有服務需求時通過平臺比對匹配,及時聯系社會組織,有效實現未成年人的社會幫扶。
第二,建立未成年犯矯正隊伍專業化程度。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中,社會工作需要較強的專業性,如對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矯正、網癮毒癮的戒除,都需要具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員完成,社會工作者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教育學、心理學相關知識。因此,社會幫扶隊伍中也要積極吸引高校相關專業學生、教師、心理學家等,提高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化水平。此外,作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主導力量,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也以通過與社會工作者的合作,提升個人能力,提升工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