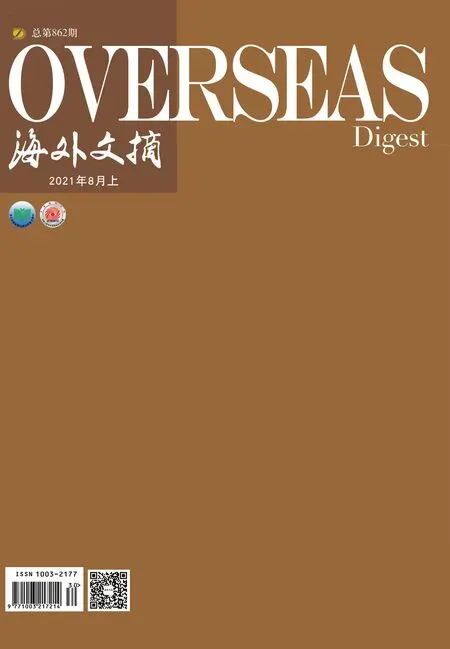資本主義國家“異化”問題研究
林莉
(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144)
1919 年,列寧發表了《論國家》的演講,不僅對孟什維克,更對社會革命黨人進行批判。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討資本主義國家“異化”問題及如何揚棄“異化”,以期對資本主義國家“異化”問題有深入的理解。
1 列寧的國家理論
在歷史風云變幻中,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國家的歷史類型數次演變,列寧從國家的起源為切入點,分析了國家的類型,進而認清了國家的本質,國家理論應運而生。
1.1 國家的起源
在列寧看來,國家機構的特殊在于“一些集團對另一些集團的勞動的占有”,同時,國家消亡的條件是世界上不再有剝削的可能。在人類社會政治國家的演進中,社會主義必然走向共產主義,從國家形態過渡到完全的自治,從政治國家走向非政治國家,由必然王國漸進自由之國度。
1.2 國家的類型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從奴隸制國家到農奴制國家,再到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形式不盡相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社會分工的出現,逐步出現了階級分化。
奴隸制國家最早產生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對立。“奴隸主不僅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并且還占有人”。在農奴制剝削階級的國家,社會的主要矛盾變為農奴和農奴主、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在農奴制社會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主要經濟成分。農奴主對農奴采取勞役或實物地租的剝削方式,將農民被牢牢禁錮在土地上,但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奴隸有所減弱。
資本主義國家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對無產者進行壓榨和剝削。“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充分說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1.3 國家的本質
列寧指出,奴隸制國家的本質“是階級壓迫的機器”。就農奴制國家的本質而言,仍然是統治者利用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采取強硬手段對絕大多數人進行統治。
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資本家通過資本邏輯,掌握資本權力,“對勞動農民群眾和無產工人進行完全控制”。國家的統治形式千差萬別,但資本家把政權玩弄于股掌之中。
“資本用國家的統治形式表現它的力量”。但無論國家形式如何多樣,“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是階級服從的機器”。如果我們不用錢生錢的邏輯,來理解資本主義時代肆意的資本擴張,就覺得行不通。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以太系統普照的光”,并用資本定義現代性邏輯。當今資本處在無定性無定型金融化的時候,缺乏原初馬克思在實體經濟中的本質性規定,但實際上不過是原初資本的極限化演繹。
2 資本主義國家的“異化”問題
異化即主體“自己否定自己”。在資本主義國家,專制政治與人民的“異化”、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異化”,以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相異化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弱點和缺陷所造成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在轉型之后很少提及“異化”這一概念,“異化”是屬于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的范疇。馬克思把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異化”概念,成功改造成為革命的無產階級揭露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的理論武器。
2.1 專制政治與人民相“異化”
從政治層面上看,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專制統治。專制政治的“反人民性”使得統治階級的統治蒙上了暴力色彩。由于異化把社會本身當成思想的真正主體,使得異化對社會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統治者為了麻醉人們,使其處于異化的境地而不自知,這就是專制政治與人民相“異化”,是統治者權力異化的典型表現。
正是統治集團對社會總體的技術控制,對社會進程的合理設計,使得壓迫和剝削日益隱蔽化。社會進入新的階段,統治上層被“管理層、聯合企業、議會所代表”,而非競爭著的企業家。因此,極權政府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而非偶然出現。權力的異化掩蓋了社會剝削的現實,專制政治的存在是對人民的否定,是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在剝削階級專制體制下,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唯有推翻了敵對性的、壓迫性的政治勢力,推翻了這種異己的政治力量,才能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美好愿望,獲得自身的解放和發展。
2.2 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異化”
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異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可避免的產物。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異化,是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以誰為中心的問題,是公共理性與個人任性選擇的問題,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誰占主導的問題,是公與私敵對斗爭的問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具有二元性。公民通過日常的政治生活,表現出了其群體社會性的一面。但在市民生活中,卻“局限于狹隘的私人利益”“脫離共同體”。
對于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核心領導霍克海默來說,包括工人在內的公民,不過是一群通過發表政論文章成為政黨或社會服務組織的成員,經由參加選舉等方式來表現他對現實的興趣。但是這種方式被霍克海默僅僅視為一種“參與”,其結果“充其量只是對這些活動做些心理解釋而已”。
因此,公民的介入也同樣基于對現存世界無條件的接納的層面上,換句話說,大眾首先承認已經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好的,隨后他們再以某種方式去參與社會中要求人們去做的一切。公民作為傳統理論的思想主體,他們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他們的工作因此只是為了理解或闡釋這個世界的合理性。
如果人們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社會蛻變成“人人反對人人”的戰場。在此種情況下,每個社會成員是相互矛盾的統一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單獨個體的市民,其“私人性”“自私性”“非社會性”表現的更為充分。與之相反,其“公共性”“社會性”“無私性”表現的較為少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 “無私性”“社會性”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自私性”“非社會性”卻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2.3 人的政治生活與市民生活相“異化”
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并不是現實的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人所以還會信仰宗教“是由于政治生活和市民社會生活的二元性”。宗教是市民社會精神的升華,人喪失了人的本質,所以才產生宗教幻覺。
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高度繁榮,看似為實現個人自由提供了充分的客觀條件,但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卻未能實現。究其原因,并非客觀條件不充分,而是由于一小部分壟斷資本家人為地阻止自由民主的進一步實現。高度發達水平的經濟與文化,不但沒有被用來為人類謀取福利,反而被統治階級所濫用,成為加強不合理統治的工具。
如此,政治生活“由于事件所迫“宣布自己只是一種手段”,其手段的目的是“通向市民社會生活”。資產階級所倡導的自由,一旦和政治生活發生利益沖突,其在理論上“只是人權的保證而已”。可見,對普通公民來說,權利就不再稱之為權利,所謂的人權只是有限的權利而已。在剝削階級社會,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打上了階級分化的烙印,二者的異化是社會矛盾的根源之一。
3 資本主義國家“異化”的揚棄
列寧認為,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解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異化的問題。建立“自然狀態”下“契約式”國家是一種理想,只有打破了市民社會結構,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的“異化”問題。
3.1 建立“自然狀態”下“契約式”國家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交換平等的契約思想為社會所認可。以自由買賣契約為基礎的社會,要“以自由契約的眼光”考察其與國家的關系。考察人類所處的“自然狀態”,是認識古典社會契約論的一把鑰匙。
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和平互助的理想狀態。在“自然狀態”下,人們按照自然法的規則,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享有上天賦予的各種權利。“但是這種享有很不穩定,有不斷受到別人侵犯的威脅”。當立法者企圖壓制被統治階級時,其便與人民處于敵對的矛盾狀態。人們不得不“尋求上帝的庇護來抵制強暴”。
法蘭克福學派的“領頭羊”霍克海默想通過“考察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或者在“自然”國家里個人的行為方式——以便找到國家形成的原因”。“社會契約是在恐懼和希望中產生的,是在我們的無邊的侵犯欲望和無邊的恐懼之間所達成的一種妥協”。以個人利益為內核的社會契約國家,沒有達到真正的普遍理性,一旦個人利益受到沖擊,社會契約就會瓦解。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貪婪本性,決定了建立“自然狀態”下“契約式”國家只能是一種理想而已。
3.2 打破市民社會結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市民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交往逐步發展起來,市民社會組織是國家大廈的基石,是觀念上層建筑的奠基。資本主義國家“異化”問題產生的根源是社會化大分工,而社會化大分工是由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關系結構所決定的。國家內部的一切爭斗,不過是“虛幻的共同體形式”下的矛盾升級。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所難免,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用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應用黑格爾“異化”概念,分析商品中的人的勞動的二重化,人的勞動的物化,以及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的對立化。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人的勞動的產物。這個社會的一切商品,都是工人勞動的結果。但這個世界卻是工人的對立物,商品反過來加強了資本對工人的統治。
一切商品在被工人制造出來之后,都成了工人不能支配的“客體”,它們甚至以直接違背工人意志的形式統治著工人自己。只有打破了市民社會結構,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的“異化”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教父”盧卡奇以其敏銳的理論洞察力,把“異化”作為關鍵詞,從而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理論實現了結合。盧卡奇認為,主體客體的真正現實的統一在于無產階級自身成為商品。當勞動者成為勞動力,勞動力自身便成為商品,異化的現實使得自身轉變為勞動者自身構筑的社會關系,即物與物構筑的商品關系。勞動者不僅是商品世界的構筑者,同時可能成為它的改變者,當勞動者認識到自身成為商品,并認識商品帶來的人的生存的異化,那么就會產生無產階級意識。
無產階級的主體性決定了無產階級必須以商品化的形式融入客體世界,這就達到了主客體統一。主客體統一,總體性完成,同一性完成。無產階級是個肉身化存在,其能夠認知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就能夠理解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就能改造這個世界,就能對不合理不完美的東西提出意見,最終徹底改變世界。
4 結語
列寧通過分析剝削階級國家的異化問題,指出專制政治“非人民性”“反人民性”的一面,由此引發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而這正是列寧提出的為什么一定要消滅剝削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因。如果國家“不是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布的那些東西”“還是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的機器”,必將由推翻資本權力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把這個機器奪過來”。擺脫政治壓迫,也就擺脫了市民社會精致利己主義的枷鎖。人們尋求政治解放,是從一種普遍的身體和心靈雙重異化中求得解放。
如此,人們不僅能在政治領域,而且在市民社會生活中,自覺克服“自私性”,更多表現“無私性”。專制政治與人民相異化,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異化,公民政治生活與市民生活相異化的問題得以克服。從而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和諧共存的關系,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