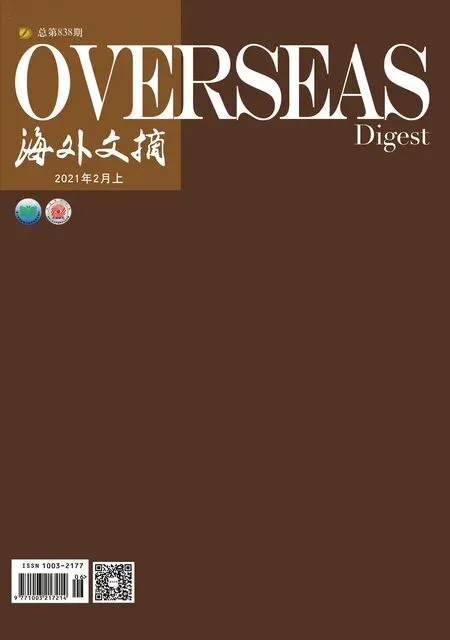《詩經·國風》婚戀詩中的自由戀愛
吳佳瑜
(西北大學,陜西西安 710000)
婚戀,是人類社會中既私人化又大眾化的行為。所謂私人化,即兩情相悅、心心相印,是個人而私密的事情,尤其在情感萌發的初期,如霧中月、水中花,是一種難以言表的心境狀態,《詩經·國風》所歌詠的,就是這種生命中美好相逢的欣悅。婚禮是公開的社會行為,是聯姻雙方通過儀式將個體的情感形式化、規范化的過程。因此,婚禮場面表現的是古人所信仰的陰與陽的合二為一,借著夫婦成禮,達到興家室美教化、合人倫、順自然的終極目的。婚戀的俗與禮,為我們充分展示了埋藏在人類心中的感性與理性。
1 男女的兩情相悅
打開《詩經》,我們最先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國風·周南·關睢》。這首詩描寫了一位男子對一位女子一見鐘情后朝思暮想、患得患失的心態,以及得到愛人應允后欣喜地籌備婚禮、恭迎新娘等行為。此詩雖然歷時千年,卻能夠跨越時空、民族、性別等界限,引起普通人群的強烈共鳴。讀罷掩卷,這位男子輾轉反側、躊躇不安的可愛形象躍然紙上,擔心忐忑并轉憂為喜的情緒起伏也淋漓盡現,他的情感和表達,與今天每位男子遇到心上人時魂牽夢縈、亦喜亦憂的情感是一致的。這說明《詩經》背后是本民族真摯的個性、自然的情感,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靈動的生命的記載。雖然后世的經學、闡釋學將它本來的面目掩蓋了,生發出許多“微言大義”,如將純潔的愛情體驗附庸為君臣關系的象征,但詩中亙古常新的情感共鳴自發地拆毀了道義的高墻,還原《詩經》質樸天然的清新氣息,恢復它原來充溢其中的人性光輝與生命律動。那么,在這首生動的小詩中,展示了上古先民情感生活里怎樣的畫面呢?
首先,在男女戀愛與結婚階段,所遵守的社會規則是不一樣的。男女在婚前的交往比較寬松,可以自由地見面、交流或互贈禮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從小詩起首句可以想見,這位男子在婚前見過自己的心上人,并為她的美好姿態而傾倒。這說明西周時期男女婚前可以自由接觸,還不曾形成森嚴的性別隔離制度。“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在水波里浮動搖曳的荇菜,猶如女子纖細柔美的身姿,接下來的詩句則刻畫了男子彈琴撥瑟以取悅女子的行為,說明兩人在婚前不僅見過,還有一定的交流,他們不僅互相吸引,還擁有共同的愛好情趣相投,心意相通,說明兩人了解程度頗深。那么,上古年輕男女在訂婚之前擁有怎樣的交往自由度?又具備哪些交往模式呢?
《詩經·召南·野有死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婚前男女交往行為的視角: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這首小詩是上古年輕男女戀愛相處情景的生動寫照。詩歌所描寫的場景是年輕男子(應當是一名獵人)用潔白的茅草包裹一頭野鹿,作為禮物送給情竇初開的年輕女子。林中獲得的獵物要用白茅草細細包裹,使其潔凈體面,因為要收下禮物的那位姑娘本身如白玉般清新而純潔。這是一幅逼真的戀愛畫面,它告訴我們,在三千多年前的黃河之濱,男女交往的行為模式與如今沒有什么大的區別,兩情相悅,便互相約會,互贈禮物,柔情蜜意地親昵接觸。但這種自由的戀愛風氣隨著時代的演變受到了遏制,在《詩經》闡釋學中,古典注釋學者自始至終不認可這是一首抒寫戀愛真實場景與心境的詩歌,否認詩中年輕男子熱情濃烈的愛意和女子羞澀含蓄的情態,將此詩附加上“惡其無禮”的罵名,強行扭曲詩意,認為本詩提倡的是男女“禮尚往來”的禮教傳統。詩中男子攜禮物而來,又加以包裹,是遵行古代“苞苴之禮”的遺風,詩的旨意在于寫禮而不在于傳情。但只要用心細讀,讀者應能自然地做出判斷,這是一首情詩而非禮教詩。我們可以感知年輕男女戀愛時陶醉快活的心態,感受到躍然于紙面的青春氣息。這也說明,在西周時期,年輕男女具有相當程度的戀愛自由,可以私下單獨見面、交談,同時互贈禮物的傳統在當時已經開始形成。
2 女子的大膽追求
《詩經·邶風·靜女》同樣是一首描寫年輕男女戀愛場面的詩歌,與《野有死麇》相比,這首詩歌更加委婉細膩,并且惟妙惟肖地刻畫了少女的靈動活潑與男子的憨態可掬: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詩歌題名為“靜女”,但詩中女子并不是心靜如水,而是名靜實動,機靈頑皮。她與相戀的男子約好在城墻角落處見面,但到了時間卻躲起來,遲遲不出現,害得男子搔首踟躕。詩歌表現了年輕女子的幽默可愛與男子的質樸真摯。女子敢于捉弄男子,說明兩人比較熟悉,已經交往了一段時間戀人之間的小小游戲說明兩人相處輕松自在,戀愛中的行為模式表明男女關系的確立是自主選擇,較為自由的。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于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于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詩經·鄭風·溱洧》這首詩歌更為真實地反映了上古社會民間自由戀愛的習俗。溱水與有水是鄭國境內的兩條河流,春季時分,河水上漲,男女相約到河邊游春。這一風俗被《詩經》闡釋學者注意到并注解出來,但同時又被他們批評唾棄:“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洗之行。”春季時分,陽氣發生,萬物復蘇,燕子歸來,是生育季的開端因此男女在春季交往也更為頻繁,可以享有最大程度的交往自由,這一風俗在《周禮·地官·媒氏》中也有相關的記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
春季上已節就是這一民間風俗的節日形式。上已節在漢代以前定為三月上旬的巳日俗稱三月三,節日內容通常有沐浴祓禊、祭祀高謀、會男女等。上巳節以沐浴開始對此,《論語·先進》提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幅春日載歌載舞圖是孔子所憧憬的人生樂事,也是儒生過上已節的主要形式,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追求的儒士自動回避了該節日的另外一項重大內涵,即自由的性行為與生育崇拜。上已時節,民間有祭祀高謀的禮俗,高襟的象征物是燕子,春日時分,燕子回歸筑巢孵卵,象征著新-輪生命的孕育與誕生。《禮記·月令》:“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謀,天子親往。”人們對高襟的祭祀代表著對旺盛生命力與生殖能力的追求,對子孫后代繁衍昌盛的渴望因此,男女不受禮俗約束的自由結合,成為本時期可以理解并值得提倡的事情。從《溱洧》這首詩歌中,我們可以發現,與前面的《野有死麇》《靜女》相比,該詩中的男女交往行為要更為開放大膽:在河水漸漲的春日,男女各自佩戴香蘭,慶祝上已節。女子問男子是否要去觀看洧水?男子本來已經去過,但覺得有家人相伴,不妨再去,欣然答應,二人在水邊嬉戲,感到非常快樂。詩歌的講述點到為止,但結合上巳節有到河邊沐浴的傳統,那么女子邀請男子到河邊去玩,便是非常大膽的挑逗行為了。因此,這首詩歌被詩經闡釋學者定義為“淫”也是不難理解的。正是這樣開放的交往模式,使我們窺見上古社會人們生機勃勃、自由自在的精神狀態與健康人性的社會環境。
3 禮樂約束下自由戀愛的被壓抑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戀愛的模式在《詩經》中并不是比比皆是的,這種愛情交往方式在象征民間聲音的“十五國風”中比較普遍,但在文士創作的《小雅》與貴族宗廟祭祀清歌的“三頌”(《周頌》《魯頌》與《商頌》)中則比較少見。文人雅士、上層貴族的婚戀生活,顯然擁有與民間不同的禮儀形式,在“雅”“頌”內很難再尋找到男女你情我愿、各隨己意、自由交往的行為記載與描寫。這進一步說明“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至春秋的真實社會形態,禮與俗在上古社會已涇渭分明。民俗是大眾化、世俗化的,作為民族深層心理潛意識沉淀下來;禮儀是高雅化的、小眾化的,作為民族精英意識形態與文化表征形成公開符號與標識。
4 結語
愛情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詩經》作為中國文學的濫觴,婚戀詩是《詩經》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十五國風”中,民間男女的自由愛情如今讀來仍然令人心向往之,《關雎》中男女在河洲之中你來我往的相互愛慕、《野有死麕》中男子對女子的贈禮以及《靜女》和《溱洧》中女子對男子的大膽追求和邀請,自由的戀歌并不是后世所說的“淫詩”,而最能反映周代婚戀習俗的藝術作品,讓我們得以窺見千年之前的民間男女婚戀時真實的圖景,為當今對于上古時代社會背景和婚戀習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生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