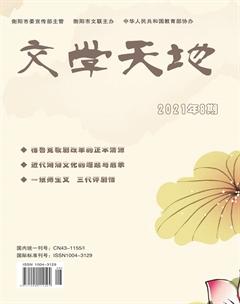紹劇音樂之【彈撥篇】
阮偉惠
紹劇,原名“紹興亂彈”,是“西秦腔”南傳于浙江的一支,興發于清康,乾年間的浙東紹興。歷經近四百年傳承,在藝人們長期實踐中,走上了一條本土化的道路。,并成為了紹興等地社日,廟會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在【社戲】等作品中都有鮮明,生動的描述。并把“紹興亂彈”(紹劇)的演劇風格歸納為“大叫”,“大跳”與“大敲”。紹劇以其慷慨激越的音樂唱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紹劇的后場伴奏隨著唱腔音樂的發展,由最初“尺調亂彈階段”的五人(司鼓,正吹,副吹,斗鈸,小鑼)發展至“正宮調亂彈階段”的六人,即“上三把”,(司鼓,正吹,弦位),下三把(副吹,斗鈸,小鑼)。
傳統的紹劇主奏樂器為板胡,琴桿短而琴弦粗,硬弓拉緊,清脆響亮。輔助彈撥樂器“斗子”又名“金剛腿”,挖木為瓢,蒙桐板有品。(C~G”定弦,其中二弦并彈,音色既亮而旺。隨著演奏的情感化.器樂化的演進,戲曲音樂的改革帶動了創作音樂的興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紹劇伴奏中引入了琵琶,阮,柳琴,楊琴等彈撥樂,增加了演奏的表現力,與“斗子”,“弦子”等傳統器樂相得益彰。
紹劇的基本唱調;【三五七】,【二凡】各有不同的藝術個性。【三五七】優美抒情,【二凡】慷慨激越,兩者相互對比,相互成套,稱之為【三五七.二凡】套。
以【二凡】為例,紹劇彈撥樂在【二凡】伴奏中,除托腔外,其伴奏旋律區別甚大,以旋律上下行的反差,見縫插針,穿針引線,努力彰顯自己的個性。紹劇【二凡】是以“正伴散唱”為演奏規矩。由于各彈撥樂器的性能和定弦的不同而形成的指法不同所帶來的“支聲復調”,是【二凡】伴奏中的主要處理手法。【二凡】中的彈撥演奏是以“彈反板”為節奏型,以“正打”的后半拍為發力點,使【二凡】似一個“流水”型骨架,一反彈撥樂器先“彈”后“挑”的基本規律,以正拍“挑”反拍“彈”的方式,并刻意地增強反拍中“彈的力度”,形成“乙張乙張”之聲,其聲效似上了發條的鐘表,給人以穩定的節奏感和強勁的跳躍感。唱時,板胡依據運腔進行伴托,唯有彈撥樂始終在正常的節奏中“挑”“彈”。弱拍強彈,強拍弱挑,難怪老藝人們俗稱其謂“彈反板”。如【中板二凡】每分鐘可達180拍以上的速度,而【快二凡】更是達到了每分鐘240拍以上,彈撥演奏員需要有過硬的基本功才能達到。一般來講,“彈”比“挑”音效更強烈,音色更飽滿,常用在句首,強拍,強音處。但紹劇【二凡】演奏的“彈”“挑”卻反其道行之,“彈”不在強拍,而在兩個八分音符的后半拍處,“挑”卻在強拍,強弱顛倒,形成“乙張乙張”(挑彈挑彈)之勢,特具其魅力。這種“彈挑法”,不但在戲曲傳統音樂中甚為罕見,就是在器樂曲中也很難找到,這是“西秦腔”古老彈撥樂演奏風格留存于紹劇的遺音。
在“過門”以及唱句“落腔”的演奏中,彈撥用“掃弦”給予以正拍上的刻意強調,使【二凡】的演奏增加旋律的跳躍感。強調各器樂演奏時的個性發揮,同時又相互彌補,相互協調,使整個伴奏流暢。“緊打慢唱”“緊唱散伴”。彈撥的旋律與板胡的旋律變化中有統一,統一中有變化,充分體現個性與共性的完美體現。二者又一次形成了“支聲復調”,使旋律更加錯綜有致,飽滿豐富。彈撥樂在伴奏【二凡】的過門時,緊緊伴隨著司鼓的板速,幫助和輔助板胡進行“正伴”,它的節奏型始終和板速一致,從而使唱散的即興托腔有了強勁的板拍壓陣。板胡的運弓似肉,彈撥樂的彈挑如骨,二者形成一種動與靜,強與弱,疏與密的對比。和【二凡】演唱中的各種“海底翻”嚴絲合縫,骨肉相依,聽是自由,實有規范,使紹劇慷慨激越之風格得到淋漓酣暢的展現。
以【三五七】為例,【三五七】以【太平三五七】為主干唱詞,以三言,五言為上句,七言為下句,構成“三五七言”唱辭文體而命名的。伴奏以笛子為主,弦樂為輔。據記載,早期只伴以彈撥樂,后來才加上板胡等拉弦樂器。【三五七】是4/4拍型,旋律悠揚,舒緩。紹劇彈撥樂器既不能同笛子,又不宜跟拉弦樂器,不然就會失去個性,例如琵琶:起頭和過門的旋律應突出琵琶音色清脆,飽滿的特點,用一弦高把位進行彈奏,并突出各個“符點”的“輪”。達到明亮,清脆。為唱句的起.接.營造發力的氣口。在唱句的進行中,可以借鑒鋼琴,吉他的伴奏方法,在旋律中按照【三五七】的調式進行分解和弦的伴奏。
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逐步演化,紹劇彈撥樂已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之作用,它的特殊演奏方式與紹劇張揚的藝術個性極其吻合。我們將在實踐中探索如何把握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進取,緊跟戲曲音樂“現代化”腳步,更需要吸取各種音樂元素,結合紹劇唱腔特點,在共性中尋找個性,使彈撥樂在紹劇音樂中演奏出更加華美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