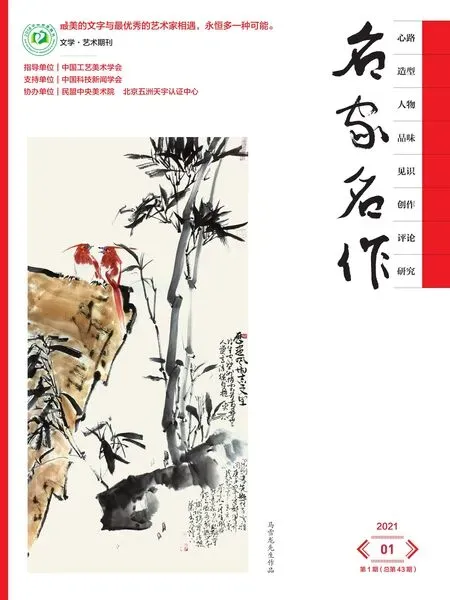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幽靈之家》的女性意識賞析
付彩艷
一、引言
《幽靈之家》是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的代表作,這部帶有女性意識的作品沿襲了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傳統,被譽為智利版的《百年孤獨》,阿連德也因此被稱為“穿裙子的馬爾克斯”。《幽靈之家》集魔幻現實主義、女性主義以及社會政治于一體,小說開始于一個小女孩的筆記,其中穿插著她的丈夫以及外孫女的敘述,用一些碎片式的語言與斷裂的情節向人們展示了20 世紀的智利社會。女作家借助對歷史的重現,完成了全書中最為重要的對新時代女性意識轉變的描寫,扭轉了人們對殖民時期智利女性的固有看法,在她看來這一階段的女性是新時代女性的典范。
二、女性意識的覺醒
1.女性意識的覺醒含義
女性意識是指女性作為人的本身對自身存在價值的領悟以及體驗。在傳統的男權社會中,主要外化表現為女性對男性社會舊觀念的反抗,對男權統治的質疑與顛覆;另一個表現是女性對自己的生存狀況的關注,開始對女性心理情感進行審視并有對生命體驗表達的愿望。
女性意識的覺醒主要有三個層面:首先是社會層面上的覺醒,基于社會階級結構研究女性對壓迫的反抗;其次是自然層面,立足于女性的生理特點,研究女性不同于男性方面的體驗;最后一個層面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探尋女性精神文化方面的獨特處境,并以女性的視角對男權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構建的文化體系進行研究。
2.女性重新獲取身體的主權
作為人的物質組成的身體,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社會形象的外顯。在男權社會的統治下,女性身體主權的獨立完整性是被破壞了的,她們依附于男性,以男性為主體,男性同樣將女性視為客體,是自己財產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女性若想追尋自我,應充分關注自己的身體,且只有在擁有身體自主權的時候,才能真正地尋回自我;而女性唯有摒棄男性的觀點,掌握身體的主導權,男權也就無法繼續肆意約束和擺布女性了。
在《幽靈之家》中,被丈夫暴力威脅數次之后的克拉臘,拒絕丈夫埃斯特萬進入她的房間與其同床共枕。這表明克拉臘開始大膽尋求身體的自主權,盡管這種追尋在壓迫下帶有一定的被動性,但是從這些被動的自覺中,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她們開始敢于向占有她們身體主權的男性發出挑戰。之后克拉臘又在埃斯特萬受傷后,掌管起三星莊園的一切,成為家族的主心骨。改變了原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也改變了婚姻中的權利關系,女性不再是被支配者,她們也有發言權,也有主體性。對于這些開始覺醒的女性而言,她們已經用行動對傳統的性別觀念提出了質疑,用自己的方式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爭取經濟上的獨立,進而獲取在地位上與男性的平等,將自己的權利奪回來。
3.女性性意識的覺醒
女性的覺醒的意識讓其開始關注自我欲望,男權統治下女性的欲望被剝奪,女性順從于男性的欲望。作者阿連德很早開始就關注兩性與愛情的關系,關注女性自我欲望的產生和性意識的反轉,自然地書寫女性的情欲,愛與精神思想并不分離,并認為這是一種對愛的傳達,透過歷史故事討論女性性意識的萌生與崛起,嘗試顛覆男權文化。
克拉臘曾對她的丈夫說:“因為夫妻關系的惡化,我們無話可說,當然也就不能再同床共枕。”阿連德用這句話向讀者展示了克拉臘性意識的覺醒,克拉臘厭惡沒有愛的性,對于克拉臘而言,情欲更需要精神上的契合。女性已不愿再做男性欲望的承受者,她們努力嘗試追求身體與精神上的結合點。
三、《幽靈之家》中女性的沉默與反抗
在《幽靈之家》中,作者伊莎貝爾·阿連德顛覆了沉默的表層意義。她筆下的新時代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逐漸覺醒,用沉默的方式去反抗,并彰顯出自我的價值,不僅人物形象更為豐富飽滿,同時促進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可稱之為一種積極的敘事策略。作者阿連德在小說中塑造了三位女主人公——克拉臘、布蘭卡和阿爾芭,阿連德正是從女性的視角重新詮釋了她們的反抗事跡,向讀者呈現出了不屈服于男性主宰并具有獨立意識的新時代女性。
1.克拉臘追求自我、顛覆權威式的沉默
克拉臘本是個性情柔弱的女子,面對殘暴的丈夫,她卻并未顯示出軟弱和妥協的一面,而是選擇用緘默來向其抗爭,當她的丈夫以她生養了個傷風敗俗的女兒為由對她和女兒施以暴力時,克拉臘毅然決然地走出了三星莊園,她的這一舉動,是對家庭暴力的有力反抗。出走的克拉臘來到街角的院落,并對這里重新整修,使這個院落成為兩性之間分離的象征,成為埃斯特萬家族沒落的象征,成為克拉臘這個捍衛獨立的勝利者的象征。
2.布蘭卡追求完美愛情式的沉默
小說中的布蘭卡是一個愛情的追尋者,她始終認為永恒的愛情才是幸福的人生。在父親埃斯特萬嚴酷的拷問下,她選擇用沉默來保護自己的愛人和愛情,就算是在父親的強壓下她被迫與法國伯爵薩蒂尼結婚,她的內心深處依然沒有屈服過,無休止地刺繡與制作各種陶器,用這種沉默的方式無聲地抗爭著,看著陶器作坊里那些“耶穌誕生模型以及一些想象出來的怪物,或許只有這樣,她的內心才能平靜下來”,“她的天性是對愛情的專一,唯一愛的人即是佩德羅第三,正是這種對完美愛情的追尋使她脫離那凄慘的命運”。
20 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弗吉尼亞·伍爾芙在其著作《一間自己的屋子》中寫道:“女性應當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個安放身體和心靈的空間。”布蘭卡意識的覺醒表現在她在自我內心構建了一個只歸屬于自己的世界,她所追尋的是內心深處的自由與獨立,是對全新生活的重新構建。
3.阿爾芭式尋求真我的深刻思考
女性借助于沉默重新審視內心,獲得心靈的啟蒙,并邁向美好未來。最開始的阿爾芭因不堪埃斯特萬·加爾西的欺凌,曾經不吃不喝等待死神,但在克拉臘的勸說下,她拿起紙與筆記錄下這周遭的一切,那個曾經受到非人折磨的阿爾芭,勇敢地面對現實世界,對未來充滿希望,等待美好時光的到來。她用自己獨特的沉默的方式向埃斯特萬·加爾西宣戰,捍衛屬于自己的女性的尊嚴,并將女性寫作由對社會的控訴深化為對自我的內省與解構,重塑了女性主體。
在阿連德的筆下,女性的沉默成為一種敘事技巧。沉默,不代表屈服妥協,更不是委曲求全,恰恰相反,沉默源自女性的性格本質,成為反抗男權社會壓迫的尖銳武器,它保衛了女性對自我的追求、對愛情的捍衛以及對真我的深刻思考。
四、《幽靈之家》中女性意識彰顯的時代意蘊
通過對小說文本的深入的探討不難看出,女性的自主意識是在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下逐漸復蘇與覺醒的,阿連德通過對克拉臘、布蘭卡與阿爾芭這三位新女性家族史的描述,呈現出一種與男性歷史截然不同的女性歷史:她們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和情欲,不再甘于附屬和屈從的地位,尋求屬于自我的主導權;她們不再充當生育兒女的工具,她們的價值也不僅僅是用來傳宗接代,而是構建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正是她們女性意識的覺醒開始動搖男權的主宰地位。對于《幽靈之家》的書寫,阿連德采用了正面的寫作取向,謳歌了那些擁有覺醒意識的新時代女性,并對女性的自主性持肯定態度,她試圖通過重塑女性自主的世界,向人們傳遞傳統的男權社會已然被動搖的信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
1.阿連德在《幽靈之家》中對女性自我覺醒付出的努力給予充分的肯定
當時的拉丁美洲,是在傳統的男權社會的統治之下,當受壓迫的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她們試圖拿回自己的主權,正是她們堅持不懈的努力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不論是擺脫男性利用情欲或者婚姻關系對她們進行的束縛,還是通過掌控家庭主導權對男性進行反抗、建立自己的威信與地位,這些都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一種外顯。或許這種個體的努力并不是整個拉丁美洲的集體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她們依然有了自我意識最初的覺醒和萌芽,并且這種覺醒已經對傳統的男權社會產生了撼動的影響。
2.阿連德在《幽靈之家》中使用了大量自創的女性語言
她對文字符號和文學意象進行自由的搭配組合,形成了新的文學語言,向讀者重現了那個千瘡百孔的智利社會;她的言語具有繁復之美,對愛情的描述更是讓人糾結萬分;雖然看似是對故事做的表面上的記錄,是在具體和零散之間的穿梭,但是在這簡單記錄下暗自涌動的情感卻感人至深。阿連德是在摸索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言語表達風格,是只有在女性自我的生活體驗中才能獲取的,與男性作家的敘述方式截然不同。
3.阿連德創作《幽靈之家》彰顯了解構傳統男性男權實驗精神
在那個時代里,話語權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話語權是建立在學會發聲、打破沉默、表述自己以及建構自我一系列的基礎之上。《幽靈之家》既是對女性主體的重新建構,亦是對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她向世界提出了最強有力的質疑。在阿連德的筆下,文學不僅是杜撰歷史故事,更是借助于想象和情感傳達出對于真理的尋求。
傳統社會中,女性對受到的不公和壓迫往往持一種隱忍、逆來順受的態度,賢妻良母式的教化思想深深影響了女性自我意識的發展,她們被禁錮在男性強勢、女性弱勢的傳統思維中,自認為不及男性,也就失去了自我覺醒的機會。然而,阿連德筆下的女性卻是不斷突破舊傳統的新女性,她們的努力和付出,幫助她們尋找到新生命,在企圖重建的憧憬中,為女性議題暗示了下一個里程碑。
五、小結
《幽靈之家》中埃斯特萬家族的克拉臘、布蘭卡和阿爾芭這三位女性,皆是阿連德精心塑造出的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智利女性形象,顛覆了傳統女性的附屬與屈服的地位。她們基于女性自我主體的生命感受,為構建自我主體性付出了努力,她們崇尚自由,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和愛欲,尋求屬于自我的主導權,她們的價值不再僅是用來傳宗接代,而是構建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實現自我價值,正是她們女性意識的覺醒開始動搖了男權的主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