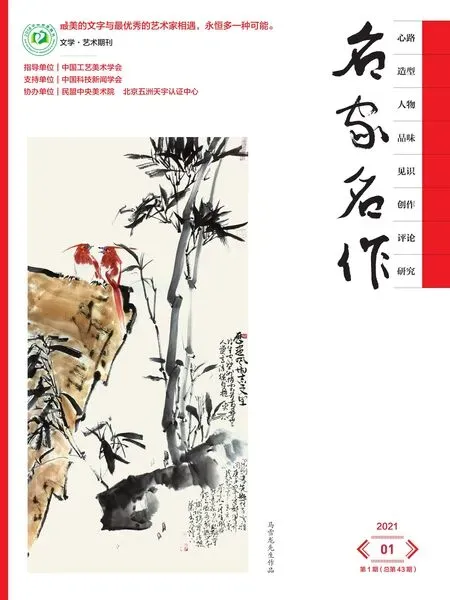從荒寒詩看陸游對柳宗元《江雪》的接受
蒲小莉
《江雪》是柳宗元的詩歌名篇之一,作于謫居永州期間,其時作者仕途坎坷,政治前途茫然。此詩短小精悍,押仄韻,描繪出了銀裝素裹、萬籟寂靜、寒江獨釣的畫面,用字質樸而意趣深冷幽遠。學者陶文鵬認為:“宋代詩人喜愛并擅長營造荒寒意境,大量荒寒詩寫于貶謫途中或謫居之地。”早在唐代,《江雪》就已如此,全詩雖無“荒寒”二字,卻契合宋代荒寒詩的意境。宋荒寒詩中所蘊含的淡泊、閑逸之風,也正如蘇軾對柳詩風格的評價:“發纖秾于簡古, 寄至味于淡泊。”。
陸游亦喜愛狀荒涼、頹敗之景,營造荒寒意境。據陶文鵬統計,《全宋詩》中有119 首詩作含有形容詞“荒寒”,其中陸游的詩占16 首,其“且謀蓑笠釣荒寒”(《舟行魯墟梅市之間偶賦》)句似從《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句化出。“南宋中興詩人對柳宗元詩歌的接受,是柳宗元詩歌接受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陸游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據此可推測,陸游的荒寒詩應受柳宗元《江雪》的影響。下文將結合具體詩歌作品,分析陸游的荒寒詩對《江雪》的接受。
一、“空”“靜”的正面與側面描寫
柳宗元《江雪》描繪了一個雪白無垠、寂靜空無、幽靜寒冷的世界,整體環境既空且靜。《江雪》的“空”“靜”,首先體現為正面描寫。“千山”“萬徑”構建了一個廣闊空間,“鳥飛絕”“人蹤滅”過濾俗世的喧囂、擁擠感,“孤舟”“獨釣”限定了僅有釣者一人,直接正面描繪,體現了“空”與“靜”。其次,柳宗元還通過側面描寫“空”與“靜”。其所構建的廣闊空間中,人物僅有釣者,將渺小的個人置于“千山”“萬徑”的大空間中,渺小與廣闊形成了對比,使本就廣闊的空間顯得更廣袤,空曠、幽靜,寒冷感更深一層。
荒寒詩以荒涼、頹敗、凄寒之景為主要描摹對象,詩歌環境也有“空”“靜”的特點。陸游的16 首荒寒詩中,“空”“靜”營造技巧與柳詩《江雪》相同。有7 首詩直接以字詞描寫環境“空”“靜”,分別是:“小壘荒寒外,高齋寂寞中”(《小壘》),描摹環境荒寒, “寂寞”寫書齋寂靜;“荒寒孤店雨,零亂野祠云”(《娥江市》),“孤”修飾旅店,人煙稀少,屋舍零星,只見零亂的祠廟和烏云;“雁過荒寒外,燈殘寂寞中”(《枕上》),渲染詩人身處野外,大雁飛過,孤燈燃盡,寂寞涌上心頭;“山澤荒寒外,門庭寂寞中”(《遣懷二首》(其一),敘寫荒寒野外漲水,詩人在門庭之內孤獨寂寞;“殘聲凄斷蟬移樹,孤影荒寒鵲繞枝”(《村東晚眺二首》(其一),描述詩人晚年孤身村頭,側重寒冷,景色荒殘,鳥鵲孤獨;“孤帆滅沒三湘曉,野店荒寒二華秋”(《醉題》),敘述詩人的羈旅行役孤獨,郊外荒涼寒冷與小店的冷落相互襯托;“春耕秋釣舊家風,門巷荒寒屋壁空”(《家風》),春耕、秋釣等野外勞作是多數農家延續的傳統,這個時節人們都在外勞作,門外巷子里、屋中都無人,顯得荒涼空曠。
以上七句詩中,三句含 “寂寞”一詞,跟荒涼、孤寂的意象組合,營造了孤獨、衰敗、寂靜的意象氛圍;三句含有“孤”字,其中“孤店雨”“孤帆滅沒”都是寫旅途的孤苦與荒寒,營造了悲涼的氛圍,而“孤影荒寒”寫出了秋夜天氣的寒涼,表現了詩人晚年的孤寂冷落,是詩人的內心感受;一句用了“空”字,修飾“門巷”“屋”空曠,環境寂靜。以上詩句正面描寫所處場域人煙稀少,營造了清靜、空曠的環境。
空間的空曠感,以側面描寫為主,借助詩句中的意象描寫體現出來,如“小壘荒寒”“高齋寂寞”“山澤荒寒”等環境描寫,擴大讀者視角,對空間有延伸、擴大作用,并在空闊的場域中用“孤”“空”“寂寞”等形容詞限定人或物的稀少,統一形成大空間與人物寥寥的對比,從而賦予環境空曠、安靜感。可知,陸游寫“空”“靜”受《江雪》影響。
二、巧借天氣寫“寒”
《江雪》的清峻寒冷之感,發于對雪天自然環境的描寫,契合了荒寒詩之“寒”。無獨有偶,陸游荒寒詩也通過天氣描寫來營造“寒”,如《小舟白竹篷蓋保長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戲作二首》(其二)詩:雪云無際暗長空,小市孤村禹廟東。一段荒寒端可畫,白篷籠底白頭翁。此詩描寫雪天天色已暗的孤村,“白篷籠”為被雪覆蓋的斗篷。雪天,孤村道路上行人稀少,僅有一個披斗篷的白發老人冒雪出行。三、四句與《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有異曲同工之妙,都不直接描寫下雪。《江雪》通過“鳥飛絕”“人蹤滅”側面表現雪大,畫出一幅寒江獨釣雪景圖;陸游借“白篷籠”表現雪大,用“白篷籠底白頭翁”畫出小村荒寒圖。披斗篷的白發老翁形象應是對“蓑笠翁”的借鑒,冰天雪地中僅有一人,“畫”出村莊的空曠、荒涼。此詩中,“荒寒”之“寒”通過雪天的環境描寫生發出來,且人物形象的設置也可見《江雪》的影子。
除繼承柳詩對雪天的描寫,陸游還描寫雨天環境寫“寒”。陸游詩中多次出現“雨”意象,如“萬里冰河入夢來,五更風雨四山秋”“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等。不同的“雨”所表達的感情也不同,“分析陸游的雨意象詩作,可以看出詩人不同時期的創作風格,少年工巧,中年宏肆,晚年平淡”。陸詩中的 “雨”意象,除了表現愛國情懷,還借用雨來寫荒寒詩之“寒”。如《秋夕書事二首》:“點點秋燈晚,翻翻宿鳥還。雨添羈枕睡,書伴小窗閑。”秋夜,屋里燈光微弱,鳥兒紛紛歸巢,羈旅中的詩人放下窗邊的書,聽著秋雨淅瀝入眠。秋雨在古詩中總是承載著羈旅愁思,“羈枕”表明陸游在羈旅之中,因此秋雨也就寄托了更復雜的感情。冷清的房間內,國家尚未統一的愁思爬上詩人心頭,此時窗外陣陣秋雨不僅使天氣更冷,令詩人為國憂愁的心也更寒涼。
陸游承襲了柳宗元《江雪》以自然天氣寫“寒”,他創新了表現“寒”的技巧,在荒寒詩中,他運用擅長的“雨”意象寫“寒”,結合自己的情感、境遇,使寒冷感更深入。
三、陸游荒寒詩對《江雪》寂靜冷清、淡泊閑遠意境的接受
《江雪》描繪的寒江獨釣雪景圖,創造了寂靜的藝術意境。此外,垂釣者——“蓑笠翁”,作為中國古代的漁父形象,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其所代表的閑適、孤傲、高古、隱逸等特點成了中國古代文人所向往的隱逸者的形象。《江雪》中的漁翁形象,營造出了本詩閑適淡泊的藝術意境。
柳宗元好用凄冷意味的字詞描寫寂靜荒冷、色彩幽暗之景,《江雪》是其中的代表。陸游荒寒詩多寫秋冬之景,常出現夕陽、殘月、秋雨、雪天、荒村、野寺、孤店、江河等場景,多為荒涼、蕭索、空曠、清冷之景,所創造的意境繼承了《江雪》詩的寂靜、清幽。如陸游的《村東晚眺二首》(其一):“藤杖穿云秋望處,葛衣沾露夜歸時。殘聲凄斷蟬移樹,孤影荒寒鵲繞枝。”詩句中用了令人感覺冷清的字詞,“露”“夜”“殘聲”“凄”“孤影”“荒寒”等,時間為秋天的傍晚,“孤影”說明只有一人,使得環境更寂靜、凄冷。陸游的荒寒詩不少都以寂靜、冷清意境為主,如“山澤荒寒外,門庭寂寞中”(《遣懷》)、“橋橫風柳荒寒外,月墮煙鐘縹渺邊”(《梅市》)、“幽居端似玉川生,茅屋支撐不更營”(《衡門晚眺》)、“春耕秋釣舊家風,門巷荒寒屋壁空”(《家風》)、“荒寒過吳宮,摧剝觀禹窆”(《遠游二十韻》)等。這些詩句描寫的環境荒涼、蕭瑟、寂靜,人煙稀少,情感孤寂,可知陸游荒寒詩與《江雪》冷清孤寂的藝術意境吻合。
陸游荒寒詩中亦有淡泊閑適的意境。柳宗元與陸游的仕途都不順暢,柳宗元謫居期間創作了大量山水散文與山水詩。陸游晚年歸隱田園,他也是“南宋退居型士大夫”。二人境遇類似,易形成情感共鳴。因此陸游的荒寒詩的淡泊意境除了受陶淵明影響外也受到了柳詩影響。
柳詩《江雪》淡泊、閑遠的意境,主要是漁父形象的垂釣者體現出來的,表達了柳宗元與世無爭,不愿卷入政治斗爭,保持自己的高潔品德,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陸游學習《江雪》用漁翁創造淡泊閑遠意境的手法,也借用漁翁、僧侶的形象營造淡泊意境,最典型的一首是《書南堂壁二首》(其二):荒寒淺村步,隱翳小茅茨。偶逐漁樵住,都忘歲月移。閑惟接僧話,老始愛陶詩。耆齒猶須幾,羸然敢自期。這首詩寫陸游的隱居生活,詩中同時出現漁父、樵夫、僧人、陶淵明這幾個人物形象,“漁樵”在中國古代有隱居者的含義,僧人更是禪意、淡泊志趣的象征。陶淵明是田園詩派的始祖,被鐘嶸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歌中的四個人物意象都指向隱居、閑適、淡然,抒發了陸游對當下隱居生活的喜愛與悠然自得。此詩通過四個隱逸者形象以及陸游閑適的隱居生活,營造出了本詩淡泊、閑遠的意境。
蘇軾把柳詩與陶詩一同列為平淡詩風的代表,陸游在接受柳詩時也接受了《江雪》寂靜冷清、淡泊閑遠的藝術意境。在冷感字詞的使用、凄冷環境的描寫上,陸游學習了柳宗元,且《書南堂壁二首》(其二)一詩中四個人物形象的描寫,有對《江雪》模仿的痕跡,可以斷定他的荒寒詩也接受了《江雪》的意境。
四、陸游荒寒詩接受《江雪》的原因探究
上文論證了陸游荒寒詩受到《江雪》影響,下面,將探析陸游荒寒詩高度接受《江雪》的原因。
首先,柳宗元、陸游相似的人生遭際觸發情感上的共鳴。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后遭貶謫,失意與痛苦往往通過文學創作抒發,《江雪》創作于詩人政治失敗貶謫永州之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寂靜、空曠環境,反映了詩人被貶謫后內心的孤寂,柳宗元塑造了一個高潔、獨立、自由、淡泊的漁翁形象,表達自己內心對自由、閑適、淡泊生活的向往。愛國詩人陸游生于兩宋之交,長于南宋,此時國家危難、民族矛盾、家庭流離等都對陸游的人生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陸游荒寒詩多作于晚年,在《江雪》中,他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閑遠淡泊,柳宗元當時的處境也觸發陸游對早年仕途不順的回憶與坎坷的人生經歷,相似的遭際引起了陸游情感上的共鳴,因此其荒寒詩高度接受了《江雪》中的孤寂、閑遠淡泊意境。
其次,陸游荒寒詩的特質與《江雪》高度吻合。宋朝的荒寒詩喜歡描繪荒涼、蕭瑟景色,寫孤寂之情,在宋朝追求“荒寒”審美意趣的潮流下,本就受柳宗元詩歌影響的他在《江雪》中看到了荒寒詩的影子。《江雪》符合荒寒特質,環境凄冷、寒涼,用詞、意境都很契合荒寒詩所狀之景。荒寒詩的“荒”與“寒”,在《江雪》中都很好地體現了出來,“荒”不僅指環境荒蕪,還包含空間的空曠感,柳宗元用“千山”“萬徑”構建了一個無邊無際的寥廓大空間,大雪覆蓋大地,飽含“荒寒”意味,這正是陸游“荒寒詩”所喜愛描摹的。
最后,《江雪》詩符合宋代山水畫的審美標準。宋代山水畫愛描繪清寒景色,“水墨寫意山水畫已成為宋代山水畫的主流,用水墨或素淡色彩”。《江雪》詩用大量留白來表現雪景,“蓑笠翁”遠看只有一個黑色的人影,水墨畫面感十足,淡雅相宜,符合山水畫的審美標準。陸游的“一段荒寒端可畫,白篷籠底白頭翁”(《小舟白竹篷蓋保長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戲作二首》(其二)),是宋代山水畫對“荒寒”之景喜愛的證明,也可知陸游亦喜愛“清寒”的宋代山水畫,“白篷籠底白頭翁”也是“蓑笠翁”演變而來的,可見陸游對《江雪》的推崇。因此,陸游在創作荒寒詩時,腦海中時常浮現《江雪》中的畫面,潛移默化地受到其影響,并表現在自己所創作的荒寒詩之中。
分析陸游的荒寒詩,他受到了《江雪》的影響較多,不僅在創造環境的冷清、幽靜上模仿柳宗元《江雪》中的技巧,在營造淡泊閑遠的意境上也受其影響,這與他和柳宗元人生經歷相似有一定的關系,也與宋代喜愛荒寒之境有關。但陸游發揮了自主創新精神,在繼承《江雪》以天氣營造“寒”的技巧上,結合自己擅長的“雨”意象,使其荒寒詩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跳出了模仿的窠臼。此外,他的詩中常蘊含家國情懷,抒發國家危亡的感傷,或描寫隱居生活,表達對淡泊、悠閑自得的喜愛。陸游荒寒詩對《江雪》的接受,既反映了柳宗元詩歌在宋代傳播和接受的一個縮影,也反映了宋代文學的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