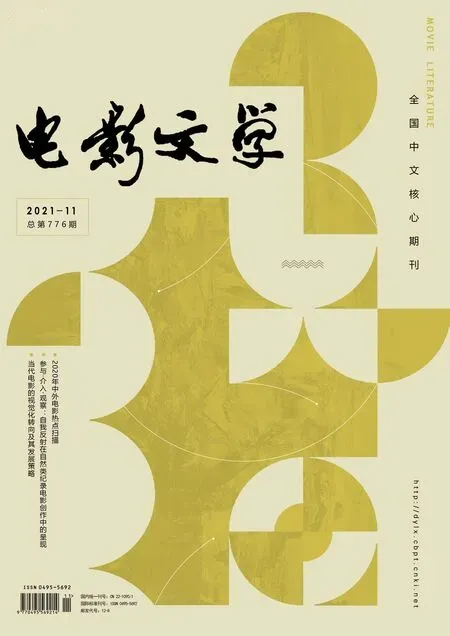底層書寫與空間政治:當下國產電影中的工廠敘事
年 悅
(天津師范大學音樂與影視學院,天津 300387)
回顧中國電影歷史,以工業題材尤其聚焦工人群體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影片可謂數目繁多。新中國成立之際,東北電影制片廠拍攝了新中國第一部表現工人階級的影片《橋》(1949)。此后,以天津本土話劇劇本改編而成的影片《六號門》(1952)引起了較大反響。這部影片以天津碼頭工人胡二一家的遭遇揭示工人階級的普遍命運及其成長過程。影片的主要演員由熟諳工人運動斗爭艱苦的真實的天津工人扮演,在塑造堅毅與智慧并存的工人形象方面尤為突出。繼影片《六號門》之后,各大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批旨在弘揚集體主義精神的工業題材影片,如《偉大的起點》(1954)、《上海姑娘》(1958)、《黃寶妹》(1958)《換了人間》(1959)、《春滿人間》(1959)、《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1960)等。在“大躍進”運動中紛紛籌建的地方電影制片廠如天津電影制片廠甫一成立就計劃拍攝《工人亦生產,學生亦工人》《為鋼而戰》《土法煉鋼》《張士珍》《穆成銳》等工業題材新聞紀錄片與人物傳記片。
如果說“新中國”工業題材影像不斷書寫著工人階級的社會主體性,那么“新時期”工業題材電影諸如《喬廠長上任記》(1980)、《血,總是熱的》(1983)、《二十年后再相會》(1984)等則從改革視角呼應著變革時代新的意識形態訴求。進入新世紀以來,國產電影創作中涌現了很多以工人群體為主角、以工廠或廠區為主要敘事空間的作品,形成了頗為值得關注的創作現象,如《二十四城記》(2009)、《鋼的琴》(2011)、《黑處有什么》(2016)、《八月》(2016)、《暴雪將至》(2017)、《少年巴比倫》(2017)、《六人晚餐》(2017)、《引爆者》(2017)、《暴裂無聲》(2018)、《地久天長》(2019)等。這些影片與歷史上的工業題材電影相比,塑造了怎樣的工人形象?其所設置的工廠空間發揮著怎樣的敘事功能?這些工廠敘事提供了怎樣的歷史想象與現實表征?在此基礎上,如何界定和解讀當下國產電影工廠敘事的意義是值得進一步展開的問題。
一、雙重群像:國企職工與“新工人”
當下國產電影創作中所塑造的工人群體形象可以概括為兩種主要類型:其一是《鋼的琴》《八月》《暴雪將至》《少年巴比倫》《六人晚餐》等影片所刻畫的國企改革歷史進程中的職工群像;另一種則是《暴裂無聲》《引爆者》等影片所描繪的當前現代化、全球化語境下的“新工人”群像。
其中,第一種群像可以概括為歷史群像,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背景下,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歷史中的工人群像。國企職工在社會改革進程中由于其技術工種、知識結構等諸多方面不適應全球化大生產而被甩出社會體制結構之外。這一龐大社會群體跌落后缺乏穩定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地位,他們的精神面貌與現實處境成為近年來很多國產電影試圖記錄與刻畫的對象。例如,在賈樟柯導演的影片《二十四城記》中,以個體陳述的方式塑造了420廠工人及其子女等多位性格迥異的國企工人形象,呈現了他們在歷史轉折中生活方式、情感經驗與代際認同等方面的矛盾,420工廠空間隱藏的正是歷史的一種“斷裂”。在張猛執導的影片《鋼的琴》中,以陳桂林、淑嫻、王抗美、胖子和快手等為代表的國企職工在工廠轉軌后下崗,為謀生而落入社會底層。陳桂林為爭奪女兒撫養權而想打造一架鋼琴,這一想法使得陳桂林及其分散在社會各個行業的工友重新回到“鋼”廠,他們以新的個人化需求和生產方式來制作“鋼琴”。影片在“集體”與“個人”的強烈對比下觸摸底層工人的歷史處境與現實命運。
相國強執導的影片《少年巴比倫》則重構了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工人群像,如小路父親、小噘嘴、牛魔王、長腳等工人形象作為時代的縮影,鑲嵌在下崗潮、三班倒、反應釜爆炸、甲醛超標環境中作業的工廠生活中。這一國企工人群體不但物質上窘迫,精神上也常常陷入困境,他們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原有的價值觀崩塌,新的價值觀尚未建立。影片著力描摹了國企工人在時代轉折之中的無力感,以及他們苦中作樂的荒誕感。
除了塑造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的工人群像以外,當下國產電影還塑造了第二種工人群像——“新工人”形象,即伴隨國家土地政策從農村土地分離出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形象。正如黃宗智所論:“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既非傳統意義的產業工人,也非傳統意義的農民,而是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農業戶籍人員。他們大多處于勞動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外,被認作為臨時性的‘勞務’人員,處于‘勞務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之中。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真正的中產階級差別懸殊,兩者幾乎屬于兩個不同世界。”
當下新生代導演十分關注社會現實問題,他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在一種鮮明的底層書寫與空間政治中塑造了“新工人”群像,并充分汲取好萊塢電影、韓國犯罪片、香港電影等類型電影經驗,構成了一種痛感現實主義風格。例如,忻鈺坤執導的影片《暴裂無聲》中,男主人公煤礦工人張保民年輕時因打架咬傷舌頭而無法發聲,為了尋找失蹤兒子而遭受煤礦老板昌萬年的迫害。張保民的無法發聲與生存絕境代表著集體失語的底層人群和沉默的大多數。再如常征導演的影片《引爆者》試圖呈現當前現代化、全球化語境下“新工人”群體在商業化大潮中被迫離開土地,利益被損害的遭遇。影片中煤礦爆破工人趙旭東僥幸躲過一次礦難,卻不幸被卷入煤礦主之間的陰謀。當下國產電影中塑造的“新工人”群像作為歷史轉型時期的復雜文化癥候,凸顯了對當下中國社會倫理秩序的深刻反思。
二、工廠空間想象的多重面目
在當下國產電影中,上述兩種工人群像所生存的工廠空間的營造通常包含破舊廠房、高聳煙囪、雜亂昏暗的生產車間、生銹機床與工具等標志性場景,既集合了工人們單調、困頓的生活狀態和情感體驗,也指稱著歷史與現實的變遷。不僅如此,工廠空間還與私人空間高度重合,依托工廠而存在的廠區建筑設施如筒子樓、球場、舞廳是具有集體主義時代特色的生活空間。上述工廠空間往往以多重面目出現,既是一種敘事空間,又飽含著更深層的文化意涵,是創作者審美意圖的外化。
工廠空間第一重面目是充滿溫情的懷舊場域,工廠作為個體經驗的承載空間而被籠罩著記憶的柔光。在當下國產電影工廠敘事中,導演往往將故事場景設定在工業城鎮里的大工廠與工人居住的廠區大院之中,圍繞工廠建立了師徒關系、家庭關系、朋友關系等社會關系網絡。這種較為封閉的空間形態充滿著對機械工業時代溫情的留戀,也經常作為影片的懷舊場域。懷舊作為一種心理現象與文化現象,是對于曾經擁有而如今失去的家園的向往。“懷舊不僅是對一段已經逝去的時間和消失的家園的思念,也是對于曾經居住在那里、現在卻散居全世界的友人的思念。”影片《鋼的琴》中的工廠空間作為懷舊場域而被呈現。那些因國企改革下崗散落在各個行業的原國企職工重新聚集在工廠廠房之中,在被塵封而又再度被重啟的工廠中,他們操作起機器重溫了分工合作的美好時光。再如影片《地久天長》中的工廠空間因為他們的歡聲笑語而充滿集體主義的溫情,也呈現了一種對逝去的集體生活的懷念和反思。伴隨反復響起的《友誼地久天長》的旋律,工廠作為一種空間記憶凝聚了工人們的情感、情緒與想象,故事得以在這種親密的“階級兄弟”關系基礎上展開。而在張大磊導演的影片《八月》中,以張小雷較為冷靜疏離的兒童視角描畫了改革背景下國營電影制片廠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個體遭際。“宏大歷史就這樣沉潛于自由松散的日常生活敘事中,成為少年成長經驗中不可或缺又難以清晰描述的一部分。”那些個體經驗散落在碎片式的工廠社區場景中,仿佛不經意地擷取的片斷任由觀眾體味。
當下國產電影工廠空間的第二重面目是作為社會異質空間表征著充滿束縛和壓抑而使人意欲逃離的“異托邦”。“與其說異托邦是烏托邦的‘反面’或對立面,不如說異托邦同時既是烏托邦,又是烏托邦的他者……異托邦相對于日常處所而言,承載著某種強烈的相異性和某種對立或對照的標志。”如果說工廠空間曾經作為國產電影中一種帶有烏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色彩,那么與此相對照的則是它的另一重面目——隔絕、壓抑與封閉的“異托邦”。例如,影片《少年巴比倫》建構了關于戴城糖精廠的故事,并按照20世紀90年代工廠空間精心設置:潮濕的水泵房、昏暗的鍋爐房和電工班,以及清一色藍色工服。影片中呈現的工廠空間顯示出風格化特征,工人們在工廠空間內從事簡單重復的工作,建構了工人們破壞、暴力以及百無聊賴的生活狀態。作為“巴比倫”的工廠空間意味著奴役和放逐,這里充滿了機械化、危險性和壓抑感,這與原本青春應有的激情和熱血剛好形成反差,這種反差促成主人公路小路個體心靈的改變與成長。再如王一淳導演的影片《黑處有什么》,通過飛機工廠防空洞、人工湖等空間氛圍的營造,凸顯了20世紀90年代工廠家屬區內少女青春的迷茫以及籠罩其中的種種恐怖與疑惑。
與此相呼應,由吳越導演、天津世紀百年影業公司出品的影片《暴雪將至》中,再無工廠熱火朝天的鋼鐵碰撞,而是在冰雨澆注之下逐漸熄滅的鍋爐煙火。在對角線構圖中鋼架交錯,冷色調的工廠冰冷得如怪獸一般凝視著世人。影片中有一段長達八分鐘的工廠內追逐的段落,在光影構圖中呈現的是在迷宮般的工廠里,人的困頓與迷失。國有工廠的標志性建筑之坍塌標志著舊時代的結束以及新時代的開啟,同時也是對工人群體主體性的放逐。在工廠衰落的歷史轉折下,命運軌跡發生了深刻變化。影片中兩次以廣角鏡頭全景仰拍鏡頭展現如迷宮一般的筒子樓,具體化的空間場景成為集體記憶與時間的坐標。曾經作為國企工人賴以生存的完整而穩定的工廠空間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也是使生長在其中的工人及其后代們不斷陷入精神迷茫與掙脫無力的旋渦。
另一方面,工廠空間還以歷史廢墟的面目呈現,是充滿危險的暴力之地。近年來國產電影在工廠敘事中最為突出的美學特征是灰色空間的建構:伴隨昏暗的雨夜和凜冽的寒風,作為法外之地頻繁出現的廢棄工廠和礦井象征著犯罪、威脅與損害時常發生的社會暗礁。在影片《暴裂無聲》中,充滿了鄉村和城市空間的符號隱喻,突出煤礦開采地陰暗、逼仄的空間來進一步深化主題意涵。而在影片《引爆者》中,工廠不僅是“廢墟”,也暗示著主人公趙旭東藏身之處和反抗之地。影片最后的場面富有象征意味,趙旭東在廢棄的工廠里不斷引爆炸藥發起反抗。以工廠空間敘事反思工業化進程對人的異化,在這里工廠既是主人公的困境,同時也是他重新建構自己主體的場域。
三、失落的主體:歷史、記憶與現實之間
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認為:“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的社會共同經驗。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是整個民族‘過去’的投影。”當下國產電影的工廠敘事或反思歷史,或觀照現實,在歷史與記憶的交織中共同呈現出對于工人這一失落的社會群體的深切關注。
當下國產電影的工廠敘事首先一個面向是反思歷史,對于歷史中的曾經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衰落的反思。他們在工廠中緬懷過去的集體感,同時也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因喪失主體位置而成為失語者。如果將工廠空間視為通往文化記憶的一種路徑,那么,工廠空間將會打通歷史和現實的通道。與此同時,國企改革作為一個標志性歷史事件和歷史記憶,構成了工廠敘事與情感表達的知識背景。德國著名學者、文化記憶理論奠基人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概念關注的是記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和文化決定的,開展文化記憶研究,不是把一個來自個體心理學領域的概念運用到對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分析中,而是強調心理、意識、社會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當下國產電影工廠敘事正是通過文化記憶建構了一個緬懷歷史的凝聚性結構,以或溫情或悲情、或戲謔或莊嚴的多時空敘事穿梭于冷峻歷史與詩意現實之間。例如影片《二十四城記》嘗試用紀錄片的電影手段叩訪“歷史真實”。與八位受訪人講述行為相切換的是葉芝、曹雪芹、歐陽江河、翟永明、萬夏等的詩句,這鮮明地構成了一種歷史與詩歌并置的凝重感。再如,影片《鋼的琴》從總體上觀照國企工人在集體主義時代作為一個“群體”瓦解之后以個人化方式進入歷史的過程。而影片《地久天長》在三十余年的長時段敘事中,將劉耀軍夫婦和沈英明夫婦等幾個普通工人家庭的悲歡離合書寫為大時代轉折下的平民史詩。
除了歷史反思以外,當下國產電影的第二種面向是觀照現實,即較為注重對當前“新工人”群體的生存境遇與身份焦慮進行探討。“較之20世紀的工人階級,‘新工人’群體的人數與規模要龐大得多,但這一群體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卻幾乎沒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們究竟是一個階級還是階層至今仍然是學者們爭論的問題。”事實上,“新工人”群體的產生可以視之為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當下工廠敘事中的鄉村不再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而是一片破敗的荒涼景象,是代表著落后的、了無生機的封閉空間。資本市場分化導致“新工人”群體成為“新窮人”,而那些被迫離開土地來到城市的“新工人”,等待他們的是回不去的家鄉也留不下的城市。在影片《暴裂無聲》中,鄉村與城市的交界處有一處山洞,這個山洞是隱藏著所有的陰謀和罪惡的淵藪,也吞噬了無數面如土灰的打工者,并即將吞噬他們的下一代。影片最后,龐大的礦山在一聲爆破中訇然倒塌,尋子無果的張保民落下眼淚,既是一位父親的心理潰敗,也是一個時代的精神之殤。因此,處于農村或城市邊緣的“新工人”群體在當下國產電影工廠敘事中往往作為漂泊者與失語者出現,他們拒絕賣掉土地可以被視為一種艱難的反抗。有意味的是,當前國產工人題材電影常常還會加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彌合歷史、記憶、空間與現實的裂隙,描畫“新工人”群體過去二十余年來不無悲涼的生存境遇。空間中的幻象常常被用來隱喻記憶的消退,逃離現實生活的幻想,以及人在歷史、現實與未來中的駐足、徘徊與彷徨。
結 語
當下國產電影中的工廠敘事描繪了20世紀90年代國企工人和“新工人”兩種工人群像,在呈現曾經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衰落的同時,也試圖反思當代中國社會高歌猛進的現代化進程中,從土地分離出來的“新工人”群體無處尋找的身份焦慮與生存困境。當下國產電影也密切關注中國工廠的變遷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歷史關聯,將工廠空間作為銘刻社會轉型的場域來連接歷史、記憶與現實。在具象化的空間坐標中尋找和喚醒流逝的時間,使人們可以清晰地體認不同代際的工人群體所經歷的集體記憶與個體傷痛。實際上,在當下圍繞工人群體與工廠空間的影像表達之中,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平凡的工人群體的選擇與遭遇深藏著某些影響和塑造歷史的因素與結構。這些底層書寫也密切聯系著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與精神動向,并始終保持著獨特的藝術品質與深切的人文關懷。在此意義上,當下國產電影的工廠敘事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