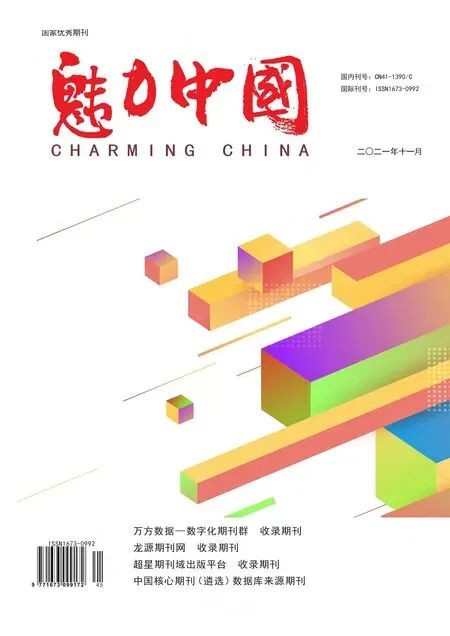芻議新常態下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發展路徑
曾海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200439)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西部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與東部沿海地區還有較大差距,同時中西部地區內部不同區域之間也存在發展差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2020 年頒布的《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以及2021 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明確要求城鄉進一步融合發展,不斷釋放可能的消費潛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發展模式,將中西部地區的綜合實力、內生動力和競爭力進一步加強。制造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是我國中西部地區持續發展的保障,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我國當前的發展態勢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需要內循環的引領,需要制造業穩健、健康、高效的發展。很多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已經出現了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局面,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產業也在尋找下一個去處。廣大中西部地區憑借其資源稟賦、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當地優惠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制造業前往投資建廠。在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制造業帶來的高污染也成為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在實現內循環的背景下,合理構建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和發展路徑對中西部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其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鄧宗豪(2021)等選取了西部地區27 個制造業兩位數行業的面板數據,驗證了當制造業規模不斷發展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制造業的集聚將有助于改善污染排放和環境質量,但是如果進一步集聚發展會產生排擠效應,將導致環境污染加重;趙海峰(2021)等研究發現中央環保督察制度的實施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如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明顯,而中小型企業的轉型升級的效率在中央環保督察組的活動下和大型制造業相比較低,整體上該制度對技術密集型企業轉型升級作用明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作用有限;袁冬梅(2021)等基于GFLS 模型對人力資源結構高級化與制造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行了實證檢驗并得出結論:人力資源結構的高級化對制造業產業升級的影響顯著為正,進一步分地域來看,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最為顯著,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多,薪酬水平的上升驅動了產業轉型升級;劉桔林(2021)發現我國的高技術制造業在東部和西部地區產業聚集程度最高,中部地區較為均衡,且空間關聯性主要發生在東部省份以及極少數西部省份,同時西部地區的高科技技術企業發展滯后,與相鄰地區難以產生“溢出”效應;李遠慧(2021)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稅收優惠對制造業的一般性創新和實質性創新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值稅優惠對中西部地區的一般性創新驅動較為明顯,而所得稅優惠對西部地區的積極作用較強;肖澤鋒(2021)等通過隨機模型研究西部地區2008 至2018 年的面板數據發現西部地區制造業的聚集對城鎮與居民的消費升級有促進作用;唐世芳(2021)等認為財政稅收政策在支持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還有改進的空間。
由上述文獻可以看到,制造業的發展對中西部居民消費升級有促進作用,制造業的集聚和污染有一定的關聯性,同時,在幫助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發展的過程中,財政稅收、環保督察、人力資源優化對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創新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發展現狀
(一)總量
從總量上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區域的工業增加值在總量絕對值上都有明顯的增長,然而從占比上看,截止到2019 年,東部地區的工業增加值總體上占比超過全國總量的半數,而中西部地區的占比為41.68%。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在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總體上比較均衡,但在絕對值上還有一部分的差距,而在占比上,中西部地區的增長相比東部地區要增長更快。

表1 1978年與2019年我國各區域工業增加值數據統計表(單位:億元)
(二)產品品類
據公開數據顯示,近二十年來,在焦炭、成品糖、原鹽、硫酸、農用氮磷鉀化肥、水泥等資源稟賦型產業,中西部地區的產量和全國占比均有明顯的攀升,同時在平板玻璃、大中型拖拉機、汽車、微型計算機設備和集成電路等中高端產業上,中西部地區的產量和全國占比也有明顯的增長。這說明我國中西部地區在傳統制造業、高耗能制造業與中高端制造業上均有發展。
(三)增長方式導向
在制造業的增長方式導向上,廣大中西部地區目前的增長方式還是以“粗放型”“投資導向型”為主,同時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不完善,中西部地區的出口經濟并不明顯,主要還是依賴于國內市場。據公開數據顯示,盡管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在節能減排上有較大改進,但“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相比于東部地區還是差距明顯;同時,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發明專利數也遠遠落后于東部企業,其在生產研發上的投入還有待提高。
四、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發展現狀的成因
(一)戰略性政策引導
中央政府意識到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分別于2000 年和2006 年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在這兩個戰略性政策的引導下,許多優惠性措施落地,地方政府也加強了招商引資力度,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開始進入新局面,工業增加值在全國的占比也逐漸上升。另一方面,除了國家層面的政策,地方政府依據當地要素稟賦和產業發展態勢制定的地方性政策也有針對性地規劃制造業的發展前景,例如成都市和重慶市政府都分別于2015 年和2021 年印發了有關支持制造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意見,對重大項目建設、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運用等方面做了詳細的支持和補助方案,鄰近城市的發展帶動了產業結構的集聚,成渝都市圈的誕生也建立在兩個城市制造業發展的基礎上。
(二)自然資源優勢和基礎設施建設
中西部地區面積廣大,許多省份都有已經探明的豐富的礦產資源。例如貴州省的汞資源、鋁土礦、富磷礦和煤礦資源,青海省的鋰礦、銣礦、自然硫與自然堿、陜西省的鹽礦、重晶石、鎳礦等,不勝枚舉,這些礦產資源天然就是工業制造業所需的原材料,對制造業的投資者來說這是一項重要的區位優勢。但同時,中西部地區遠離海港,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長期以來相比東部地區落后。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截至2019 年,全國公路總里程超過500 萬公里,其中2017 年開始中西部地區的公路里程增長占據全國公路里程增長超過了8 成;而鐵路總里程在2021年已經超過了14.63 萬公里,高速鐵路達到3.79 萬公里,“四縱四橫”鐵路網全面建成,“八縱八橫”鐵路網逐漸加密,這些交通基礎設施連接著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降低了制造業企業的物流成本。
(三)從東部沿海轉移至中西部內陸
東部地區土地和人力資源成本等不斷上升,迫使部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不得不尋找成本更低的洼地。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成本相比東部地區具有比較性優勢,是制造業轉移的好去處。同時產業自身的發展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也會導致產業從生命周期相對成熟甚至是衰退階段的地區遷往生命周期導入和發展階段的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之間的差距正好提供了這樣的生命周期的差距,促進制造業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內陸遷移。
五、發展路徑建議
(一)政策引導產業轉型升級
在高質量發展要求的背景下,廣大中西部地區除了梯度承接引進東部地區的制造業轉移,還應該結合當地自身發展水平,制定相應政策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生產制造率,降低單位能耗,實現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積極發揮財稅作用
必須看到,中西部地區雖然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初具規模,但還有許多省市還在探尋發展路徑,因此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手段對包括制造業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還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財政上,中央財政在投資時應引領盤活社會資本的參與,提高轉移支付的效率,控制地方政府發債行為并規范發債的用途;在稅收上,應用差異化的稅收手段引導制造業產業的投資和一些產業的集聚。
(三)優化營商環境
制造業的持續發展需要長久穩定的環境,因此,保持政策的穩定和透明而非朝令夕改,避免出現政策方向的急轉彎,提振企業持續發展的信心;進一步簡化辦事流程,逐步提升審批、審計等方面的行政辦事效率,幫助企業減少非生產經營性的成本支出;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能力,定期走訪企業,在金融、生產、知識產權保護、勞動力培訓等方面真正解決企業的發展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