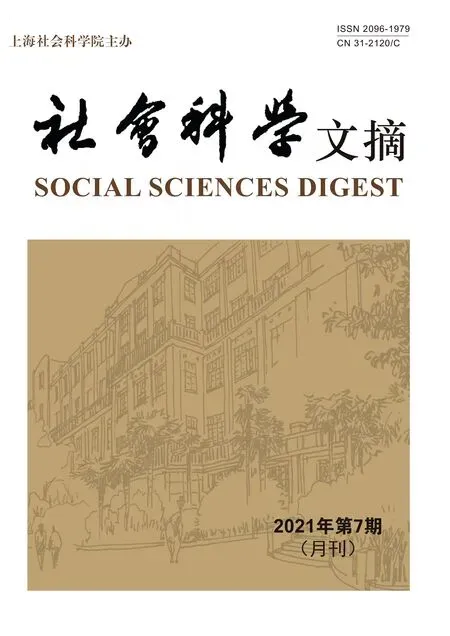先秦民族史觀鉤沉
——兼論周朝“夷夏”之辨
文/彭華
關(guān)于“種族/民族”與“文化”,陳寅恪曾經(jīng)有許多論說(shuō)。許多研究者都不約而同指出,陳寅恪“種族(民族)與文化”觀的要義在于:“種族(民族)與文化”是研究中國(guó)歷史(中古史)與文化的關(guān)鍵,而判別“種族(民族)”的標(biāo)準(zhǔn)是“文化”而不是“血統(tǒng)”。惟因受論述對(duì)象和研究興趣所限,陳寅恪的行文未能及于中國(guó)先秦時(shí)期的民族觀。
筆者的看法是:大體而言,以“文化”判別中古以來(lái)尤其是全球化以來(lái)的“種族(民族)”,無(wú)可厚非;但是,以之觀照先秦時(shí)期的古中國(guó),則不可一概而論。本文所考察和論述的重點(diǎn),可以一分為二:(1)判別“民族”的標(biāo)準(zhǔn)何在?(2)“夷夏”之辨的要義何在?
從發(fā)生論/本根論而言,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鑒定民族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視角
(一)生理特征與體質(zhì)鑒定
在這一方面,完全可以借鑒生物學(xué)、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理論、方法與成果,尤其是關(guān)于“種族”的研究成果。“種族”屬于生物學(xué)、體質(zhì)人類學(xué)上的術(shù)語(yǔ),并且首先是生物學(xué)概念,它主要考慮的是生物學(xué)因素而非文化因素,即在體質(zhì)上具有某些共同的遺傳特征、共同的生物學(xué)基礎(chǔ)的人群。本處所說(shuō)的“在體質(zhì)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遺傳特征”,包括膚色、眼色、發(fā)色和發(fā)型、身高、面型、頭型、鼻型、血型、遺傳性疾病等。
對(duì)于現(xiàn)代的人群和民族,可以通過(guò)觀察、測(cè)量、檢測(cè)等手段進(jìn)行鑒別和鑒定,或者通過(guò)科學(xué)手段進(jìn)行DNA分析。比如說(shuō),為了解決現(xiàn)代人的起源問(wèn)題,有所謂“線粒體夏娃理論”的提出。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的人群和民族,可以通過(guò)發(fā)掘所得的遺物(尤其是骨骼和牙齒)并有機(jī)結(jié)合歷史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資料,進(jìn)行考古人類學(xué)、體質(zhì)人類學(xué)、分子生物學(xué)的研究。在這一方面,中國(guó)的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工作者已經(jīng)進(jìn)行了行之有效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寶貴的成果。
其實(shí),對(duì)于體質(zhì)人類學(xué)所揭示的不同人群(民族)具有不同生理特征(遺傳特征)這一結(jié)論,中國(guó)古人是有所認(rèn)識(shí)的。比如,早在春秋時(shí)期,“博物君子”孔子對(duì)此已有認(rèn)識(shí)(詳見(jiàn)《國(guó)語(yǔ)·魯語(yǔ)上》所載“獲骨焉,節(jié)專車”事)。到西漢,《淮南子》的作者有了更為詳細(xì)、更為豐富的認(rèn)識(shí)(詳見(jiàn)《淮南子·墬形訓(xùn)》)。而隋人蕭吉《五行大義·論諸人》對(duì)四夷的說(shuō)法,亦頗可參照。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五行大義》在圖式上出于“五行”整齊排列的需要,在思維上難免有不合實(shí)際的聯(lián)想與比附,但是,它確實(sh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方之人“在體質(zhì)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遺傳特征”,這是值得肯定的。
(二)祖先傳說(shuō)與世系追記
中國(guó)古代典籍在記述王侯、大夫、貴族之時(shí),尤其注重淵源和世系的敘述。其典型者,如《世本》《帝王世紀(jì)》以及《史記》之本紀(jì)、世家。本處所說(shuō)的“祖先傳說(shuō)與世系追記”,特指并且專指具有真正的“共同的血緣關(guān)系”的民族(族群),亦即在DNA鑒定上可以認(rèn)定的同一民族。惟有如此,方可視為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世系”“共同的記憶”。
馬克斯·韋伯認(rèn)為,“族群是這樣一些群體,要么由于體貌特征或習(xí)俗相近,或者由于兩者兼有,要么由于殖民和移民的記憶,從而對(duì)共同血統(tǒng)抱有主觀信仰;這種信仰對(duì)于群體構(gòu)建肯定具有重要意義”。安東尼·史密斯在給“民族”和“族群”下定義時(shí),亦將“共同的神話和祖先”“共同的神話”“共享的記憶”列為構(gòu)成要素。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大致認(rèn)定“族群”是分享共同的歷史、文化或祖先的人群,它一般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共同祖先的神話”即“共同的要素”之一。所謂“共同的神話和祖先”或“共同祖先的神話”,約略近乎本處所說(shuō)“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世系”。
本處所說(shuō)“共同的血緣關(guān)系”“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世系”,因?yàn)榫眠h(yuǎn)洪荒而不易找尋讓人人都信服的證據(jù)。但睡虎地秦簡(jiǎn)《法律答問(wèn)》的一段文字,確實(shí)是鮮活的例證:“臣邦人不安其主長(zhǎng)而欲去夏者,勿許。”可(何)謂“(去)夏”?欲去秦屬是謂“(去)夏”。“真臣邦君公有辠(罪),致耐辠(罪)以上,令贖。”可(何)謂“真”?臣邦父母產(chǎn)子及產(chǎn)它邦而是謂“真”。可(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殹(也)。
由以上簡(jiǎn)文可知,秦人已經(jīng)以“夏”自居(自稱),視臣屬于秦的少數(shù)民族的父母所生之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國(guó)家的公民為“真”(他稱)。至于如何判斷是“夏子”還是非“夏子”,由簡(jiǎn)文可知,秦人注重的是血緣,并且尤其注重的是母方的血統(tǒng)。即母親必須是秦人(“秦母”),其子方為“夏子”。
從生成論/過(guò)程論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是判別民族的主觀標(biāo)準(zhǔn):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角
(一)共同的語(yǔ)言文字
文化人類學(xué)認(rèn)為,語(yǔ)言文字是通過(guò)后天的學(xué)習(xí)獲得的。在一個(gè)民族的形成過(guò)程中,語(yǔ)言文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語(yǔ)言文字的形成,是一個(gè)民族形成的標(biāo)志之一。因此,語(yǔ)言文字可以成為民族識(shí)別的依據(jù)之一。
對(duì)于語(yǔ)言和民族的密切關(guān)系,周朝時(shí)期的人士早已有認(rèn)識(shí)。《禮記·王制》說(shuō):“五方之民,言語(yǔ)不通,嗜欲不同。達(dá)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春秋時(shí)期的戎子駒支,曾經(jīng)坦言“諸戎”與“諸華”有諸多不同,而語(yǔ)言不同即其中之一,“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摯幣不通,言語(yǔ)不達(dá)”。
在中原華夏族看來(lái),蠻夷戎狄語(yǔ)言與華夏族語(yǔ)言的差別是如此巨大、如此難懂,簡(jiǎn)直形同“鳥語(yǔ)”。孟子譏諷操難懂的南方方言者為“南蠻鴃舌之人”,《后漢書》將南方的少數(shù)民族歸入“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yǔ)之類”。剔除其中的民族偏見(jiàn)與民族歧視的成分,孟子和《后漢書》所反映的歷史(民族和語(yǔ)言)還是客觀的。
非常可貴的是,早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中國(guó)古人不但認(rèn)識(shí)到可以通過(guò)語(yǔ)言判別民族,而且認(rèn)識(shí)到語(yǔ)言與民族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并非鐵板一塊,即語(yǔ)言的改變并不影響族群身份的認(rèn)同。《呂氏春秋》說(shuō):“戎人生乎戎、長(zhǎng)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zhǎng)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zhǎng)乎戎,戎人長(zhǎng)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也就是說(shuō),楚人和戎人的族群身份,并沒(méi)有因?yàn)檎Z(yǔ)言的改變而發(fā)生變動(dòng)。
(二)共同的社會(huì)生活
本處所說(shuō)的“共同的社會(huì)生活”,與斯大林所說(shuō)的“共同經(jīng)濟(jì)生活”有交叉、有重合,特指衣食住行等。茲略舉數(shù)例,以為證據(jù)。
《尚書》:“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被發(fā)左衽”是“四夷”的裝束,與“華夏”的“束發(fā)右衽”判然有別。《禮記·王制》對(duì)“中國(guó)”“四夷”之別的概括頗為全面:“中國(guó)、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yǔ)不通,嗜欲不同。”《呂氏春秋》的概括亦相當(dāng)全面:“蠻夷反舌、殊俗、異習(xí)之國(guó),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
(三)共同的禮制風(fēng)俗
本處所說(shuō)的“禮制風(fēng)俗”,即古書所云“禮俗”。中國(guó)古人所說(shuō)的“文化”,即“文治教化”,亦即“為文所化”。其中,禮是“文化”的大宗。以“文化”判別“民族”,實(shí)即以“禮俗”判別“民族”。
在中國(guó)古人的話語(yǔ)體系中,“中國(guó)”之所以為“中國(guó)”,“中華”之所以為“中華”,并非僅僅是因?yàn)榫佑凇疤煜轮小保嗟氖且驗(yàn)橛卸Y樂(lè)之隆、仁義之施、文化之美。《戰(zhàn)國(guó)策》曰:“中國(guó)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wàn)物財(cái)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shī)書禮樂(lè)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yuǎn)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莊子》曰:“吾聞中國(guó)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章太炎曾經(jīng)一針見(jiàn)血地指出,“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guó)名,亦且非一血統(tǒng)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
正因如此,在整個(gè)周朝時(shí)期,禮制成為判別夷夏的極其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比如,《左傳》定公十年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再如,杞國(guó)封君為大禹后裔,其血統(tǒng)屬于華夏系統(tǒng),其禮制亦屬于華夏文化系統(tǒng),但因杞國(guó)國(guó)君在春秋時(shí)期使用“夷禮”,故而被時(shí)人視為夷,國(guó)君亦被貶稱為“杞子”。又如,秦國(guó)祖先雖然是“帝顓頊之苗裔”,但在東周之時(shí)仍然被視為夷狄。其原因之一即禮俗,“秦越千里之險(xiǎn),入虛國(guó),進(jìn)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wú)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zhàn)始也”。
(四)共同的歷史記憶
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大致認(rèn)定“族群”是分享共同的歷史、文化或祖先的人群,它一般具有“共享的歷史記憶”等要素。中外各民族的史詩(shī)、各族群的譜牒所展示、所反映的實(shí)際上就是“共同的歷史記憶”,亦即史密斯所說(shuō)“共享‘黃金時(shí)代’的記憶”。
所謂“史詩(shī)”,是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或英雄傳說(shuō)的敘事長(zhǎng)詩(shī),具有民族歷史的性質(zhì),如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奧德賽》等,以及古中國(guó)的《格薩爾王傳》(藏族)、《瑪納斯》(柯?tīng)柨俗巫澹ⅰ督駹枴罚晒抛澹┑取_@種代代相傳的“歷史記憶”,不僅是“共同的”,也是“共享的”。
所謂“譜牒”,是記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書籍,是“記載一家一族的歷史”。《國(guó)語(yǔ)·楚語(yǔ)上》記錄了楚國(guó)大夫申叔時(shí)教導(dǎo)太子的內(nèi)容,其一即“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dòng)”。所謂“世”,即“謂先王之世系也”(韋昭注)。《國(guó)語(yǔ)》的記載和韋昭的注是可信的,業(yè)已為出土文獻(xiàn)所印證。陜西省扶風(fēng)縣莊白村出土的史墻盤,記述的是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跡以及作器者微氏家族的發(fā)展歷史。
(五)共同的民族意識(shí)
本處所說(shuō)“共同的民族意識(shí)”,即“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民族認(rèn)同”,有時(shí)也稱為“族群認(rèn)同”,指某一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將自己和他人認(rèn)同為同一民族,對(duì)這一民族的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態(tài)度。
“華夏族”作為一個(gè)單一民族,是自夏代以來(lái)就是客觀存在的。“華夏民族意識(shí)”是在夏商周時(shí)期逐漸產(chǎn)生的,最終形成于春秋時(shí)期。東周之時(shí),華夏族的“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是極其鮮明的;時(shí)人普遍認(rèn)為,華夏民族(中國(guó))與蠻夷戎狄(四夷)是截然不同的兩大陣營(yíng)。這種民族意識(shí)的經(jīng)典表述,便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需要注意的是,對(duì)于“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不可一概而論,而應(yīng)當(dāng)具體分析。在先秦時(shí)期(尤其是在東周時(shí)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guò)這樣一種情況:就血統(tǒng)而言本來(lái)屬于華夏族的諸侯,但因熏染了蠻夷夷狄的習(xí)俗,故又以蠻夷、夷狄自居。其典型例證,有燕國(guó)、吳國(guó)、越國(guó)、楚國(guó)等。
1.燕國(guó)。先秦時(shí)期,曾經(jīng)存在過(guò)兩個(gè)燕國(guó),一個(gè)是姞姓燕國(guó),一個(gè)是姬姓燕國(guó)。本處所說(shuō)的燕國(guó),指的是姬姓燕國(guó)。歷史上的燕國(guó)國(guó)君曾經(jīng)竟然以“蠻夷”自居(“寡人蠻夷辟處”),而燕國(guó)勇士秦武陽(yáng)(秦開之孫)也被人稱為“北蠻夷之鄙人”。
2.吳國(guó)和越國(guó)。就吳國(guó)和越國(guó)之王室而言,他們?cè)谘夑P(guān)系、祖先傳說(shuō)、歷史記憶方面與華夏民族(禹)、周朝王室(太王)有關(guān)系,可以劃入華夏族系統(tǒng);但其行為、風(fēng)俗、心理已與中原華夏族截然有別,故被中原諸侯視為“蠻夷”“夷狄”。吳、越國(guó)君亦自我認(rèn)同為“蠻夷”“夷狄”。
3.楚國(guó)。楚國(guó)羋姓,出自“五帝”之一的顓頊,與華夏族的黃帝、炎帝有血緣關(guān)系。按照出土文獻(xiàn)的記載(如望山楚簡(jiǎn)、包山楚簡(jiǎn)、葛陵楚簡(jiǎn)、安大簡(jiǎn)等),楚國(guó)出自祝融。在楚簡(jiǎn)中,祝融與老童、穴(鬻)酓(熊)并列,被稱為“三楚先”,是楚人祭祀的三位先祖,而祝融亦屬顓頊之后。但是,楚國(guó)國(guó)君后來(lái)以“蠻夷”自居。
燕國(guó)、吳國(guó)、越國(guó)、楚國(guó)的國(guó)君之所以以“蠻夷”“夷蠻”自居,其重要原因便是因?yàn)樗麄冄尽⒔邮芰诵U夷戎狄的文化(禮制風(fēng)俗、社會(huì)生活)。
總而言之,“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固然可以作為判別民族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之一,但確實(shí)不可一概而論。最為經(jīng)典的反證是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孟子》),但舜和周文王都被尊為華夏族的“圣人”。
對(duì)蠻夷戎狄的民族偏見(jiàn)與民族歧視,是周朝夷夏觀的主流:政治人類學(xué)的視角
本處的這一判斷,可以說(shuō)是學(xué)界的共識(shí)。比如,田繼周在《先秦民族史》中指出:第一,“周朝民族間的不平等,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夷、狄、戎、蠻等少數(shù)民族的歧視和壓迫上”,“明堂位的排列,反映了對(duì)少數(shù)民族的不平等的歧視觀點(diǎn)”;第二,在周朝的著作中,經(jīng)常可以看到把戎狄比作“豺狼”“禽獸”的記載。
除以上兩點(diǎn)之外,還可以補(bǔ)充另外一點(diǎn),即東周時(shí)期民族不平等思想、民族歧視觀念的形成和確定,儒家實(shí)際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孔子之作《春秋》,恪守的法則是“內(nèi)其國(guó)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jìn)于中國(guó)則中國(guó)之”。在孔子的心目中,華夏民族的文化無(wú)疑是高于蠻夷戎狄的。降而至于孟子,則進(jìn)一步提出要“以夏變夷”,反對(duì)“以夷變夏”,“吾聞?dòng)孟淖円恼撸绰勛冇谝恼咭病薄L子谩斗Y梁傳》的說(shuō)法,即“不以中國(guó)從夷狄也”,而其大義在“存中國(guó)也”。孔子、孟子與《穀梁傳》的這些話語(yǔ),是“夷夏之辨”或“華夷之辨”的經(jīng)典表述。它們揭示了古中國(guó)“夷夏/華夷”觀的“三部曲”:“夷夏有別”是客觀存在的事實(shí),“以夏變夷”是主流的價(jià)值取向,而“存中國(guó)”則是終極的追求與目標(biāo)。儒家這種“夷夏有別”“以夏變夷”思想,對(duì)后世影響極大。
結(jié)語(yǔ)
結(jié)合西方的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理論與方法,審視中國(guó)的傳世文獻(xiàn)與出土文獻(xiàn),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
其一,判別“民族”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則可以一分為二:(1)基于先天的生理因素的生物學(xué)基礎(chǔ)是鑒定民族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如生理特征(遺傳特征)、血緣關(guān)系(包括祖先傳說(shuō)與世系追記)等,尤其是在民族形成的早期階段(比如夏商周三代或東周時(shí)期),這種民族鑒別更為行之有效。(2)隨著民族的頻繁交往尤其是民族的日益融合,后天的文化因素日漸成為判別民族的主觀標(biāo)準(zhǔn),亦即以“文化”判別“民族”。這些主觀標(biāo)準(zhǔn),包括共同的語(yǔ)言文字、共同的社會(huì)生活、共同的禮制風(fēng)俗、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民族意識(shí)等。不過(guò),在“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上,需要審慎對(duì)待,不可一概而論。
其二,對(duì)蠻夷戎狄的民族偏見(jiàn)與民族歧視是周朝“夷夏觀”的主體內(nèi)容,而“以夏變夷”則是其主流導(dǎo)向,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義所在。東周時(shí)期民族不平等思想、民族歧視觀念的形成和確定,儒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