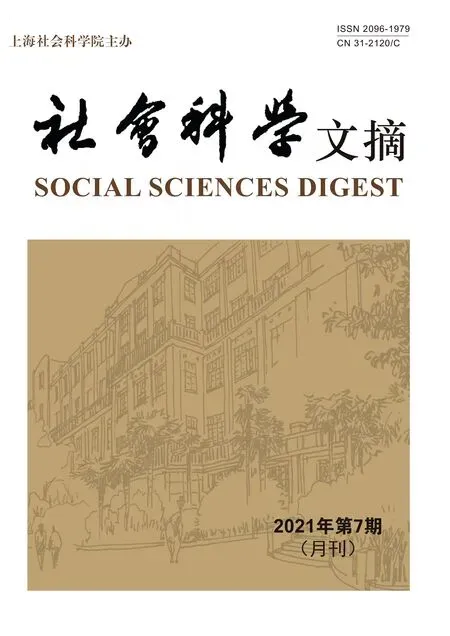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正統在我”:中古正統建構與文學演進
文/王偉
在中國古代,正統建構既關系天下穩定,也攸關每一個王朝和帝王的執政合理性,因而,其在政治文本、思想文本和文學文本中均有呈現。十六國南北朝各政權對抗時間久長,政權更迭頻繁,且與華夷、南北等問題相糅合,故此一時期的正統之爭在國史上尤為激烈,對文化及文學發展的影響亦特深巨。本文擬以正統爭奪為語境,對十六國君主的文學形象建構、南北文學對立和隋唐文學融合等問題進行新的思考和探究。
十六國胡主“雅好文學”與正統制造
西晉永嘉亂后,十六國君主“俱僭大號,各建正朔,或稱王爵”。然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幾乎所有胡主都意識到,唯有在文化身份上獲得華夏民族認同,方能“擅中華之稱”。但由于胡漢矛盾激化,“夷夏之別”亦由先秦兩漢時的文野分際逐漸轉向種姓之辨,故胡主欲在中原建政樹統,種族之別是必先克服的障礙,而“制造祖先”以改變文化血統則成為其破解此難題的重要手段。十六國胡主常通過對族群記憶與祖先記憶的重新建構,帶動族群邊界移動,以實現對本民族族群身份的重新塑造,進而調適“中國人”的成分與性質以淡化華夷界限。具體到操作層面便是“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即攀附中華圣賢為祖,對己族塞外歷史予以刻意遮蔽或“選擇性遺忘”,從而“制造”出華夏正統的身份,使“當下通過歷史關系的調整變得具體并獲得意義”。此在劉雄等人的身份構造過程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劉雄乃劉淵弟,其墓志所體現出的血緣譜系,反映了前趙君臣建立正統的努力。劉淵是十六國時較早樹立王旗者。進入中原后,他將歷史上漢匈間的舅甥關系這一歷史資源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源,起事之初自稱“冒頓之后”,后謂“漢氏之甥”。稱王后,他遠祀漢高祖及其以下三祖五宗,且近尊蜀漢劉禪,把漢匈兩族最高貴的政治血統巧妙嫁接,為其政權建構起充分的歷史基礎。此種“制造祖先”的做法在其他胡主處亦屢見不鮮,部分胡主甚至將祖先建構的觸角延伸至華夏先祖。如后秦開國君主姚萇之父姚弋仲云其為“有虞氏之苗裔”,大夏國主赫連勃勃則云其為“大禹之后”。此于《晉書·載記》中頗常見,其結構化的情節是:一個遠古華夏的英雄或其子孫,因各種原因遠徙邊地,后成為本地土著的統治者和開化者,而本土民眾也就自然成為他的后裔。通過記憶回溯和文人學者的稱頌贊詠,胡主在政權內部反復論說自己的合法性與正統性。這類祖先制造模式的頻頻使用,充分表現出胡主在文化譜系中將自己的族源與華夏文化進行嫁接的努力和為自己的政權尋求合理性法統、文化依據的熱情。
和中原歷代君主一樣,少數民族領袖不僅利用華夏原有的符號系統,如祥瑞、圖讖、德運,甚至還利用天文星占和史書編撰來論證自身的正統地位。據《晉書·載記》載,十六國君主們從孕育、出生、外表都具有一系列異于常人的表現。這種模式化書寫套路,基本遵循了《史記》《漢書》等經典對古之圣賢和受命天子的書寫標準,將原屬華夏圣賢的身體符號予以復制。這既滿足了胡主們的自我期待,也左右著讀者的閱讀認知,從而創造出社會化的崇拜趨向,充滿著濃郁的政治意義。另外,沿用華夏歷史敘事模式,讓人在閱讀十六國北朝歷史時,不自覺將其代入秦漢魏晉華夏帝國的正統譜系中,從而在敘事模式或框架中不露聲色地植入正統建構的意圖。
在“制造祖先”和“身體復制”外,以文學為途徑塑造其文德形象也成為正統建構的有效手段。如《晉書·劉元海載記》云前趙國主劉淵自幼好學,對“《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淵從祖父劉宣“好《毛詩》《左氏傳》”。劉聰“善屬文”,曾撰“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劉淵族子劉曜亦“善屬文,工草隸”。可見前趙數代國主及皇室成員多善詩能文,幾可肩隨漢魏皇室。前燕國主慕容皝雖進入中原稍晚,但也“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后燕國主慕容寶亦頗“工談論,善屬文”。后秦國主姚興長子姚泓“尤好詩詠”。成漢國主李雄第四子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南涼國主禿發傉檀子禿發歸年十三,曾撰《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其父禿發傉檀將之比為曹子建。前秦苻堅“博學多才藝”,其弟苻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時人擬之王粲。苻堅從兄子苻朗每談虛與玄,不覺日之將夕,及臨刑,志色自若,并賦詩言志,頗得老莊之趣。
史料所塑造的崇儒尚文的胡主形象,在真實的歷史語境中常充滿矛盾,其中不難見出史料拼湊以求潤飾的撰述目的。歷史書寫是頗受政治激勵與操縱的文化生產過程,特定政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常利用政治權力對歷史書寫與文學生產進行干擾。十六國各政權之國史是政權自身形象建構的生動文本,對君主形象之潤飾又是其題中要義。雖然十六國國史被毀者甚眾,但通過散見及殘留的文本,仍不難見出南進中原的十六國君主們希冀通過篡改國史而力圖凈化和重構自我形象的努力和用心。至北魏,崔鴻訪尋十六國國史,編訂《十六國春秋》,后又為房玄齡《晉書》取資,據此可知十六國《國史》《十六國春秋》《晉書》間存在著完整的文獻因襲鏈條。換言之,《十六國春秋》《晉書》在撰述和史料采用上均受到十六國國史的影響,《十六國春秋》和《晉書》對胡主多虛美隱惡之辭,這與其說是出自北魏崔鴻或唐代史官之手,不如說是十六國史官和國主苦心孤詣、聯手潤色的結果。
綜之,十六國胡主借助文學文本,塑造其文德之君的形象,編織“正統在我”的合法性證明,此不僅吻合華夏民族的心理期待,亦符合經典敘事的話語邏輯,易獲得華夏民族的認同,從而奠定其執政的合法性,并在政權內部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終使文學文本派生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整合功能。
南北朝各方“引善自向”與文學的相互定義
公元439年,北魏結束了十六國以來的紛亂政局。在正統觀念上,北魏除了沿襲十六國原有的“血統正統論”,還進一步展衍出“空間正統論”和“文化正統論”思想。“空間正統論”主要是仿效“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天體運行規律,確立以中原為中心的地理正統觀念。與地理空間論并行的還有“文化正統論”。北魏入主中原后,在文化建設上不斷加強去夷即夏的努力。孝文帝自幼就雅好讀書,其在位期間,還多次以華夏正統繼承人的身份頻繁參與祭祖、祭天、祭圣等活動。通過一系列舉措,旨在“以儀式感和莊嚴感,來彰顯帝國與文化的威權與正統”,進而強化北魏在華夏文化與歷史鏈條中的正宗身份。
與此同時,北朝君臣也還致力于不斷削弱甚至消解東晉之正統性,南北正統爭奪和文化沖突遂呈現出異常激烈的態勢。如南北使臣互聘就更多以折服對方為目的,以維護己方正統。陳慶之使北時曾云“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當在梁朝”,楊元慎則予以反唇相譏,并從地理中心論的角度突顯北方乃正朔所在之優越性。北魏時,南齊劉纘奉命出使北魏,謂:“此山去燕然遠近?”。北魏主客令李安世反唇回曰“亦由石頭之于番禺耳”,斥南齊為蠻夷。他們的言辭既是政治宣言和立場宣示,也是正統文化觀念的呈現。受此影響,南北雙方對己皆充滿心理優勢和正統自信,對彼則充滿警惕和敏感。《洛陽伽藍記》卷一所云的“推過于人,引善自向”正是各政權在文化上互相詆毀以構建有利于己之文化形象的慣常手法。這不僅反映在官修史書與政治外交場合,也大量存在于民間和社會大眾的文化觀念中,并與華夷、南北等固有觀念相糅合,從而使南北朝時期的正統對抗與爭奪顯得復雜而多元。
此風所扇,文學創作與交往遂再次成為爭顯優勢、建構正統的重要場域。首先,文學的傳播與接受體現了征服與征服者的歷史。《羌胡伎》《橫角鼓吹》等曲多源于北境,其辭亦多以胡語寫就,傳入南朝,雖以異國情調帶動起新的流行趨勢,但“歌辭虜音,不可曉解”,在南北對立的背景下,南人對于北人曲辭的翻譯與接受必先經過心理和情感的認同,從而使歌辭烙下文化沖突和正統之爭的印記。《魏書·祖瑩傳》嘗載,王肅自南入北后,官拜尚書令,曾于尚書省內作《悲平城》一詩,為彭城王元勰誤作《悲彭城》詩,從而使一場詩歌創作與吟詠活動中暗含著緊張、激烈的文化沖突。“平城”與“彭城”在雙方詩作中均以極具主觀色彩的政治景觀存在,因而在正統爭奪中具有深刻的象征含義。彼此對對方故土和記憶的傷害,顯示出濃郁的文化對抗意識。
另外,據《洛陽伽藍記》載,王肅所娶北魏(陳留)公主于詩歌應答如流,反應敏捷、承接巧妙均顯示出北魏洛陽時期貴族婦女于文學上的造詣深厚。然而楊衒之隱藏在其中的文化態度頗可玩味,其以北魏為本位的文化心態,使《洛陽伽藍記》一方面借文字以達到抑制南朝文化之目的,另一方面又積極維護并夸飾北人成績,以彰顯、提升北朝的文化品位,褒貶損益之間,“正統在我”的心理隱然可見。
使臣作為國君之代表,維護國體之正統乃其職責所在,然一旦文學交流有損于正統建構,則文學亦會因此成為定義彼此的工具。“梁常侍徐陵聘于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徐陵雖在北地對魏收文集予以接受,但其一旦返回南方,則沉之于江,這固然與二人詩美標準之差異性體認有關,但更與徐陵代表的南方文化自身所充斥的文化優越感有關。徐陵對魏收的做法,魏收又施于傅縡,甚至將其贈詩譏為“以蚓投魚”,借貶低對方以建構自我文化優勢之動機甚明。
隋唐之際正統追尊與文學融合
公元589年,隋滅陳而一統天下,現實政治中的外繼性正統對抗遂暫告結束,但隋唐政權究竟以梁陳、西魏北周、東魏北齊何者為政治統緒,成為擺在隋唐君臣面前的重大政治問題。對此,官方與知識思想界的認識似并不一致。早在隋滅陳后不久,楊堅就與群臣自覺繼承了北周的正統秩序。之后,李唐代隋而起,依五德轉移說推導,奉周、隋子孫為二王后,自覺繼承北朝法統。天寶八載(749年)七月,玄宗詔封元魏后人為韓國公,意味唐室將其所繼承的北朝法統已由隋、周上溯至北魏了。
綜合來看,隋唐的北朝正統論,基本遵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的秩序展開。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滅陳,國家一統,政治與地理版圖雖已一體,但文學與美學上的對立仍在持續,數百年對立所致的文化隔閡難在短期彌平,其必以慣性影響特定時段的文學、文化演進。
在《隋書·文學傳序》中,魏征對南北朝文學的觀察主要聚焦在北魏太和元年(477年)至北齊天保十年(559年)這八十余年間,并體現出如下特點:
首先,其以北魏—東魏—北齊的歷時性敘述路線,表明魏征對文學的觀察與其對正統歸屬的考量基本一致,都是在東魏—北齊的視角下展開的。而對南方文學的評斷,則基本是以北方文學為背景和坐標的,是在北方(北齊)話語體系中展開的。其次,魏征對待南北文學表面雖似公正折中,實則暗含正統之爭下的文學優劣判斷。其論述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觀念上:內容(詞義)/形式(宮商)、陽剛(貞剛)/陰柔(清綺)、理性(理勝)/感性(文過)、實用(時用)/抒情(詠歌)。魏征對南朝文學的表彰截止到梁武帝天監年間,之后他對宮體詩予以抨擊,云其“詞尚輕險”,從而給宮體詩以“亡國之音”的政治評價。與此同時,魏征還利用其“受詔總加撰定”的身份“對南方文學頗加指責,而獨厚北方文學”。以往論者多從儒家角度辨識其意義,其實當中亦蘊含文化正統爭斗中取勝一方的眼光。文學多與道德捆綁,成為政治的祭品,尤其是在南北分裂動蕩的局面下,北方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勝利必然帶動對南方文化的強制性收編。
隋唐一統后,南北對立從原本政治、地域的分裂轉化為文化隔閡,南人所一力推行的“南文/北武”逐漸被“南文/北質”的二元結構所代換。文/質這對概念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具有悠久歷史。在南北朝時,南人出于政治需要,將北方塑造成蠻荒、自然的邊地,以強調北人之鄙野。然“自然”是一個意涵模糊、富有張力的概念。從消極層面看,“自然”是粗疏、荒蠻的;從積極方面看,“自然”又是質樸、天然、不事鉛華的。在初唐,勝利的北人接受了“自然”的界定,但著力消解其“荒蠻”的一面,強調其“質樸”的一面。隨著“自然”涵義的遷移,雖然統治者繼續把南人置于“文”的地位,文/質的二元對立卻產生了新的意義。在“質”映照下的“文”,已不具有積極的意義,甚至有過度雕琢和修飾的貶義。初唐君臣將南北朝正統之爭背景下相互否定的歷史再次重演,通過對“質”之價值的肯定與崇敬,對“文”之意義的弱化,其實質仍是樹立北朝隋唐正統論的觀念。
質實而言,南北兩種異質文學的激烈碰撞,只能通過對傳統的梳理,建構彼此皆能接受的文學源流與傳統,方能真正完成文學融合。對南北朝文學而言,彼此都認可并接納且時間距離最近的文學傳統便是建安文學。在北朝文學“尚質”傳統的影響下,盧思道、薛道衡等在創作中多展現出豪壯悲涼的特點,其所蘊含的生命精神的回歸正契合建安文學特質。遺憾的是,他們對此并無理論闡發,進而難以帶動一時創作風尚轉向。于南方文人而言,對北朝文學的疏忽并不妨礙其理論思考的深入。劉勰指出南朝文學具有“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的缺陷,類似的反思性話語在鐘嶸《詩品序》、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中也有體現,但這都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自我圓滿,要具有可操作性,同樣需要在創作中尋求可供參照的對象。另外,南朝文學批評對建安文學的高度評價并不意味著他們在理論上意識到南北文學融合的必要,而只是表明他們已認識到南朝文學對建安文學的繼承是片面的,從而呼喚被遺忘的生命精神的回歸。
結語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中古各政權有關政治正統地位的建構與爭奪對文學發展之方向與內在演進所產生的影響深巨。文學作為意識形態,它不但被社會文化中現存的意識形態所決定,同時又在生產著意識形態,塑造甚至改變著意識形態。因此文學創作也主動參與到正統建構的過程中去,為其提供爭奪場域和形象建構的手段,形態各異,卻都服務于“推過及人,引善自向”的目標。二者互相涵育,不僅促進了十六國至南北朝文學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呈現,也為隋及唐初南北文化與文學的真正融合提供契機和可能性。唐代文學創作高潮的到來,就是各種文化與文學元素經過“百川東到海”式的激蕩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