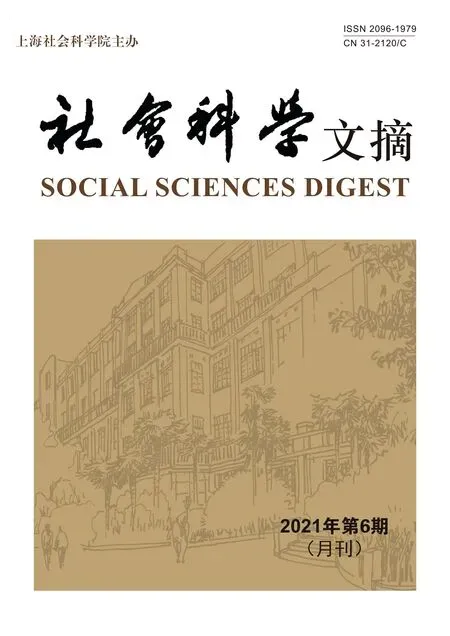二里頭文化:華夏正統的締造者
文/曹兵武
二里頭文化以豫西洛陽盆地二里頭遺址及其典型遺存命名,目前已發現遺址500余處,其分布以豫中和豫西的環嵩山周邊地帶為中心,鼎盛時期北至晉中,西至陜東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區,南至鄂北,東至豫東,其影響范圍則更大。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二里頭遺址經過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測年和校正,時代大致上被確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間。二里頭文化崛起并興盛于傳統中原的腹心地帶;在時間上晚于河南龍山文化而早于以鄭州商城為代表的商代二里崗文化;二里頭遺址本身也是鄭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區僅有的超大型、內涵豐富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因此,無論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都不影響其在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早期華夏文明形成與演進中承上啟下的關鍵性角色的地位。從考古學文化內涵來看,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遺址也的確有諸多非同一般的表現,與之前和同時期的諸考古學文化包括龍山時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遺址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點。
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橫空出世
首先,二里頭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個新文化。很多學者都從類型學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過二里頭文化的淵源。隨著考古學發現與認識的深入,多數學者同意,就作為當時日常主用和考古學文化最精確標記的陶器組合來看,二里頭文化主要是在當地河南龍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類型和嵩山以北的王灣類型融合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豫東的造律臺及豫北的后崗二期文化等因素,經短暫的新砦期快速發展而成。當然在此前后,山東、安徽尤其是西北方向的陶器等文化因素也曾大量涌入這一地區。因此,二里頭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明確地表現出這種對周鄰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廣泛吸收與整合創新的特點。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學文化往往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變或者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轉折性變化,二里頭文化顯然是選擇性地甚至是主動地聚合了周鄰包括遠方的多個考古學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頭遺址所見鑄銅、玉器與綠松石加工和應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貝等新鮮因素,大都是廣泛借鑒并經過改造提升和賦予新的內涵后再加以使用。在其社會的經濟基礎和考古學文化的物質形態中,傳統中國的五谷六畜,除了馬,其余已初步齊備,復合型的農業經濟儼然成型,同時已有了高度發達并專業化的制石、鑄銅、造玉和制骨等手工業及專門作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當屬率先采用復合范制造青銅容器并作為壟斷性禮器的高超技術。顯然,相對于之前多地零星發現的并未在生產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類小件銅制品,只有二里頭文化才可以被視為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青銅時代的源頭。
其次,二里頭文化在當時的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了突出的超越性。二里頭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廣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僅超乎原有諸文化或文化類型之上,還向周邊地區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響。就縱向時間軸來說,二里頭文化的出現是其所在地區經過仰韶時期區域一體化的高峰、分化、相對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較大范圍的統一與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階段一樣,也對周鄰文化產生了廣泛的輻射性影響。如果以二里頭式牙璋、雞彝等特色標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來衡量,其輻射范圍之大完全不亞于仰韶文化頂峰階段的廟底溝類型。不同之處是,二里頭文化的出現讓周鄰諸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如東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東南的馬橋文化等,以及長江中游地區的考古文化——黯然失色了,這些周鄰文化不但缺乏二里頭文化那樣的高級產品,而且原來已有的發達的制陶業等手工業也顯示出粗鄙化趨勢。這顯然是這些文化的社會上層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受到抑制性影響之后,對意識形態物品的有意放棄所致。
以上兩點使二里頭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時期周鄰乃至當時東亞地區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學文化,也不同于各地百花齊放階段的諸文明制高點,如紅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二里頭文化的脫穎而出具有鮮明的超越性,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華夏正統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區形成的標志,誠如許宏先生的概括:二里頭文化讓早期中國文明格局從滿天星斗發展到月明星稀。
文化大統的形成與地域協同防御模式的出現
蘇秉琦先生認為,早期中國各文化區基于早期農業的區域性文化傳統,都經歷了古文化古城并次第發展到古國這一階段。戴向明先生認為,龍山時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可能已經走到了王國階段。而二里頭文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更進一步走到了王朝——萬邦來朝的階段。周邊諸考古學文化或者被二里頭文化所整合,或者要面向二里頭文化來朝拜正統,同時也受制于這個正統所代表的一個更大的文化大傳統的鉗制。而此后的歷史進程表明,在早期中國文化的相互作用圈中,還上演了接續這個正統乃至爭奪這個正統的歷史趨勢,直到秦漢時期穩定的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比如,商與周都是與二里頭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卻共同接續完成了同一個文化正統,不僅加盟了這個文化大統,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樣將其發揚光大。而在考古所見的整個早期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里邊,可以認為是二里頭文化締造了這個超越各地區早先的族群文化傳統的大傳統,并讓其他區域性文化傳統主動或者被動地降格為小傳統。
自農業和定居的村落產生之后,各地逐漸孕育的地域性文化傳統都可以被視為一個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體。這種傳統可以細分為血統、器統、藝統,還有心統(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統、學統、正統)等,它們各有譜系傳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個特定地理單元內基于早期農業的萌興,緣于血緣關系自然地發生、發展和擴展,并與周鄰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間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其中,仰韶文化曾經借助區位優勢和大暖期的環境機遇,在區域傳統的形成與發展中占得先機,率先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據廣大分布范圍,為華夏傳統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語言基礎。
在以農業部落為載體的區域一體化高峰階段,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普遍發展出以內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設防聚落為統領的金字塔式復雜社會。二里頭文化則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地域協同式防御模式,以鞏義稍柴、鄭州大師姑和東趙、新鄭望京樓、孟州禹寺、平頂山蒲城店等多個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對二里頭大邑形成拱衛之勢,而二里頭自身則僅在行政中樞部位建設宮城進行有限的防御。二里頭和這些次級中心聚落的所在,構成文化的中心區,而超出這個文化中心區的重要地點,比如交通要道或關鍵的資源地,則運用防御性極強的中心聚落將其置諸管轄之下,如夏縣東下馮、垣曲古城、商洛東龍山等。這一全新的空間防御與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崗文化全盤繼承并擴展。考古發現表明,鄭州大師姑、滎陽西史村、新鄭望京樓、垣曲古城、商洛東龍山等重要遺址紛紛在二里頭文化消亡之后在二里崗階段進行了改建或重建,繼續扮演區域性中心聚落,和新崛起的鄭州商城形成共榮關系。二里頭自身也在延續的同時漸漸被近旁的另一個二里崗文化的大邑偃師商城所鎮壓、取代。顯然,這些現象應該是國家或者國統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現。
以國家政統為核心的文化正統的誕生
二里頭文化這種能夠整合各區域傳統的更大的文化傳統,或可以政統之始視之。區域傳統演進過程中自然也伴隨社會分化、統治與被統治的分層之分,以及相應意識形態的詮釋系統,但族群內部和族群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則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階級和各類文化因素的系統嵌套和整合。因此,盡管早期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里的若干地區都曾經發展到復雜的初級文明社會,但終未邁過國家文明的門檻。二里頭文化在對當地和周鄰諸族群的文化要素的傳承、交流、吸納、整合、改造和輻射中,締造了一個超越區域內部不平等乃至區域間相互攻擊、掠奪的新型的相互作用與社會治理模式,并可能達成了某種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識形態共識。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超越諸族群文化傳統之正統和大統,又被隨后的二里崗文化所接續。顯然,被接續的正是以國家政統為核心的一種華夏文化正統,此后,它又繼續被周人和秦人接續并發揚,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的中華帝國演進。能概括這樣一種政統及其文化和社會形態的,也只能是“國家”這一新的發明創造。所以,中國的國家文明自二里頭文化始。
支撐這一國統的正統文化觀念,比如宇宙觀、意識形態系統、祭祀系統、禮制系統等,同樣在二里頭文化中得到快速發展并被傳承下來。考古發現主要體現在繼承創新的高等級器物的生產工藝和組織形態方面,其中尤以青銅禮器及其代表的禮儀文化最為重要。二里頭遺址迄今已發現的青銅器超過200件,有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幾乎包括當時東亞大陸各文化中的各類青銅器類,而青銅容器則為二里頭文化綜合各地青銅冶煉、制陶工藝及造型技術和觀念等所進行的獨創,已經發現的器類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組青銅禮器。鑄銅作坊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緊挨宮城南部并以圍垣環繞,使用時間自二里頭文化早期至最末期,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中國鑄銅作坊,并且可以肯定是由宮廷管理并進行生產的。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極具特點,和東部海岱、紅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飾玉、巫玉以及西部齊家、石峁、清涼寺等文化的財玉、寶玉等在制作與使用方式上也表現出根本性區別,比如玉鉞、玉刀、玉璋、玉圭等,盡管較多地借鑒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與其本來的裝柄方式和用途已經無關,而多直接用在各種場合中表現貴族的權威。發掘者許宏先生推測它們或許已經是作為在宮廷上昭示君臣關系的“玉圭”或“笏”來使用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二里頭階段已超越了原來喪葬與巫術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禮玉文化。再往后,又進一步借鑒并整合各地尤其是東部巫玉豐富的文化內涵,發展為更加完善的中國傳統禮玉體系。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義已經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顯然,二里頭這些復雜的高等級器用與工藝品背后蘊含著新的意識形態觀念,已經形成了與國家正統相對應的新的知識、含義和禮儀系統。
由此可見,二里頭文化在中原較廣闊的范圍內實現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與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結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均體現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態。究其原因,一是得益于中原內部族群與文化互動的前期基礎和特點,二是受到自仰韶晚期以來中原周圍次第進入區域一體化高峰的各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受到源自西北地區的人群與新鮮文化因素的強烈刺激。到龍山時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進和環境的變化,各地考古學文化間互動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強。中原地區因為仰韶時期之后相對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對適中的地理環境,可能還要加上黃河在新氣候環境背景下沖積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間這個因素,成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個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劇向這里聚集,形成交疊融合的態勢。同時,由于羊、小麥、冶銅等新文化因素的引進,加上持續的高強度開發與環境變遷,在距今4300年左右,北方地區人口大規模增加,文化開始蛻變,相互之間的競逐空前加劇。今天的長城沿線地帶在這一階段興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樣的巨型中心軍事聚落,這可能也成為相當廣闊地域內的野蠻征服掠奪者迫使晉南盆地地區人口大規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復雜社會的原因。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經試圖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經初步跨越國家的門檻,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時空張力下被顛覆而崩潰。作為仰韶興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文化的動靜不可能對中原腹心地帶的族群沒有影響。它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自己的區域性整合,并主動向各方出擊,尤其是著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將晉南作為資源要地和緩沖地帶置于自己的管轄范圍,以尋求在先進文化資源和日益復雜的互動格局中占據比較優勢的地位。
趙輝先生在《“古國時代”》一文中將這一波巨變概括為社會復雜化或中國文明形成進程的第三波,但除了趙先生所說時空上的異同之外,這一波的模式和意義也和前兩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發性的,是農業文化傳統次第進入區域一體化的高潮,仰韶文化拔得頭籌,而東方大汶口—龍山、東北紅山、東南的崧澤—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嶺—石家河等各有精彩華章,甚至后來居上,快速步入高級酋邦社會。其中大汶口、屈家嶺等環境優裕、物品豐盈型社會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舉挺進中原,估計也會有不少移民趁機填補此地仰韶后期的相對空白。但隨著第二波源自北方的激蕩,長城以北自廟底溝二期以來各種快速變異和新穎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斷南下,其多米諾骨牌效應橫掃長江中下游甚至更南的東亞大地,讓龍山時代的文化格局為之驟變,區域傳統間的競逐進入白熱化階段,連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樣的巨型中心聚落所表征的早期文明也轟然坍塌。而以二里頭文化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了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鑄出以國家為載體的華夏文明的正統和文化自覺。
結語
古人常說逐鹿中原。中原地區的地理位置確實便于各族群和文化的你來我往,但是如果說仰韶文化還只是一種因為人口增長引發對外拓展的不自覺的奠基與輻射效應,那么二里頭文化才是真正的整合式聚變,顯示出吐納有序的輻輳效應,使得中原地區在東亞大地脫穎而出,最終樹立起華夏文明的文化正統地位。所以,環嵩山的中原被稱為華夏文明的搖籃不僅是當之無愧的,而且是相當獨特的。這里既是東亞大陸南北地理與氣候的交匯地帶,也是中國地勢西北高地和東部低地的交接之處,還是黃河中下游黃土流失和堆積的轉換點,溯河而上和沿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應十分明顯。不同時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術、產品等在中原地區層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條件下易于開墾的土地具有極強的黏著力,中原地區很早就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罕見的族群和文化熔爐之一,由此成為早期華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選擇。
人類在東亞大地上的活動由來已久,但是真正的文化意義上傳承不斷的族群集團和國家文明的形成,則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產生以來各區域性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個過程包括了舊石器時代業已奠基的南北兩大板塊的碰撞融合、東亞基于早期農業社會的區域性文化傳統及其相互作用圈的充分發育和攪拌發酵,甚至包括西亞、中亞文明因素的不斷涌入和刺激。華夏文明核心從仰韶的雛形到二里頭的定調,實則是一個不同族群、技術、物品、觀念以中原為軸心的不斷交融、磨合的長期過程。作為各種文明要素集大成者的二里頭文化的橫空出世,已經是不斷融合、反復融合、合之又合的結果。但是,二里頭文化以其獨特的模式合出了新意,合出了自信,并合出了一個跨族群的格局和境界,最終合成了一個脫穎而出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和大統,凌駕于各區域性文化傳統之上并被整體性地傳承和光大,整個東亞文化相互作用圈由此完成了從多元到一體的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