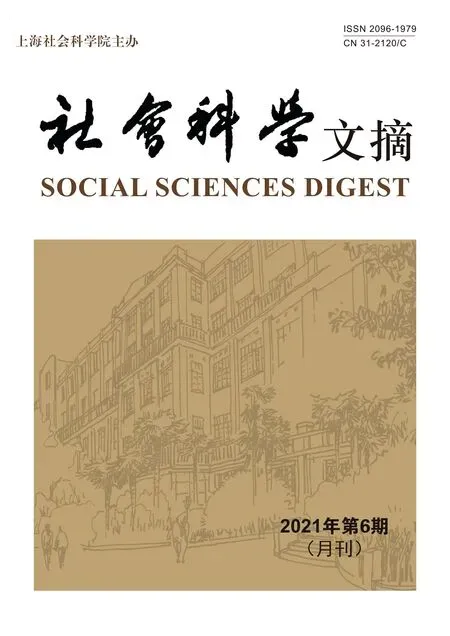近代西方人西藏研究的國家競爭與學術流變
文/崔華杰
近代以來,以傳教士、游歷家和外交官為主的西方人深入西藏地區(qū)開展宗教傳播、資源勘測和地理調查等工作,在探查地方的同時留下不少筆記。其不僅記錄了在這一地區(qū)的所見所聞所感,還著意描述經行地的物產、民族、典章、制度,尤其史地情形。部分西方人專意蒐集、整編漢文史料,加以外文文獻考辯詳釋,疏通中外載籍譯名,考釋西藏的地理、歷史與人事,有時還引入史學輔助學科對相關文獻和文物做深入考察,從而在研究上出現了學術化和史學化的傾向。
立足印度:殖民時代下的地理勘察和情報搜集
近代西方人對西藏的學術興趣,始自于政治和經濟利益所衍生的文化需求。18世紀以來,英國逐漸侵蝕印度,將之作為在亞洲進行殖民擴張的據點。西藏與印度隔山相望,不僅擁有神秘的宗教文化、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且是中國西南地區(qū)的關口,英國對打開西藏門戶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
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東印度公司先后派遣喬治·波格爾(George Bogle)、塞繆爾·特納(Samuel Turner)等人赴藏搜集情報。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英國已掌握了西藏的一些信息,有多部地理游記問世。1834年,駐孟買英軍上尉亞歷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出版《印度到卡布爾、韃靼和波斯紀行》,在中亞地理概述一章涉及布哈拉和北京與西藏的地理溝通與人員往來。1836年,奧地利博物學者查爾斯·胡格爾(Charles Hügel)發(fā)表的行記講述其在喜馬拉雅山脈和喀什米爾山脈一帶的考察。東印度公司隨員威廉·穆爾克羅夫特(William Moorcroft)和喬治·垂柏克(George Trebeck)曾深入喜馬拉雅山一帶調查地理概況,合撰《印度、旁遮普到喜馬拉雅山麓之行(1819—1825)》一書。
可以看出,這時地理游記成為西方人了解西藏這個“神秘之地”的主要渠道,并有著學術轉向的變化。從學科屬性來看,游記本是文學的一種書寫形式,原本用來贏得市場,娛樂大眾,因而在歷史和地理的描述上頗有異國風情而備受讀者青睞。然而,隨著與殖民主義的相伴隨行,游記開始承載西方人認知西藏過去和現在的信息資源,其文本的表現形式和研究指向發(fā)生改變:文學中的“娛樂性”開始向學術中的“求真求實”改變,從贏取市場青睞的通俗性讀物開始變?yōu)閲烂C認真的學術研究著述。由此,西方人的西藏研究在近代時期波瀾初起。
走向合作化:專業(yè)學會引領下的研究分流
西方人在西藏研究第一階段的成果,基本上是站在域外觀察西藏的產物,且多散見于個人努力,可謂是東鱗西爪、難成系統。隨著探索的深入,特別是經專業(yè)學會的推動,此種缺憾逐漸在學術的發(fā)展演進中得到彌補。
盡管此時已有多部地理游記涉及西藏研究,其所建構的知識話語卻難盡如人意,以至于時人感嘆說“放眼歐洲,沒有一位西藏研究者”。這種局面在19世紀中期發(fā)生了改觀。經緯度坐標知識的細化和觀測方法的改進提供了專業(yè)方法的保障,世界知識的需求促進了地理的探險和發(fā)現,印度帝國的建立帶來了擴張殖民利益的欲望,其結果促使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等地理學研究專業(yè)團體開始重心東移,意欲發(fā)現“神秘之地”西藏。為此,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主席羅德里克·麥奇生(Roderick Murchison)號召開展“喜馬拉雅、西藏和印度斯坦”一帶的地理探測和學術研究。
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為代表的專業(yè)學會不僅積極鼓動和集中會員力量對西藏開展專題研究,還將其會刊打造為學術交流的平臺,發(fā)表關于西藏研究的各類文章,并呈現如下的研究特點:
首先,通過實地調研和文獻研讀,厘清西藏的“地理外延”。1850年,基督教路德公會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建議開展對藏東邊界的實地考察。1872年,英國軍人蒙哥馬利(T.G.Montgomerie)潛入西藏,留下關于南部的考察報告。1875年,克萊門特·馬克海姆(Clements Markham)按地理方位將西藏劃分四大區(qū)域進行論說。
其次,探查地質、物種和經貿信息,挖掘西藏在殖民擴張中的經濟功用。西藏雖處高原,但物產豐饒,鹽金兩礦豐富,西方人頗為垂涎。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支持下,一批西方人打著科學考察的幌子,競相探查西藏的經濟情形。如蒙哥馬利在數次涉藏探險中探查金礦和鹽礦分布,英印官員海華德(G.W.Hayward)深入葉爾羌和喀什探查鹽業(yè)產區(qū)及商業(yè)流通區(qū)域。
最后,利用中外文獻,探討西藏的宗教特質和民族起源,界定西藏的“身份特征”。一是重視西藏佛教的源流及其宗教生活。如《美國東方學會雜志》呼吁要重視從佛家典籍搜檢佛教歷史的學術路向。二是探尋西藏所謂的“種族起源”。這類研究多站在基督宗教本位,尋找西藏與歐洲在文化和種族的聯系。如站在語言學的角度鉤沉西藏與雅利安人的種族方面關系,如從人種學分析藏族的身體特征,以輔證西方學界廣為流傳的“中國人西來說”。
總之,在專業(yè)學會的推動之下,西方人在西藏研究上呈現合作化的態(tài)勢。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考察實質上還不是一種“在地化研究”,即深入西藏、利用漢藏文獻開展西藏歷史和現實的書寫。對于此種不足,羅德里克·麥奇生在總結學會1871年度工作時有所認知,強調在研究中“不僅要重視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語言、歷史和考古學成果,更要了解馬可波羅足跡遍及區(qū)域之地志”。這一進入中國本土并開展“在地化”研究西藏的號召在中英《煙臺條約》簽訂之后成為現實。
“大角逐”:英俄學術競爭與研究的史學化
1875年英國以馬嘉理(Augustus Margary)事件為由強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及“另議專條”,允許外人來藏游歷,自此西藏門戶大開。先是英國公民以個人身份前往西藏地區(qū)探險,如1878年英國軍官吉為哩(William John Gill)從川西深入藏東。接著,英政府公然派遣使團,以期與西藏進行政治上的接觸。1886年印度孟加拉政府財務秘書馬科蕾(Colman Macaulay)經清總理衙門準許,率使團往藏游歷。
較之英國,俄國在西藏研究上起步略晚。憑借沙俄在《北京條約》攫取的烏蘇里江以東大片領土,該學會在華的地理調查有了活動空間。沙俄帝國地理學會派考察隊南下,尤以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y Prjeválsky)為首的考察團隊在西藏地理調查上能與英國一較高下。普爾熱瓦爾斯基被譽為“現代第一個成功到達羅布泊的歐洲人”,在青藏高原地區(qū)開展的“科學偵察”,“在山志學、水文學和民族學等領域的成就為其他旅行者難望項背”,先后獲得歐洲多國地理學會的獎章。
在英俄“大角逐”的國際關系背景之下,以地理調查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學術研究,不管是在經費支持還是研究目的方面,事實上均難以擺脫與殖民主義相伴共生的關系,正如英屬印度總督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談及西藏地理考察時所說:“政治可以輕而易舉地偽裝在科學的外衣里。”然而,剝離偽裝在科學外衣里的政治目的,也應看到背后涌動的學術潛流,其主要表現有:
從學科發(fā)展上看,西藏研究史學化傾向明顯。英俄兩國在西藏的地理調查,不管是關注地文特征、山川河流、地質構造還是聚焦于各類自然資源,在學術歸類上更接近于地理學當屬無疑。隨著對地輿、物種、資源等地域的物理情形研究的深入,西方人開始重視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等人文元素在西藏研究上的作用,既著意對研究對象的地理與環(huán)境做共時性表述,更嘗試從歷史流變、地理沿革和民族情形做歷時性分析,呈現出由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向史地研究的學術變遷路向。如1907年在倫敦出版的《“未知王國”:一部關于西藏西部的歷史》一書,有論者在評述該書時指出,除對藏西地區(qū)的地理情形做概貌描述,并涉及西藏之方言、風情、民俗和社會之外,該書最大的學術價值還在于對藏西地區(qū)自7世紀中期以降的歷史進行了“清晰且連續(xù)的記述”,蘊藏著“歐洲人難以利用的諸多歷史記載”。
在研究方法上,西藏研究強調學術的總結、交流與爭辯,注重史學批判。如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對沙俄帝國地理學會、法國地理學會、意大利地理學會調查成果密切關注,成為學術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學術爭辯方面,如有學者指出法國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名著《在韃靼和西藏旅行》在史事描述上“全然錯誤”“文過飾非”,然而英國漢學家裕爾(Henry Yule)等人予以辯護,認為古伯察之記述難免掛一漏萬,其長于歷史敘述的優(yōu)點應予以肯定。總之,在史學交流與評判的過程中,西方人不僅重視史料來源和征信,如考釋前人文獻史料、訂正史實、疏通中外譯名、標注重要文獻出處,還重視對已有成果的分析和評價。這不僅是西方人西藏研究在專業(yè)化上的表現,更是其走向史學化的重要表征。
在理論應用上,跨學科意識萌發(fā),促進西藏研究多面向深入。考古學、古文字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被運用到西藏研究中,拓寬了單一學科解釋的狹窄路徑。如斯坦因(Marc Stein)在中亞地區(qū)所從事的專業(yè)考古,利用實物史料的傳播歷史來解讀“中國古代宗教和藝術早期發(fā)展階段”以及“中國古代文化生活的重要階段”。
總之,在英俄競爭的背景之下,西方人西藏研究盡管帶有現實性和功利性的特點,然而還是呈現出一些顯而易見的學術變化:內容上從傳統的地理、地質、經濟等物質生活延伸至語言、思想、宗教、政治等精神領域;方法上從社會、民族和生活的事實描述過渡到民族身份認同、政治外交關系和文明進化的學理分析。這樣,西方人西藏研究所發(fā)生的知識體系轉化,即由區(qū)域特征調查為主的地理學轉向以史地研究為表現的歷史學,這也是學術演進的自然結果。
地方、國家和洲際:美國西藏研究的區(qū)域視角
在西藏研究上,與形成“大角逐”學術競爭的英俄兩國相比,美國無疑屬于后起之秀。雖然早在1843年,美國東方學會首任會長約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在其會刊創(chuàng)刊號上提請注意“韃靼、西藏和蒙古”等地,然而囿于此后的中國國內現實,美國在西藏研究上不得“地利”之便。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帶團游歷藏邊地區(qū),美國在西藏研究上始為國際學界矚目。
清廷覆亡前后,西藏政局不穩(wěn),處于多事之秋。1910年,十三世達賴離開拉薩向印度流亡。1912年民國肇始,將西藏納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此后,在波譎云詭的地區(qū)政治環(huán)境之下,美國學界號召加強對中國的區(qū)域歷史研究,以增進對現實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理解。1921年美國教會史家賴德烈(Kenneth Latourette)指出:“現在中日兩國及其鄰邦的問題,更是引起西方關注,歐美學者逐漸有了責任和權利去研究這些民族的新近歷史和遠古歷史”,“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我們更睿智地理解位于太平洋彼岸的邦國”。
出于政治目的,長期以來西藏在部分西方人的研究視域里乃是一個“獨立的”政權實體。與這種政治訴求互為表里,此階段西方人研究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立足地方審視西藏一地,突出西藏的特質,在語言文化、宗教傳統、文化歸屬和區(qū)域關系上構建西藏的身份認同。
對西方人而言,語言是身份認同最易辨識的標簽,這是因為語言不僅是族群內部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保存和傳遞民族文明的媒介,可以說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藏語屬于哪種語系、語族、語支和語種?對民族、政治、社會和文化產生的影響如何?因此,對藏語中的外來語、西夏語與藏語的聯系、藏語書面語言的起源等語言學領域的研究著述在民初之后數量見多,漸為學術風尚。語言之外,宗教則是西藏被外界容易識別的另一個符號。佛教歷史、佛教經義、佛教人物均有研究者涉獵。在建構語言和宗教的身份屬性之后,自然推演到民族這一概念。
概言之,西方人利用藏語文獻,強調西藏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態(tài)的獨特性,表面上主要探討西藏的身份屬性,但結合當時的國際政治環(huán)境,明顯能揭示出其本質乃是強調西藏與中國內地的身份差異,意圖虛構西藏乃是獨立政權實體的形象,以滿足其外交利益訴求。然而,他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政治現實是,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始終實施著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這種政治外交現實,不得不促使西方人將西藏與內地連接起來,具體而言就是站在國家層面分析西藏與內地的互動和聯系。
站在國家層面觀察西藏,首要前提就是承認西藏乃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qū)域。首先,在部分西方人的地理話語表達中,西藏為中國固有土地已確實無疑,如在1925年一篇探討西藏與東南亞地理關聯的文章中,西藏這個地理名稱前已加綴限定詞“中國”,標注為“中國西藏”。接著在政治話語中,西藏也被納入中國政體的范疇,如柔克義撰寫長文回顧西藏與歷代中國中央政府之關系,向西方介紹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政治整合和文化影響。
承認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的行政權力之后,站在國家層面觀察西藏就擁有學術合法性和正確立論的前提。1939年出版的《西藏:從中文史料看其地理、人種和歷史概論》一書,即是利用漢藏文獻詮釋西藏史地。這種“中國取向”在理論上的益處,正如1948年《太平洋評論》發(fā)表的一篇文章的概括,其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主流文化”和“亞文化”之別。所謂“主流文化”體現于內地村鎮(zhèn)社群,其基礎是廣泛存在且規(guī)模較小的農業(yè)區(qū)域;“亞文化”則流行于邊疆地區(qū)。因此,只有理解處于地理邊疆的亞文化地區(qū),“才能正確看待中國”。
沿襲站在國家層面審視西藏這個學術路向,還有研究“攀升”至洲際的層面予以詮釋。這種“洲際取向”的學術源起,事實上概因西藏在溝通中國內地與邊疆、聯結中國與亞洲的地緣優(yōu)勢。1925年,斯坦因結合其科學考察經歷,指出內亞這個地區(qū)因“地理特色”而在世界歷史文明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定義的內亞地區(qū),在地理位置上是“北起天山,南倚將西藏分割成盆地地區(qū)的昆侖山脈”。后來,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認為所謂“內亞地區(qū)”主要是指未擁有海岸線的地區(qū),“包括西藏地區(qū)、外蒙古、阿富汗以及蘇聯下屬的一些共和國,亦涵蓋中國西北地區(qū)的甘肅和寧夏地區(qū)”。不去細究“內亞”的具體地理范圍,我們大致可以發(fā)現西方人將西藏納入洲際乃至世界的地理視角,意在從內陸空間來加深對亞洲區(qū)域歷史乃至全球歷史的理解。
如果說地方視角強調的乃是西藏相較之其他中國區(qū)域所彰顯的“個性因子”,那么,國家層面和洲際研究取向的落腳點則是揭示西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共性因子”。歸結到學術實踐層面,站在地方、國家和洲際等不同空間維度考察可以起到彼此補益之作用,正如拉鐵摩爾在內亞視角上的立論所言,“既能整合伊朗、印度、中國、日本和俄國這些外環(huán)研究”,“又能深入蒙古、土耳其、通古斯—滿洲和西藏等內核研究”。由此觀之,美國學界吸收“外環(huán)”和“內核”之成果,注重理論創(chuàng)新,將西藏納入區(qū)域研究的學術實踐,最終實現了西方人西藏研究從地理游記轉向區(qū)域研究的學術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