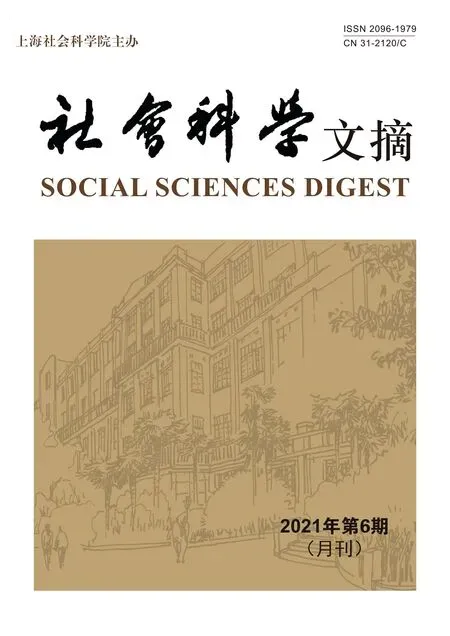西方史學思想中的歷史想象觀念探析
文/金嵌雯
“imagination(想象)”一詞系源于拉丁語“imāginātiōnеm”,最初有客觀事物在頭腦中的構想、摹仿、再現和描繪之意。在漢語中,“想象”一詞為動賓結構。《說文·心部》:“想,冀思也。”《說文·象部》:“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韓非子·解老》:“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由此,漢語的“想象”也有依據客觀事物在頭腦中進行構想之意。在現代哲學解釋中,“想象”基本意指“飛離在場”,即一種“使本身不出場的東西出場”的“能力”或“經驗”,它可以是一種回憶,也可以是一種在思想或心靈中對圖像或其他不是直接源自感官之概念的構想。通常而言,想象是文學和藝術家的必備工具。但想象是否為歷史認識所必需,卻是一個爭議中的話題。一方面,歷史學的要義在于求真,這要求史家嚴格依據史料探究過去事實,警惕想象參與;另一方面,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史家無法再感知、知覺或直接觀察的事件,就使過去不在場的事物再次顯現而言,想象對歷史學至關重要。關于想象在史家頭腦中發揮的作用問題,國內學者如張耕華、杜維運、李劍鳴等都曾作出論述。他們肯定想象是史家所能使用的一種思維工具,但同時認為史家要“適度”“平衡”“輔助”性地運用它,以確保歷史的真實。這樣的說法得到學界的大體認同,但仍留有一些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如果說想象確實是史家的一種思維工具,那它是必需的嗎?假設史家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證據,那么他還需要想象嗎?想象的參與是否意味著背離實在?本文試圖圍繞著這些問題,回顧和考察西方史學思想中不同學者針對歷史想象的思考,總結、比較其中的共識和差異,以期引發學界對歷史想象問題的重視。
想象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位置
受柏拉圖推崇永恒在場之“理念”的影響,與“摹仿”相關的想象始終在希臘哲學主流中受到懷疑和抑制。直到啟蒙時代,康德和維柯提供兩種對想象在思維中所發揮之重要作用的不同理解,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
康德將想象視為人類知識得以形成的先決條件之一。他認為人類具備著一種“創造性的想象力”,它是先驗的,發揮著溝通直觀與范疇、感性與知性這兩種本質上異質的認識能力的作用。它能夠把雜亂的表象帶到綜合中,又能通過時間規定與知性范疇契合,從而把同一性帶到綜合中。具體來說:其一,它可以把已不在場的先行表象在思維中再生出來,與繼起的表象綜合為一個完整的整體。例如,將第一天中午到另一天中午這段時間作為整體來思考。其二,它能夠通過“圖式”把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觀結合為經驗知識。例如,將感覺中直觀到的書和“書”這個概念綜合為看到一本書的單一經驗。因此,在知性建構人類科學知識大廈的過程中,先驗想象力扮演著積極的推動者和創造者的角色。同時,知性概念和經驗材料又規定著想象力:前者賦予其以必然性,不致讓其成為天馬行空的、盲目的東西;后者賦予其以實在性基礎,不致讓其成為一種虛幻的空想。
維柯則在不同層面理解想象。反笛卡爾者維柯認為,由于人創造了歷史或人類世界,因此人能夠認識歷史或人類世界。在原始階段,人類借助想象“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畫像”,形成“想象的類型”,從而“把同類中一切和這些范例相似的個別具體人物都歸納到這種范例上去”,形成對事物的認識。由于個體和范例間具有相似性,借由想象所得到的“想象的類型”必須被創造得恰如其分。因此,這些想象類型可以被視作真實的。隨著人類階段的成長,想象之中誕生理性。想象因而被維柯提升到與邏輯同等的地位上。如果說邏輯作為理解的一種方式,是抽象的,是對概念的推演,那么想象作為理解的另一種方式,是具體的,是對意象的運用。
康德和維柯對想象的理解深刻影響了之后學者們對歷史想象的認識。某種程度上,歷史想象便是這兩種想象雜糅的產物。在有關歷史想象的早期論述中,威廉·馮·洪堡認為,歷史認識不僅要觀察到孤立的、零碎的外部事實,更要憑借感覺、猜測去把握事件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和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創造性認識——理念,由此形成的歷史認識方可稱為真實的。而要把握內在因果聯系和理念,就必須運用想象。這種想象不是純粹的幻想,而是直覺或關聯能力。通過它,史家可以填充和聯結他所直接觀察到的雜亂無章的片段,找到個體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但不同于康德式想象獲得的普遍知識,洪堡強調歷史本身的多樣性和個體性。同時,洪堡也試圖區分出歷史想象與文學想象,他認為,不同于詩人,史家必須將想象置于對實在的經驗和觀察之上。洪堡的看法不是孤立的,到20世紀初期,我們仍然能夠找到其相似觀點。
對歷史認知中想象的論證
在洪堡時代,西方歷史學逐漸從修辭學中脫離出來,成為以科學研究為主要目標的獨立學科。這要求史學家把歷史學同神話傳說區分開來,告別用想象來構想真實事件的這種前現代行為。一些促成和接受專業化的史家有意識地試圖抑制想象。不論是客觀主義史家代表人物蘭克,還是浪漫派史家麥考萊,都認為想象在修辭上起作用,屬于次要的語言裝飾,史家必須自律地將論述事實作為第一要義。盡管麥考萊承認想象將使史家敘述“生動又感人”。他們的觀點代表著一種被普遍接受的但尚未被檢驗的“規范”:史學的求真意味著史家要憑借科學方法,盡量捕捉瑣碎的事物,發現過去“尚未講述的故事”,謹防想象在修辭上添枝加葉,從而使歷史記述與過去實在相符合。但實際上,史家的思維工作并非如此簡單,即使假定修辭中的想象能夠被排除出去(事實上這不可能),起著康德式認知作用的想象也無法被剔除。20世紀初,史學家艾伯特·哈特做了類似于洪堡的論述。隨后,柯林武德更為系統、更為有力地論證了歷史想象在認知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柯林武德認為,想象在歷史思維中發揮著兩種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史學家需要利用想象,在已確知的固定事實之間插入史料所不曾提及的東西。這里的歷史想象相當于一種理性推論,發揮著綜合式的建構功能,其將點狀的事實構成線,連成一個整體。二是對史料及其中論斷進行批判、選擇的過程也需要想象的參與。由歷史想象所構成的整體圖畫是史家借以批判、選擇史料的標準。因此,柯林武德很重視歷史想象的認知作用,稱其為“先驗的想象力”。
與康德“創造性的想象力”類似,柯林武德認為歷史想象同樣是人天生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人類心靈普遍和必然的方面,它能夠讓我們“看見”超出實際感官感知的客體。但歷史想象又稍不同于認知想象,它“以想象過去為其特殊的任務”。一方面,歷史想象針對的是史家無法經驗的、一去不復返的事物,“那不是一種可能的知覺的對象(因為它現在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歷史想象歸根結底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其最終實現的不是康德知覺想象所得到的普遍的、科學的類。然而,如果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那么,歷史想象就與文學藝術家的想象相似,因為文學藝術家正是要憑借想象描述出不同個體及其個性,進而構造出一幅融貫的整體圖畫。柯林武德承認這一點,但他仍然區分出兩者。他認為,不同于小說家,史學家的圖畫還必須力求真實:首先,史學家的圖畫需要能夠在空間和時間中定位;其次,這幅圖畫需要與它自己相一致;最后,這幅圖畫必須與證據處于特殊的關系之中。這樣,通過與知覺想象和文學想象相區分,歷史想象的特征便顯現出來。
柯林武德對歷史想象作為史家先天能力的論述破除了大部分實踐史家認為史料是判定歷史真實性標準的經驗主義觀點。現在,史家觀念中所認知和建構的融貫之網成為判定一切歷史事實的試金石。歷史想象被柯林武德確定為一種先天的、在觀念中客觀把握事實的必要裝備。當代學者杜森曾將柯林武德的這種證明視作歷史知識建構的“底層基礎”。歷史想象是“底層基礎”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假如沒有了歷史想象,史家得到的將是一堆沒有經過批判的史料堆積物。
在柯林武德這一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公開之后,大部分史家漸趨承認歷史想象在史家思維中發揮著不可簡化的作用。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聞名的實證史家埃爾頓,亦承認史家在認識歷史時不可否認地會經歷選擇證據的過程,在資料不完備的狀況下,須借由想象設想證據生成的環境和證據間的相互關系,想象使知識富有意義。這已和蘭克的觀點十分不同。但埃爾頓仍然堅持歷史想象僅僅是一種補充,而想象創造的事物不同于知識。隨后海登·懷特對歷史想象觀念的更新再次抨擊了這種經驗主義觀。
為比喻性歷史語言辯護
1973年,海登·懷特出版其成名作《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在著作中,懷特將他所分析的四位史學家和四位歷史哲學家的作品全部視為本質上由想象建構起來的歷史闡釋。這里的想象,懷特視之為一種“以詩性言語、文學寫作和神話思維中特有的意象與比喻式的關聯模式為特征的思維類型”。在懷特看來,史學家歸根結底是在“比喻式的關聯模式”——可被區分為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類型的轉義——的引導下,分別在情節、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蘊含層面,將在史料中呈現的諸多“混亂”“無秩序”的事件連接起來,編織出一個可理解的歷史世界的。這一整體的歷史世界,雖然能夠在時空中定位,但卻無法在符合論的意義上將之與過去實在一一對照起來。因為借由比喻性的敘事再現,史學家或多或少地已為過去實在增添了某種倫理和審美上的意義。區別于將柯林武德的歷史想象視為在歷史知識的“底層基礎”中發揮著作用,杜森認為,懷特的歷史想象運行在歷史知識的“上層建筑”層面。前者相對于歷史研究,后者相對于歷史書寫。但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往往難以區分。懷特所說“比喻式的關聯模式”,并不像蘭克或麥考萊認為的那樣僅僅為文字上外在的修辭裝飾;相反,它深刻影響甚至主導著歷史學者認識歷史的過程。
具體而言,首先,懷特的轉義概念來自維柯。一如維柯將想象視為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懷特也將詩性轉義視為史家本身所具備的、區別于演繹邏輯的認知方式。在史家理解和熟悉過去的經驗世界之前,轉義便已在其頭腦中發揮著預構作用,決定著他將史料解碼和再編碼的方式。其次,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也是一個將過去實在主題化和敘事化的過程。在敘述中,史家通過將諸多事件組織成具有某種情節結構的敘事,進而讓事件“顯現”出某種意義。例如,馬克思通過將波拿巴上任這一事件回溯為一個“笑劇”,進而反映出這一歷史事件的某種性質,使人得以理解它。在懷特看來,經驗世界中復雜的過去事件本身雜亂無章,我們在歷史敘事中看到的所謂秩序和完整性皆由史家構想而成,因此歷史敘述不可避免地混雜著虛構性。然而,“虛構”并不等于“虛假”,“虛構”可以指被制造出來的東西。而史家回溯性地為事件賦予的意義正是這樣一種被歷史話語制造出來的東西,它呈現出人們在倫理和審美層面對過去事件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無疑可以為“真”,這種“真”類似于普遍的“詩之真”,其檢驗標準在于史家所構想之意義的適當性或可信性。因此,這也是緣何像《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樣尖銳、準確地把握了歷史意義的作品,即便假設其中的個別史實有所出入,但依然不會影響到它的“真實性”。
在此,懷特和柯林武德一樣,都堅持了想象在理解史料、構造敘事的過程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他們也都認為想象參與其中而獲得的歷史知識可以達成真。柯林武德認為這種知識是特殊、具體的;懷特認為它同詩一樣,能夠揭示事件的某種普遍性質或意義。但在對待文史關系的問題上,懷特要比柯林武德激進得多。這不是說懷特否認歷史實在的存在,或者認為歷史研究可以不依靠證據自由散漫地發揮。其不同之處在于,懷特強調史家用來講述歷史的語言和寫作形式本身也有其“內容”,就像用來盛水的杯子本身有不同的形狀、材質那樣。懷特批評柯林武德沒有看到,史家是帶著某種特殊視角和語境來認識、塑造歷史的。而在柯林武德看來,歷史中的意義是史家通過同情式重演自然而然把握的。
懷特的觀點是否走得太遠了,仍是一個留待探討的問題。一方面,懷特試圖通過強調歷史中的普遍意義,來呼吁人們可以從歷史中獲得當下行動所需要的靈感和前進的方向;另一方面,懷特的確沒有將如歷史話語與歷史證據間關系這樣更加“地基式”的論題置入思考中,他的理論沒有辦法認識某一歷史再現在認知層面緣何是錯誤的。他雖然觸及了“底層基礎”,但也規避了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多少使得“上層建筑”不太牢固。這也使得在海登·懷特之后,不少史學理論家重新回到對歷史論證和歷史邏輯的探討上。
結語
由上,我們梳理了西方史學思想中不同的歷史想象觀念。或許,對歷史想象的思考能夠為我們調和歷史學的科學和藝術向度提供很好的視野和落腳點。同時,不同思想者的論證皆表明,歷史想象在強調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歷史思維活動中不可或缺。如果史學家試圖獲得一段融貫的、真實的歷史敘事,那么,歷史想象必然參與其中。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所謂后現代主義歷史觀——海登·懷特本人即是這一思潮的重要推手——對歷史中主觀要素的揭示,認為歷史記述能夠與過去實在完全或部分符合的這種天真的、“攝影術式”的歷史真實觀念已不再具有說服力。現在,很少有哪位具有反思性的史學家能夠自信地宣稱自己的研究是一面徹底客觀的“實在之鏡”,全然反映了過去發生之事。當然,在逐條描述的編年史層面,我們能夠做到將歷史事件在過去的時間、空間中定位,但一旦跨越到歷史進程的整體層面,我們便無法排斥主觀的參與。從這一層面上說,歷史知識終將是人類思想的產物。而對歷史想象的思考表明,史家的主體觀念與歷史之真并不相互排斥。甚至,史家的主體觀念構成了歷史“真”之判斷的準繩,這里的“真”,不僅意在史實的準確性,而且關涉歷史整體的融貫性和歷史之義的適切性。
然而,也必須意識到,僅僅有想象的參與并不一定能夠達成歷史之真。換言之,歷史想象絕非任意、無所指涉和天馬行空的,它有其限度。這種限度,一方面體現在它需要數據和史料的支撐,需要“事核”,它終歸不同于文學想象。另一方面,它更需要經過史家自身的理性批判,需要在善與美的維度上考察其“創造物”是否切合于人性的普遍原則。在這點上,這種限度是內在的,與證據的多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