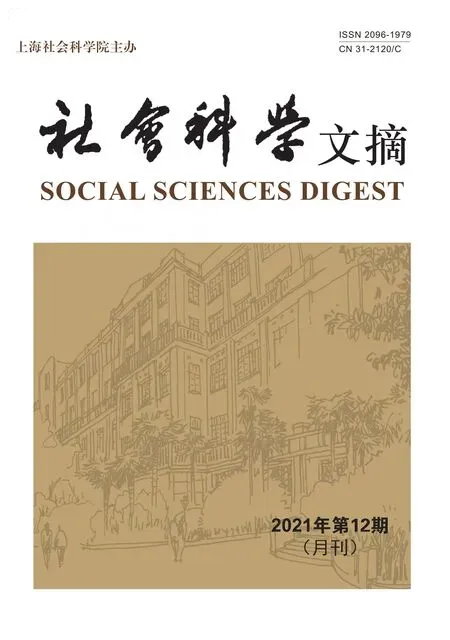經典、經學與經典之學
文/楊國榮
一
從廣義的視域看,經典可以理解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沉淀和前人思維成果的凝結。這一意義上的經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而更多地以智慧為其內容。知識和智慧需要加以區分:知識主要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把握對象,自然科學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即屬于知識性的學科,其特點在于以分而論之的方式把握對象。經典的內容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知識性的認識成果,其特點也不在于分別地把握世界和人類社會某個領域或某一對象,而是側重于跨越界限,從整體上理解現實世界。從現實的層面看,經典不同于一般文獻或典籍的特點,也體現于此。與智慧的以上指向相應,經典首先關切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
以《莊子》而言,其作者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書中也曾提到儒家的六經。在《莊子》看來,“《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里所說的《書》《禮》《樂》《易》《春秋》屬儒家的經典,“事”“行”“和”“名分”,可以視為廣義的人的存在方式,“陰陽”則關乎宇宙或對象世界的存在形態。荀子也對儒家經典作了類似的概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此所謂“天地之間者畢矣”,更具體地肯定經典涵蓋了宇宙人生的總體原理,對以上原理的把握,則不同于知識性的理解,而是呈現為智慧層面的領悟。與智慧的追尋相聯系,人們關切的問題涉及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人的理想存在形態,如何達到這樣一種好的生活、理想的存在形態,等等,其中涉及成己與成物,包括成就何種自我,造就怎樣的世界。在智慧這一層面,經典既注重“成就什么”,也關注“如何成就”,兩者都包含規范性的內涵:把握真實的世界關乎對世界的說明,而成就理想的世界則指向對世界的規范。由此,經典所凝結的智慧也從不同的方面切入了宇宙人生的深處。
如果僅僅從知識的層面看,則經典中所包含的若干內容在今天看來也許顯得缺乏深度,有些方面甚至過時了。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知識領域如物理、數學、化學等方面,今天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所達到的知識水平可能已超過了以往一些思想家。但是,在智慧的層面,卻顯然不能這樣說。以往的思想家通過深層的洞察、創造性的想象,以及基于自身的知和行而達到的對世界的理解,往往包含著創造性的智慧內涵。凝結于經典中的智慧,體現的是先人對形上之道與人自身歷史活動的深沉體悟。
作為以智慧為內容的思想載體,經典展開為一個生成的過程。就儒家的六經而言,其中的《尚書》包括《堯典》《禹貢》《甘誓》《洪范》《康誥》《秦誓》,等等,從所涉及的內容看,它們乃是關乎不同時代的“事”,并形成于不同的年代,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表明,經典本身并非預成或既成,而是經歷了形成的過程。如果不僅僅限于經學,而是從更廣義的經典之學來看,其中的經典更是處于生成的過程之中。事實上,經典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廣義的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人們總是不斷地在成己與成物的過程中探索宇宙人生,由此形成的認識成果,則凝結于不同時代的經典之中。就中國思想的演化而言,從先秦到近代,對宇宙人生的追問綿綿不斷,而思想領域的不同經典則漸漸形成于這一過程。經典的形成,離不開人的接受和認同,但并非僅僅取決于人的主觀意愿。事實上,歷史上曾出現眾多的文獻和經典,唯有真正展現文化積累意義的文獻,才能為歷史所選擇,并逐漸沉淀為歷史中的經典。
上述意義中的經典既是思想創造的源流,又構成思想傳承的依托。孔子曾區分“作”與“述”,其中的“作”更多地體現了思想的創造,“述”則以思想的承繼和延續為指向。歷史地看,在經典中,“作”所表征的創造與“述”所凝結的傳統,往往合二為一。在人類思想的前后發展過程中,經典一方面使思想不斷呈現創造的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承先啟后而形成綿綿相續的傳統。經典的作者在歷史的演化中常常會被湮沒,一些經典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甚至難以考定,但經典本身卻在歷史留存下來、代代相傳,并從一個方面構成了思想和文化傳統的承擔者。在文化傳統的形成過程中,作為承擔者的經典可以表現為文化的主導方面,也可以滲入文化的不同領域。以文化的主導形態出現的經典,往往被賦予某種神圣的形式,歷史上的五經或六經,便呈現這一特點;融入文化不同領域的經典,則更多地以其創造內涵而產生實際的歷史影響。
從其形成來看,經典總是與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和地域相聯系,就此而言,經典呈現某種地方性或地域性,后者賦予經典以某種特殊性的品格。但是,經典所包含的智慧內涵,同時又具有普遍意義:真正的經典總是同時構成了世界文化的共同財富,并呈現世界性的意義。經典既在形而上的層面追問世界的普遍原理,也在社會政治和人生領域探討人自身如何“在”,其中的看法不僅展現了認識世界的歷程,也滲入了對人自身存在的關切;作為人類文明的凝結,其意義已超越了特定的空間和地域。在歷史進入世界歷史的背景下,經典所內含的這種普遍意義得到了更為深沉的展現。
二
這里,需要對經學和經典之學作一區分。從中國文化的演進看,從漢初開始,經典便與經學相關聯。前文提及,經典承載著一定的文化傳統,就中國文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而言,經學以及經學中的經典同樣產生了深遠而難以否認的作用,從普遍的價值觀念到日常的行為方式,等等,經學都對中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塑造作用。
如果從現代學術思想這一角度對經學做進一步的考察,便可注意到,經學本身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與文獻的研究相關,屬廣義的文獻之學。歷史地看,從漢代設立經學之后,以文獻研究為內容的經學形態就開始逐漸出現。漢代經學有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分,比較而言,古文經學中相當一部分的內容,便涉及文獻方面的整理、考訂和詮釋。到了清代,特別是乾嘉時期,隨著清代漢學或樸學的興起,文獻整理、考訂、詮釋方面的經學內容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經學本身也逐漸形成某種實證化的趨向,后者具體表現為與近代科學相近的研究方法,包括注重證據、善于存疑、無征不信,以及運用歸納、演繹的邏輯方法,展現虛會(邏輯分析)與實證(文獻印證)相結合的研究進路,等等。這種實證化的研究方式,構成了與文獻之學相關的經學的重要方面。
經學的另一個方面與價值取向相聯系,表現為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功能的觀念形態。從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的發展來看,作為文化主導方面的經學,無疑蘊含著這一內涵,具體而言,在經學之中,包括不少普遍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原則,這些方面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蘊含著意識形態的作用和功能,它從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方面引導著傳統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經學不僅包含對社會政治領域中普遍關系和運行過程的認識,而且賦予具有特定歷史形態的名教以多方面的內容,后者既對當時的政治體制提供了正當性的說明,也對人們的行為以及人格塑造具有教化意義。
以價值觀念為內涵,表現為意識形態的經學取得了不同方面的特點。首先,就對象來說,它主要關乎五經或六經,后來是十三經。漢初設五經博士,即分別以《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為依據;唐代增加《周禮》《儀禮》,并將《春秋》分為《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由此五經演化為九經;后又加上《孝經》《論語》《爾雅》,形成十二經;南宋進一步新增《孟子》,經學的對象最終形成十三經。以上對象雖有五經與十三經的演變,但都表現為經學之域的經典。從內容上說,前面已經提到,經學涉及普遍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原則,其意識形態或名教之維的內涵,主要便體現于這一方面,經學的教化作用,也以此為主要依據而展開。從研究方式的角度來說,這一意義上的經學更多地趨向于義理的認同:對以往的經典內容,首先是無條件地接受和認同,而不是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在實質的層面上,這種研究方式也可以說是以義理的認同壓倒了批判性的反思。
經學的兩重內容,即作為文獻研究的經學與作為價值觀念的經學,在清代漢學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展現。在清代樸學或清代漢學中,一方面,實證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由此逐漸形成了文獻研究方面注重實證、校勘、訓詁等研究進路,如上所述,這種研究方式后來逐漸趨向于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方法。如果注意一下現代學人對清代樸學的理解,便可以注意到,他們往往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式歸入近代科學家如牛頓、伽利略的研究方法之列。胡適便表現了這一趨向,在他看來,“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即伽利略—引者)、牛敦(Newton,即牛頓—引者)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筑在證據之上”。“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確實,從方法論角度來說,作為經學的實證化趨向的典型形態,清代樸學的研究進路已具有某種實證科學的意義。
另一方面,以價值觀念為內涵的經學,在清代也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清代樸學固然表現出實證化趨向,但依然具有經學的性質,其考證以群經為中心,校勘、小學、歷算等包含實證性研究,往往表現為經學的附庸,這使清代樸學很難擺脫義理認同超越批判性反思的經學傳統。在清代樸學看來,經學之域的六藝、五經本身便可視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六藝者,群言之標準,五經者,眾說之指歸。”從這一前提出發,清代樸學無法超越經學的視域。
可以看到,經學所內含的兩個方面,即與文獻研究相關的實證之維與體現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趨向,在清代樸學或清代經學中都得到了典型的體現。以義理認同壓倒批判性反思的經學研究進路,同時賦予經學方法以某種獨斷論或權威主義的形式,即通常所說的經學獨斷論,便從思維方式等方面體現了經學的以上特點。
歷史地看,作為價值觀念系統的經學所包含的一般理念和原則既有普遍性的規定,也包含特殊的內容。從普遍之維看,經學凝結了對人類演進、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以及規范系統的理解,其中包含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的內容。早期儒學基于對人倫關系的理解而提出的仁道原則,便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指向,后者具體展開于精神世界、社會領域以及天人之際。精神世界體現的是人的精神追求、精神安頓和精神提升,其具體延伸關乎宗教性和倫理的維度,以及具有綜合意義的精神境界。儒學的理論關切同時體現于政治、倫理和日常的生活世界,這些對象包括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和自我的關系,社會領域指向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早期儒學的這些價值關切,在后續的經學中都得到了不同層面的體現,事實上,經學中的價值內容,可以視為早期儒學思想的系統闡發。這一意義上的經學觀念,無疑有其普遍的文化意義。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傳統意識形態的載體或名教系統,經學之中又包含不少具有歷史印記的內容。在價值的層面,經學既關乎對社會人倫的理解,也涉及應當如何做的規范性要求。在經學的視域中,社會人倫與宗法關系總是相互交融,以宗法的關系定位個體,則構成了經學的重要特點,與之相關的個體,則主要便表現為宗法依存關系中的存在。在歷史的一定時期,這一品格無疑構成了人的不可忽視的存在規定,但從現代的角度看,人則呈現更多樣的存在形態,僅僅以宗法關系理解個體,顯然有其歷史限定。
從社會的層面看,經學往往將夏商周三代或更遠古的唐虞之世視為理想的社會形態。歷史的演進則相應地被視為遠離理想形態的后退過程。在經學的傳統經典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類觀念。這種理想在過去的歷史意向,與進化論出現之后的現代思維,也存在某種張力。盡管現代性存在種種問題,對現代性視域中的歷史觀念也可以作各種批評,但相對于主要回溯過去的歷史視域,這種現代意識顯然提供了不同的看法。如何在過去、現代與未來的交融中,形成對歷史演化過程的真切理解,無疑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經學同時包含一定的規范系統,后者主要規定應當做什么、應當如何做。以政治領域而言,經學承繼早期儒學的政治原則,強調“為政以德”,主張對民眾“道之以德”。同時,基于禮的觀念,經學主張建立包含尊卑等級差異的社會秩序。對儒學而言,在缺乏如上社會區分的條件下,社會常常會陷入相爭和紛亂的境地,而當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各安其位、互不越界之時,整個社會就會處于有序的狀態。這種尊卑上下之序與政治領域的君臣關系相互交融,賦予君主在政治生活中以主導的地位。
可以看到,在個體與社會、過去與未來、政治秩序的理解等方面,經學自身存在多方面的歷史限定,后者與經學的獨斷方法相互交錯。對經學的以上方面,無疑需要進行具體的反思,這是理性地對待經學的價值內涵所無法回避的。
三
除了歷史中的經學之外,經典還關乎更廣意義上的經典之學。傳統的典籍往往被歸入經、史、子、集不同之類,依據這種分類標準,則經典似乎主要與經學相關。然而,從更廣的視域看,不僅經學包含其自身的經典,而且史、子、集也有自身的經典。以“史”而言,《史記》《漢書》等早已具有經典的意義;在“子”這一層面,不僅本來屬“子”的《論語》《孟子》已成為經學之域的經典,而且先秦諸子,如《老子》《莊子》,以及后起的各家,也逐漸成為不同的經典;至于“集”,則《楚辭》《文選》以及漢唐宋明的各家詩詞文集,也同樣在文學等領域獲得了經典的意義。與之相聯系,就經典之學而言,其對象并不限于經學意義上的“五經”或“十三經”,而是包括更廣范圍中的文化和思想經典。事實上,文化發展、思想演進中所形成的多樣創造性思想系統,在凝為著作并逐漸獲得了經典的品格之后,便成為經典之學考察和反思的對象。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從荀子、董仲舒、宋明理學中的各家,到永康學派、永嘉學派,直至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諸家,他們的著述都應進入經典之學的視野,成為其考察的不同對象。
從觀念層面上說,經典之學視域中的經典,包含更廣意義上的思想內容,可以視為人類認識成果的多樣體現。這一層面的經典首先涉及普遍的價值原則,以《老子》《莊子》這一類道家的經典而言,其主導的價值取向便體現于自然原則,后者與儒家以及經學中的仁道原則相對,注重合乎對象自身的法則。按老子的理解,在作用于物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最合適的方式是“為無為”。具體而言,“為無為”意味著人的行為方式完全與自然之道或自然法則一致,呈現合法則性。作為價值原則,自然原則所強調的主要是合目的與合法則不能彼此分離。在處理天人關系方面,這一原則注重兩者之間的合一;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以上原則一方面要求抑制社會規范的專橫,避免行為準則成為外在的強制,另一方面則反對扭曲人的內在天性,其中體現了對人的內在意愿的尊重。這一意義上的價值取向與前述經學的價值觀念有所不同,展現了另一重價值意義。
從研究進路看,與價值形態的經學在方法上趨向于義理認同超越批判性反思不同,經典之學具有更為多樣的特點。以現代思想的演進為視域,則廣義的經典之學至少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情感認同和理性分析的統一。對于傳統經典,一方面,無疑需要具有情感層面的認同,后者意味著對歷史中形成的經典表現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也需要以理性分析的態度,對傳統經典可能具有的理論限度,予以充分的認識和把握。如果僅僅強調理性的分析,缺乏情感認同,則思想與文化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經典便容易僅僅被視為認知的對象,其價值內涵則難以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如果單純地注重情感認同而忽視理性分析,則可能走向經學意義上的衛道立場。從觀念和義理的角度來說,經典總是包含對宇宙人生、對人類如何行動和實踐的思考,其中包含普遍的理論意義,但同時,經典又不可避免地有其特定的歷史印記和歷史的限度。前者表明,歷史中的經典對今天的生活實踐往往依然具有范導性,后者意味著應對以往的經典需要作實事求是的理性分析。
其次是對話。回溯經典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在不同層面上與之對話。這一意義上的對話既不同于盲目尊崇意義上的仰視,也有別于無條件否定形式下的俯視,而是表現為理性的平視。具體而言,它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基于反思,對經典提出問題,并進一步從經典之中尋找這些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其二,考察經典本身提出了什么問題,今天又如何去回應經典提出的這些問題。
再次是比較。對話主要是側重于從經典本身思考問題,比較則不限于單一的經典,而是要求從更廣的視野中去理解經典本身。以儒學而言,其特點之一是“派中有派”,先秦時期有孟荀的區分,從荀子到唐代柳宗元、劉禹錫,再到宋代的陳亮、葉適,以及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構成了儒學注重外王、事功的路向;從孟子到唐代的韓愈、李翺,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則構成了注重內圣、心性的進路。儒學的不同進路具體而微地體現于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多樣經典,對這些體現不同進路的儒家經典的比較研究,無疑有助于更為深入地把握儒學的深沉內涵。中國思想史中的各家各派,同時又是在百家爭鳴中與不同學派的論辯中發展的。理解這些學派人物,無法撇開他們與其他學派之間的互動。不同學派在學術、思想上各有側重,對社會、人生、宇宙等等,往往也給予了不同的關注,這種不同的探索,同樣具體地凝結于各自的文本之中,通過文獻的比勘和理論的研究,既可以分別地把握不同學派的思想內涵,也有助于推進對其中特定學派和人物思想的理解。
廣而言之,傳統經典的詮釋,同時涉及中西思想之間的比較。近代以后,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已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從中西文化的關系看,一方面,需要防止單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趨向,另一方面,又應警惕另一極端,即簡單地回歸傳統。以中西之學作為背景,比較合理的方式包括兩重維度。一是以西學作為理解中國已有經典的理論參照系統,這一意義上的西學近于“他山之石”。在原有形態下,傳統經典中不少觀念的含義往往未能充分彰顯,借助于西學的理論框架,則有助于揭示其深層的意蘊。二是以中國經典中蘊含的思想回應西方思想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經典之學的以上內容,側重于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進一步看,這種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經典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人們的理論思維能力。經典既是思想載體,又凝結了前人的思維歷程,作為人類文明的成果,它們包含如何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閱讀經典與經典對話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重新經歷前人的思維歷程,通過重走前人的思維之路,解讀者和詮釋者自身的思維能力也可以得到切實地提高。其次,經典不僅僅是以往的歷史陳跡,它同時也為今天進行理論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任何的時代思想創新都不可能從無開始,而是需要以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作為它的出發點。同時,新的思想建構又不同于重復,它應當增加或提供以往經典尚未注意到或相對缺乏的方面。在此意義上,思想的創新與經典的演化之間,具有多重的關聯。可以看到:一方面,經典在歷史的層面呈現其不可或缺性——經典的回溯有助于理解傳統文化及其內核;另一方面,它們在現代又具有思想建構的意義——其創造性的內涵同時構成了今天理論思考的智慧之源,后者賦予經典以新的思想生命力。
概而言之,經學涉及經典,但經典不限于經學,經學的產生、作用都有歷史性,其內容也包含自身的限定。從現實的層面看,今天的思想使命,不是簡單地復興、回歸經學,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傳統經學;對經典的考察,則應當由傳統的經學而引向更廣意義上的經典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