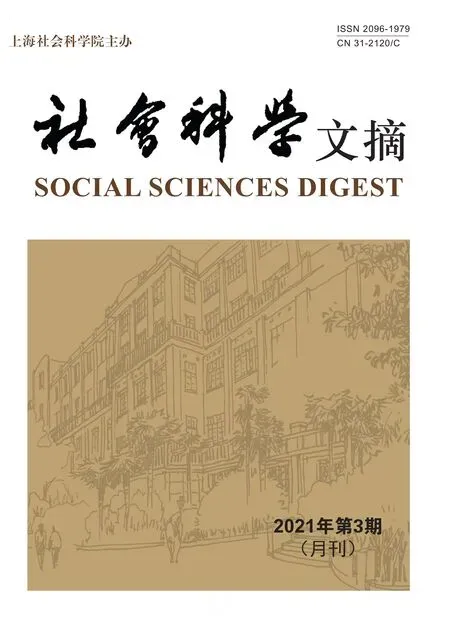百年變局中的歷史轉換與戰略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推動中國學界以更為寬廣的歷史視角來審視當今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西方學界近年來有關世界局勢發生變化的討論也時有發生,“后美國”和“后西方”等就是這些討論創造出來的新概念。但百年變局必然以一系列的歷史轉換為基礎,中國學界應該在這方面深入探索,認清百年變局中正在轉換中的世界歷史進程,從而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歷史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提供必要的思考。
西方學界有關“百年變局”的討論
西方學界沒有用“百年變局”這樣的概念來刻畫變化中的世界局勢,但相關討論早已經開始,并且帶有深重的危機感。有關西方“衰落”的觀點早已林林總總,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集中在“后西方”世界走向的問題上。
早在2002年,美國知名學者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就發表了《西方的終結》。當時正值美國反恐戰爭逐步擴大,“文明沖突”的預言似被應驗之時。但庫普乾認為,“9·11”恐怖襲擊只是刺破了冷戰結束和西方勝利所帶來的安全感,對美國的霸權沒有任何影響。崛起的挑戰者也不是中國或伊斯蘭世界,而是歐盟,一個正在整合歐洲各民族國家優質資源和歷史野心的新興政體。兩年后,他又出版了《美國時代的終結:美國外交政策與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一書,重申美國正在與歐洲分手,幾十年的戰略伙伴關系正在讓位于新的地緣政治競爭關系。他在最后一章《歷史的再生》中還特別指出,美國時代的終結不僅是美國優勢地位的終結和向多個權力中心世界的回歸,而且與工業時代的終結和數字時代的開啟同步。2008年,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出版《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一書,認為過去500年來世界發生了三次結構性的權力轉移,即西方世界的崛起、美國的崛起和當下正在發生的“他者的崛起”,世界正在步入“后美國世界”和“后西方世界”。有些學者對“后美國”和“后西方”世界的前景非常悲觀。2008年,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和外交評論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出版了《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一書,提出1945年之后國際關系的發展是一種“冒進”,鼓吹“歷史的終結”的人看到的是“海市蜃樓”,“世界再次回歸正常”。2018年,他又提出1945年之后建立的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偏差,世界秩序將重回20世紀30年代,重回歷史,重回叢林世界。當然,更有許多學者在討論“后美國”或“后西方”世界的時候圍繞中國的崛起做文章。斯蒂芬·哈爾波(Stefan Halper)認為,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幻想已經不復存在,也不存在中美共治的可能性,中美之間的競爭最后將是“孔夫子和杰斐遜”的對決。
在美國學界,最為努力系統闡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并為其辯護的是約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他認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并非起始于1945年,而是起始于歐洲的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他反對自由主義秩序正在終結的觀點,認為這個秩序是開放的,即使美國衰落了,這個秩序仍將延續下去。他也反對把中國和俄羅斯視為“修正主義”國家,認為中、俄等國只是想在現有秩序的框架中爭取更大發言權。當今國際競爭實質上是話語權的競爭,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者挑戰國際體系等級的根本性對立。當然,他也承認中國的崛起給這個秩序帶來的變化是史無前例的。他不認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會帶來新價值主張的觀點,認為開放和對規則的認同是東西方的共識。在國際自由主義的諸多主張中,開放性與流動性正是中國所呼吁的。
事實上,美國和西方學界有關“百年變局”的討論的基本出發點依然是西方的“主體”思維,依然圍繞著西方“主導”地位的變化,闡釋“百年變局”的利害得失,因此依然沒有跳出“西方中心論”的怪圈。但實際上,百年變局中的歷史轉換的深度已經遠遠超過西方學者的預判和想象。
百年變局中的歷史轉換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不僅是對當前國際形勢的高度概括,更是立足于歷史制高點上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因此,學界不僅需要對當今國際事務的重大變化進行深入、縝密的考察,而且應該將其放在一個更為寬廣和久遠的歷史視野中去研判,發現我們在這個變局中正在經歷的歷史轉換,為應對這個變局提供更具戰略意義的思考、更具啟發意義的理念。這些歷史轉換的跡象近年來愈加明顯,它是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歷史演進累積的結果。歸根結底,一個“后西方世界”的輪廓正在顯現出來。
第一,是非西方的崛起,特別是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改變了近代以來西方與非西方力量對比,其中尤以中國的崛起影響巨大,經常被與西方和21世紀世界的前途聯系在一起。實際上,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現為非西方國家的整體性崛起。這樣一種歷史的轉換不僅表現在非西方國家GDP總量已經超過了西方國家,而且改變了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
第二,表現在非西方國家之間新的經濟協作關系的形成,“亞非歐大陸的回歸”,非西方國家進入了更為獨立自主的發展時期,甚至出現了“一個沒有西方的世界”的說法。原來意義上的“世界體系”正在趨于解體,正在轉換成一種更為復雜的分工體系,整個世界正在按照“超級版圖”組合起來,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群已經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節點。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互聯互通網路的深入蔓延,歐亞非在經濟上更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歐洲正在消解,歐亞大陸正在“重回馬可波羅世界”,改變了近代以來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基礎,也削弱了美國對歐亞大陸的支配和平衡能力。
第四,冷戰期間構建起來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正在走向解體。西方在歷史上并不是一個恒久的存在,現在人們所認同的西方是在“二戰”結束之后,歐洲對世界的領導權轉移到美國手里時構建起來的。冷戰的終結被認為是西方的“勝利”,但隨著這一勝利的到來,西方陷入了種種“困局”,原來意義上的“西方陣營”事實上已經走向解體。
第五,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終結。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已有許多。特朗普政府“美國至上”的理念和行動加劇了美國與其盟國的分離,推動了國際關系多極化的發展。喬·拜登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獲勝,他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特朗普政府嚴重破壞的世界,一個美國主導權難以“修復”的世界。而特朗普的作為,使美國將面對一個“沒有長期以來一直支持美國利益的機構、聯盟和善意的世界,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形成了”。
以上種種,都是“人類社會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的不同表現。西方已經“走下神壇”,世界的“中心—外圍”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歐亞大陸傳統地緣政治結構正在消解,“西方陣營”的存續基礎已經不復存在,美國主導地位的現實條件正在消失,世界正以一種新的面貌展示在我們面前。面對這個新的世界,我們需要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進一步認清歐洲歷史經驗的局限性,重新認識和闡釋世界歷史的階段性發展,重新認識和闡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的發展變化,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和建構。同時也需要我們立足現實,在迎接新的挑戰中拓展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期,推動大國形成更多共識,擺脫西方學者“重回叢林世界”的“咒語”,讓“后美國”和“后西方”世界成為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
百年變局中的現實挑戰與戰略機遇
中國的崛起被西方學界普遍認為是百年變局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中國也必將在變局中遭遇方方面面的挑戰,當然也會不斷面臨新的戰略機遇。中國的崛起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階段,但只要我們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審時度勢,就能夠保持中國崛起的進程不被打斷,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首先,是中美關系或“新冷戰”的挑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美國總統大選,加劇了中美之間已經日趨緊張的雙邊關系。特朗普總統為了掩飾“抗疫”的失敗而竭力“甩鍋”中國,刻意激化中美矛盾,為美國那些一直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冷戰思維的保守勢力創造了發揮作用的空間,致使中美關系出現了建交40年來最嚴重的歷史性曲折,并且形成了被許多人認為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局面。有關中美關系是否進入“新冷戰”,學界有不同觀點。美國學者何漢理(Harry Harding)認為,將其稱為“第二次冷戰”是誤導,但否認這是一場冷戰也是虛偽的,應該是冷戰的2.0版,即兩國在經濟上業已形成高度相互依賴情況下展開的競爭和對抗。特朗普政府的作為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不利影響。但其在將中國置于美國這個迄今世界上經濟與科技實力最強大國家的最主要競爭對手位置上的同時,也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與社會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勵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早日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戰略目標。不可否認,盡管美國的世界地位已經不如往昔,但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國和強國,在經濟、金融、科技和軍事等幾個大國競爭的主要領域占據優勢地位。然而,美國社會在2020年大選之中已經陷入空前的政治分化和“極化”的狀態,美國的兩黨政治似乎已經難以表達美國社會政治訴求日趨多樣化、復合化的現實。“新冷戰”既不是美國社會多數人的共識,也不是戰略家深思熟慮的結果。中國不僅不接受“新冷戰”的提法,而且對美國政治理性的恢復和中美關系的積極變化抱有耐心和信心,中國始終相信重塑新的戰略共識符合雙方的長遠利益。
其次,是非西方大國群體性崛起的挑戰。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僅僅是中國的崛起,還有其他非西方大大小小國家的崛起,世界在百年變局中進入了一個更為多元化和多極化的時期。這些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國,既想重塑昔日的威嚴,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又要面臨持續推進經濟與社會發展,不斷消化已有和新產生的種族、宗教矛盾的艱巨挑戰。在中美關系逆轉的情況下,它們既想把中美競爭視作拓展自己戰略空間的機會,甚至在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上向美國一方偏移,成為美國阻止中國崛起的伙伴,又難以割舍中國的投資、中國的產品、中國日趨龐大的消費市場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驅動的全球產業鏈的拓展。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不斷縮水,中國提供的機遇在不斷擴大,中國與其他新興大國之間尋求更多共識的空間應該是逐步加大的。
最后,是全球化的新危機和新機遇。關于全球化的進程起于何時,學界見仁見智。但無論以哪一個時段為起點,人們都會發現全球化的進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會遭遇不同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地區在全球化不同的階段,成為不同的所謂的贏家或輸家。但全球化的進程從來沒有在不斷出現的“逆全球化”的沖擊之下停下來。當前全球化所遭遇的“逆全球化”危機,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社會關系失衡,民粹主義蜂起,政治分裂和“極化”嚴重,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另一方面是全球問題凸顯,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大國之間難以形成共識。無疑,“后美國”或“后西方”世界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就是一種思想上和理念上的超越,全球化的新危機應該轉化成全球治理達成新共識的新機遇。
全球化歸根結底是一個不斷拓展的全球現代化的進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全球不同地區在不同類型的“民族國家”框架下組織起來,以不同的經濟基礎、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社會構成和20世紀不斷變化的時代背景,卷進現代化的進程中來。在這之中,世界經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地位的興衰,經歷了美蘇兩個不同陣營之間的競爭和蘇聯陣營的解體,現在又迎來了非西方大國和非西方世界的群體性崛起、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失序”這樣一個歷史轉換的重要時刻。實際上,這樣一個時刻的孕育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全世界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開始在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競爭與合作。全球化的深入拓展和“逆全球化”的不時“反撲”,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新興大國的沖突和對抗,以及競爭與合作,都是正常的。“后美國”和“后西方”世界的前途取決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政治多極化形勢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如何找到最大的利益公約數。中國的未來不僅僅取決于與美國的競爭與合作,還取決于自身發展模式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這是百年變局中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也是中國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戰略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