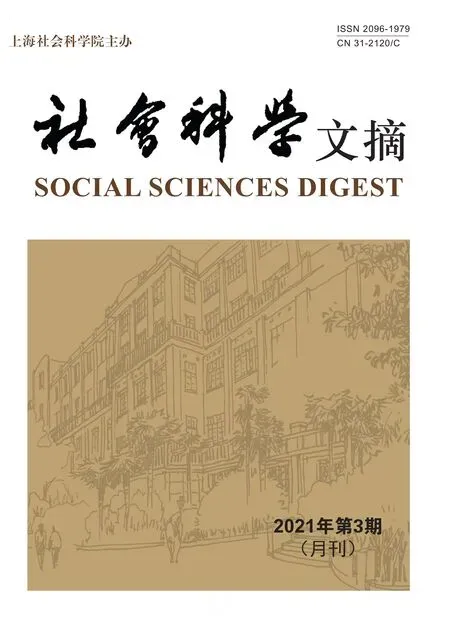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動因與路徑選擇
全球氣候治理是當代最復雜的系統性治理,在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包括多元行為體和多維治理機制在內的機制復合。“多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相繼出現在《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協議書》《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方針》《生物多樣性公約》及《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等公約談判過程和內容中。從全球氣候治理與談判來看,“多利益攸關方”(Multi-stakeholder)概念的確定是一個漸變過程,“多利益攸關方”包括了社會組織、跨國公司、城市等在內的主體。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和2020年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都強調多利益攸關方合作對實現《巴黎協定》2℃升溫目標和碳中和的重要性,并首次在上述聯合國峰會議程中將主權國家領導人和非國家行為體代表的發言位置并列。
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和治理的發展進程
多利益攸關方主要是指國際法主體的多層和多元化現象,全球氣候“自下而上”治理的特點和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各種不同理論的興起與發展為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合法性做了充分鋪墊,增強了多利益攸關方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多利益攸關方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的地位、參與路徑和議程設置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斷的提升:
第一,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談判和治理的地位上升。在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等為核心的全球氣候談判過程中,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的話語權經歷了不斷提升的演進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治理進程中,社會組織、跨國公司、地方和社區、個人的作用已有所提升,但其數量和有效參與都未得到國際條約的普遍承認。2003年《京都議定書》進入履約階段后,全球氣候談判進入新階段,多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得到飛速發展,以社會組織與國際社會組織為代表的多利益攸關方在氣候談判中實現了數量增長和身份轉變。2011年德班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變革動力”倡議,使得非締約方也成為全球低碳轉變的重要主體。2012年多哈氣候大會則強調了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在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損失與損害等方面的貢獻。2015年,《巴黎協定》以正式公約形式規定了:“歡迎所有非締約利益攸關方,包括民間社會、私營部門、金融機構、城市和其他次國家級主管部門努力處理和應對氣候變化。”這使得氣候治理不僅僅是國家自主貢獻的“自上而下”,也包括多利益攸關方“自下而上”的努力,從而開啟了全球氣候治理的新紀元。
第二,多利益攸關方通過更靈活的機制影響氣候談判與治理進程。多利益攸關方主體憑借靈活參與、媒體報道和社會監督等不斷影響氣候大會談判的權力構造。首先,多利益攸關方運用靈活的談判參與方式,促進各主權國家就都能接受的方案達成共識,尤其是在談判陷入危機時,可以幫助彌補治理赤字和合作困境。其次,多利益攸關方通過新聞傳播等手段使氣候治理傳播到公共領域,構建公共傳播綠色領導力,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最后,多利益攸關方以自己的專業化知識增強了氣候治理的科學權威。
第三,多利益攸關方推進了氣候治理“優先議題”設置、促進了氣候談判議題動態調整與變革。在議題的選擇上,多利益攸關方要設法選擇與本身利益相關又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議題,從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議題設置上,聯合國氣候公約秘書處提出以締約方與非締約方共同利益為導向,為聯合國氣候談判確立優先議題事項,從而提升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大會的積極性,《馬拉喀什全球氣候行動伙伴關系》通過結構化的框架鼓勵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大會。
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不斷發展的多元動因
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達成以來,傳統基于主權國家的氣候政治博弈在全球集體行動中時常產生治理赤字,導致無法實現控制全球升溫的人類利益。多利益攸關方在氣候談判的歷史初期并未得到應有重視,在“后巴黎時代”,多利益攸關方逐漸走向氣候談判中心,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可從國際法演進、氣候談判權力結構轉型、美國等大國氣候領導力赤字,以及聯合國自身改革等維度分析:
第一,從國際法維度來看,氣候治理規則體系碎片化為多利益攸關方提供了更多的制度參與空間。氣候治理體系碎片化主要體現為氣候治理領域的擴展與氣候治理國際國內法治體系的脫節。隨著可持續發展指導原則的功能性擴展,大氣部門、能源部門、農業部門、交通部門、海洋部門和經濟部門等重要領域都介入了氣候治理。氣候治理法制體系脫節現象嚴重。氣候治理本身集多元化的利益、權力、信息與信仰于一身,很難形成一種綜合的、一致的體制規則,而最后產生的各種治理規則共存的治理方案,也擴展了多利益攸關方的制度參與空間。
第二,氣候變化治理的權力結構逐漸下沉,“軟治理”“軟權力”逐漸上升。多利益攸關方通過多維“軟權力”產生了重要影響,彌補了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主權國家政治博弈的集體行動赤字。氣候治理體系是主權國家構成的網絡化結構,利益集團的分散與不規律重組又是氣候治理“共治”困境的重要原因。歐盟(EU)、傘形集團(Umbrella Group)和“77國集團和中國”(G77+中國)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以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的三個關鍵談判聯盟。在國際權力變遷的復雜背景下,集團內部利益與政治博弈也存在結構性變化,諸多國家談判集團利益訴求不一,導致通過全球政治談判達成自上而下的共識成功率趨于降低。推進全球自愿參與和自下而上的氣候行動需要軟治理,主權國家處于物質能力基礎上的結構性領導地位,而多利益攸關方則保持在社會監督、輿論傳播等基礎上的軟權力。
第三,全球氣候談判中的大國領導力赤字隨“逆全球化現象”日益凸顯,非國家行為體為回應“逆全球化現象”,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政治,形成話語權建構的新路徑。在特朗普政府氣候政策全面倒退的時期,美國多利益攸關方在參與氣候公共外交活動方面卻日益活躍,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地方氣候行動。相關理念也融入拜登政府2021年關于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中。
第四,多利益攸關方參與也是聯合國氣候治理體系變革的需要,它能有效拓展聯合國氣候治理的社會支持,緩解執行赤字。首先,聯合國氣候治理機構有待進一步調整。其次,聯合國氣候治理機構的科學性與權威性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進行鞏固。多利益攸關方能夠就氣候變化的科學事實表達獨立意見,是聯合國氣候信息公布的有力支持者,聯合國吸收更多的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增強了在專業上的科學性,尤其是多利益攸關方在當前諸多氣候信息上的掌握,能夠為聯合國提供更加真實可靠的氣候數據。由于聯合國在資金來源上的依附性,多利益攸關方的參與能夠拓展公共財政來源渠道。隨著氣候治理從減排溫室氣體發展到海洋、外空等多元空間治理,氣候治理機構的運行與治理實距也越來越需要資金支持。氣候治理經費在來源渠道和分攤方面存在較大的依賴性,聯合國體制下的會費大多以主權國家貢獻為主,作為氣候融資重要主體的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能夠有效提升聯合國氣候治理的基金融資效率。
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治理發展的局限性與路徑選擇
以氣候變化談判為中心的全球氣候治理系統不斷演進,呈現出各行為體之間復雜、多變和持續的互動進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的上升期位于《巴黎協定》制定之后,如何與主權國家在并存模式下增強協同效應仍存在多種困境。首先,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價值訴求存在差異化。多利益攸關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球氣候治理,但個人、企業、國家等多利益攸關方在面對氣候變化時的價值取向仍有不同。在參與氣候談判和治理時,存在各自分散的政治偏好與利益聯盟,具體表現為:私營部門“天生”的逐利特性、不同智庫專家在氣候變化及氣候政策上存在認識分歧、社會組織自身管理腐敗等問題。這些不同的價值偏好影響了多利益攸關方之間相互協同的發展,也使得多利益攸關方在同主權國家的互動模式中存在合作、對抗和服務等多種可能。從當前來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不同國家對氣候治理的態度有所差別,也體現出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治理的國別不平衡性,如美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的“強勢”氣候公共外交可能會間接壓制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再次,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治理的獨立性較弱。從國際法角度來講,有限的國際法地位使其參與氣候治理的規模和程度受到限制。多利益攸關方并非國際法意義上受到普遍承認的主體,與主權國家是一種共生并存關系,而不是替代邏輯。正是由于主體上的局限性,多利益攸關方在強權政治的主導下,通過倡議、游說等手段參與氣候治理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組織的獨立性挑戰主要體現在資金來源的附屬性。當資金短缺時,社會組織可能更傾向于從事商業活動,以自身發展為優先,無法兼顧氣候治理。跨國公司參與氣候治理主要是通過綠色投資,但跨國經營風險波動使低碳投資的連貫性難以保障,進而使氣候低碳鏈的發展可持續性受到考驗。
針對上述局限性,面對多利益攸關方價值差異化帶來的協作沖突,需要對多利益攸關方進行適當管理,挑選出合格主體參與氣候談判進程;對于多利益攸關方在代表性上的不足,關鍵在于增加代表機會供給,在堅持多邊主義的基礎上,注重以“受氣候變化影響”劃分的代表均衡;對于獨立性困境,需要從國際法和自身視角,增強其在國際條約體系中的地位。
第一,以“自上而下”的聯合國管理制度實現多利益攸關方于氣候談判的漸進參與。雖然氣候治理范式呈現從“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轉型的趨勢,但并不意味著主權國家主導的氣候治理模式被拋棄。聯合國體制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主渠道,對氣候公約的達成、氣候治理知識的宣傳及氣候行動的監督都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締約國的“自主貢獻”報告制度等依然具有督促締約方國家加快氣候行動的推動作用。將多利益攸關方納入非締約方范疇,與締約方實現氣候治理的直接談判與協商,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的新階段。但由于多利益攸關方涉及主體較多且日益活躍,加強對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機制的構建有利于氣候治理體系的有序化演進。結合經社理事會對社會組織的管理機制,應為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治理設置規范:其一,參與對象擴大化;其二,建立統一的協調機制;其三,落實好多利益攸關方的激勵機制;其四,構建監督機制。
第二,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邊主義”推進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談判進程。《巴黎協定》的動態機制要求194個締約方就復雜冗長的條約的每一個細節做出協商一致的決定,而隨著時間推移,代表不同利益的談判集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立場,氣候政治談判已經產生了效應遞減現象。與主權國家政治談判不同,無論是全球層面、區域聯合治理還是國內層面,多利益攸關方靈活參與蔚然成風,其參與氣候談判的路徑主要分為“大多邊主義”與“最小化多邊主義”兩種方式。“大多邊主義”氣候聯盟強調平權國家之間實現多邊氣候治理,“最小化多邊主義”強調主權國家與多利益攸關方共同參與單元構建。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最小化多邊主義達成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協議,使得責任承擔主體社會化。
第三,提升多利益攸關方在氣候談判體系規則中的地位,完善自身管理機制。從強制力角度劃分,氣候談判規則體系包括硬治理和軟治理兩種類型。前者以《巴黎協定》等國際條約為代表,后者主要為不具有強制力和非國際公約的規則體系的統稱。從治理效果來看,軟法具有彈性的執行遵約系統,并且規則的制定較為靈活。在較多情形下,遵約效果反而優于硬法。因而在氣候談判體系中,應該進一步加大多利益攸關方進行軟法規則制定的權利。除軟規則制定權外,還應完善對地方、社會和市場力量參與氣候治理的監督機制,之前的監督主要是通過社會輿論、媒體傳播等途徑發揮功效,影響力較不穩定。在氣候規則體系中,將多利益攸關方正式納入遵約督促程序,賦予其提交調查報告、提起司法訴訟等權利。
中國多利益攸關方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現狀與應對
在多利益攸關方不斷參與氣候治理進程中,中國城市、跨國公司、社會組織也越來越重視國際合作,并在氣候地方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然而與西方把多利益攸關方參與作為有效的公共外交政策工具不同,目前中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全方位提升相關能力和制度建設,實現中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的行穩致遠。
第一,中國多利益攸關方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現狀
來自中國的多利益攸關方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從民間治理網絡的快速發展到城市優先表率作用的發揮,中國正在全球治理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自簽署《巴黎協定》以來,來自中國的組織與企業不斷提高其參與全球氣候行動的積極性,共享來自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先進理念與實距。另一方面,城市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重要性不斷突出。作為碳中和與氣候合作進程中的重要非國家行為體,城市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地位日益被重視。與此同時,更應當意識到中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仍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深化中國多利益攸關方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思考
中國想要加強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地位,還需進一步加強多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度,積極運用多利益攸關方途徑參與全球氣候談判與治理,具體包括完善中國氣候援助實施方式、加強私營部門的投入和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等方式,并且加強同多利益攸關方的合作,來深化中國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在全球氣候治理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多利益攸關方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斷增強,多利益攸關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全球治理體系亟待變革,多利益攸關方存在多種局限,但多利益攸關方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地位、參與路徑和議程設置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斷的發展。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應加強本國多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度,既幫助解決多利益攸關方參與氣候治理的困境,又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更加強中國在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領導力和話語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