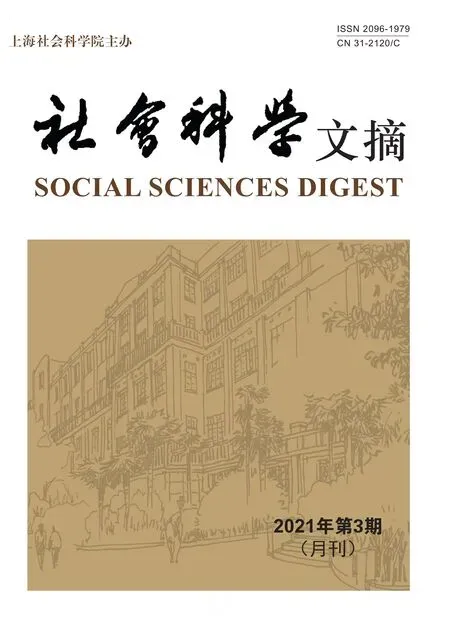中國古代長城的歷史角色
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在條件具備、實力強大時,一般都盡可能地在邊疆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但當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權逐漸陷入制度煩瑣、官僚腐敗而導致的低效困局,經濟收入被各種權勢集團侵占,自然災害造成人口流徙,軍隊戰斗力下降,邊疆開拓便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這時候其往往轉而在邊疆地區采取防御政策。不僅如此,由于中國古代中原王朝是農業政權,即便在條件具備之時,時常也會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大規模推廣農業經濟的臨界點,轉而采取保衛勝利果實的防御立場。也就是說,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在相當時期,甚至部分王朝在大部分時期,整體上其實處于防御立場。正是為了加強防御,中國古代在陸地邊疆尤其北部邊疆,長時期、大規模修筑長城。明代以后,面臨海上的挑戰,中原王朝在東部沿海同樣構建了長城防御體系。長城雖然在中國古代長期保護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盤”,卻一直未能主動解決來自邊疆的威脅。由之所帶來的“反噬效應”反而加劇了中原王朝的財政危機、社會危機,最終導致全面的政權危機,成為中國古代歷史變遷的重要因素。
中國古代長城防御體系的立體特征
在防御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為了防御北方族群,在北部邊疆,長時期、大規模地修筑長城。中國古代之所以修筑長城,是出于戰術、財政、政治等多種考慮。
在古代世界,騎兵的出擊快速迅捷,因而具有很強的沖擊力與機動性,在作戰中占據明顯的優勢。在中國古代,北方族群憑借騎兵戰術,在與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大多數時間占據著優勢。為了應對北方族群騎兵的沖擊,中原王朝不僅要解決步兵如何抵御騎兵的戰術問題,而且要面對北族騎兵戰略上的聲東擊西,“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的靈活性所帶來的飄忽不定,以及中原軍隊千里尋敵所帶來的糧餉、物資供應問題。在古代社會,交通運輸條件較為落后,戰爭所必需的后勤供應對于財政收入有限的古代政權來說,是一項巨大的負擔。不僅如此,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農業經濟之上,對于戰爭所引發的社會動蕩與勞動力減少,更顯得缺乏耐受力。因此,中原王朝對北方族群的作戰,不僅是一項軍事問題,還是一項財政問題,最終是一項關系政權全局的政治問題。為此,中原王朝嘗試以修建長城加以應對。長城具有五種戰術功用,能夠有效克服北族騎兵的沖擊力與機動性。
第一,長城最外層是連綿的烽火臺,守臺士兵看到北族騎兵,便可以通過傳遞烽火、狼煙等形式,將敵情傳遞給長城沿線軍隊,使其可以根據來犯敵軍的數量、進攻方向,進行有針對性地調動與部署。
第二,烽火臺以內是邊墻。邊墻以一道墻的形式,直接御敵于國門之外,從地形上阻擋了北族騎兵,從而保護了中原王朝統治的“基本盤”,保障了正常的農業生產。北方族群如果要穿過邊墻,勢必要挖墻,或者尋找薄弱環節,這樣其快捷的機動性便會有所下降。同時,即使北族騎兵挖墻而過,進入長城內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補邊墻,北族騎兵返回時也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圍追堵截。
第三,長城除邊墻外,還包括壕塹、鎮城、營堡、城寨、墩臺,是一種立體防御體系。中原王朝修筑邊墻時,往往從墻外取土,從而在邊墻外形成了一道壕塹,相當于城墻的護城河,這增加了北族騎兵越界的難度。由于北部邊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時,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這樣不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馬匹可以飲水吃草。同時,中國北方降雨較少,農業種植需要借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農業區也呈現沿河分布的格局。為保護農業區、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鎮城、營堡、城寨、墩臺等長城設施,在北族騎兵到來時,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層層阻截,機動開展戰爭,從而彌補了步兵的短處,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騎兵優勢。
第四,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不僅修筑長城設施,而且在北族騎兵進犯之時,將附近的民眾、牲畜、物資收容進鎮城、營堡、城寨、墩臺中,實行堅壁清野的戰術,防止人口、物資被北方族群搶掠,實現阻止敵軍的戰略目的。同時,王朝政府還倡導民眾修筑民堡,在廣闊的北部邊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僅最大限度地實行堅壁清野的戰術,而且將民眾武裝起來,進行軍事訓練,從而實現了北部邊疆社會的普遍“軍事化”,使北方族群進入長城地帶后,面臨著“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第五,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墻體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橫向的,而且有多道縱橫的墻體,從而將北部邊疆切成一個個包圍圈,北族騎兵一旦進入,便很難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別有大邊長城、二邊長城,西部又與寧夏鎮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墻。
總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通過在廣闊的北部邊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構建起立體的長城防御體系:一是不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騎兵優勢,而且將自身步兵的短處充分掩蓋起來,在防御中實行局部的進攻,將自身的戰術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二是不僅通過堅壁清野,充分保障了邊疆民眾的生存、經濟生產與生活物資,而且破壞了北族騎兵“因糧于敵”的戰術和搶掠民眾、物資以壯大自己的戰略目的;三是不僅克服了北族騎兵的沖擊力與機動性,保住了自身統治的“基本盤”,而且減少了軍事調動、戰爭所帶來的巨大財政開支,有利于自身的社會穩定與政權穩固。概而言之,在解決北方族群問題上,長城是一項具有多種功能且現實有效的軍事工程。
中國古代關于長城的政治爭議與政治取向
但在中國古代,圍繞長城的爭議,自其修筑之始,便長期存在,一直伴隨長城修筑之始終。對于長城的爭議,主要來自軍事理念、財政觀念與政治文化等層面。
首先,從軍事理念而言,長城由于是被動性的軍事防御設施,從而不是具有開拓疆土愿望的政權所優先選擇的軍事方案。在具備一定軍事實力的情況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還是更為傾向于通過進攻形式,徹底解決軍事威脅,開拓邊疆,彰顯尊嚴。
其次,修筑長城需要耗費大量財力,勞役民眾。主張從“民本”思想出發、節約財政、愛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團對此具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感。中國古代實行“量入為出”的財政制度,修筑長城的巨大開支,是每個政權在開展這項工程之前,都必須考慮的問題。大規模修筑長城所帶來的賦役征發,不僅有可能對正常的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沖擊,而且容易引發社會動蕩與民眾叛亂,從根本上威脅政權的穩固。
最后,中國古代“內政為本”的政治觀念,對包括修筑長城在內的所有軍事方案,都傾向于發出強烈的政治倫理批判。這種政治觀念認為解決好內政問題,是維護政權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的“節用而愛人”,便是這一政治觀念的具體體現。
長城的“反噬效應”與歷史影響
中國古代圍繞長城的爭議,還有另外一種考慮,即長城終究是一項防御方案,無法主動、徹底解決北方族群的威脅,從而使中原王朝與北方族群的戰爭呈現出長期對峙的狀態。并且,伴隨著防御持續日久,中原王朝軍隊戰斗力逐漸下降,長城防御的實際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長城防御便逐漸陷于被動的態勢。這不僅給中原王朝帶來了巨大的軍事壓力,而且給長城邊疆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并最終形成“反噬效應”。
長城邊疆所在的地區為生態環境較為惡劣、生態災害易發的“生態高危區”,是經濟方式較為單一、經濟條件較為落后的“經濟落后區”,是國家財政長期處于危機狀態的“財政危機區”,同時又是大規模戰爭連綿不斷、社會長期處于“軍事化”的“軍事風險區”。簡單地說,長城邊疆在災荒多發、經濟落后、財政匱乏的同時,還長期支撐著大規模戰爭,從而成為中原王朝地緣政治版圖中最為脆弱、風險系數最高的區域社會。在正常條件下,長城邊疆社會已經處于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困境,一旦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爆發,長城邊疆社會便會迅速崩潰。由于長城邊疆社會呈現高度的“軍事化”局面,一旦社會崩潰,被武裝起來的長城邊疆軍民便會揭竿而起,他們所擁有的組織性、戰斗力都會成為政權的巨大威脅,即形成所謂的“反噬效應”。
關于長城“反噬效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滅亡于長城周邊的軍民叛亂與清軍入侵。在陜西榆林長城防御體系構筑不久的明成化末年,延綏鎮已是北疆諸鎮中財政最為困窘者。由于榆林長城體系立足于防御,而未主動、徹底解決河套問題,蒙古逐漸南下河套、固定駐牧,對榆林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也使延綏鎮的財政危機不斷加劇。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長期有效機制,明朝將整個榆林社會發動起來,征召民眾進入軍隊、驛站等軍事體系,并倡導民眾修筑民堡,實行自衛,榆林從而形成高度“軍事化”的社會。明末陜北發生了大規模的嚴重旱災,明政府為了應對財政危機,采取了大幅度裁減延綏鎮軍事體系外圍部分的措施,直接導致包括驛卒李自成、士兵張獻忠在內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李自成等人借助其豐富的軍事經驗,橫掃了大半個中國,最終滅亡了明朝。
而結束明末農民戰爭、取代明朝的軍事力量來自明遼東長城外側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遼東長城邊疆原屬明朝的羈縻衛所,這一地緣特征在努爾哈赤發布的《討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確表述。用滿文記述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五恨曰:“許多世代看守皇帝邊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邊墻外側,曾經長期充當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緣角色。在第一恨中,其不僅指出建州女真負責為明朝看邊,還與明朝開展朝貢貿易:“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于萬歷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建州女真借助長城外緣的地緣優勢,不僅能夠長期得到來自明朝的生存物資,還能不斷招徠漢人翻越長城,進入東北平原,并融合草原上的漢人。憑借多族群的優勢和長期積累,清朝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實力,最終取代明朝,統一全國。
可見,長城一方面長期保護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盤”,維護了中原王朝的社會穩定與邊疆穩固;但另一方面,長城作為一種防御方案,無法主動、徹底地解決北方族群的威脅,守軍在長期消極因循中反而呈現戰斗力下降的戰略劣勢,最終在長城邊疆社會的“反噬效應”下,政權瓦解。因此,對于長城作用的評價,應放置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具體歷史背景中,多角度地客觀分析,從而避免落入單純肯定或單純否定的窠臼。
作為生態界限而非族群界限的長城
絕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除了北朝長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間的界限之外,其他長城都是漢人與其他族群的界限,但歷史事實并非如此。雖然中原漢地農業經濟較為發達,但普通民眾承擔著沉重的賦役,尤其是北部邊疆的民眾勞役更重,且時常遭受邊疆戰亂的沖擊。為逃離這一困苦的生活環境,北疆不少漢人越過長城,潛逃至草原地帶。這一現象西漢時期便已出現,有記載表明,不少漢人越過長城,投奔了匈奴。
而在明代,這一現象愈發嚴重。例如,明正德時期,給事中毛諫奏:“臣又聞虜中多半漢人,此等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此患。”而在這一時期,發生在寧夏鎮興武營的一場對話也揭示了這一歷史現象:陜西三邊總制王瓊命寧夏鎮糧食運往甘肅鎮,邊墻之外的蒙古聽到邊墻以內不斷運輸的聲音,派遣五名部眾前來偵查,而這些部眾本為寧夏鎮韋州人,只是因為“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才脫離明朝,北入草原。
遁入草原的漢人,聚居于明長城之外,從而形成了大片定居的農業聚落,被稱為“板升”。“板升”的規模很大,分布在山西大同以北的南北四百里、東西千余里的廣闊區域內。他們將蒙古高原的游牧經濟方式改為農牧結合的復合經濟方式,從而推動了明清時期蒙古高原的經濟方式的轉型。
不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漢人,還有白蓮教徒。這些教徒造反不成,從而有組織、成規模地進入蒙古草原,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從而成為明后期挑動邊疆戰爭的政治勢力。“板升”曾為蒙古進攻明朝積極出謀劃策,蒙古首領俺答汗每次進攻明朝之前,都要和“板升”首領趙全商議。明嘉靖十六年(1537),山西巡撫韓邦奇曾指出蒙古作戰方式與之前有所不同。在他看來,這一變化根源于大量叛逃的明人、明軍的出謀劃策。“板升”還竭力推廣漢人的政治體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為蒙古可汗,“板升”集團又進一步鼓動他模仿漢制,登基稱帝,而趙全被俺答汗任命為把都兒汗,統治“板升”漢人。“板升”集團不僅擁立俺答汗稱帝,而且建議他攻占、統治長城邊疆,模仿五代時期石晉故事,建立與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權。
可見,長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漢人與北方族群的界限。在歷史上,漢人與北方族群不斷有跨越長城,加入對方族群的行動。這些人越過長城的形式與動機雖有多種,但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都是為了擺脫原先的困苦生活。可見,長城所隔開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說,長城內外實際上更多體現了生態環境及由此造成的經濟方式上的差別,而非族群之間的界限。從這個角度來看,稱長城為“生態長城”,更能揭示長城最為根本的角色。
明代東部沿海長城防御體系的構建
由于長期缺乏來自海洋上的敵人,元代之前,中國古代一直缺乏對于海疆的軍事經營,軍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陸疆,而非東亞海域。到元代,處于戰國時期的日本列島,遭遇長期戰亂,于是不斷有武裝浪人進入東亞海域,元人將之稱為“倭寇”。“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部沿海,這一問題一直延續到了明初。為了解決“倭寇”問題,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便開始在東南近海地帶,修建了類似于長城的各種軍事設施,比如營堡、墩臺等,從北至南,沿東部沿海地帶綿延分布。主持此事者是明代開國功臣湯和,湯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紅軍的一支——起家于海盜的方國珍之侄方鳴謙部。而在嘉靖時期防御“倭寇”的時代背景下,戚繼光進一步在東南沿海普遍修筑邊墻,由此構建起東部沿海的長城防御體系。
結論
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為加強防御,在北部邊疆建立起長城防御體系,明代在海洋空間開始出現實質性挑戰后,在東部近海地區同樣構建了長城防御體系。然而,長城無法徹底解決來自北方族群與東部海域的威脅,反而經常產生“反噬效應”,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與社會動蕩,甚至帶來全方位的政權危機。可見,長城不僅在中國古代邊疆社會打上了明顯的烙印,而且是影響中國古代歷史變遷的重要因素。長城雖然是政權之間的界限,但并非族群之間的界限;是一條生態過渡區的界限,卻成為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民眾可以跨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