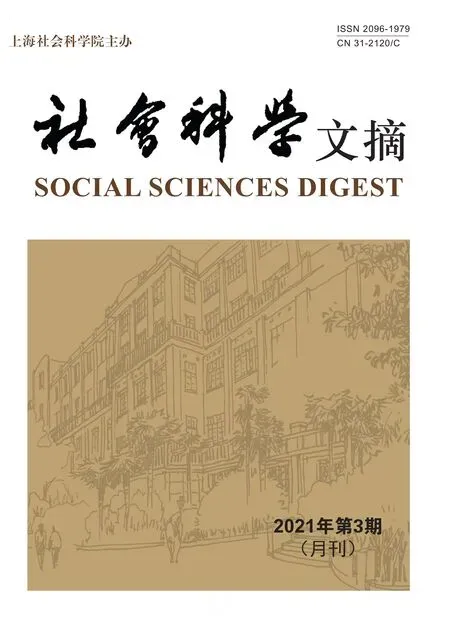從媒體理論到文化技術研究
說到“德國理論”,學界的目光似乎仍聚焦在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闡釋學以及第一代至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身上。本文嘗試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理論的另一種發展作出勾勒和初步總結,這就是以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等人為代表的德國媒體理論以及由之衍生的文化技術研究。我們會看到,這一理論思潮與所謂“法國理論”處在或對立或補充的關系中,在其發展中,又和當下的后人類研究產生了深刻共鳴。凡此種種,都使之成為近30年來德國最重要的理論出口。
一
如同“法國理論”或“耶魯學派”,新德國媒體理論或“德國媒體理論”首先是英美學者在描述、概括諾伯特·博爾茨(Norbert Bolz)、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迪特爾·默施(Dieter Mersch)、西比爾·克雷默(Sybille Kr?mer)、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沃爾夫岡·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人的理論研究時采用的集合名稱。本文將采用新德國媒體理論這個說法,以使之區別于本雅明、阿多諾、霍克海默以及哈貝馬斯等與法蘭克福學派相關的媒體理論研究。這一理論代表學者的思想產生自相同的學術環境,帶有相似的傾向性和理論特點。
首先,這一理論的發展動搖了聚焦于文本的闡釋學在“二戰”后德國理論界的統治地位,對“交流的物質性”予以重點關注。“交流的物質性”強調一種非闡釋性的無意義,它既是意義的基礎,也是意義的深淵,而被傳統文學研究、哲學研究忽略的“媒體”正是這一物質性的具體體現。由此,媒體成為一種認識論工具。甚至,從媒體出發,我們還能揭示出作為一種話語的闡釋學本身產生的原因、功能及其歷史局限性。
其次,對交流之物質性的強調也使新德國媒體理論與英美以內容分析為主的大眾媒體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區別開來。如我們所知,自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編碼/解碼”理論以來,英美的媒體理論研究就將重心放在媒體呈現的內容即“再現”上來,并從社會學角度探討再現的條件及影響等。與之對立,新德國媒體理論探討媒體的技術層面及再現的物質機制本身。在這方面,基特勒對電影、留聲機和打字機以及計算機軟件等的研究,西格特對郵政系統的研究,恩斯特對數字媒體的媒體考古學研究以及擴而言之文化技術研究本身,都是顯明的例證。新德國媒體理論對內容分析的摒棄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它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與媒體關系研究分道揚鑣。它以“媒體分析”甚至是某種“技術狂熱”取代了法蘭克福學派那里普遍存在的“媒體恐懼”。
當然,新德國媒體理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作出新的詮釋,并在新媒體語境下用媒體分析取代了話語分析。在這種意義上,有學者認為它可被稱為“德國的后結構主義思想”。新德國媒體理論學者就是后結構主義思想在德國傳播中的中堅力量和堅定捍衛者,其研究也體現出后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比如,基特勒的媒體理論就曾被人描述為德里達、福柯、拉康理論與麥克盧漢媒體思想的結合。他曾富有創造性地將留聲機、打字機和電影與拉康理論中對真實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劃分聯系起來,使之一一對應。不過,這些學者也對后結構主義思想提出最深刻的質疑。比如,基特勒就認為,福柯的話語理論只和圖書館、書籍或“寫下的句子”有關,適用于印刷或書寫文化,在面對聲音檔案或電影膠卷時就無能為力了。更重要的是,福柯忘記了“在最后落在圖書館之前,甚至書寫本身也只是一種溝通媒介、一種技術”。由此,相對福柯關于打字機鍵盤上“QWERT不是話語”的論斷,基特勒認為打字機本身就是“決定我們的處境”的一種主要媒體。此外,西格特也曾對德里達提出的“郵遞原則”進行了拓展,認為它意味著延異本身的產生就依賴于技術條件的操作。西格特曾總結道:“(新德國媒體理論)通過將話語從其哲學或人類學之源逆轉到其歷史和技術根底,克服了法國理論對話語的癡迷。”
二
新德國媒體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基特勒,其學術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基特勒的研究以文本或者說“話語分析或經典文學文本的‘考古學’”為中心,并已經體現出福柯、拉康等人的影響。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基特勒對包括留聲機、電影、打字機等傳統媒體技術以及計算機等數碼科技展開廣泛探討,出版了《電影,打字機,留聲機》《視覺媒體》等著作。正是在前一部著作中,他提出“媒體決定我們的處境”這一論斷;而在數碼媒體方面,他也曾驚世駭俗地提出“不存在軟件”等命題。最后,21世紀以來,基特勒將精力和時間投入到更廣闊意義上的“文化技術”的研究中來,在學術生涯的最后幾年對西方歷史上的音樂和數學標記體系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出版了厚重的兩卷本《音樂與數學》(2006年,2009年)。當然,無論在德國學界還是英美學界,基特勒最為人所知的還是他提出的著名的“話語網絡”(Aufschreibesysteme)理論。所謂“話語網絡”,指的是“使某一給定文化能夠選擇、存儲和處理相關數據的技術與機構網絡”。從信息理論的發出端、信道、接收端和控制論中的反饋理論等出發,基特勒對1800年以德國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文學為主要內容的“話語網絡”和1900年電影、留聲機和打字機誕生后德國乃至歐洲現代主義文學為主要內容的“話語網絡”進行深入探討。概括地說,我們可以把“話語網絡”理論與福柯的知識型或話語理論類比起來,只不過,如果說在“知識考古學”中,福柯最終仍是將知識型或話語奠定在屬于語言范疇的“陳述”及其條件上,那么支撐起基特勒“話語網絡”的則是包括言說、閱讀、書寫等語言功能和打字機、電影、留聲機等技術媒體在內的形形色色各式不同的“媒介”。
基特勒之外,西格特在其《中繼:作為郵政體系之一個時代的文學》(1993年)中,就郵政體系對文學創作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這種影響基于文學創作本身的“中繼結構”,因為文學所傳遞的事物依賴于作者事先對創作內容、意圖等的隱瞞。我們自然可以把西格特所謂的“中繼結構”與德里達的“延異”聯系在一起,但西格特更為關注的是具體的郵政和信息傳遞技術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舉例來說,他認為17世紀郵遞的發明和大眾化促成了18世紀中期書信寫作的性別化:閱讀書信猶如聆聽和解讀某人內心的獨白或懺悔。不過,如許多批評者指出,從總體上看,西格特對郵政系統與文學創作關系的論述時而顯得牽強,對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論述也缺乏說服力。但對文學研究來說,西格特這部著作最大的優點或許就是讓我們切實意識到通信技術和媒體的發展與文學創作的演進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關聯。2003年,他又出版了《數碼通道》一書,對數字技術和數碼媒體進行了極其廣泛而又深入的考古學研究。
與基特勒和西格特強調媒介之技術特性的路徑略有不同,克雷默提出了以傳播行為為核心、強調“媒介性關系”的媒體理論。在2008年出版的《媒介、信使和傳輸:媒體哲學的一種途徑》中,克雷默提出媒體理論中兩種競爭性的原則:“技術”或“郵政”原則,“個人”或“色情”原則。依據“郵政”原則,通訊或傳輸是非對稱的、單向的,而媒介則成為通訊的必要條件,在發出者和接收者之間建立關聯。我們看到,這正是傳統信息理論所定義的通訊。與此相反,“個人”或“色情”原則將通訊視為一種社會互動或對話,其目的是理解或“共識”。據此,通訊是一種對稱的、相互的過程,它需要消除任何介入性媒介可能帶來的干擾。在克雷默看來,“色情”原則就體現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和“公共場域”理論中,其目的是將本質上歧異的世界轉換為同質世界、將差異轉換為同一性。通過對本雅明、讓-呂克·南希、米歇爾·塞爾、雷吉斯·德布雷等理論家的解讀,克雷默致力于“恢復郵遞原則以及通信的傳輸模型的地位”。在他看來,通信的傳輸模型以及“郵遞”原則明確地體現在“信使”(messenger)概念中,因為首先,信使的功能是中介不同的世界又繼續維系區分開不同世界的距離;其次,信使能讓我們感知到某物,由此以物質形式使非物質事物具體化,這也意味著任何傳輸都是某種展示;最后,信息的具體化意味著信使的解體,信使必須消失在信息內容背后。克雷默認為天使、病毒、貨幣、翻譯者、精神分析學家、證人、地圖等都是信使,而每一個信使的形象都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它也可以“作為可反轉的形象發揮作用”。比如,天使可能轉換為魔鬼,貨幣會帶來貪婪,翻譯者會成為錯譯者,而證人也可能作偽證。
三
在后繼的發展中,新德國媒體理論又衍生出“文化技術”(Kulturtechnik)研究這一在當前德國理論界占據重要地位的學術潮流。上面我們看到,基特勒已經開啟了這一轉向。“文化技術”覆蓋的范圍極為廣泛,如西格特所說,舉凡“標記卡、書寫工具、打字機、話語操作符號(如引號)等不起眼的知識技術,黑板等教育媒介,鋼琴等樂器,字母表化等規訓技術等”都是“文化技術”。或者,用另一分類法來說,“文化技術”不僅包括傳統媒體理論所研究的電影、留聲機、打字機等模擬媒介和計算機等數字媒介,更是將書寫、計算、閱讀、繪畫、音樂創作等文化行為,圖表、鐘表、日歷、標記卡、書寫工具、透視法、地圖、字母表等“知識技術”以及語言學習、音樂訓練、法律程序等規訓技術納入自己的關注范圍。就此,可以說“文化技術學”是在人類學、文化學等更廣闊的理論視野中對新德國媒體理論的進一步推動和衍生。
在《文化技術:網格、過濾器、門和其他對實在的表述》一書的前言中,西格特曾回顧了“文化技術”一詞在德國文化史中從“農業或農村工程學”(19世紀晚期以來)到“閱讀、書寫、計算等基本能力”(20世紀70年代以來)再到新德國媒體理論視域下“文化技術”的三次詞義變遷,繼而對自己眼中文化技術學研究的特征作出了總結。從西格特的總結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他對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德勒茲的生成哲學以及后人類主義相關理論的借鑒,而基于一種過程性的本體論,西格特也對文化技術或媒體的居間性、中介性作出了在我們看來非常重要的強調。
不過,就文化技術學研究來說,在西格特之外,還存在著另一條非常重要的進路。在與藝術史家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合撰的《文化、科技、文化技術——超越文本》中,克雷默對所謂“文化的話語化”作出批判。所謂“文化的話語化”,也就是在“語言學轉向”的影響下,人們“將文化僅僅視作文本”。在兩位作者看來,“文化的話語化”有三種顯著缺陷:首先,“對圖像的認識論力量作出了誤判”;其次,“對數學形式主義不加支持”;最后,它“一邊倒地將媒體—歷史和媒體—理論研究集中在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的關系上來”。他們認為,文化技術研究可以糾正上述三種缺陷,并為我們的文化和媒體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在我們看來,克雷默和布雷德坎普對文化技術研究的最重要的貢獻仍是對語言學化的文化的深刻批判,并凸顯了數學形式主義和圖像的地位和重要性。這一傾向也體現在兩位作者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說,在兩位作者身上,文化技術研究切實地與科學史、藝術史、圖像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并由此拓展了自身的領地,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文化技術的理解。
四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轉折點前后,新德國媒體理論又有新的發展,這或許可以沃爾夫岡·恩斯特為代表。恩斯特通常被認為是媒體考古學家,其研究以檔案概念為核心,只不過,如果說福柯、德里達等人提出的“檔案”理論仍將重點放在文本檔案和敘事之上,恩斯特則將視野拓展到當前以軟件和算法計算為基礎的數碼檔案或數碼記憶。在這種意義上,恩斯特的理論同樣是在新媒體語境下對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的進一步拓展。此外,秉持基特勒對媒介之技術屬性的強調,恩斯特也將媒體理論研究放置在對具體媒體設備上來。更重要的是,恩斯特對媒體的時間性或機器時間進行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媒體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與人類歷史迥然區別開來的“時間—決定性的視野”(time-critical perspective),或者說,(數碼)媒體對信號的處理、操作、執行和同步化等構成一種“微觀—時間性”(micro-temporality),后者對立于人類歷史的“宏觀—時間性”(macro-temporality),并讓我們看到了媒體技術或機器自身所擁有的某種活躍的能動性。這自然會讓我們聯想起如今在英美學界大行其道的后人類主義,只不過,可以說恩斯特對媒體技術本身產生其中的社會背景及其可能的政治意涵置之不顧,由此抹除了“后人類理論”中可能的政治維度。在其最新著作中,恩斯特更是將他所強調的技術媒體的微觀—時間性與他所謂的“聲波性”(“sonicity”)概念聯系在一起,這里的“聲波性”指向的與其說是人對聲音的感知,不如說是技術媒體和機器在對信號的處理中產生的“操作性的時間性”,而人類的音樂只是這種時間性的一個象征和類比而已。
五
以上我們對近40年來德國涌現的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研究作了一番梳理。對國內的文學理論、媒體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來說,這一理論流派或許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首先,新德國媒體理論對媒體的技術層面或“交流的物質性”作出突出強調,這也使它區別于英美以“表象”為核心、以內容分析為重點的大眾媒體研究及文化研究,這種區別在后來的文化技術研究中表現得或許更加明顯。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學研究為我們開辟了媒體理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條新路徑、一種新方向。其次,新德國媒體理論是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與麥克盧漢等人帶來的“媒體覺醒”的融合,后結構主義思想在文化技術學發展中的影響也清晰可見。由此,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研究為我們繼承、推進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提供了一個堪稱完美的示范,這對于我們吸收、引進一般意義上的西方理論也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最后,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研究具有明顯的“后人類主義”傾向。事實上,西格特本人就曾論及這種傾向,并認為如果說英美學界的后人類理論研究主要以生物學理論為靈感來源,并將重心放在批判性動物研究上,那么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學的后人類理論特性則體現在對技術以及人與技術共生的強調上。就此來說,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審視、反思人類學差異的新視角。
當然,這一理論流派最重要的意義或許還是在于,雖然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學沒有提出某種總體性的“媒體本體論”,甚至對“何為媒體”問題不加定義,但它仍為我們思考何為媒體、媒體何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和參考。就此來說,新德國媒體理論和文化技術學也可以為我們建設某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媒體理論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