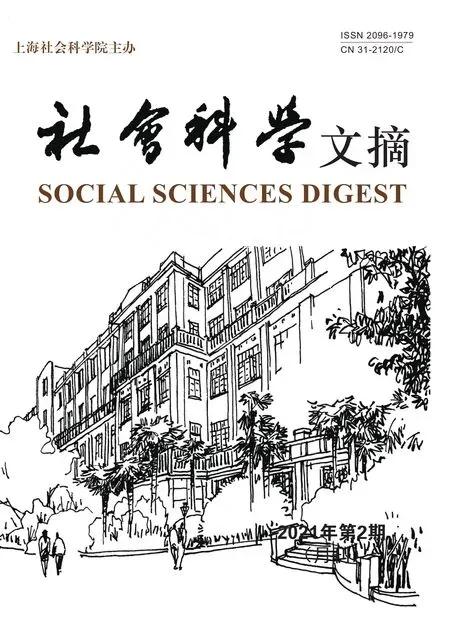公共衛(wèi)生危機與西方民粹主義的國家依賴
文/林紅
2020年必然會在人類災難史、防疫史以至政治史和經(jīng)濟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這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影響了從微觀到宏觀的人類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在政治學的視野中,這場疫情提供了如此豐富的經(jīng)驗材料和研究選題,圍繞著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利益紛爭,既折射出國內政治,也攪動了國際政治,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全球政治將因這場疫情而發(fā)生重大改變。在被新冠疫情改變了的政治與經(jīng)濟生態(tài)下,西方民粹主義將延續(xù)它的波浪式發(fā)展態(tài)勢,從平緩中突起,繼續(xù)接受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的修飾,成為政治生活的重要構成。
危機干預:國家強勢回歸與政府職能擴張
危機是一種歷史常態(tài),人類社會在文明進步的過程中遭遇過無數(shù)次危機。波蘭尼用“雙向運動”一詞來概括他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的理解,即自由生長的市場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反過來,社會也將組織起來以尋求自我保護。在危機背景下,社會所能獲得的最強有力的保護來自民族國家內部。當危機呈現(xiàn)出市場失靈、社會失序的嚴重情形時,政府是社會與公民所能指望的重要力量,而社會與公民對政府保護能寄予什么樣的期待,取決于政府職能發(fā)揮的意愿與能力。在公共衛(wèi)生危機與經(jīng)濟危機接連襲來、國家力量和政府角色空前突顯的當前時期,歐美國家中潛伏或顯在的民粹主義思潮與運動將會獲得什么樣的機會,值得深入地探討。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在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框架下,政府形成了對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的決定性作用。然而,關于政府的經(jīng)濟功能與社會功能,人們一直爭論不休。一些人主張政府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干預仍舊不夠和政府監(jiān)管放松,因此政府“要加強對金融體制的監(jiān)管力度,對現(xiàn)有監(jiān)管體系進行改革”。但是,另一些人則對政府職能擴張表示抗拒甚至強烈抵制,他們尤其擔心危機過后政府不愿意退出對市場和社會的干預,擔心國家主義、威權主義約束市場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2020年這場嚴重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爆發(fā)之時,國家在動員、組織和調配抗疫資源等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全球治理、國際合作卻嚴重不足。這種反差的結果是,市場是全球性的,危機也是全球性的,但解決方案卻不是,它目前而言仍然只能是本國的。事實上,當今時代的全球性危機可以說是“地方性危機的聚集”,并且任何解決方案本身都是逆全球化的。由于全球危機實際上是各國危機的集合,在尋求地方性方案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就被凸顯出來了。這一現(xiàn)象的背后,是漢密爾頓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極力主張的“行政權的活力”,用福山的話來說,則是“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將自由裁量權下放給行政部門,尤其是在危機時期”。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實行的“羅斯福新政”是在經(jīng)濟危機條件下實踐政府干預的范例。彼時,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應依靠財政政策來刺激經(jīng)濟增長,而“嵌入式自由主義”理論主張市場機制與政治-社會機制的嵌入式發(fā)展,兩者為國家職能的強化提供了理論支撐。戰(zhàn)后20多年間,西方國家的經(jīng)濟職能和社會職能得到了充分發(fā)展,但是由于經(jīng)濟增長的乏力和財政赤字的沉重負擔,福利國家政策最終被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所替代。從此,新自由主義為經(jīng)濟全球化提供了一整套以市場為中心的價值規(guī)范和運作規(guī)則。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國家角色、政府職能才重新得到強調。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和經(jīng)濟危機的悲觀前景再次為國家強勢回歸提供了機會。福山認為在公共衛(wèi)生危機面前,國家將不得不進行干預。著名經(jīng)濟學家羅默和加博也發(fā)表文章表示,美國要避免出現(xiàn)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只有聯(lián)邦政府才能協(xié)調和資助應對這場危機所需要的巨大的工業(yè)動員。3月27日,美國政府出臺了總額約為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以防止美國經(jīng)濟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而陷入深度衰退,這是美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財政刺激計劃。與這一空前的經(jīng)濟刺激計劃相隨的,是美國政府經(jīng)濟與社會職能的進一步擴張。
危機驅動:民粹主義復興的“關鍵節(jié)點”
民粹主義是西方近現(xiàn)代史上的常客,常常與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相伴隨。這種在危機中生長出來的反抗力量,一方面順應了民眾在經(jīng)濟危機重壓下尋求保護的需求,另一方面直接服務于非建制派精英訴諸民眾力量以尋求政治重組的目標。2016年達到頂峰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因全球化過程中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失衡而形成,但具體觸發(fā)和加劇它的則是一系列危機事件,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的歐債危機和2015年前后發(fā)生的歐洲難民危機。對于被全球化改變了政治經(jīng)濟結構的大部分國家來說,民粹主義已發(fā)展成為一種常態(tài)化的反建制思潮與運動。
從經(jīng)濟面來看,經(jīng)濟危機將普通勞動者置于脆弱和恐慌的不利處境,為民粹主義積蓄可以輕易動員的民意。疫情令人沮喪的迅猛發(fā)展、全球統(tǒng)一行動的缺失和歐美國家各施各法的抗疫政策,使得資本市場和社會心理十分敏感和悲觀,各界普遍預測到經(jīng)濟下行甚至衰退的前景。金融市場價格首先受到了嚴重沖擊,金融危機進而會對實體經(jīng)濟產(chǎn)生影響,導致停工停產(chǎn)、消費萎縮、供需失衡、物資短缺,最終實體經(jīng)濟出現(xiàn)停頓、混亂和衰退。全球性經(jīng)濟危機的出現(xiàn)將嚴重沖擊各國生產(chǎn)與消費體系,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體系中,不同的社會成員面臨的危機打擊并不一樣,資本家可能損失利潤和市場,而廣大雇傭勞動者則將失去維持生計的工作。新冠疫情的爆發(fā)對普遍民眾的最大影響是失業(yè)率的急劇攀升。失業(yè)的現(xiàn)實威脅對于普通勞動者而言意味著經(jīng)濟焦慮甚至生存危機,他們中的許多人未必能安然度過漫長的疫情防控時期,這是他們對政府和權貴精英不滿與憤怒的重要根源。
從政治面來看,經(jīng)濟危機可能重組政治機會結構,民眾或將成為政治重組的關鍵力量。經(jīng)濟危機由價值規(guī)律即雇傭勞動者與資本交換在結構上的必然不對稱所決定,它可能演進為社會危機并引發(fā)政治斗爭。在政治斗爭中,資本所有者和靠工資為生的大眾之間的階級對立將進一步加劇。在美國,2009年右翼性質的茶黨運動和2011年左翼性質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標志著美國的政治機會結構開始調整。在德國,2008年之后的經(jīng)濟衰退致使傳統(tǒng)政黨的選民大量流失,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和對德國議會的滿意程度雙雙下挫,這種政治生態(tài)為德國選擇黨等右翼民粹政黨的興起以及反全球化反歐盟和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義運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機會。從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到2008年以來的大衰退,最近一百年間兩次最重要的金融危機都見證了民粹主義的大反彈。歷史經(jīng)驗表明,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對問題狀態(tài)、危機事件的一種應激性反應,它是潛伏還是爆發(fā),取決于危機本身的刺激程度。在沒有經(jīng)濟危機強烈刺激的時期,民粹主義的經(jīng)濟與政治主張不太被人關注,并被主流社會嚴厲排斥;而當危機出現(xiàn),尤其是當深刻而廣泛的經(jīng)濟危機來臨時,民粹主義開始顯現(xiàn)和加劇,這既是對經(jīng)濟危機造成的失業(yè)率上升和福利收縮的抗議,也是對新的政治機會結構的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義固然是一系列危機的產(chǎn)物,但是在民粹主義與經(jīng)濟危機之間卻不存在一種能夠簡化的因果鏈條,即很難單向判斷民粹主義只是經(jīng)濟危機的結果。經(jīng)濟危機確實是民粹主義運動的點火器,但民粹主義運動反過來會成為經(jīng)濟與政治危機的助燃劑。在缺乏政治信任和經(jīng)濟平等的制度條件下,民粹主義與經(jīng)濟、政治危機事實上是互為因果的關系。新冠疫情將許多國家?guī)肓艘环N由公共衛(wèi)生危機發(fā)展而來的經(jīng)濟危機,為民粹主義的繼續(xù)存在提供了適合的條件。這一輪的經(jīng)濟危機可能是劇烈而短暫的,但是應對公共衛(wèi)生危機本身必須由政府領導與組織,必須依賴于國家權威,因此,國家的作用將繼續(xù)強化,政府的職能將有所擴張。后疫情時期的西方民粹主義將延續(xù)2008年以來右翼保守主義路徑,在與民族主義合流的同時更突顯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的特質。
激進與保守:民粹主義對國家的雙重依賴
民粹主義是抗爭性大眾運動的代名詞,它早已內嵌于資本主義體制之中。在19世紀的傳統(tǒng)社會解體危機中,美國人民黨等民粹主義運動應運而生;而在20世紀中期西方的福利國家實踐中,民粹主義暫時偃旗息鼓,人們相信國家在盡力照看著他們,“中產(chǎn)階級社會”能夠提供一種相對平等的普遍富裕;但是當20世紀80年代福利國家難以為繼而被新自由主義取代之后,大眾失去國家的一貫庇護,自由市場統(tǒng)領了經(jīng)濟,并幫助資本控制了政治,民粹主義的大眾抗爭開始醞釀并最終卷土重來。
民粹主義重現(xiàn)江湖的經(jīng)濟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助長的不平等現(xiàn)象。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經(jīng)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福利國家難以為繼而開始潰敗。為了應對沉重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西方國家選擇了市場導向的經(jīng)濟全球化道路,為社會提供保護的能力和意愿大大減弱。隨著全球化過程中經(jīng)濟不平等的日益嚴重,民眾日益不滿與焦慮,逆全球化潮流開始形成,右翼保守主義重返政治舞臺。
然而,民粹主義潮流反抗的不是國家,而是壟斷權力與資源的建制派精英和資本精英。民粹主義確實幫助了一些非建制派精英通過操弄民意而獲得政治好處,但是民粹主義本身是依賴于國家的,它希望國家可以照顧好民眾,使他們免受市場和資本的傷害。傳統(tǒng)的左翼民粹主義在政治上強調國家提供福利、救濟失業(yè)、保護傳統(tǒng)、關照弱勢、保障公平等內容,但一些被打上民粹主義標簽的經(jīng)濟主張則具有某種保守主義的右翼性質,比如強調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重視基礎設施建設、預算赤字擴張和資本控制等。應該看到,民粹主義對國家的期待具有激進與保守的雙重特性。
在國內層面,民粹主義對國家的態(tài)度具有激進主義的左翼色彩,主張依賴國家的力量實現(xiàn)更平等的財富分配和更有意義的民主參與。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會遭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原因在于金融性資本性收益大大高于勞動性生產(chǎn)性收益,資本家從全球化所獲得的收益與普通勞動者相比極其懸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美國發(fā)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一種對富人與建制派精英合謀的強烈反抗;在法國,國民陣線在選舉中節(jié)節(jié)勝利,“黃馬甲運動”表達了對當政者置民眾生計于不顧而企圖征收柴油稅的強烈反抗;在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激進左翼政黨發(fā)動了反對政府削減社會福利、壓低工資的緊縮性政策的民粹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經(jīng)濟精英主導著經(jīng)濟政策,他們有強烈的動機和足夠多的手段使自己的收入盡量不受經(jīng)濟危機影響,經(jīng)濟危機的爆發(fā)將不平等的影響推高到足以引發(fā)政治重組的臨界值。民粹主義成為政治重組的重要力量,與其反建制、反精英特質有直接關系。在民粹主義者看來,經(jīng)濟危機的出現(xiàn)與嚴重的經(jīng)濟不平等有關,建制派精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貧富分化過于懸殊不僅是經(jīng)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說明市場機制已經(jīng)失靈,政府必須強化其經(jīng)濟與社會職能,幫助社會中被嚴重剝奪的弱勢人群,保障公平和正義。2020年的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失業(yè)和經(jīng)濟衰退,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大規(guī)模的金融援助和經(jīng)濟刺激計劃,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失業(yè)救濟和其他福利保障。盡管自由派陣營對財政赤字全力抗拒,但政府干預是左翼民粹主義所需要的。
在國際層面,民粹主義者對國家的態(tài)度具有保守主義的右翼色彩,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堅定支持者。民粹主義者希望保障大眾權益與福利,并把這一希望寄托在強大國家之上。在歐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和政客不約而同地提出類似“重建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訴求,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重新偉大”是如此,要求脫歐的英國民眾是如此,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和德國選擇黨的支持者們同樣如此。民粹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們認為應該將國家從全球市場和壟斷資本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令國家重新強大,回歸傳統(tǒng)民族國家的強勢地位。2008年以來,民粹主義引領了反市場、反資本主義和反全球化的保守主義浪潮,使民族國家得到了強化自身地位和擴張干預范圍的歷史機會。貿易保護主義作為逆全球化運動的基本態(tài)度,體現(xiàn)了民粹主義對市場與資本的不滿、對強大國家的企盼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維護。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保守性質的經(jīng)濟民族主義,其核心目標是保護民族國家的經(jīng)濟主權。在美國,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急于擺脫各種國際機制的束縛,逆轉本國在制造業(yè)領域的不利地位,促使制造業(yè)回流從而解決就業(yè)問題;另一方面對跨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踩剎車,竭力阻止發(fā)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沖擊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在歐洲,由于民主赤字危機、多元文化整合危機和大眾傳媒變革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再加上民族國家認同在歐洲各國內部仍然非常深厚,民粹主義政黨在各國議會的席位不斷增加,反歐盟、反歐元與反移民、反難民的訴求相互呼應,民粹主義社會運動此起彼伏。
民粹主義對國家有著本能的依賴,這是大眾政治對建制派精英掌控各種資源并決定國家方向的反抗。一部完整的民粹主義發(fā)展歷史離不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層面,并且表現(xiàn)出對內對外的兩面性,對內是以階級政治為導向、以爭取平等正義為目標的左翼民粹主義;對外是以種族政治為導向、以維護民族利益與文化傳統(tǒng)為目標的右翼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在政治光譜上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它可能向左端移動,與社會主義合作;也可能向右端移動,與民族主義合流。在民族國家的時代,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依賴于國家意志與國家力量。
結語
經(jīng)濟危機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下的常態(tài)現(xiàn)象,但它又與政府的職能及其履行存在缺陷有關,它的解決離不開政府的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職能的正常發(fā)揮。周期性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既測試了以“政府-市場-社會”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結構的穩(wěn)定性,更考驗了以自由平等為價值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健康度。民粹主義是由選舉民主衍生而選舉程序完全無力應對的復雜情境,它不僅挑戰(zhàn)既有民主制度,而且試圖重組政治結構,甚至提出了民主應該實現(xiàn)什么目標的根本問題。拉克勞認為民粹主義只是一種政治邏輯,并無固定的社會基礎或者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指向,它與現(xiàn)有社會制度有關,并且內生于各類社會變動之中。
當前全球性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嚴重破壞了艱難復蘇中的世界經(jīng)濟,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嚴峻考驗,甚至可能重塑國際政治格局。同時,這場危機可能加劇社會成員對外部因素的恐慌,從而強化某種排外的政治觀念。恐慌的情感與文化可能激發(fā)極端民族主義,助長右翼民粹主義,埋下排他的而非融合的、對抗的而非協(xié)商的危險種子,對于經(jīng)濟危機的應對與國家治理的現(xiàn)代化極為不利。無論如何,討論經(jīng)濟危機中的政府干預及其對民粹主義的影響,最終要回歸到對西方民主質量和國家治理的討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