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主教柵欄墓地藝術探微
□ 陳欣雨
北京柵欄墓地作為天主教在華的標志性墓地,“柵欄石門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最古老的見證之一”(1)Maurice Fabre, Peking. Ses palais, ses temples et ses environs.guid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f, illustré par Y. Darcy, compositions originals de J. Malval.Tien-tsin, Chine, Librairie Fran?aise, 1937. p. 280.。除了墓碑文字背后所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外,整個墓地藝術不容忽視。縱觀中國石刻藝術,歷史悠久,神韻非凡。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經商周玉石雕刻、秦漢陵墓雕刻,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佛教、道教造像石刻的發展高峰,再通過兩宋民間世俗化的轉向,到了元明清時期,總體而言石刻藝術開始式微,然而柵欄墓地所具有的獨特宗教元素讓它在整個中國石刻藝術史上別樹一幟,熠熠生輝。從柵欄墓地藝術不僅可對傳教士的在華地位以及生存處境一目了然,亦可看到中西墓碑藝術與文化的完美融合。
一、以碑載文——柵欄墓地采用傳統刻字碑形制
一般刻字碑主要由三部分,碑首、碑身和碑座,柵欄墓地遵循石刻的固定形制,由于現存墓碑基本都是官方賜予,且等級較高,皆為刻字碑。“其墓碑大多為螭首方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墓碑為其中較為高大者。每塊石碑上分別用中文、拉丁文等不同文字鐫刻墓志銘,或詳或略,長短不一,記載墓中傳教士所屬團體、姓名、國籍、在會時間、來華年代、官職、卒地、亡期、年齡等個人資料”(2)向以鮮:《中國石刻藝術編年史》(愉悅卷兩宋遼金西夏元明清),北京:東方出版中心、中國出版集團,2015年,第1 152頁。。
碑首主要是體現碑主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整個柵欄墓地大多數的碑首下為云盤,上作蟠龍(盤龍)或者游龍紋飾,圖式多為雙龍戲珠。根據碑身厚薄而定龍之規模,一般為兩條或四條,分居左右,龍體倒立,龍頭朝下,龍足盤交,中心留出“篆額天宮”位置。一般情況下,碑首的寬度、厚度都比碑身大,如此雨雪不直接淋于碑身之上,對碑身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碑身即墓碑主體,載有碑主生平或歷史評價。柵欄墓地墓碑至為特別之處,在于碑身鐫刻文字按照書法傳統豎版書寫,主要為漢文與拉丁文對照,其中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二人墓碑還有滿文。漢文大多采用的是魏碑或正楷字體。拉丁文亦規范工整,嚴謹扼要。碑側多刻纏枝紋,又稱“纏枝花”“萬壽藤”,最常見的是蔓草型卷草纏枝紋樣,并配以葉片、花朵或果實,以象征常青、連綿不斷之吉祥含義。如今碑身兩側皆嵌有金屬條,基本已氧化生銹。這是由于墓碑從諸圣堂墻上拆下又重新在東園豎立過程中為了吊裝方便而被加入。“為了將兩部分(筆者:碑身和碑座)更牢固地聯結在一起,接縫部位使用灰泥膩子勾縫,雖有利于保存,但水分較易滲入,導致鐵條氧化”(1)中國國家文物局、意大利外交部發展合作司、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意大利中央修復研究所:《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保護修復方案》(內部資料),2010年,第12頁。。碑座由整塊石材制成,形狀為長方體,上沿作棱邊狀,與地面接觸部分多以浮雕裝飾的圓雕托。柵欄墓地由于特殊的官方地位和歷史變遷,除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墓碑與歷史相符以外,現存的其他很多碑座、碑身與歷史并不相符,這是由于諸圣堂被拆毀后,嵌在教堂墻外的傳教士墓碑散落在校園各處,碑座與碑身分離,而無序堆放數十年后,多數碑座遺失。直到1986年修建東園碑林時,這些殘碑才有安身之處,因當時建園是以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誕辰三百周年為契機,故將郎世寧墓碑放在東園左側顯眼處,其余墓碑無序擺放,很多碑身和碑座相錯成列,當時豎立墓碑的原則即只要碑身的隼與碑座相合即可。如今整個柵欄墓地,帶有紋飾的碑座僅存二十通,多刻有海水江崖,雙龍戲珠,祥云靈芝等紋飾。頗有意思的是,在碑身和碑座上亦存有佛教萬字符“卍”以及八法器(金魚、寶傘、寶瓶、妙蓮、右旋白螺、金剛結、勝幢、金輪)等,說明當時為過世傳教士打制墓碑、刻制碑文的石匠并不清楚天主教與佛教的信仰區別,甚至二者之間的沖突,而是以普遍公認的美好寓意物品作以墓碑紋飾。
除了墓碑以外,墓地現存石門亦是傳教士官方身份的集中體現。石門上刻有滿、漢文所寫“欽賜”二字。石門左右照壁為六邊形的對稱云龍圖案,周邊飾以祥云,龍紋與云紋融為一體,既取意虛幻飄逸的境界,又呈現威嚴肅穆的氣勢。
在東園碑林左側存有一石羊,此石羊被馬愛德稱之為“湯若望遺失的羊”(2)Edward Malatesta, J. S. J.,The Lost Sheep of Johann Adam Schall: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Zhalan [Shala]Cemetery.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1592—1666]. Edited by Roman Malek, S. V. D, Volume 1. Jointly published by China-Zentrum and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Sankt Augustin, 1992, p. 1.,是湯若望墓地規模的印證。由于他的墓地是傳教士墓地中獲得皇帝賜予的最高待遇,因此在其碑前放置石供桌、石五供外,還專門修以甬道安放石像生,石像生沿甬道分列左右,石馬、石人、石獅、石羊、石望柱各二,“(湯若望)墓地的規制確乎很高,他的墓,同時象征著關于湯若望的紀念得以恢復,除了供桌以外,還有象征供品的成列,這里有成對的大理石人物和動物,這些人物是為了在另外一個世界服務死者的”(3)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du Pei-T’ang, 1916. p. 34.。1726年《世界新聞報》(Welt-Bott)載文評論說:“湯若望神甫安息在一架真可以說帝王一般的墓架之上”(4)魏特(Alfons V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2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第202頁。,“其中湯若望的墓地是至為重要的,規制如同皇家貴族,一系列的大理石雕塑分列左右。在墓地甬道的盡頭是一個祭壇,兩步一臺階,階梯平臺上放置有大理石中式花瓶(有十字花紋香爐),祭壇的左右兩側分別有八步臺階,入口處立有圣人像(5)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2.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ericaine, 1905, p. 1 027.。可以看出,這是皇權權儀衛的縮影,故柵欄墓地不僅僅是來華傳教士的安息之所,亦是皇權護佑下的異國天鄉。
而柵欄墓地如今僅存的三座墳冢,皆為傳統墓葬規制。傳教士墳冢采用的是“馬鬣墳”,又稱為“馬鬣封”。比如關于南懷仁的墓穴介紹,“墓穴坑有六尺深,七尺長,五尺寬,坑穴四周以磚砌墻,底部是兩道約一尺高的磚砌支架,棺柩被放在其上。然后,人們把坑穴四周的磚墻再砌高大約六尺或七尺,將墓穴以拱形封上,并在墓頂上放一十字架”(6)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編,鄭德弟、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1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6—268頁。。由此可見,傳教士所采用的墓冢形式為傳統的墳墓規制。然而如今墓地墳冢皆為修復而成,故并非原制。
二、共慕天鄉——柵欄墓地集中展示天主教墓葬元素
柵欄墓地作為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繼利瑪竇之后,墓園陸續安息著來華傳教士百余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分屬不同的修會,此外,還有國籍不詳的神父亦埋葬于此。故整個柵欄墓地相繼發展出多塊墓地,先后有葡萄牙墓地、意大利傳信部墓地(方濟各會墓地)、歐洲人墓地、遣使會墓地、圣母會墓地、修士墓地、仁愛會墓地、教徒墓地等,還包括殉難者藏骨堂(致命亭)等,每一塊墓地都有分屬的修會標志,從而使得這塊墓地充滿多元的異域宗教特色,成為天主教在華的重要地標之一。
而在柵欄墓地最典型的天主教元素乃為十字架。每個教堂頂上皆有十字架,圣母堂“其墓頂上也安放了一個十字架”(1)《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1冊),第268頁。。根據日本記者中野江漢(Nakano Koukan)回憶,整個墓地的核心是一座高大的十字架,墓碑以此為基準陳列。而教徒墓地中央亦為一座十字架,以作為墓地標志。而在殉難者藏骨堂(致命亭)的正面安置著十字架和耶穌像(2)中野江漢著,韓秋韻譯,《北京繁昌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30頁。。在圣母會墓地,“墓石上建有鐵制的十字架”(3)《北京繁昌記》,第330頁。。此外,具體到傳教士墓碑,在碑首的篆額天宮一般都刻有十字架或修會標志。柵欄墓地中以髑髏地十字架(Cross of Calvary or Graded Cross)、拉丁十字架(Latin Cross Fleuree or Budded Cross)為主。髑髏地十字架又叫分級十字架。臺階代表著耶穌受難十字架所立的小山——髑髏地,又名“各各他山”,位于耶路撒冷西北郊,是羅馬統治者處死猶太人的刑場。一般髑髏地階梯為三級。拉丁十字架亦可稱花蕾形十字架,十字端的三葉形代表了三位一體,即天主教的天主,即圣父、圣子、圣神為一體。在十字架中心背后一般有四隅斜刺的刻痕,象征耶穌受刑罰時帶著的荊棘冠冕,代表基督受難。荊棘冠冕與榮耀冠冕分別位于十字架上中心的背后和前方,從死到生,象征耶穌的復活。十字架底座近似愛奧尼式,而四周有方框或藤枝草蔓紋式。此外,柵欄墓地中還有希臘十字架,底座為一等腰梯形(象征髑髏地)。
在這些紋飾中,除了常見的十字架之外,還有字母“IHS”,“IHS”為“In Hoc Salus”的簡稱,即“借此(十字架)得救”的意思,并且是希臘文耶穌圣名“ΙΗΣΟYΣ”——Iesus Hagiator Soter的前三個字母所得,與拉丁文“J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穌為人類救世主)的意思相同。故一般情況下,“JHS”與“IHS”同為歌頌耶穌之功,在天主教墓地中使用甚為普遍。而若在IHS四周有三顆釘和太陽光,則為耶穌會標志。三顆釘,代表耶穌基督受刑時一顆釘在雙腳交叉處,另外兩顆分別釘在兩只手上,亦代表三位一體思想。太陽光,代表耶穌就像上帝發出來的“光”。在柵欄墓地中,墓碑碑首篆額天宮處的圖飾即是典型的宗教符號,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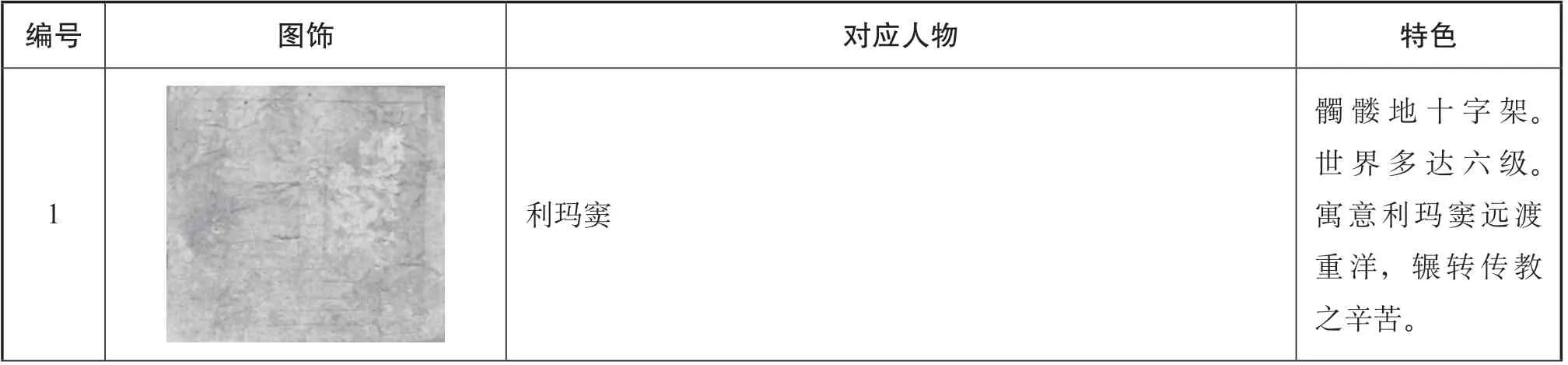
表1 柵欄墓地墓碑碑首篆額天宮圖飾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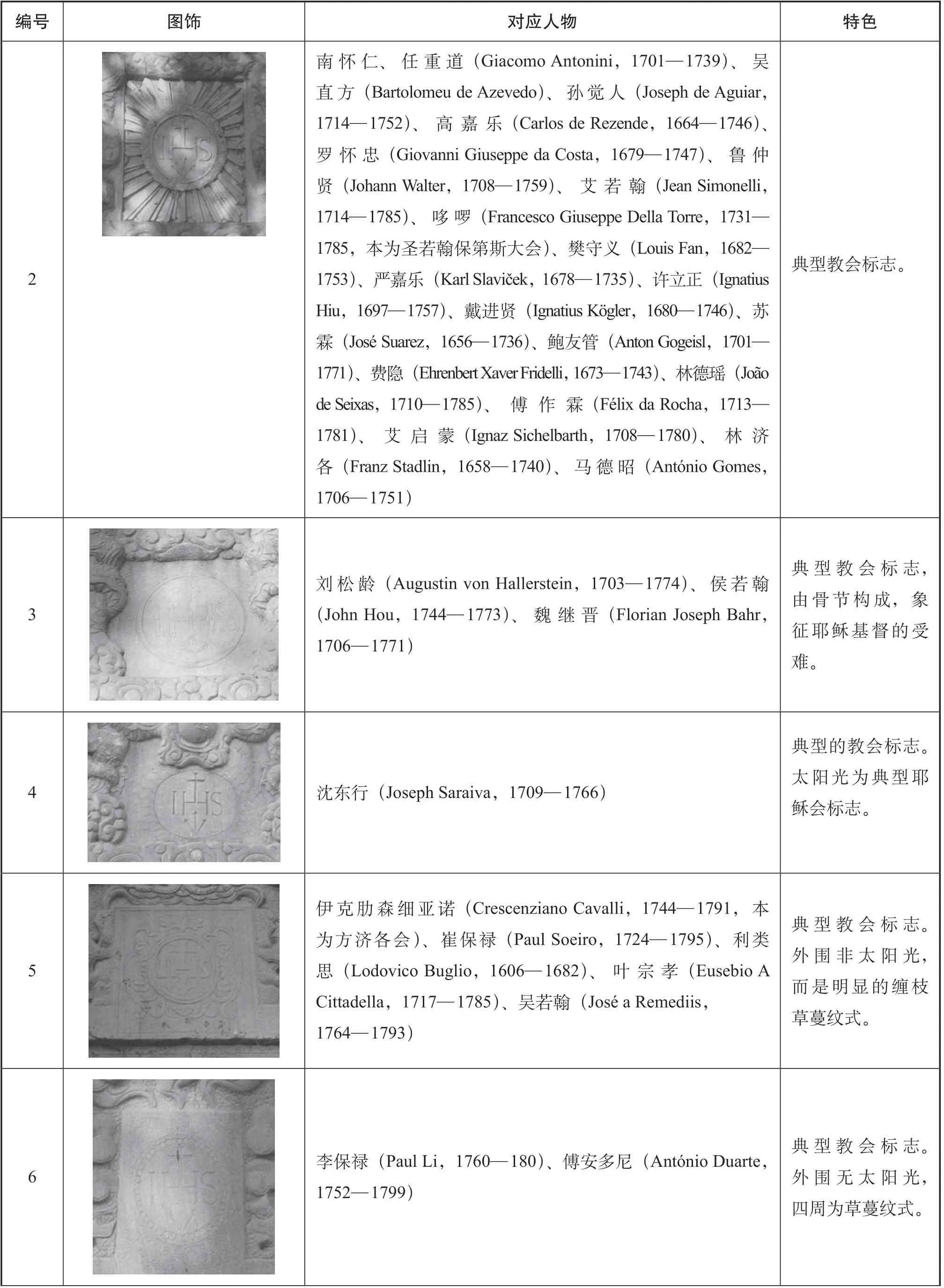
(續表)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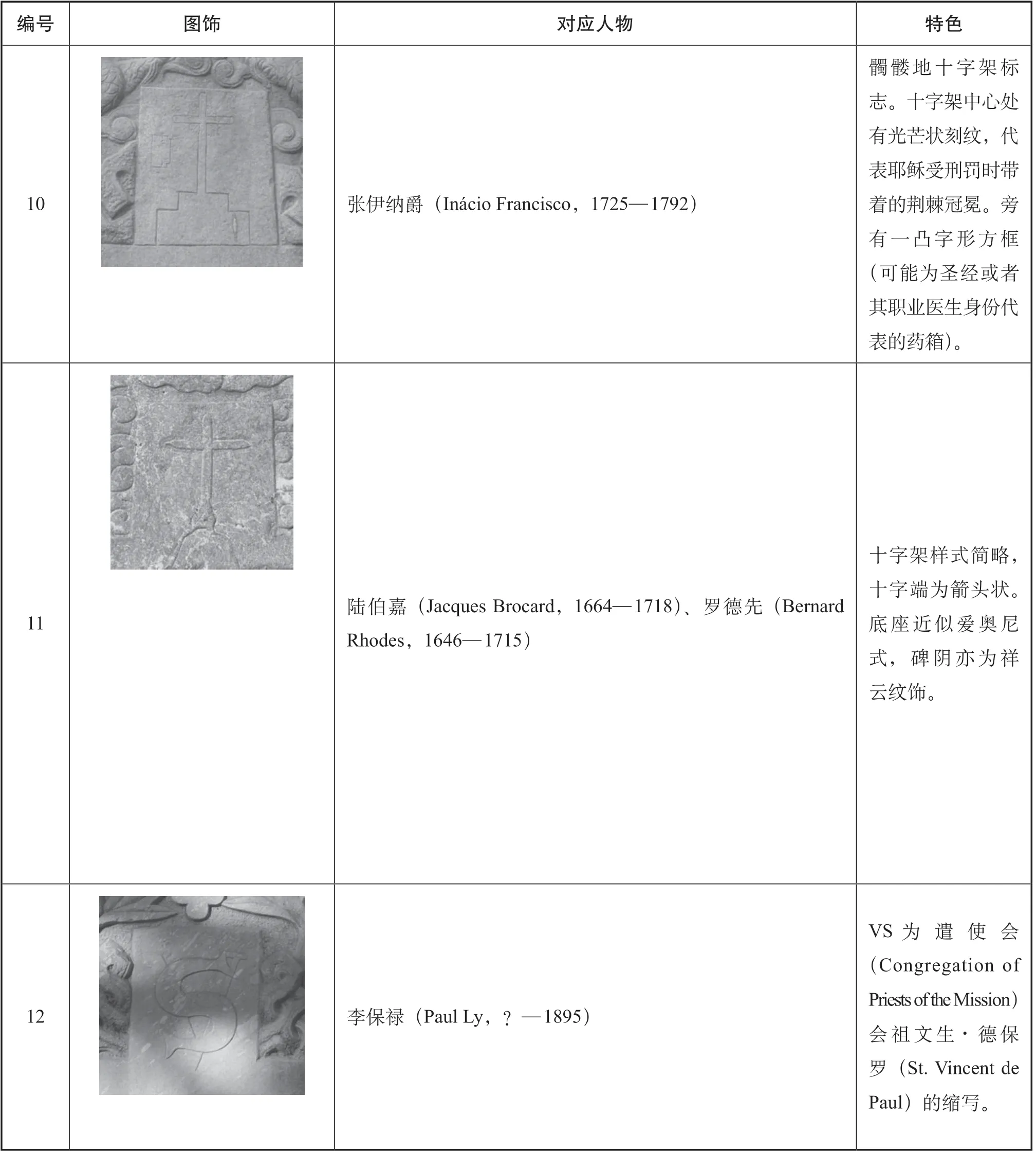
(續表)
三、多元索隱——柵欄墓地創生出中西合璧墓葬藝術
柵欄墓地藝術中最大特色便是在跨地域、跨時空的發展中,吸收了來自不同文化的墓葬元素,并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在信仰層面表達了對天主的愛慕和追隨,又在世俗社會層面在歌頌逝者功德的同時,體現出對皇權的敬畏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本土化”嘗試。這是基督宗教在中華大地傳教的一次大突破,以實物作為索隱天主教義的載體,使得神權與皇權在特定的狀態下得以共存。
作為承載碑主生前重要信息的墓碑,柵欄墓地幾乎所有的墓碑都是中西墓葬元素的融合,代表著信仰十字架或修會標志與代表皇權的盤龍的完美結合。在文字上,墓碑都以雙語呈現,甚至還有三語,這種多語言墓碑從客觀上就決定了它所蘊涵的碑主信息擁有更廣闊的閱讀群體。而柵欄墓地墓碑中,漢文和拉丁文所表達的意思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有差別甚大的情況。這也體現出傳教士在華復雜的政治環境。其中比如安文思、利類思的墓碑漢文部分,主要是呈現皇帝的上諭,突出在華朝廷對其的認可程度,而在拉丁文部分除了介紹在華特別是在四川的傳教之功外,還反映出他們在華的真實遭遇,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和牢獄之災,而他們來京后,除了修建東堂外,還通過宣傳教義和翻譯、刊印書籍堅持傳教。拉丁文的信息比漢文更加充實。伊克肋森細亞諾主教的墓碑,中文部分較之于傳教的艱辛內容更強調他在華傳教經歷以及他的職位,而拉丁文部分更為詳細地記載了他在華遭受的磨難。艾若翰漢文部分陳述相對婉約,言其在艱苦中堅韌而卒,而在拉丁文部分對他的遭遇介紹得更為詳細,被捕后卒于獄中。由此可見,墓碑文字作為其生平的載體,以不同的側重點記載其在華生活,在比較中不僅可以探究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亦可發掘來華傳教士的歷史貢獻和文化內涵。
在柵欄墓地歷史上,有兩塊紀念碑尤為特別,一塊鐫為“圣寵之源”(1)2018年6月在北京市委黨校校內殘碑清理過程中重新發現。參見陳欣雨:《二○八年滕公柵欄墓地新整理文物考》,《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第127頁。,另一塊鐫為“常生之根”(2)“常生之根”碑現存于北京市石刻藝術博物館內。。二碑在義和團運動之后,被鑲嵌在新建諸圣堂外墻上,其碑石均為長1.09米,高0.86米,厚0.35米,底座高0.13米,厚0.37米。碑陽仿擺屏飾,上部為橫額式,四框浮雕纏枝草蔓紋飾,框芯剔地陽刻榜書。而底部有如意紋,上下為斧剁無紋飾,左右兩側拋光。在“圣寵之源”碑陰中榜刻有“議大夫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督察……治拾捌年歲次辛丑仲秋”(3)2018年6月在北京市委黨校校內殘碑清理過程中重新發現。通過碑陽、碑陰比較,碑陽為完整底座和碑身,碑陰字體不全。可能是順治年間碑石的二次利用。根據其官職名稱“通議大夫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督察……”以及時間“順治十八年”即1661年,推測原碑所指人物可能為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養量(生卒年不詳)。。“圣寵”指稱“仁慈天主看救主耶穌的功勞、賜予人的超性神恩,助人上愛天主下愛世人,救自己的靈魂。圣寵有兩種,即寵佑和寵愛”(4)若望編:《圣寵與圣事》,《中國天主教》2017年第4期,第46頁。。因此,“圣寵之源”即代表天主。“常生”即“永生”,“常生之根”乃指生命之本亦是來自于天主。
就墓碑上所鐫刻的紋飾,亦融合著中西方文化元素。如在安文思、利類思、鄭瑪諾墓碑碑陰的篆額天宮刻有十字架與小寫“ihs”所構成的“壽”字。在傳統墓葬文化中,“壽”字寓意長壽圓滿,寄托了生者對逝去故人的美好祝愿。此“壽”字一方面融合了天主教的信仰元素,另一方面亦契合了中華傳統的墓葬訴求。此外,在2018年新整理出一方碑石,幾近完整,浮雕樣式精美,多層鐫刻,規制龐大,中間為花體字母“A”“M”重疊而成象征萬福瑪利亞(Ave Marie),而自內向外一道道光芒動人心魄,周邊為傳統的祥云如意紋飾環繞。此塊刻石將天主教具有特殊含義的太陽光與中國傳統吉祥寓意紋飾以浮雕的形式完美而自然的結合在一起,再一次體現了柵欄墓地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
柵欄墓地石刻藝術是典型的中西墓葬文化的融合,一方面使得基督宗教信仰在異鄉得以保存和延續,體現出天主教在華傳教過程中本土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遵循中華墓葬文化的傳統,重視慎終追遠、崇德報功的文化觀念,莊嚴肅穆又不失風格。天主教自圣方濟各開始傳入中國,至利瑪竇而卒柵欄墓地,“所歷之種種困苦艱難,誠非身歷其境者,所能道其只字”(5)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8頁。,“利瑪竇者誠為中國開教之功人哉”(6)同上。。自此后,柵欄墓地得以不斷擴大和發展,見證了天主教在華發展的興衰,透過墓地石刻藝術,可強烈感受到傳教初期的欣欣向榮,特別是以湯若望、南懷仁為代表的黃金時代,上至王公大臣,下達平民百姓,皆受澤于傳教士的治歷鑄炮、測驗地震等功,故其墓地規制亦是重臣之屬,以至湯若望“建立石碑以志盛事”(1)《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150頁。,墓葬儀式空前盛大。盡管期間也遭遇沈?、楊光先之難,而整個17世紀天主教教務情況也因傳教士的官方地位和朝廷認可而頗為可觀。然而從雍正至道光年,隨著“禮儀之爭”的惡化,傳教士被驅逐、教徒被抓捕和教堂被充公,柵欄墓地所葬傳教士皆為“領票”之士,也說明他們不僅永別故土,而且在華并不如前受到優待,江河日下,甚至諸多被捕入獄,受難而卒。故在他們的墓碑上,漢文和中文所表達的內容各有所重,這是應時的無奈之舉。其中也不乏諸多國籍神父,他們多葬于柵欄墓地。“當教難危急之時,所賴以施行圣事,扶助教士信德者,中國神父之力居多,其中尤以何天章、龔尚賢、樊守義、程儒良、羅秉中、高若望、陳圣修、沈東行諸人為最著”(2)同上,第181頁。。徐宗澤在這里所列舉的中國籍神父中葬于柵欄墓地且現存墓碑的就有四位。而后隨著耶穌會的解散和遣使會對柵欄墓地的接管,圣母會的入駐,整個墓地增添了“法式”建筑和墓碑,并且使得古老的柵欄墓地得到了守衛和保護。因此,柵欄墓地的石刻藝術與整個天主教在華傳教史是緊密相連的,墓地為來華傳教士提供了最有力、最延續的實物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