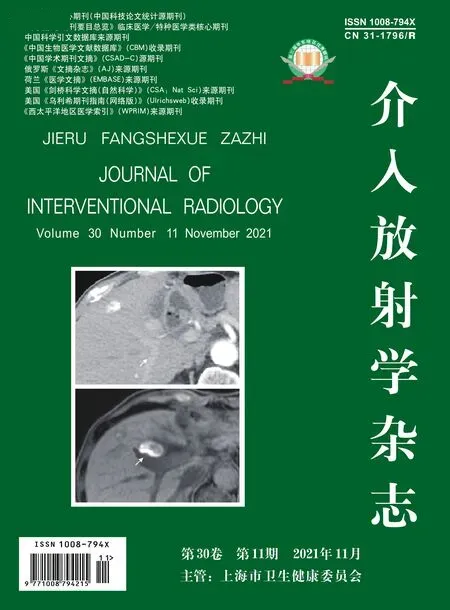顱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機制及治療新進展
何 鈺,王建波,王 武
顱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ICAS)是腦卒中的主要原因,占腦卒中33%~50%[1],中國人群中患病率約為46.6%[2]。有研究表明,頸內動脈狹窄、大腦中動脈狹窄和椎基底動脈狹窄導致的年病死率分別為12.4%、6.8%和11.6%[3]。隨著腔內介入治療技術和材料不斷發展,腦血管支架植入術已成為ICAS首選治療策略,并廣泛應用于大腦中動脈狹窄、頸內動脈和椎動脈起始部等常見部位狹窄。但是支架植入術近期并發癥中最常見的是圍手術期遠端栓塞和出血事件,其次是缺血再灌注損傷,遠期并發癥中影響最嚴重的是支架內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有研究將ISR定義為植入支架內或緊鄰動脈血管(5 mm內)狹窄>50%,絕對管腔損失>20%[4]。有腦血管支架植入術后遠期隨訪研究顯示,ISR總體發生率為14.4%,前循環中發生率比后循環中更高[5]。ISR還會進一步導致遲發性腦血管缺血事件發生。這些因素均使腦血管支架廣泛應用受到限制。因此,探索ISR發生發展及治療,有助于降低腦血管支架植入術后遠期不良事件發生率,拓展腦血管介入治療適應證,改善支架術后遠期療效。
1 ICAS
1.1 病因和病理學基礎
ICAS病理學基礎為內皮細胞功能障礙和炎癥引起的血管壁脂質異常堆積,諸多因素促進其發展。目前已確定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種族、高血壓、血脂異常、代謝綜合征、胰島素抵抗、吸煙、糖尿病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等[3,6]。隨著年齡增長,腦動脈抗氧化保護作用顯著減少,致使其易受到氧化應激和炎性反應的影響,導致脂質迅速堆積。種族差異可能歸因于遺傳易感性和生活方式差異。研究發現KALRN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突變位點與中國北方ICAS人群密切相關,其可能機制為基因位點促進新內膜增生和平滑肌細胞增殖,并通過減少一氧化氮產生導致ICAS[7-8]。高血壓改變了血管內血流動力學和血管壁剪切力,導致血管壁損傷,激活炎癥逐級反應。脂質異常分為保護性[(高密度脂蛋白(HDL)和載脂蛋白A(Apo A)]和損傷性[(低密度脂蛋白(LDL)和載脂蛋白B(Apo B)],前者通過促進巨噬細胞膽固醇流出,同時抑制LDL氧化、平滑肌細胞遷移及血小板聚集,起到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后者則相反,內膜中LDL累積導致斑塊形成,最終引發ICAS發生和發展[3]。吸煙增加氧化修飾并改變一氧化氮生物合成,影響顱內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和發展。綜上,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激活血管壁炎性反應,引發一系列復雜的生化反應,如細胞外基質積聚、內皮活化、單核細胞和T細胞浸潤、內膜增厚、纖維帽形成和血管生成,隨后斑塊逐漸生長,最終導致進行性狹窄。根據這種級聯反應,病理學上對ICAS進行演變過程分型[9],見表1。

表1 ICAS演變過程的病理學分型
1.2 治療方法
ICAS治療方法主要包括藥物治療、外科手術(頸內動脈內膜剝脫術和腦血管旁路移植術)和介入治療。隨著腦血管成形術和支架植入術廣泛開展,其獨特優勢顯現。例如,作為微創治療,其術中、術后不良事件發生率低,避免了手術并發癥發生,同時遠期療效提高,包括良好的血運恢復能力及可觀的遠期通暢率[10]。其與頸內動脈內膜切除術相比,患者創傷小,住院時間短,術后生活質量提高[11]。然而有文獻報道頸動脈支架植入術與頸內動脈內膜剝脫術相比圍手術期腦卒中發生率和中期ISR發生率較高[12],因此還需要遠期大樣本病例研究進一步求證,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難題。現今最基礎治療仍然是藥物治療,包括雙聯抗血小板聚集藥物和他汀類藥物等,尤其是對高風險腦動脈狹窄患者,積極且合理的序慣性藥物治療很重要[13]。
2 腦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ISR
2.1 病因和病理學基礎
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后ISR研究發現,ISR發生與血管損傷和過度修復密切相關[14]。血管支架植入往往會導致血管壁機械損傷,引發一系列免疫和生化連鎖反應,致使支架內內皮細胞和平滑肌細胞增生,從而發生ISR。腦血管支架植入術后金屬支架導致內皮細胞脫落和內膜損傷,一方面引起內膜炎性反應,釋放炎性因子,加劇內皮細胞功能障礙,抑制內皮細胞遷移和增殖,血管壁內皮修復延遲,另一方面原位血小板黏附于損傷部位并釋放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轉化生長因子、表皮細胞生長因子等,這些細胞因子對血管平滑肌細胞具有趨化性和促有絲分裂作用。因此,內皮化延遲和血管平滑肌細胞遷移和增殖被認為是ISR關鍵機制(圖1)[15]。支架內新生動脈粥樣硬化(in-stent neoatherosclerosis,ISNA)指支架附近新生內膜內有富脂質泡沫細胞聚集,伴或不伴壞死核形成,是一種延遲性并發癥,其特征是新內膜內泡沫細胞簇、牙髓核和鈣化,形態類似于動脈粥樣硬化斑塊[16]。功能障礙的內皮細胞也被認為是ISNA的基礎。

圖1 ISR病理機制
除以上主要因素外,ISR發生還與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基礎疾病和抗血小板聚集藥物抵抗等因素有關。吸煙可引起動脈內皮細胞受損,炎性細胞聚集、黏性增加。糖尿病可導致血液黏稠,降低凝血因子生物活性,增強血小板聚集[17]。此外,還與選擇支架類型、大小、長度以及血管彎曲、直徑、狹窄范圍、狹窄程度相關[18-19]。支架是否具有較好的柔韌性,往往會改變血管壁力學特性,柔韌性低會降低其順應性,患者術后ISR機會增加。
2.2 治療方法
目前對ISR的認識尚處于如何降低其發生率階段。據研究報道,局部給藥是預防和治療ISR的理想策略,因為ISR往往影響血管的一小部分,全身治療通常無效,或反而引起意外不良反應。藥物洗脫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通過在狹窄段局部釋放負載藥物,調節血管炎癥并防止內膜增生,可提高腦血管成形術和支架植入術療效,降低ISR復發率。
DES最早應用于冠狀動脈,隨后用于下肢動脈成形術[20],目前探索在腦血管中的應用[21]。DES第一代涂層藥物為紫杉醇、西羅莫司,抑制平滑細胞增殖和遷移;第二代DES改善了藥物釋放動力學,采用更具生物相容性材料并改變了支架構造,涂層藥物大多為西羅莫司衍生物;第三代DES采用具有更好生物相容性或生物可降解聚合物,以減少炎癥、延遲動脈愈合和ISR可能性,但臨床應用中仍有延遲性ISR發生。DES更替體現出對ISR認識的深入,研究初期強調平滑肌細胞增殖在ISR中的作用,逐步發現同樣起作用的還有內皮細胞過度異常增殖;隨后研究發現支架對血管壁屬于一種異物損傷,刺激炎性反應;直至近幾年,開始重視內皮細胞功能恢復。有學者研究提出超早期完成內皮化,促進內皮細胞功能恢復,包括對內皮細胞、血管壁保護和支持后,可能降低平滑肌細胞過度增殖[22]。遺憾的是,至今仍未發現非常理想的活性藥物,既促進內皮功能恢復,又抑制平滑肌細胞增殖。
到目前為止,DES研究關鍵點主要體現在藥物選擇、支架或涂層材料、藥物釋放機制等方面[23]。已開發和測試許多藥物,通過口服或DES、納米顆粒直接輸送至病變部位,有10多種藥物或生物分子用于治療冠狀動脈和下肢股動脈區域ISR(表2)。納米顆粒在藥物載藥的應用對藥物載藥系統有效性和安全性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24]。其優勢體現在:①靶向藥物遞送,實現局部作用,可降低全身不良反應;②可同時負載多種藥物,且負載量更大;③更好地改善藥物穩定性和溶解性,提高藥物療效;④最重要的,還能控制藥物穩定劑量持續釋放和程序性釋放。例如,納米離子雙相釋藥使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立即釋放,促進內皮細胞黏附、增殖,延遲紫杉醇釋放,避免其對內皮細胞的負面影響,同時抑制晚期平滑肌細胞過度增殖[23]。

表2 ISR治療藥物或生物分子
ISR機制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ISR發生后治療仍是難點,目前尚無統一的再介入治療標準或指征。藥物洗脫球囊血管成形術是冠狀動脈狹窄裸金屬支架和DES植入后ISR治療的可靠選擇[39-40],并列入相關臨床指南。腦血管應用中首選藥物涂層球囊再擴張,其次為支架或DES再植入,但目前僅證實應用于頸動脈及椎動脈開口處ISR有效[41-42]。主要原因在于支架再植入雖可提供良好的血管重構,但可能進一步損傷血管管徑,并于此植入金屬支架重復ISR過程,中遠期無明顯優勢。
3 ISR治療幾個問題和展望
首先,關于腦血管支架植入術后覆蓋支架表面的內皮細胞來源,仍有爭議。有研究表明CD34抗體涂層支架的抗體與內皮細胞膜受體結合,吸引內皮細胞聚集,從而促進早期內皮化[43]。再者,對表面形成的內皮細胞功能進一步研究發現,支架表面改性有助于內皮細胞功能恢復,內皮細胞早期成熟可延緩或阻斷ISNA發生[44]。基因洗脫支架可能具有一定潛力,因為靶向基因療法可能會上調生長因子或減少內膜增生,阻斷血栓形成[45]。這些具有研究潛力的ISR可能機制,立足于促進早期內皮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實現生物可降解聚合物、無聚合物涂層和完全可降解生物支架,通過活性分子藥物直接或間接作用選擇性抑制平滑肌細胞并保護內皮細胞。理想的DES應具有這樣的功能,即允許早期結構重新內皮化,抑制平滑肌細胞增殖[16,46]。Goel等[47]研究提出血管重塑這一全新概念,即動脈直徑永久性改變和血管痙攣或擴張引起的動脈尺寸暫時性變化。這一概念拓寬了支架植入術后ISR治療領域。如何通過介入支架植入治療,實現對病變段血管重塑,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實踐。完全可吸收生物載藥支架可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目前DES仍會出現遲發性血栓或ISR[48],這也被認為是延遲血管再內皮化的結果。因此,DES技術改進需要考慮如何通過抑制不適應的內膜增生內環境,促進血管內皮化和修復,進一步提高支架安全性。
總之,ISR是一種過度傷口愈合反應或不良適應反應,其治療是一不斷探索問題和解決問題過程。目前藥物洗脫球囊可將藥物釋放至不同的ISR病理過程靶點,如紫杉醇抑制細胞增殖,曲美他嗪保護內皮等,并在冠狀動脈ISR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49]。其他幾類藥物,如抗炎藥物、抗氧化藥物、抑制細胞增殖和遷移藥物等也已開發,并于動物雌激素疾病模型進行實驗。這些藥物可選擇性影響平滑肌細胞增殖和遷移,而不僅是內皮細胞。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開發與新型藥物結合的藥物洗脫球囊或藥物涂層球囊。目前研究的生物活性分子局部和靶向給藥,有望改善血管介入治療效果,然而許多靶向血管藥物尚未達到臨床要求。未來研究必須解決新一代DES和完全生物可吸收支架遠期安全性問題,以維持有效的功能性內皮細胞和有利的血管內環境,從而減少支架血栓和ISR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