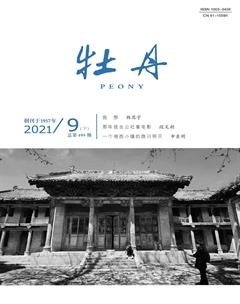《堂吉訶德》的敘事結構解讀
小說《堂吉訶德》主要描寫的是一名叫堂吉訶德的青年從卑微的下等奴隸成長為反抗上層貴族暴政的英雄的故事。這本小說總體上透露著一種浪漫主義氣息,主要表現在描寫堂吉訶德成長過程的內容,大部分讀者品讀起來感覺荒誕不經。但作者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身上賦予的堅毅性格始終能引起讀者共鳴。究其原因,小說《堂吉訶德》的敘事過程中雖然有著曲折離奇,但作者用巧妙的筆法將堂吉訶德置身于貼近真實的結構空間中,由周圍環境人物的真實反襯堂吉訶德的夸張,在這種夸張的寫法風格中帶給讀者感同身受的傷感。《堂吉訶德》沒有反復強調悲慘的境遇,也沒有刻意表現堂吉訶德堅毅的行為,每一個情節都是寥寥幾筆,卻令讀者印象深刻,這體現出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藝術感染力,使文學境界全面升華。《堂吉訶德》的敘事技巧呈現多樣化,如視角轉換的敘述、讀者與文本之間設置多重閱讀障礙、亦幻亦真的游走敘事等。本文以作者塞萬提斯對小說《堂吉訶德》所描繪的敘事結構為引線,解讀其中的精妙之處。
一、人物敘事的巧妙
(一)行為豐富與內心空白對比
從敘事內容來看,作者通過周遭環境和人物描寫堂吉訶德的行為,構成了堂吉訶德多面的特征。但他的心靈世界在被描寫時卻是空白的,似乎他就是紙片人,有一種先天的鈍感,說起話來不痛不癢,其他人對他說的話也是很平淡的,有些描寫過于浮夸,反而呈現出冷幽默,但就是這種對比明顯的感覺讓讀者更加喜歡。任何一部優秀文藝作品的產生都絕非偶然,其思想內容深深地扎根于現實土壤中。堂吉訶德來到一家破敗的客店,店主人打扮得很潦草,境遇較為貧困窘迫,但是堂吉訶德卻看不出,在行為上表現得極為豪邁。但是堂吉訶德更加潦草,他卻毫無覺悟,反而是向店主人吹噓自己的榮耀。盡管堂吉訶德對店主人端上的食物都垂涎不已,他依然口不對心地擺擺手:“本騎士早就吃慣了。”堂吉訶德對店老板心里有著憐憫,卻在口上未曾饒過半分,總是嗆得店老板張不開嘴。他的憐憫更像是嘲諷,高高在上地俯視著對方。事實上,店老板也在嘲諷著他:“我知道您寬宏大量,我的大人。”店老板認定他是一個瘋子,只是陪他演一出戲。作者構造出人物行為與內心鮮明的對比感覺,從而讓讀者看到真實的世界與虛幻的心靈世界,發現現實中令人窒息的生活主題。同時,作者極力淡化內容流露出的傷感,創造出唯美的視覺效果,使讀者在意境中追尋新的審美體驗。
(二)荒誕中反射價值觀
《堂吉訶德》就像是一出別開生面的鬧劇,很多情節看上去不知緣由、不知歸處,但就是奇妙地發生了,而且戲劇性地收場了。塞萬提斯將鬧劇貫穿整部小說,實際上就是用這種荒誕的幻想影射不切實際的現實。這種敘事方式就像一面鏡子,不斷放大才能看見細微的脈絡,那就是堂吉訶德的宿命悲劇。
堂吉訶德對騎士小說的熱衷已經到了接近瘋狂的地步,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威風八面的騎士,不愿意待在有安全感的鄉土,而是選擇外出尋覓能展示自己鋼鐵意志的危險地界。但是全書在危險地界的描寫字句上著墨較少,反而勾勒出堂吉訶德在與人打交道時的荒誕不羈。唐吉訶德對店老板說:“是這樣,我要勞您大駕而您又慷慨應允的事,就是要您明天封我為騎士。”
在堂吉訶德看來,風沙彌漫的恐怖天氣和吞噬人類的野獸,才是能讓他正視的對象,他始終沉浸在自己內心的世界無法自拔,忽視了人世間最平凡的生活。若用正常人的眼光來看,都會把堂吉訶德當成危險人物,他看上去腦子不太靈光,還拉著眾人和他一起演出無聊的戲劇,這讓習慣早出晚歸的人們無法忍受。
二、不確定性的距離敘事
《堂吉訶德》在讀者與文本之間設置了多種閱讀障礙,借助距離敘事的模糊真實和虛構,營造出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氛圍,充分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這種不確定性的距離敘事使故事文本虛幻縹緲,情節被分解得支離破碎。
作者透過其他人物的幾句話和背景的旁白解說串聯出一段故事,又借助周圍環境的襯托和其他無關人物的故事,引發讀者想象主人公堂吉訶德的性格特征。不同于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方式,在《堂吉訶德》中,讀者可以找到某一段描寫當成一個獨立的故事,而堂吉訶德倒像是一個不相干的人物,活在記憶里。“上帝,老天爺,主啊,救救他……”“在桑丘的吶喊助威下,堂吉訶德拿起長矛,沖向風車……”這種描寫方式讓讀者充滿好奇心,從而加強了一種視覺與思維上的疏離感:當讀者看到描寫堂吉訶德的字句時,又會覺得與自己的想象不符合;當讀者推測小說后半部分堂吉訶德所發生的故事時,又被離奇的字句所挫敗。但堂吉訶德身上傳遞的堅毅性格又無形中指引著讀者繼續閱覽,讓人欲罷不能。
三、文字頭尾基調的不可思議
《堂吉訶德》的另一層敘事結構,就是在描寫的字句中極盡奢華,用盡溢美之詞,將各種喧囂嘈雜的形聲字和表示輕巧華麗的疊詞運用得爐火純青,但在故事的結尾又用一種旁白、以真實人物的口吻警醒讀者,這種描寫實際上是當頭一棒,讓人沉浸在故事氛圍時突然清醒,更有振聾發聵之感。
“堂吉訶德,一個年老的鄉村紳士,懷著偉大騎士的靈魂,苦苦思索著無人能明白的理想,在庸碌現實中——想非現實的夢,他尋找著夢境。”塞萬提斯在小說中運用了大量字句烘托出堂吉訶德故事的詭譎,結尾卻極其平淡,與前面的基調完全不符,令讀者覺得不可思議,但細細品味之后又會覺得理所當然。在書中的前半部分,塞萬提斯交代了堂吉訶德外出游歷的原因,竟然只是因為他喜歡看騎士小說,對里面騎士的內容經歷心馳神往,從而突發奇想要出遠門,這個理由極其荒誕而幽默。但是堂吉訶德又沒有帶任何工具,絲毫不具備騎士的覺悟,反而在一路上像可憐的乞丐一樣處處碰壁,惹出啼笑皆非的故事。例如,店老板為了捉弄堂吉訶德而搞出舉辦來的加冕儀式等,看上去是明顯的耍弄,堂吉訶德卻沒有分辨出來,反而高興地接受了,令讀者覺得堂吉訶德智力低下且不具備生活能力。這里的字句描寫極其幽默荒誕,但是到了故事的結尾之處,堂吉訶德坐在由破磚堆成的土丘上,兩只腳彎曲地并攏,頭發亂糟糟的,手上還端著店老板送的冷飯……這似乎與結尾他被卷進大風后的遭遇如出一轍,也和文本中堂吉訶德遭遇的故事有所印證,但是卻顯得與全文風格有違和感,似乎這樣的堂吉訶德才是真實的。小說以騎士作為一個暗線,貫穿始終,但是又沒有真正表現出騎士的那種大無畏精神,反借助堂吉訶德這樣一個小人物,用一場虛幻旅行完成騎士體驗,更顯得騎士精神的荒誕可笑。
四、模糊的時間軸——倒敘與插敘
小說《堂吉訶德》取材于中世紀的西方,當時君士坦丁堡的騎士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圈地運動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沉重的苦難。塞萬提斯在這部小說中所刻畫的堂吉訶德身上帶有中下層百姓的影子,又無他們的真實感。塞萬提斯另辟蹊徑,通過堂吉訶德荒謬的人生故事,使其令人不可置信地到達成功的頂點,但最終堂吉訶德穿著騎士服飾游走在刮著龍卷風的沙漠時,又令人唏噓不已。小說采用這種敘事模式,目的是貼近這種現實中帶點荒誕的風格,給讀者營造一種破碎的空間感。塞萬提斯故意模糊了清晰的時間軸,讓讀者感覺能追尋到真實的背景,卻又因為時間線的不明確而無法確定。
五、結語
作者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的身上寄托著人文主義理想,而這個理想通過堂吉訶德的言語和行動表現出來。小說在嘲笑堂吉訶德不切實際的同時,也看到他身上的可貴品質,這讓堂吉訶德的形象更具有思想內容和精神特征,使得他的形象的喜劇性與悲劇性緊密結合,更加突出人物形象的悲劇性。
(江西科技學院)
作者簡介:楊曉艷(1981-),女,江西南昌人,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為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