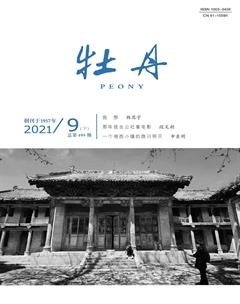《莎菲女士的日記》《伸子》異同論
丁玲和宮本百合子兩位女性作家幾乎出生于同一時期,并幾乎于同時期成為左翼文學作家。《莎菲女士的日記》與《伸子》同為兩位作家在成為左翼文學作家前發表的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兩部小說都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顯示出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同時,由于中日兩國近代社會和文學思潮發展進程的錯位,兩部作品在女性意識表現方面又有著明顯的不同。本文將結合社會歷史背景及文學發展思潮,從家庭、疾病、對抗三方面比較兩部作品中女性意識表現方式的異同,探究兩位女作家前期女性意識的異同,并試圖從兩部小說中一窺她們同時期成為左翼文學作家與女性意識覺醒之間的關系。
一、家庭
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父親的形象僅出現過3次,且在整個小說中并不具備“權威”的代表和“需要反抗”的對象的功能。作為家庭的核心成員,“父親”在小說中功能的減退,意味著家庭的缺席。丁玲在青春時代見證了新文化運動的吶喊聲逐漸微弱,激情的反叛舊式家庭的時代已結束,家庭內部激烈的父子矛盾已開始消退,“父親”已經不再是需要反抗的對象,在小說中反而成為莎菲的心靈慰藉。對于莎菲和丁玲本人而言,此時的“出走”并不帶有反抗的色彩,家庭于兒女而言不再是需要去反抗或者憎恨而產生反動力的場所,家庭一方面成為不能發出足夠前行動力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成為兒女不愿意返回的永遠的故園。但家庭賜予了兒女人身自由,莎菲則需要在新舊交鋒達到高潮后不斷跌落的復雜社會中找到精神出路。
丁母雖然很不滿意丁玲耽于讀書,“因為放棄了其他的事”,但作為女革命家向警予的至交,她并不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大王……的故事深深的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對丁玲的個人思想解放與寫作生涯產生了啟蒙式影響,家庭對于丁玲的影響是正面的。作為自傳體小說,《伸子》中的伸子在自由面前,比莎菲要多面對的是中產階級家庭。伸子的母親作為中產階級,只希望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人。伸子自作主張在美國與佃結婚,回到日本后遇到的是母親連綿不絕的冷嘲熱諷,已成為事實的婚姻遭到了家庭的反對。異常的是,伸子的父親同樣在女兒的婚姻中沒有起到傳統印象中的阻礙作用。當佃想博得伸子父親的好感而挽救婚姻時,試圖與伸子父親結成男性統一戰線,用以抵消伸子母親對其的排斥與反感。但在此過程中,伸子父親并沒有加入這種同盟關系,伸子和父親之間并沒有矛盾,因而伸子與家庭的對抗主要體現在母女關系上。
伸子與母親的關系,體現了近代思想與封建思想在女性婚姻及思想自由上的一種交融,伸子母親對女兒的要求也體現了兩者的融合。這種融合表現在她對女兒價值的判斷上,即女兒的價值由兩種價值構成,一是男性賦予的價值,二是女兒的個人價值。她并不排斥女兒個人價值的創造,但更強調男性賦予女性的價值。前者可通過女兒隨父親出國學習等可見,后者則體現在母親對女兒婚姻的反對。伸子結婚是未經過家庭允許完成的,挑戰了家庭的權威,這也是伸子母親不滿其婚姻及佃的原因之一。而佃的家世、職業、年齡和性格等進一步加深了母親對女婿的負面印象。因為他并不是門當戶對的結婚對象,阻礙了自己對女兒期望價值的實現。此外,伸子的母親并不阻止伸子寫作,但對伸子在作品中描寫的自己的形象頗為不滿,使得本已心生嫌隙的母女二人之間產生了新的危機。比起女兒的個人價值,伸子的母親更加重視男性賦予女性的價值,這一失衡是造成母女關系危機的根本原因。
普遍認為,女性個人價值的實現與男性給予女性的價值是背道而馳的,而女性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婚姻也通常是矛盾的。伸子擁有了婚姻,但并沒有得到男性賦予的價值,又遭到家庭的反對,這使她處于需要進行雙重斗爭的處境。她不僅需要與家庭抗爭以保全婚姻,又必須忍受婚姻的無趣,并在婚姻中追尋個人自由。伸子與家庭抗爭的結果是夫妻二人搬出父母家,擺脫大家庭,開始了獨立的婚姻生活。但這個勝利并不是快意的,佃的工作是通過伸子家庭關系尋得的,搬家也是伴隨著無奈與對婚姻生活的恐懼的。伸子很快便陷入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的無聊和煩悶中,和幾乎與沒有家庭權威阻礙的莎菲一樣,生活在漫無目的的憂愁當中了。
莎菲的家庭缺席與伸子的家庭阻礙,對二人的影響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的。莎菲所代表的女性群體已無家可歸,需要尋找新的出路;伸子所代表的女性群體則在家庭權威和婚姻中感覺壓抑,同樣急于尋求新的道路。在那個時代,中日知識女性需要新的舞臺來彰顯其主體的存在。
二、疾病
兩部作品當中都出現了因肺病導致的咳血等描寫,《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疾病的主體為作為女性的莎菲,《伸子》中疾病的主體則為伸子的丈夫——男性的佃。
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對日本近代文學中疾病的意義進行了深度分析,認為日本近代文學中出現的疾病,主要是肺結核,在許多文學作品的敘事中不再只是單純的醫學上的疾病,而有著豐富的內涵。事實上,肺結核在中日近代文學中都有著巨大而較為復雜的隱喻意義。“從浪漫派開始,該意象被倒轉過來了,結核病被想象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浪漫主義文學和結核病之間存在某種關系是不言自明的。日本浪漫主義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發端于19世紀末,衰落于20世紀初,中國浪漫主義則在20世紀20年代發展起來,20年代中期以后漸漸被左翼文學的浪潮淹沒而式微。
《莎菲女士的日記》寫于中國浪漫主義末期,浪漫主義思潮中肺結核的隱喻較為貼合地體現在了莎菲身上。“隨著這種疾病加重,一個人如何變得消沉。”肺結核被描述成一種消耗身體使人消沉的病。“依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大概存在著某種熱情似火的情感,它引發了結核病的發作,又在結核病的發作中發泄自己。”同時,它被神話成使人變得感情迸發的疾病,這在莎菲身上也并不矛盾:一方面,她覺得生活寂寞、凄涼而無意義,在因肺結核導致的生死思緒中掙扎;另一方面,她對愛情、對男性美有著熱烈的向往和追求。這種兩極的碰撞形成了莎菲性格的核心——既顧影自憐又向往自由。
而《伸子》中的伸子活力無限,精力旺盛,這種形象的出現與日本浪漫主義的退潮無不關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丈夫佃,佃的肺病出現時,二人的婚姻已經危機重重,佃用試圖博取伸子的同情方式極力挽回。事實上,吐血不一定是肺結核,但佃吐血后特意將帶血的紙拿給伸子看時,他是將吐血—結核病—死亡關聯起來的。可是,畢竟此時還未能確診他是否患有肺結核,然而他認為自己活不了多久,與其說他渴望患上肺結核,不如說他渴望肺結核的隱喻意義——憂郁、悲傷、透明、脆弱等。在這一點上,佃和莎菲的不同之處在于,莎菲身上是確實帶有這種隱喻意義的,而佃只不過試圖讓伸子認為自己有此種隱喻意義。可惜的是,不管是確診前還是確診后,伸子都表現得格外冷靜。“她覺得,病就是病,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非常清楚的。”浪漫主義的疾病隱喻在伸子那里變得毫無意義,或者說她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隱喻,這體現出疾病隱喻的消失,因為浪漫主義在日本確實已日落西山。而拼命想抓住最后一縷殘陽的佃,不僅顯得迂腐可笑,也在妻子面前失去了作為丈夫的最后魅力。
疾病在兩部作品中顯示出來的意義有無自然與中日兩國文學發展潮流有關,而疾病寄宿者的角色不同,也顯示了疾病由于其隱喻的變化而產生的對小說人物和情節的影響。《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肺結核,凸顯了莎菲身上看似矛盾卻是統一的獨特性格——她既脆弱又殘忍,生活簡樸,看似寡欲卻多欲,沉浸憂傷但時而也表現灑脫,絕望又不斷給自己創造希望。《伸子》中,佃欲給自己強加的疾病隱喻的各種因素反而招來了伸子的厭惡,加速了二人婚姻的破裂。但是疾病在此處的作用卻十分相似,疾病讓莎菲變得“游戲人間”,它也讓向往自由已久的伸子有了更多的理由掙脫束縛,疾病為推動兩人走向新的舞臺提供了內在、外在的動力。
三、對抗
《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葦弟和《伸子》中的佃總體性格十分相似,溫暾,軟弱,愛哭。葦弟傾心于莎菲,但莎菲不為所動,并有意壓低其存在感,顯示出明顯的女強男弱,莎菲并不需要與其對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凌吉士是莎菲熱烈追逐的對象,如何與他接近甚至親近是莎菲的煩惱之一,為了解決這種煩惱,莎菲采取了具體的行動。她一共搬家三次,有兩次都是為了得到凌吉士。在得到凌吉士的吻之后,她第三次搬家,離開了北京。前兩次搬家對于莎菲來說只是一種追逐游戲,她并不需要與搬家、與凌吉士對抗。因此可以說,小說中并不包含男女的正面對抗,莎菲需要對抗的是自己,性的實現和精神的滿足在她那里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對方肉靈的不統一才是她最大的苦悶,畢竟肉靈統一是她自己設置的標準,這反映了新時代女性的一種內在要求。最后,性的實現稍占上風,很快又敗落下來,沒有得到理想愛情的莎菲失意地離開。莎菲的主動出擊、不斷搬家、對身心合一愛情原則的守衛,都顯示出近現代女性的特點,她們不用再待字深閨接受強加于她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主動、自由和有主見。可惜的是,愛情失敗后的“出走”同樣也不快意,因為她的生活尚未找到出路。
由于《伸子》屬于自傳體小說,伸子的經歷和宮本百合子的經歷是重合的。伸子和佃自由戀愛結婚,婚后,伸子逐漸感受到婚姻的無趣以及對自己的束縛,但通過伸子的敘述可以看出,這種束縛并不來自佃本身。《伸子》中的戀愛到離婚的體驗主體是伸子,讀者更容易看出伸子思想的變化,但同時應該看到,佃是伸子/宮本百合子眼中的佃,因而佃的形象上缺乏投在葦弟和凌吉士身上的第三者目光。而且,《伸子》是在兩人離婚后所寫,此時伸子/宮本百合子對丈夫已經沒有戀愛感情,因而小說中寫到兩人的戀愛和結婚時讀者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也是容易理解的,因為作者此時在佃的形象塑造上并沒有投入太多的正面情感,從婚后的各種事件和細節,如收養子、肺病、旅游等情節都可以看出宮本百合子/伸子對前夫是懷有強烈的不滿情緒的。在伸子與佃的關系中,伸子被塑造成一個幾乎沒有缺陷的人,但是世上并沒有完美的人,力圖塑造完美但實際不完美的縫隙之間無非是宮本百合子/伸子的個人意識,即個人抗爭。佃的“口頭獻身精神”、無趣和軟弱,都不能構成宮本百合子/伸子想與之離婚的根本理由,唯一的理由是她有無限熱情,家庭耗不盡、裝不下。正如她的自白:“可是,伸子的熱情,在佃一個人身上卻沒有消耗罄盡。她的生命如同用北海道牛的奶水滋養的細胞那樣豐富、旺盛、貪婪。”她不能夠忍受的并不是佃,而是無所事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她曾反復自我催眠,她和佃之間是有感情的,她做過不少努力,想修復二人之間的關系,總是盼望能重歸于好,但很明顯,婚姻又裝不下她過剩的熱情,因此修復心理和不滿心理形成了矛盾。這種矛盾多表現為對佃的負面描寫,婚姻束縛了伸子,伸子是被束縛者也是受害者,而束縛者——婚姻,即佃,是加害者,因此佃在伸子眼里是缺乏魅力的負面人物。在《伸子》中,伸子是完美的,而佃是不完美的,但這不過是宮本百合子的主觀評判,這種主觀評判是伸子的個人發展欲望與現實不符導致的,因而伸子始終是在和自己的欲望斗爭。
當然,對莎菲與凌吉士、伸子與佃關系造成影響,并構成兩位女主人公內部斗爭的重要因素還有性。《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對性的表達即使放在今天也使人震撼:“我把他什么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莎菲毫不掩飾對美男子的欲望,同時對好友為避免“生小孩”便分開住的做法嗤之以鼻,顯示了審視男性、將男性他者化及個人解放的超前思想。她不僅有如上所述的在靈與肉之間的掙扎,還陷入自責自棄當中。她看上了美男子,便采取計策接近他。但同時,她又本能地覺得“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得到好結果的。”“我懊悔,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不出來的。”一方面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欲望,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不正經。
而《伸子》當中,宮本百合子只是隱晦而內斂地表達了自己的欲望。在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她與佃離婚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與佃有較大年齡差而導致性欲望無法得到滿足,但是,宮本百合子在作品中并不愿意過多提及此事,從而塑造出一個趨向完美、相對而言少欲望的女性形象。莎菲與伸子作為青年女性,有對性的一般欲求是正常的,但是一個自責內疚,一個試圖掩蓋,顯示出她們內心自我形象構筑的斗爭和矛盾,也體現出社會對作為“正常女性”與對性的欲望的對立要求,實質上透露出傳統對女性去主體性的要求,這種要求即使到現在依舊存在。
莎菲和伸子的形象,特別是莎菲的形象從誕生以來就頗受非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習慣于他人的平面形象,而傳統文化對女性的平面形象要求尤為苛刻。但人都是立體的,不是非好即壞,莎菲和伸子的內部對抗正體現了她們的真正存在,那就是她們是活生生的、立體的人,而不是傳統文化強加給女性的單調平面形象——要么是冰清玉潔的“圣女”,要么是邪惡丑陋的“巫婆”。
四、結語
無論是家庭,還是疾病和自我對抗,它們都讓兩位主人公走向了同樣的結局——出走。關于“娜拉的出走”,從五四時期開始就引起了從文壇巨匠到普通學者的熱切關注與討論。娜拉出走后的命運我們不得而知,它存在于我們的推測和期望當中,而莎菲和伸子/宮本百合子出走后的命運卻明明白白地展現在了我們面前——她們用筆和行動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為左翼文學和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然,并不能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伸子》中體現的由與家庭和自我的抗爭、自我形象的構筑等形式呈現的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丁玲和宮本百合子成為左翼文學作家的充分必要條件,即使拋開社會因素等的影響,二者也并非完全的因果關系。她們只是當時左翼文學作家中的少數,社會思潮的推動等外部因素也對她們進入左翼文學的天地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可以說,正是女性意識的覺醒,讓在擁有不同國籍、不同家庭、不同處境、不同愛情對象的她們意識到自己處于愛情難得而生活無光的境地,因而急于尋找出口。成為左翼文學作家是“其自身心理發展和性格邏輯的必然,而非外力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她們成為左翼文學作家的內在最根本原因及動力。
(武昌理工學院)
作者簡介:汪娟(1986-),女,湖北孝感人,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為日本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