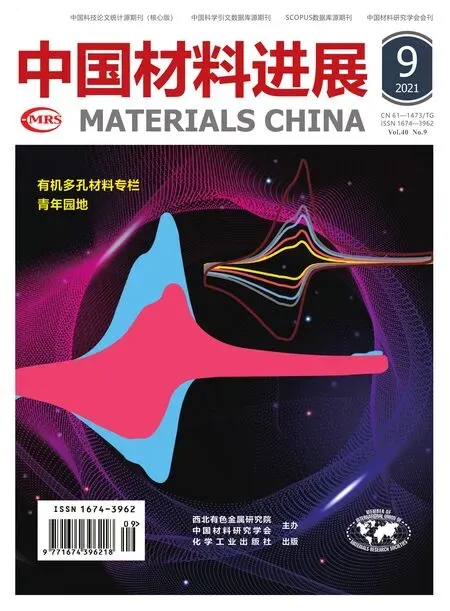碳納米管海綿導熱性能的實驗研究
劉心穎,林 歡,董 華
(青島理工大學環境與市政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033)
1 前 言
從1991年日本研究實驗室[1]發現碳納米管(CNTs)以來,碳納米管以其優異的力學、電學、熱物理性能以及良好的化學性能受到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2, 3],成為新時代最具發展潛力的納米材料之一。為了實現碳納米管材料的實際應用,定向控制碳納米管的自組裝工程技術成為了關鍵的一步。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生產的需求,一種碳基海綿——碳納米管海綿,順應時代的腳步孕育而生。
碳納米管海綿通過改變以碳納米管為基礎的宏觀結構,表現出高比表面積、高孔隙率、強韌的機械強度、優異的導電性能及電化學性能,在能源存儲[3-5]、催化[6]、吸附[7]、復合保溫材料[8, 9]等領域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使其在學術領域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極大關注和研究。從保溫性能的角度出發,碳納米管海綿作為一種新型的碳納米保溫材料,具有低導熱系數,起到隔熱、絕熱的作用。使用保溫材料對減小能耗、充分利用資源,以及促進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和非凡意義。針對不同場合的保溫需求有所不同,無論是建筑、航天航空、海洋還是服飾材料,具有隔熱絕熱特性的多孔材料都在扮演著重要角色[10]。碳納米管海綿作為最具有前途的保溫材料之一,導熱性能的實驗研究顯得尤為重要。Gui等[9]制備出的碳納米管海綿在200~360 K溫度下,導熱系數小于0.15 W·m-1·K-1,具有良好的隔熱性能。但是,碳納米管海綿為何會呈現低導熱系數,仍有待進一步探索。據有關文獻報道[11],通過冷凍干燥法制備得到的石墨烯-碳納米管復合海綿導熱率低至0.021 W·m-1·K-1,和空氣的導熱率(0.026 W·m-1·K-1)在一個數量級上,然而這種碳海綿中片層之間僅為簡單的物理接觸,這使得其機械強度不盡如人意。Baetens等[12]報道了傳統氣凝膠材料被作為建筑熱絕緣材料應用在節能建筑中,而傳統氣凝膠材料的韌性普遍較小,環境敏感且生產成本高,存在無法承受荷載的風險。相比之下,碳納米管海綿結構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和韌性,能夠在熱絕緣材料領域里滿足更多場合的需求,這意味著碳海綿導熱性能的研究具有長遠的價值。
目前,在國際上對碳納米管海綿的研究集中在力學、電化學和吸附性能方面,在導熱方面主要通過增加碳納米管海綿復合材料的導熱性能以提高其在相關領域的散熱能力為主[13, 14],而對其在保溫隔熱方面的報道頗少。為了實現碳納米管海綿在各個領域的應用,了解其在室溫下的熱機制屬性,為其作為一種先進的保溫材料提供理論依據和數據支撐,本工作將采用瞬態電熱(TET)測量技術對其導熱性能進行研究,并結合SEM照片,從微尺度傳熱的角度分析碳納米管海綿的導熱特征。
2 實 驗
2.1 實驗材料
熱性能實驗中使用的碳納米管海綿樣品購自江蘇先豐納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如圖1所示。該碳納米管海綿由氣體碳源通過化學氣相沉積法制備而成,密度為10 mg·cm-3,孔隙率為99%,碳納米管內徑為10~20 nm、外徑為30~50 nm。圖2為該樣品的SEM照片,由圖2c可以清楚地看到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由很多絲狀物無序纏繞縱橫交織在一起,其孔隙空間布局是由無數多壁碳納米管及管束無序塔接組成,單個孔隙大小從幾納米到幾十微米不等。

圖1 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照片Fig.1 Image of carbon nanotube sponge sample

圖2 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的SEM照片Fig.2 SEM images of carbon nanotube sponge sample
碳納米管海綿中存在大量的孔隙,從微觀角度上來看,這些孔隙的存在形式取決于固體材料在孔壁和孔棱的分布形式,這也決定著多孔材料的各種性能。碳納米管海綿孔隙包含碳納米管相互堆積形成的堆積開孔和多壁碳納米管本身的中空管腔結構。當碳納米管頂端為開口狀態時,管腔結構形成的是開孔;反之封閉狀態時,形成的是閉孔。毫無疑問,這些不同的孔隙結構對材料的導熱能力有著本質影響,這一點將在后面章節進行分析。在文獻[8]中,降低碳源的給進速率將有助于提高碳納米管海綿的孔隙率,但是不同孔隙率的碳納米管海綿都具有相似的孔隙分布趨勢,均存在微孔、中孔以及較大直徑的堆積孔,密度越低的碳納米管海綿則具有更大的堆積孔。
事實上,碳納米管海綿的孔隙率大小更依賴于較大孔徑的堆積孔。從幾何的角度來看,大多數的多孔材料都是由骨架固體物質進行非等同單元無規則堆積而成的,包含著不同數量的面和棱圍成的具有不同大小和形狀的孔隙。有研究表明[15],即使是最紊亂的泡沫堆積方式也遵循支配蜂巢等孔隙有序規則材料一樣的拓撲規律。簡單來說,碳納米管纖維在空間上可被看作線,作為孔棱;線與線交織形成孔穴的頂點,共同組成孔穴壁面,根據Euler定律[15],在三維孔穴集合體中,頂點數V、面數S、棱數E和孔穴數H關系為:-H+S-E+V=1。
另外,碳納米管由于范德華力作用[16]而在相互交織重疊處形成“結頭”,如圖2d所示,這種交錯塔接的網絡結構也使得碳納米管海綿在宏觀上呈現出良好的穩定性。
2.2 實驗原理
瞬態電熱(TET)測量技術[17]是一種測量材料熱擴散系數的方法,被測量材料可以是導電、半導或非導電一維導熱結構的固體材料,圖3為TET測量技術實驗原理圖。這種方法具有快速、準確、有效的測量特點,其準確性已經通過研究現有材料的已知熱擴散系數得到證實。研究表明,TET測量技術對材料的熱表征結果與已知參考值的偏差小于5%[18]。由于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的尺寸遠遠大于納米數量級的內部孔隙,這使得焦耳加熱作用對測試樣品產生的體積熱在空間上是均勻分布的,而且該樣品可以被近似看作一維導體材料。因此,可通過TET測量技術快速準確地得到樣品的熱擴散系數,這種可行性在前人的試驗研究[19]中已經得到充分證實。下面將用理論分析結合實驗來解釋如何獲得樣品的有效熱擴散系數。

圖3 瞬態電熱測量技術實驗原理圖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ET technique
實驗前將樣品搭接到兩端電極上,通過對樣品施加一個階躍性直流電流誘導焦耳加熱,使得樣品的溫度存在一個小的上升,導致其電阻改變,進而產生電壓波動。在這個電加熱過程中,被測量樣品會在瞬間時域內達到熱穩定狀態,利用溫升(電壓時間變化)和傳熱的數學模型最終可得到樣品的熱擴散系數。由于整個電加熱實驗都處于密閉的真空(0.3~0.4 Pa)腔體內,因此可忽略熱對流對實驗測量結果的影響,僅需考慮熱傳導、焦耳加熱和環境熱輻射對實驗結果的作用。在TET測試實驗中,示波器顯示電壓變化Vsample和樣品平均溫度變化可表示為式(1)和式(2):

(1)
其中,I為負載電流;R0為樣品電阻;L為樣品長度;k為樣品導熱率;αeff為有效熱擴散系數;q0為單位體積的加熱量,在整個實驗過程中為定值;η為樣品電阻溫度系數;t為時間。理論上樣品歸一化平均溫升T*(t)可表達為式(2):
(2)
事實上,實驗中直接測量溫升大小是比較困難的,因此通過電壓的變化將歸一化溫升表示為T*exp=(Vsample-V0)/(V1-V0),式中V0、V1分別為樣品兩端的初始電壓和最終的穩態電壓。然后,將溫升實驗值T*exp和理論值T*進行數據擬合,最終選取擬合最佳結果作為該樣品的有效熱擴散系數。為了降低實驗誤差、提高數據準確性,實驗中對每組樣品進行多次熱擴散系數測量,接著計算得到一個平均值作為該測量樣品的最終有效熱擴散系數值αeff。
2.3 熱輻射影響的去除

2.4 實驗儀器和步驟
本文中主要使用到的實驗儀器為偏光顯微鏡(型號DM2700P,德國Leica微系統有限公司)、數字示波器(型號DSO-X3052A,美國Agilent科技有限公司)、數字萬用表(型號15B+,美國Fluke公司)、微電流源(型號KEITHLEY 6221,美國KEITHLEY儀器公司)等。
首先用刀片將塊狀碳納米管海綿朝一個傳熱面切成均勻等厚長條狀樣品CNTS1、CNTS2。接著,將樣品懸浮搭接在兩個潔凈的鋁片和硅片之間,并用夾子將其緊緊固定在基底上,以保證樣品和硅電極之間具有良好的熱接觸和電接觸。電極通過鋁螺釘和硅膠層相互連接,使得兩個鋁電極組成的樣品夾附在真空腔體內。為了輸入電流并記錄電壓輸出,將電流源和示波器并聯到鋁電極上。通過輸入不同大小的電流,同時使用示波器監測每個電流下時域電壓波動響應,最終獲得電壓-時間曲線波形圖。之后切斷負載電流并縮短樣品的測量長度,并進行下一組長度樣品的實驗測量。對于樣品CNTS1,實驗將該樣品分成了8個長度進行測試,編號分別為CNTS1-1、CNTS1-2…CNTS1-8,具體樣品尺寸如表1所示。

表1 樣品CNTS1和CNTS2的尺寸參數Table 1 Size parameters of samples CNTS1 and CNTS2
3 結果及分析
3.1 利用TET技術測量熱擴散系數
以碳納米管海綿CNTS1為例,下面將詳述樣品熱擴散系數的表征過程。樣品CNTS1-1長為8.50 mm、寬為0.62 mm、厚為0.66 mm,對其施加10 mA的直流電流,此時樣品的平均電阻為62.45 Ω,并且得到一個壓降比為0.91%的電壓波形圖(如圖4),示波器顯示電壓隨著時間的增加而快速下降隨后達到一個平衡狀態,這意味著電流誘導樣品焦耳加熱產生的溫升很小。

圖4 樣品CNTS1-1電壓波形圖Fig.4 Voltage oscillogram of sample CNTS1-1

表2 樣品CNTS1的在瞬態電熱測量實驗中的參數Table 2 The measurement parameters of sample CNTS1 in TET experiment
圖5顯示了樣品CNTS1的αeff/L2線性擬合圖。由于溫升較小,樣品的有效熱擴散系數與αeff和L2成線性正相關。當L2趨近于0時,即可得到樣品CNTS1的真實熱擴散系數αreal為1.14×10-5m2·s-1。

圖5 CNTS1樣品的有效熱擴散系數αeff和L2的線性擬合圖Fig.5 Linear fitting of the effective thermal diffusivity change against L2 for sample CNTS1
3.2 碳納米管海綿的骨架熱擴散系數
事實上,前面章節所提到的碳納米管海綿的真實熱擴散系數αreal是海綿體骨架和海綿體內空氣熱傳導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為了探求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的本征熱擴散系數,本研究引入了Schuetz等[21]的多孔介質導熱模型,得到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的骨架導熱率理論表達式為:
kintr=3kreal/φ
(3)
其中,kintr為碳納米管海綿的骨架導熱率;kreal為碳納米管海綿的真實導熱率;φ為多孔介質的固相體積分數,在本實驗中所使用的碳納米管海綿樣品中該參數是非常小的。
Krishnan等[22]在研究中已證實當多孔材料樣品的固相體積分數很小時(φ<6%),可以采用式(3)對樣品骨架導熱率和真實導熱率的關系進行表述。Liu等[17]在多孔材料的固相體積分數未知的情況下,通過使用該導熱模型確定了石墨烯泡沫多孔材料的骨架導熱率。從本研究對象出發,孔隙率達到99%的碳納米管海綿樣品完全滿足該導熱模型的適用條件。以測試樣品CNTS1為例,引入導熱率和熱擴散系數關系表達式組:
(4)
式組中,ρCNTs表示組成碳納米管海綿的多壁碳納米管的骨架密度,該參數由生產廠家南京市先鋒納米有限公司提供,約為2100 kg·m-3;cp為多壁碳納米管比熱容[23],取值709 J·kg-1·K-1。于是,方程可改寫成αintr=3αreal,并計算得出樣品CNTS1的本征熱擴散系數αintr為3.43×10-5m2·s-1。進一步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即碳納米管海綿樣品的真實熱擴散系數為1.01×10-5~1.14×10-5m2·s-1,本征熱擴散系數為3.03×10-5~3.43×10-5m2·s-1。

表3 碳納米管海綿樣品在TET測試技術下的熱表征結果Table 3 Thermal characterization results of carbon nanotube sponge samples by TET testing technique
進一步考慮該樣本的骨架導熱率kintr和真實導熱率kreal。根據方程組(4),在其他物性參數均已知的情況下,將不難得出樣品的骨架導熱率為45~51 W·m-1·K-1,而真實導熱率則可達到0.15 W·m-1·K-1。
3.3 碳納米管海綿的界面換熱系數
在隔熱保溫的實際運用中,除了材料本身的導熱情況非常重要之外,由于多孔材料孔隙率高,具有較大的比表面積和良好的流通性,所以當有流體流過材料時,材料的表面熱交換作用也尤為重要。但是,這并非本實驗研究的重點,因此本節對碳納米管海綿的界面換熱系數進行簡單的介紹。
重慶大學王濟平[24]通過建立多孔泡沫材料表面傳熱性能實驗臺對多種泡沫材料進行表面換熱特性研究,發現多孔材料表面換熱系數隨流體流速的增大而增大,隨孔隙率的增大而減小;并且在相同流體流速下,表面換熱系數隨固體骨架導熱率增大而增大,其中石墨泡沫在3 m·s-1的空氣流擾動下,其表面換熱系數達到了475 W·m-2·K-1以上。這些研究結果與文獻[25-27]中多孔材料表面傳熱特性規律一致,因此也同樣適用于碳納米管海綿界面換熱系數的特征描述。
當孔隙分布均勻時,碳納米管海綿的孔隙率越大,孔穴所占的體積就越大,其固體骨架結構的體積占比減少,這樣一來,就削弱了固體結構對氣流的擾動能力,進而導致表面換熱能力減小。固體骨架導熱率的大小對泡沫材料的界面換熱系數也有著本質影響,對于由高導熱固體材料組成的碳納米管海綿,當熱量通過碳納米管骨架流入碳納米管海綿時,傳熱熱阻相對較小,因此其表面換熱能力更強。這無疑對碳納米管海綿的隔熱保溫效果是不利的,同時對如何降低碳納米管海綿的傳熱系數有了啟發。研究人員[28]對隔熱瓦(一種與碳納米管海綿有著類似纖維固體骨架三維塔接結構的多孔材料)表面噴涂了具有高輻射率的玻璃涂層,當表面溫度高達900 K并歷時800 s后,背面溫度仍可保持在289.6 K。這說明高輻射涂料層反射和吸收了表面的大部分熱量,進一步緩解了材料的隔熱壓力。
3.4 碳納米管海綿的熱運輸機理
在前文中描述了碳納米管海綿骨架和孔隙等結構特征,接下來將從微觀層面分析它們對傳熱的響應方式。一般來說,多孔材料[29]是一種由兩相或多相物質組成的共同空間,熱量傳遞過程比較復雜,其等效導熱率的結果主要取決于材料的形態結構和物性這兩方面,如孔隙率、孔隙分布、比表面積、真密度、體積密度等。Alam等[30]通過激光脈沖測定法研究分析了12種不同孔隙率的石墨泡沫材料,其表觀密度為0.23~0.65 g·cm-3、有效導熱率為3.88~174.9 W·m-1·K-1,揭示了材料的容積性質對石墨泡沫導熱性能的影響。根據相關報道[31],多孔介質中多相組成結構的物性差別會導致各相物質對導熱性能方面的貢獻大小不同,當多孔材料骨架結構具有高導熱率時,流體對材料導熱性能作用較小。
碳納米管海綿是一種典型的多孔介質。在碳納米管海綿中,熱量傳遞主要包括骨架間的聲子碰撞和孔隙間的熱輻射效應及固氣兩相之間的對流換熱[20]。由于本實驗研究是在真空環境下進行的,并剔除了熱輻射效應的作用,因此在本節不討論對流和熱輻射的影響,僅從純導熱過程進行分析。
碳納米管海綿中存在大量的孔隙,不管是納米級的中空孔隙還是微米級的堆積孔隙,這些孔隙的存在都嚴重阻礙了空氣在海綿中的熱對流,當孔隙直徑小于空氣分子的平均自由程時,空氣分子之間的微小對流傳熱作用將消失,使得材料導熱率降低。有研究顯示[15],泡沫材料的時效性會影響其導熱率,這是因為多孔材料中既存在開孔又存在閉孔,經過一個時間期限,封閉的氣體從閉孔中擴散出來,低密度的空氣擴散進去,將會使得泡沫材料的導熱率增加達50%。因此,開口孔穴分數也會在小范圍程度上影響碳納米管海綿熱運輸的結果。
另外,碳納米管海綿內部的孔隙和骨架之間的相界面可能會阻礙聲子熱運輸,并且使得導熱路徑變得曲折,這也是為什么單根碳納米管導熱率非常高(k=6000 W·m-1·K-1)[32],而碳納米管海綿的卻很小的主要原因。圖6為碳納米管海綿骨架材料在無空隙和孔隙分布均勻理想的情況下的熱傳遞過程,正是因為孔隙的存在,導致了內部晶格的缺失,增大了聲子在骨架結構中的傳導阻礙,進而降低了碳納米管海綿的導熱率。當孔隙排布隨機時,孔隙使得熱流流動方向更為頻繁地改變,大大增加了接觸熱阻,對降低材料導熱性能的效果更明顯。有研究表明[11],多孔介質的有效導熱率不僅隨孔隙率的減小而增大,并且與孔隙的均勻度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模擬計算可以得出有效導熱率是孔隙均勻度的增函數。

圖6 碳納米管海綿骨架結構的熱傳導模型Fig.6 Heat transfer model of carbon sponge skeleton structure
理論上,碳納米管海綿材料的骨架導熱率可以由Debye模型得到:
(5)
其中,cP為多壁碳納米管的比熱容,ν為聲子的平均移動速率,l為聲子的平均自由程。
在本實驗中,重點考慮碳納米管海綿本身的物理結構及結構缺陷等因素。如圖2a和2b所示,測試樣品的傳熱表面存在大量無規律褶皺,且由于測試樣品是從1 cm×1 cm方塊樣品上切割下來的,樣品邊緣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粗糙度。在熱量傳遞的過程中,能量的傳輸依賴于聲子進行點陣振動的傳播,而這些結構缺陷使得在聲子傳播中形成聲子散射[33],大量落在傳熱表面,導致了聲子平均自由程減小,從而阻礙了聲子的熱運輸過程,進一步降低了碳基材料的導熱率。同時,碳納米管海綿本身無序排列結構內的弱范德華力造成了低模量和毗鄰原子振動的弱耦合,也縮短了聲子平均自由程,使得其傳熱效率大大降低。裴娛[34]通過改變多壁碳納米管管束的生長方向制備了具有高導熱率的碳納米管復合陣列三維宏觀體,從而證實了管束順長整齊度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樣品的接觸熱阻。觀察本實驗樣品傳熱面的結構表征,除了聲子散射的作用,碳納米管交織“結頭”形成的無數個納米級的點接觸,造成了無數個接觸熱阻,導致了樣品的低導熱性能,如圖2d所示。
4 結 論
本實驗介紹了采用瞬態電熱測量技術對碳納米管海綿樣品在室溫下導熱性能的探究過程,測定了樣品真實熱擴散系數為1.01×10-5~1.14×10-5m2·s-1。考慮到碳納米管海綿材料的多孔骨架結構,本實驗借助 Schuetz多孔介質導熱模型得到了碳納米管海綿的骨架熱擴散系數約3.03×10-5~3.43×10-5m2·s-1,真實導熱率可達到0.15 W·m-1·K-1,這使得它成為一種非常有前途的隔熱材料。通過樣品SEM照片解釋了碳納米管海綿低導熱率的主要原因:由于材料表面的結構缺陷和本身高孔隙率,較大的接觸熱阻和傳熱表面邊緣的聲子散射是影響熱運輸的重點所在。本實驗結果將為碳納米管海綿在隔熱保溫領域的應用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對碳納米管宏觀體后續的熱運輸研究具有指導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