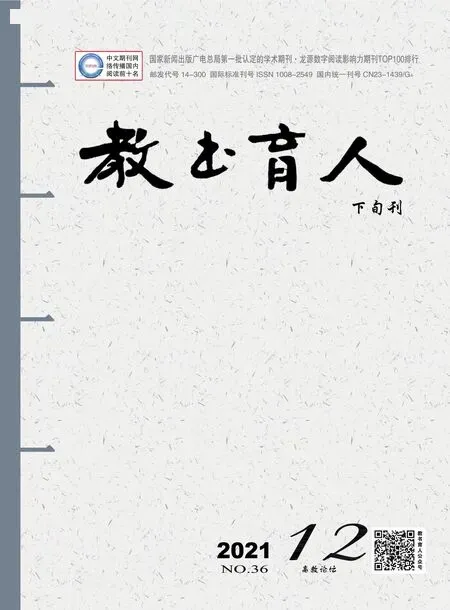我國數字出版本科教育發(fā)軔、現(xiàn)狀及發(fā)展策略研究
朱禮敏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數字出版起源于西方國家,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網絡信息通信技術、網絡信息存儲技術以及流媒體技術上,融合并超越傳統(tǒng)出版而發(fā)展起來的新型出版產業(yè)。[1]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諸多原因,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yè)起步較晚,但得益于近些年技術領域的迅猛發(fā)展,我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在數字出版領域的發(fā)展差距正逐步縮小。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技術的融入,當下的數字出版已經不是以往狹義的“傳統(tǒng)內容數字化”,而是緊密結合“互聯(lián)網+”“媒介融合”的時代背景。出版數字化的轉型升級正全面滲透并影響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更加速了該進程。在產業(yè)迅猛發(fā)展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數字出版行業(yè)內部的人才缺口。如今數字出版行業(yè)內部的中堅人才力量大多是由傳統(tǒng)出版人員轉化而來,這類人才雖具有豐富的出版從業(yè)經驗,但對飛速進步的新興技術涉獵不深,故很難滿足快速發(fā)展的產業(yè)對人才的要求。而高校無疑是為業(yè)界和學界持續(xù)輸出人才力量的重要陣地,所以高校如何培養(yǎng)高素質的、適應時代發(fā)展潮流的數字出版人才就成為不可忽視的關鍵問題。
一、 我國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設立起源
出版在我國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但在人們的傳統(tǒng)認知中,出版一直是一個“重術輕論”的行業(yè),故一直沒有被建設成系統(tǒng)的學科體系。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國才出現(xiàn)了正規(guī)的出版專業(yè)高等教育。而身為舶來品的數字出版產業(yè),在國內被建設為標準化學科的時間則更晚——2008年北京印刷學院首次開設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數字出版專業(yè)的設立是國際和國內眾多因素共同推進下的結果。
(一)國際背景
全球化在21世紀的重要標志是“信息全球化”,在互聯(lián)網技術、通信技術以及數字技術快速發(fā)展的背景下,不少國家都競相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計劃。[2]發(fā)展數字出版產業(yè)是其中一個重要實踐。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就開始了從傳統(tǒng)出版向網絡、電子出版轉型的嘗試。依托強大的科學技術支撐、完善的出版政策機制和強有力的法律政策保障,美國很快成為數字化大背景下數字出版產業(yè)的佼佼者。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在數字出版行業(yè)的成功實踐帶動了世界其他國家傳統(tǒng)出版數字化轉型的步伐。
(二)國內條件
首先,從政策導向看,1996年,我國出臺《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guī)定》,該文件從多方面對電子出版業(yè)發(fā)展提出了系統(tǒng)的要求。2005年,我國加大對數字出版產業(yè)的扶持力度,舉辦中國第一屆數字出版博覽會。[3]“十一五”期間,又相繼出臺了《互聯(lián)網著作權保護法》《關于發(fā)展電子書產業(yè)的意見》等法律法規(guī)。尤其在2009年國務院正式下發(fā)的《文化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里明確了傳統(tǒng)出版向數字化轉型的發(fā)展方向。[4]
其次,從技術層面看,我國數字技術、互聯(lián)網技術的迅速發(fā)展也為傳統(tǒng)出版實現(xiàn)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可能,因此出版業(yè)亟須綜合掌握新興技術和出版專業(yè)知識的復合型人才。
最后,從用戶需求看,進入21世紀后,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新世紀最初十年,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普及率不斷提高。在信息互聯(lián)時代,人們的思維也從傳統(tǒng)向數字化轉型。據2007年《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我國有超過200萬人有閱讀電子書、電子雜志和手機報的習慣,約占統(tǒng)計總數的20%。[5]《2010年中國數字出版產業(yè)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手機閱讀用戶比例已達到總體手機網民數的75.4%。[6]顯然,在技術變革背景下,隨著移動終端持有量的不斷增長以及新的閱讀習慣的逐步形成,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傳統(tǒng)出版提供的服務,開始對數字出版內容及產業(yè)有了更高的要求。面對龐大的市場需求,數字出版專業(yè)人才的缺失就成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所以,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以填補巨大的人才缺口就成了推動數字出版產業(yè)高效發(fā)展以及傳統(tǒng)出版順利轉型的關鍵所在。
二、 我國數字出版專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
(一)我國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分布與變化情況
2008年,北京印刷學院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并面向全國招生。2011年,又有部分高校分批次開設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據統(tǒng)計,截至2020年底我國共有18所高校開設了本科數字出版專業(yè)。從學校層次上看,主要有2所985院校,12所公辦本科院校,6所民辦本科院校。在學校地域分布上,華東地區(qū)有4所院校在本科階段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分別是:金陵科技學院、浙江傳媒學院、閩南師范大學和曲阜師范大學。華北地區(qū)有3所,分別是:北京印刷學院、山西傳媒學院和天津科技大學。西南地區(qū)有3所,分別是:四川傳媒學院、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學院和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西北地區(qū)有3所,分別是:西北師范大學、蘭州文理學院和西安歐亞學院。武漢大學、中南大學和湘潭大學位于華中地區(qū)。綏化學院和遼寧傳媒學院位于東北地區(qū),華南地區(qū)暫只有廣西師范大學漓江學院設有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7]從開設學校數量變化上看,對比之前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院校數量穩(wěn)步攀升的情況,2017年至2020年這4年間,有3所學校撤銷該專業(yè),分別是:曲阜師范大學、浙江傳媒學院和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學院;有6所學校新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分別是:閩南師范大學、蘭州文理學院、山西傳媒學院、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廣西師范大學漓江學院和遼寧傳媒學院。誠然,撤銷專業(yè)這一事實可以用近年來高校各專業(yè)發(fā)展趨勢發(fā)生變化,逐漸轉向內涵式發(fā)展這一背景來解釋,但是開設專業(yè)后短短幾年內就撤銷的現(xiàn)象依然值得我們重視。
(二)人才培養(yǎng)目標與人才培養(yǎng)模式
人才培養(yǎng)計劃是根據人才培養(yǎng)目標確定的。北京印刷學院作為國內最早開設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的院校在人才培養(yǎng)目標上強調要培養(yǎng)“既能掌握數字出版技能與傳播技能,又具有現(xiàn)代漢語言文學以及現(xiàn)代科學文化素養(yǎng)的復合型人才”。武漢大學信管學院給數字出版本科生設立的培養(yǎng)目標為“培育具有廣博的人文社科知識、具備完備的編輯出版知識和數字化信息技術實踐能力的人才”。中南大學則是立足于研究國內數字出版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數字出版產業(yè)實踐基礎進行培養(yǎng)目標的設定。其他院校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的培養(yǎng)目標也不同程度地強調理論性、實踐性、復合性。[7]
人才培養(yǎng)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現(xiàn)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論的指導下,依照特定培養(yǎng)目標和人才規(guī)格,用相對穩(wěn)健的教學內容和評估方法、課程體系和管理制度實施人才教育。目前只有少數學校在本科階段開設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故不同院校根據其自身實際情況和對數字出版行業(yè)的理解設定了不同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在設立之初,少數學校極為敏銳地注意到數字出版和傳統(tǒng)出版專業(yè)的不同,故在培養(yǎng)模式上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創(chuàng)新。例如:武漢大學和中南大學等985重點大學在培養(yǎng)模式上銳意創(chuàng)新,兼顧專業(yè)教學和校外平臺建設。但大部分院校在學生培養(yǎng)模式上仍顯創(chuàng)新度不足。
(三)主要課程設置
課程設置指學校選定的各種課程的設立和安排,主要包含兩方面,分別是:合理的課程結構和合理的課程內容。在課程結構規(guī)劃上會考慮課程設置先后順序、課程設置邏輯關系等諸多方面。在課程內容規(guī)劃上主要考慮合理的內容認知、主要的方法論和時代發(fā)展的要求。而專業(yè)主要課程無疑是二者的核心部分。縱觀我國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的本科院校的情況,由于學校層次、地理位置、專業(yè)特色、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的諸多差異,院校的主要課程設置也有著明顯不同。例如,武漢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yè)隸屬于信息管理學院。武大在出版方面本身就具有豐厚的底蘊,出版發(fā)行學更是其王牌專業(yè),因此數字出版專業(yè)吸納出版發(fā)行學課程設置的部分經驗。曲阜師范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yè)依托院內王牌專業(yè)教育技術學,開設很多信息技術相關課程。北京印刷學院以計算機和新聞傳播學為主要課程。湘潭大學以新聞傳播學和信息資源管理為其主要課程。四川傳媒學院和電子科技大學皆以新聞傳播學和計算機為主要課程。[8]
總體來看,在專業(yè)設立之初,數字出版主干課程大多為整合院系優(yōu)勢專業(yè)課程體系的結果。以曲阜師范大學為例,數字出版專業(yè)于2014年正式成立,在課程體系上依托傳媒學院優(yōu)勢專業(yè)教育技術學、新聞學和數字媒體藝術學,課程體系具有雜合性特征。從教育技術學專業(yè)中引進計算機相關課程:數字圖文處理、數字動畫設計以及數據庫相關課程,從新聞學專業(yè)中引進傳播學、現(xiàn)代漢語以及古代漢語課程,從數字媒體藝術專業(yè)引進數字媒體編輯和多媒體信息合成等課程。誠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能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升學生認知廣度,但是這一做法存在不可忽視的弊端,即:與數字出版直接相關的特色課程較少。
三、我國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存在的問題
(一)數字出版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不健全
受傳統(tǒng)觀念及教育模式的影響,我國大部分高校仍在沿用傳統(tǒng)出版人才的培養(yǎng)模式。
首先,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人才需求存在沖突。這種教學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教材為主、實踐為輔。目前許多高校的數字出版主干課程都是以“概論課”“導讀課”的形式實現(xiàn)的。本科生對數字出版產業(yè)的了解大多來源于課本和教材。課本和教材雖然具有權威性,但是隨著技術的發(fā)展,一些經典教材來不及修訂或再版,不能收錄業(yè)界中新的觀點,這從某種程度上導致學生的認知與整體業(yè)界實踐脫節(jié)。同時,過度注重教材的使用會使學生墜入教條主義的誤區(qū)。
其次,考核方式重理論輕實踐。大部分院校數字出版專業(yè)的期末考試或者學期考核都是以閉卷理論考試的形式實現(xiàn)的,極少有課程考查操作實踐。
第三,人才培養(yǎng)模式開放性不足。許多高校提出了“專業(yè)教學+校外平臺”的培養(yǎng)模式,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但是由于標準難以統(tǒng)一,資源相對匱乏,從課程設置到師資力量再到實習實踐,學校的教學與業(yè)界產業(yè)脫節(jié),著重于校內資源的運用,這就致使高校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落實上仍有著傳統(tǒng)編輯出版的特點。大部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只抓理論,不重視實踐,導致在實習過程中缺乏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動手實操能力的欠缺也導致學生在就業(yè)過程中難以尋覓到專業(yè)對口的工作。
(二)數字出版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完成度低
數字出版專業(yè)本科生應具有較強的編輯出版專業(yè)技能、過硬的計算機綜合操作能力以及豐厚的人文社科知識,這是出版行業(yè)由傳統(tǒng)向數字轉型所必需的能力。首先,要熟練掌握編輯出版相關知識,如出版基礎與出版實務相關法律法規(guī)以及版權保護知識等,了解整個出版的流程,涉獵上中下游產業(yè)。除了必要的專業(yè)能力,還要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管理能力,尤其是數字化產品運營能力,力求實現(xiàn)產學研的無縫銜接。其次,數字出版專業(yè)人才需掌握計算機和其他方面技術知識。計算機知識是數字出版合格人才必備的素養(yǎng),包括數據庫原理與應用、計算機圖文處理、計算機網絡技術基礎、信息系統(tǒng)分析與設計以及多媒體信息合成等。同時也應多關注國內國外新技術發(fā)展動向。第三,數字出版專業(yè)人才應具有豐富的人文社科知識。數字出版屬于文化產業(yè),出版物種類繁多復雜,內容包羅萬象,這意味著數字出版的專業(yè)人才要能夠平衡知識體系中的“博”與“專”。大多數學校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都難以兼顧上述三個方面,或重視編輯出版基礎和人文社科知識等理論能力,或重視計算機綜合操作而忽視理論基礎。學校對數字出版專業(yè)內涵理解各有不同,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也存在分歧。
(三)數字出版本科課程設置不合理
數字出版本科課程設置不合理,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拼盤式課程體系,難以體現(xiàn)數字出版專業(yè)特色。例如西北師范大學和曲阜師范大學等院校在數字出版專業(yè)課程設置上依托學院優(yōu)勢專業(yè),對優(yōu)勢課程進行整合,引入其他學科的主要課程,雖內容翔實,卻難以體現(xiàn)專業(yè)特色。第二,課程體系偏重傳統(tǒng)出版,數字出版課程相對較少。一些高校雖設置了數字圖文處理、數據庫管理、數字校對與排版和網絡出版技術等數字出版所要求的課程,但是傳統(tǒng)出版課程的傳播學、編輯出版學、編輯出版史等仍占據課程量的很大一部分。第三,課程設置與產業(yè)發(fā)展銜接不緊密,不能了解行業(yè)發(fā)展最新動態(tài),無法滿足企業(yè)對人才的要求。在所有開設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的院校中,只有北京印刷學院、武漢大學和西安歐亞學院配備了實習實踐基地,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實習實踐基地并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數字出版師資力量匱乏
首先,從數字出版專業(yè)開設課程看,主要分為傳統(tǒng)出版課程、數字出版課程以及人文社科課程。這樣的課程設置和數字出版行業(yè)的新興動態(tài)對教師隊伍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即:熟練掌握數字技術,有傳統(tǒng)出版和其他人文社科知識背景。故在院系內組建符合要求的優(yōu)質教師隊伍就成了棘手的難題。
其次,目前有部分教師在知識結構上無法滿足數字出版學科的發(fā)展需要,現(xiàn)有的師資隊伍能同時兼修編輯出版知識和數字技術的教師數量較少,在教學方法上也沿用傳統(tǒng)出版的教學模式。學校資源的更新跟不上數字出版產業(yè)的發(fā)展,具體表現(xiàn)在:硬件設施不完備致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忽略實踐,不能接觸產業(yè)最新技術。實習基地不健全致使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大打折扣。
最后,數字出版是一個新興產業(yè),興起時間較短,許多活躍在數字出版一線的專業(yè)技術人員雖然有大量相關工作實踐,但是面對急速發(fā)展的行業(yè)出現(xiàn)的新問題也是在不斷摸索中實踐的。同時這些技術人員自身與高校的交集也不是很多。故難以實現(xiàn)資源的強強聯(lián)合。[7]
四、 我國數字出版本科教育專業(yè)建設對策
(一)厘清數字出版學科內涵
完善數字出版專業(yè)建設需要厘清數字出版學科內涵,高校之間互相溝通學習,產學研相結合。建立完善的數字出版本科評價標準,完善課程體系和專業(yè)質量建設,建立核心課程群:首先建立健全出版基礎課程群,無論是數字出版還是傳統(tǒng)出版,出版基礎課程都有重要的意義,數字出版學科建設應結合專業(yè)實際,建立少而精的出版基礎課程。其次,建立出版法規(guī)與政策課程群,明確版權知識與出版運營管理是出版專業(yè)學生的必備素質,故加強這類課程設置對學生來說極富意義。第三,建立數字出版專業(yè)技術課程群,這是數字出版專業(yè)的重點,也是數字出版專業(yè)有別于傳統(tǒng)出版專業(yè)的核心內容,高校結合產業(yè)發(fā)展,建立健全培養(yǎng)機制,加大專業(yè)課開課數量,保證課程質量,不應盲目追求數量也不能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與傳統(tǒng)出版課程混淆。最后,高校應注重實習實訓模塊,健全實習機制,使本科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二)創(chuàng)新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
高校應對培養(yǎng)模式進行細分,緊跟產業(yè)熱點,因材施教。首先,理論加實踐培養(yǎng)模式。數字出版作為一個新興產業(yè),市場人才極為匱乏,故高校在進行人才培養(yǎng)時應與其他已經成熟完善的學科相區(qū)別,應注重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培養(yǎng),力求畢業(yè)生能力與市場需求不脫節(jié)。其次,科研導向性培養(yǎng)模式。我國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建設已初見端倪,在任何新興學科的建設中,科研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學校在本科階段應鼓勵并支持學生在老師帶領下進行科研實踐,鼓勵有志于學術研究的學生繼續(xù)深造。第三,企業(yè)需求導向培養(yǎng)模式。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的高校應當與數字出版企業(yè)密切聯(lián)系,根據企業(yè)需求制定具體培養(yǎng)計劃,從企業(yè)引進相關技術人才參與教學活動,根據市場需求完成高質量人才培養(yǎng),保證培養(yǎng)數量。[9]
(三)完善數字出版本科課程體系
我國高校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的課程設置應結合行業(yè)發(fā)展動態(tài),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進行精準定位。本科生應注重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比如數據庫管理、出版運營管理、人際關系交往等。高校為解決教學與產業(yè)實踐脫節(jié)的問題,必須著力增加實踐性、實用性課程。適當壓縮出版基礎理論課程,采取少而精的策略,壓縮數量提高質量,增加實用性課程數量,增設專業(yè)課和選修課,擴大學生可選范圍,在實踐中穿插理論課程。同時高校必須著力聯(lián)系建設實踐基地,增加學生實習見習機會,如工作實習見習、互換交流、學術研討會與社會實踐調查等。再者,開設數字出版專業(yè)的學校應加大交流力度,定期進行學科建設研討,商定課程體系建設,各校之間進行人才交流引進。
(四)全面提升教學團隊師資力量
雄厚的師資力量是提高數字出版本科專業(yè)教學質量的基礎,人才是行業(yè)繁榮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在數字出版專業(yè)建設初期,數字出版產業(yè)和數字出版學科建設都面臨著挑戰(zhàn)和機遇。面對出版行業(yè)人才缺失、高校教師缺乏教學經驗等諸多問題,壯大師資力量、提高教師團隊專業(yè)素質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樞紐。
首先在提高人才素質方面,學校可以采用“引進來+走出去”的策略。所謂“引進來”即引進別校客座教授或從數字出版企業(yè)引進資深人員進行授課,將數字出版企業(yè)優(yōu)秀人員及技術人員引進高校。所謂“走出去”即組織教師去優(yōu)秀數字出版企業(yè)參觀學習,鼓勵教師承擔科研任務,走進企業(yè)進行實踐,產學研相結合,將實踐所得應用于教學過程中,提升教學的靈活度與時新性。同時學校應當合理配置資源,加大數字出版教學硬件資金投入力度,為學生創(chuàng)造良好的實習實踐環(huán)境,提升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
融媒體時代數字出版行業(yè)的競爭歸根結底在于人才的競爭。高校作為向業(yè)內輸送人才的重要陣地,必須堅持以市場需求和行業(yè)發(fā)展為導向,做好人才培養(yǎng)定位,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主動適應技術變革背景下人才的動態(tài)需求,助力新時期我國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