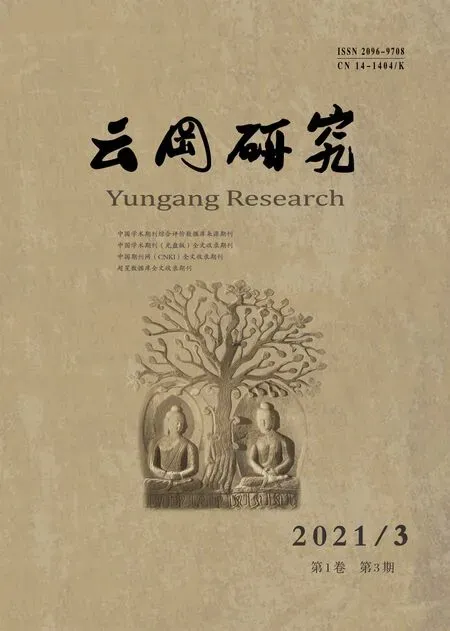論北魏前期國家性質與胡漢豪族
薛海波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江蘇南京210042)
在北魏孝文帝遷都前,北魏國家處于由部落聯盟體制向專制集權、皇權至上的官僚制過渡階段。在長期游牧部落生活中形成的平等、分權、財產共有等觀念,以及游牧經濟占主導的國家經濟結構,使鮮卑胡族部落酋豪與北魏皇權的斗爭不斷。與此同時,漢族豪族以被征服者和合作者的身份,被納入北魏國家官僚體制的道路同樣不平坦。本文要考察的是在北魏前期國家體制中,皇權、原部落聯盟中鮮卑酋豪、漢族豪族三方的政治關系,以期認識北魏是如何對胡漢豪族勢力進行支配和整合的。
一、北魏前期國家的建立與代北鮮卑酋豪的關系
北魏國家是建立在以拓跋鮮卑為核心的部落聯盟體制之上,因此,北魏國家的官僚體制也必然要以部落聯盟為基礎加以構建。由于拓跋珪是靠著諸部大人的擁戴始得復國,部落酋長的實力極大,拓跋珪雖稱魏王,但與其他部落酋長的高下尊卑之別并不十分明顯,從登國元年(386年)至皇始二年(397年)部落大人就叛服無常。[1](P39)如果拓跋珪不建立受其直接支配的官僚體系,不確定和其他部落大人的君臣關系,圍繞著國家權力的爭奪,就有可能就會使北魏像先前的五胡政權一樣迅速崩潰。在北魏建立之時,拓跋珪除了沿襲了代國時期的部落官制外,出于拱衛皇權的考慮,開始建立直屬于自己的類似于侍衛性質的內朝官。據《魏書》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封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2](卷113《官氏志》P2972)就部落聯盟類型的政治體而言,聯盟首領的權威,完全建立在對外戰爭的勝利和掠奪之上,因此,建國伊始,拓跋珪利用其與后燕戰爭不斷取勝的權威,不斷地加強著皇權和完善官僚體系。登國十年(395年)拓跋珪在參合陂大敗后燕,挾戰勝的威勢于皇始元年(396年)“初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2](卷2《太祖紀》,P27)皇始二年(397年)北魏占領河北消滅后燕,天興元年(398年)拓跋珪即皇帝位,11月“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2](卷2《太祖紀》,P33)北魏國家體制雖然采用了一些漢族王朝的組織機構,如臺省制度等,但是本質上卻是一個以拓跋鮮卑和少數胡族主導的非漢胡族政權。這一政權性質,在神瑞二年(415年)為了解決平城的糧食供應是否遷都鄴城的爭論中,顯示無疑。據《魏書》卷35《崔浩傳》載:“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國家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云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如從北魏國家官僚體系的設置上看,據《魏書》卷113《官氏志》記載,天興四年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天賜二年(405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異姓二人,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可見,在中央和地方代人胡酋掌握著實權。北魏又設有大量用于牽制和監督職能的胡族比況官。①參看鄭欽仁:《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稻鄉出版社,1995年,第34頁。所謂“比官”大體有兩種意義:其一,即所設的制度與中國過去官制比況,但實際上當時還沒有被用以比況的中國官制。其次,所設的官制與中國官制比況,而兩者并存。(第162頁)《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載:“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為傳驛,”在拓跋珪不斷強化皇權、構建北魏國家官僚體制的同時,他還利用國家力量將部落大人實力的基礎部落組織加以解散,“其后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2](卷83上《外戚上·賀訥傳》,P1812)從此,部落酋豪失去了部眾,基本上不再成為可公然向北魏皇帝挑戰的政治勢力。拓跋珪雖然建立了專制集權的國家體制,解散了部落組織,但是由于其直接控制的地區僅是今山西、河北和內蒙一部分,周邊強敵林立,加之尚需對中原的漢人保持軍事高壓的態勢,拓跋珪又不得不依靠跟隨其“打天下”、定居在代北的原鮮卑部族大人、普通部眾以及少量的漢人,從而逐漸形成了掌握北魏核心權力的“代人集團”。[3]代人集團主導著整個北魏的官僚機構,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代人在中央文武要職所占的比例92.8%,地方首長是86%,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仍達到76.2%、74%。[4]皇帝的侍官也從代人中選拔,天賜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內詔命,取八國良家,代郡、上谷、廣寧、雁門四郡民中年長有器望者充之。”[2](卷113《官氏志》,P2974)代北酋豪子弟大多是以直宿禁中、有著侍衛性質的中散官起家。②參看鄭欽仁:《北魏官僚機構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1995年,第244頁。中散官包括可分為中散、主文散、奏事中散、侍御中散等四種,在北魏的內廷職官中自成系統。中散官名稱的由來,或是游牧部族制里的職官、取中國之字義而漢譯成中國式的官名者。其名稱則因職官之性質近于散官,而在禁中服務,故取名為中散。代人子弟憑“以功臣子”、“以父任”的資格以中散(第五品中)起家的共22例,《魏書》中任中散者共63人,其中代人33人;以侍御中散(第五品上)起家的共10例,《魏書》中任侍御中散者共24人,其中代人16人。[5](P164-165,P229-231)從以上史實可見,代北酋豪及其子弟憑借先祖的功績通過任子制在北魏禁中職官中居于主導地位,從而很快能夠進入北魏權力核心。而這恰恰反映了作為非漢政權的北魏國家對其統治支柱代人的信任和依賴,而顯貴的政治地位和權力,也是代人長期成為北魏統治支柱的重要原因。
此時北魏在經濟上仍是以游牧和戰爭掠奪為主,在社會組織上剛剛脫離的部落組織成為編戶的鮮卑部眾,尚難以適應建立在農耕基礎上的專制集權的官僚體制,北魏太宗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將名義上的中樞機構尚書省廢除,也沒有影響北魏國家體制的正常運行,可見采用以代人為主導、部族性、胡漢混雜、以胡制為主的國家體制,更為適合當時北魏國家的需要。北魏前期國家權力主要是由原部族大人執政,[6]天興元年(398年)12月,“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云。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東、西、南、北部,皆以諸公為之。大 人 置 三 屬官 。”[2](卷113《官氏志》,P2972-2975)然 而 ,從 拓 跋 珪 的 舅 舅賀訥在離散部落后“無所統領,終于家 ”的 情 況 看 ,部落大人及其子孫能夠被納入北魏國家官僚體系中的畢竟是少數,如至天賜元年(404年)“上幸西宮,大選朝臣,令各辯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余人。”[2](卷2《太祖紀》,P42)在先前的部落聯盟政治體制下北魏的官僚,大多是由部落首領根據成員的才干、武功加以選拔。隨著部落組織的解散,原各自部落的氏族組織也隨之解散,如何選官賜爵就成為了難題,為此,“天賜元年(404年)十一月,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辯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2](卷113《官氏志》,P2974)而用于辨別姓族的大師、小師的設立,則有利于代人各自宗族的構建和形成。由于官位、爵位的承襲關系到家族的興衰,在官僚化作用下代人豪酋的中逐漸形成了強烈的宗族意識。如陸琇,為獻文帝時太保陸馥第五子,“馥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茍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遂立琇為世子。”[2](卷40《陸俟傳》,P905)然而,在官僚化的推動下、在解體的氏族組織上形成的宗族組織,必然缺乏漢族士族家族中靠潛移默化幾代人才形成的禮法和家教,[7]因此,至太武帝時北魏統治集團上層的鮮卑酋豪在與漢族士族的接觸中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素養,但是與熟知禮儀的中原士族相差甚遠,如北魏的開國功臣穆崇孫穆壽其家毫無禮法,“遇諸父兄弟有如仆隸,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諸父馂余。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2](卷27《穆崇傳》,P665)又如慕容白曜弟子慕容契“輕薄無檢”。[2](卷50《慕容白曜傳》,P1122)由于沒有禮法的約束,鮮卑酋豪在婚媾上自然也沒有貴賤、門第之分,以致在文成帝在和平四年下詔書嚴加斥責。[2](卷5《高宗紀》,P121)然而,觀念的形成并不能因為下幾道詔書而改變,代人婚媾不重門第,花費奢靡、不合禮法的情況至孝文帝之初仍然沒有改變,在太和二年(478年)五月,文明太后下詔曰:“乃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2](卷7上《高祖紀上》,P145)而鮮卑酋豪在長期的游牧生活形成的財產共有,掠奪戰利品的習慣隨著征服者身份的確立,使貪污行為成為北魏官場的一個通病,這必然會對北魏國家的統治造成不利的影響。
對于北魏皇帝而言,原部落酋豪的毫無禮儀、文化的粗野面貌可以不管,不分貴賤的婚媾行為可以不究,肆無忌憚的貪污行為也可以放任,但是在部落聯盟時代形成的沒有禮法、貴賤和財產共有的觀念意識,使得在已經官僚化的鮮卑部落大人的頭腦中很難形成與皇帝之間尊卑貴賤的君臣關系,這就很容易因為權力的占有而爆發政治斗爭。拓跋珪也對深知在皇權的確立和官僚化的過程中,權力被束縛變為臣子的部落大人集聚著相當的不滿情緒,他非常擔憂“慮群下疑惑,心謗腹非”,為此于天興三年(400年)十二月乙未,下詔宣揚拓跋氏稱帝是天命所為,其他人不要有非份之想。又于該月丙申下詔聲明皇帝具有著權力和地位的最終決定權:“而今世俗,僉以臺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然而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范。茍以道德為實,賢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2](卷2《太祖紀》,P38)但是作為剛剛由部落聯盟的共主變為一國的君主,仍然有著“謂百僚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的擔心,[2](卷2《太祖紀》,P44)由于代人部落酋豪在北魏國家中的支柱地位,他無法進一步在制度上加強皇權,為了鞏固皇權就只能尋找借口誅殺朝臣,據統計在誅殺的26人中,雖然有早期投附北魏的漢人,但多數是掌握朝政軍事大權的宗室和部族酋豪,其中宗室5人、部落酋豪12人,約占總數的70%。①具體參看李憑:《北魏的平城時代》之《道武朝殺黜臣僚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11-414頁。而道武帝誅殺朝臣的行為,給剛剛建立的北魏國家官僚體系處于恐怖政治的狀態之下,“于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為希少”。[2](卷2《太祖紀》,P44)而北魏前期北魏朝廷各派政治勢力,圍繞著最高統治權的爭奪不斷爆發宮廷政變、導致乳母干政、太后聽政、皇權旁落的原因,很可能與北魏前期胡族國家政權性質、鮮卑酋豪掌權的國家權力體制有關。
二、北魏前期胡族國家性質與漢族豪族的政治地位
北魏國家胡族國家性質,使得以拓跋鮮卑為主的代北酋豪牢牢的掌握著國家權力,“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2](《舊本〈魏書〉目錄序》,P3065)在其入主中原之初也免不了類似于對被征服的漢族進行屠殺,如對漢族豪族聚集的清河地區就是如此,《宋書》卷95《索虜傳》載:“開(拓跋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8](P2322)由于其征服者的地位,和自身文化的粗野,必然對于漢族采取簡單粗暴的統治方式,據《南齊書》卷47《王融傳》載:“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9](P818)然而,隨著北魏國家官僚體制的建立和占領區的逐步擴大,沒有文化的部落酋豪顯然無法滿足官僚制的需要,而處于被征服地位、熟悉先朝制度經典的漢族豪族既可以為北魏皇帝設官立制,又可以支持皇帝抑制部落大人,因此,將漢族豪族納入官僚體制勢在必然,[1](P31)如《魏書》卷2《太祖紀》載:“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茍有微能,咸蒙敘用。”就漢族豪族而言,從西晉末年以來飽受異族的征服統治,民族意識也被保身全家所取代,被異族政權吸納是較為平常的事情。然而,北魏對漢族豪族的吸納卻帶有著較強的強迫性質,如皇始二年(397年)清河崔玄伯就是被強行拉入到北魏的統治集團之中,“(太祖)征慕容寶,次于常山,玄伯(崔宏)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被“遣騎追求,執送于軍門”,[2](卷24崔玄伯傳》,P620)至明元帝仍是如此,據《魏書》卷3《太宗紀》載:“(永興五年,413年)詔分遣使者,巡求雋逸,其豪門強族為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臨疑能決,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用,以贊庶政。”然而,實際卻是用武力的方式將地方土豪遷到代地加以控制,遭到漢族豪族的強力反抗,“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征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于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2](卷24《崔玄伯傳》,P622)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北魏不同與先前在華北定都的五胡政權,它的都城平城在游牧氣息十分濃厚、胡風盛行的代地,習慣于農耕的漢族豪族難以適應當地的社會環境,漢族豪族對于代人掌權的北魏國家體制也不是不知,即使是到平城的朝廷出任官職也是毫無實權,還要與不知禮儀的胡酋共處,加之背井離鄉又沒有生計上的保障,因此,漢族豪族寧可在自己的家鄉出任主簙、功曹一類的地方佐吏,終老鄉里也不愿到平城出任要處處小心謹慎,時刻有著性命之憂的中央官,北魏國家雖然沒有全面控制中原基層社會的實力,但是將一些地方上的豪族代表人物“押送”京師還是不成問題的,因此,以國家武力強制主導,是漢族豪族官僚化的一個顯著特征,這使北魏國家對漢族豪族始終有著絕對的支配權。
至太武帝時北魏統一北方的戰爭基本結束,開始“偃武修文”,大規模地將有著文化優勢的漢族豪族征召至官僚體系中,據《魏書》卷4上《世祖紀》神?四年(431)詔曰:“‘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潁、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又據《魏書》卷48《高允傳》載:“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箸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可見,太武帝此次征召漢族豪族分為兩類,一類是“親發明詔”北魏朝廷高度關注的家世如盧玄之類的北方代表性豪族,另一類是“不耀名譽”影響局于州郡的漢族土豪。而據太武帝于延和元年(432年)下詔曰:“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2](卷4上《世祖紀上》,P81)說明漢族豪族仍然對入仕北魏朝廷有著很大的疑慮。太武帝大規模的征召漢族豪族加入統治集團,并不是要打破原有的鮮卑酋豪及其子弟掌握政權的權力結構,而只是要給以漢族豪族借鑒其統治經驗,強化皇權的工具而已,如應征漢族豪族主要任職于與皇帝行使行政權力最近、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的中書、秘書二省。[10](P50)其中有10人拜中書博士(起家官),4人后轉為中書侍郎,[11](P120)又如在參預詔命、撰修工作的秘書監一職從太武帝至孝文帝之前任此官者共8人,其中漢族豪族6人。[5](P73)處于被征服地位的漢族豪族由于毫無功勛、部族背景,如果要在北魏朝廷占有一席之地,只有緊緊地依附于皇權。由于北魏中前期諸帝的文化素養不是很高,這使得出仕于北魏朝廷的漢族豪族不是靠著自身的文化特質,而是陰陽占卜術數才能得到北魏皇帝的寵幸,如清河崔浩,“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兇,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核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2](卷35《崔浩傳》,P807)漢族豪族的政治權益完全系于皇權,因此,如何使皇權穩固成為漢族豪族政治活動的中心目標。明元帝末年,信奉儒教的漢族豪族代表人物崔浩為了鞏固皇權,曾一度要恢復西晉時期士族執政時實行的五等分封制。[12](P127)這與北魏國家的胡族國家性質相違背,因此遭到了鮮卑酋豪的強烈反對,剛剛繼位(424年)的太武帝只好將其免官。就太武帝而言,崔浩在國家體制上的復古想法畢竟是出于鞏固皇權的考慮,因此,在始光中進崔浩爵為東郡公,拜太常卿,重新復出。雖然太武帝對崔浩等漢族豪族較為信任,但是太武帝更為依靠的代北酋豪,如劉潔“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于是超遷尚書令,改為巨鹿公。”[2](卷28《劉潔傳》,P687)由于代人在北魏的官僚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在皇權強化的壓制下,面對著依附于皇權,在文化上與其截然不同的漢族豪族,在潛意識中形成了一股排斥漢族豪族乃至皇權的心態,從而使太武帝及依附于他的漢族豪族在國家大政決策的過程中,往往處于少數的不利地位。崔浩靠著太武帝的支持,在國家大政的決策上頻頻與朝廷的鮮卑酋豪交惡。如在始光三年(426)崔浩與長孫嵩在是否攻打赫連昌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又如神?二年(429)太武帝計劃討伐蠕蠕,遭到了保太后、安原、劉潔等鮮卑酋豪的堅決反對,崔浩責罵公卿大臣曰:“今圣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2](卷35《崔浩傳》,P818)又如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九月,太武帝欲伐蠕蠕,劉潔認為“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谷,以待其來”得到了群臣的支持,而崔浩則力主太武帝北伐。[2](卷28《劉潔傳》,P688)而太武帝對漢族豪族的任用,對代人群體意見的不屑一顧,最終導致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宗室、代人劉潔等發動政變,“(劉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故諸將不至”,導致魏軍大敗,“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太武帝弟拓跋丕)。”[2](卷28《劉潔傳》,P689)這一政變很快被太武帝及太子拓跋晃平定,十一月底太武帝在返回平城的路上就頒布詔書任命皇太子監國,據《魏書》卷4下《世祖紀》載:“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隨即將劉潔、南康公狄鄰及張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中山王拓跋辰等八將,以北伐失其,斬于都南;太武帝的弟弟拓跋丕、拓跋范也受牽連致死。①何德章認為在太平真君四年的政變,拓跋丕本有追逐帝位的圖謀,而拓跋范牽涉其中,劉潔也才會有自己當皇帝的企圖。然而“功臣”們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劉潔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為在此以前拓跋燾、崔浩等人進行的“太平之治”活動業已經危及他們的政治利益。《北魏太武帝朝政治史二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七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7-49頁。
而太武帝“無情”打壓鮮卑酋豪無疑會使崔浩產生只要依附于皇權,皇權就會支持其士族政治理想的錯覺,加之崔浩為太武帝滅赫連、平沮渠、降馮燕、賓李涼,以及數次北擊柔然立下大功,太武帝對其的依賴一度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13](P186-187)因此,“位高權不重”的崔浩遂將漢族士族門第觀念推行到北魏國家政治之中。如崔浩為了“行政教,興禮儀”,借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燾率軍平定蓋吳,在長安佛寺發現僧人的種種不法游說太武帝下詔滅佛,禁止代北酋豪信仰佛教。又如崔浩全然不顧太子拓跋晃所堅持以經驗賢能的任官標準,硬是要將士族子弟憑借門第“坐至公卿”的理想加以實施,據《魏書》卷48《高允傳》載:“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在太武帝平定涼州后,深愔魏晉文化的河西漢族士族大多被遷至平城,崔浩對此群體多方幫助提攜,據《魏書》卷52《張湛傳》載:“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宋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見稱于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為之解焉。’”而河西士族在太武帝的眼中則是抵抗北魏的“死硬”分子。又如崔浩在鮮卑酋豪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在婚媾上卻炫耀漢族士族的文化優勢,據《魏書》卷38《王慧龍傳》載:“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嚧鼻,江東謂之鼻嚧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這使得司徙長孫嵩極為不滿,‘聞之,不悅,言于世祖,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因此,在崔浩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門第、家學判定高下,排他性極強的漢族士族群體。他們依靠著自身的文化優勢對掌握軍政實權的鮮卑酋豪的信仰加以摧毀,在社會關系上對其加以鄙視,還要將門第納入到選官體制之內,而這些遠遠超過了北魏太武帝利用其群體的文化優勢咨政,平衡粗野的鮮卑酋豪的政治空間,太武帝和漢族士族代表人物崔浩之間的政治回旋余地則越來越小。崔浩要推行的“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的主要反對者則變成了太武帝。據《魏書》卷46《李欣傳》云:“初,李靈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侄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于世祖。”可知,崔浩所舉三人均為當時漢族豪族的第一流高門子弟,而段霸身為宦官,在入宮之前其家世僅為雁門土豪,高讜為渤海豪族,在門第上照上述三家子弟有較大的差距,根據門第選官也激起了一些在朝廷任官、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的漢族豪族的強烈不滿,這使得太武帝不得不親自出面干預,“世祖意在于,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還,箱子等罷之。’”如果崔浩推行士族政治理想繼續進行下去,不僅使北魏以鮮卑酋豪掌權的權力結構發生混亂,而且也會使得北魏統治的支柱代人和北魏皇室產生離心,這對于北魏國家的存亡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太武帝只好借“國史之獄”將以崔浩為代表的北方高門士族加以屠殺,《魏書》卷35《崔浩傳》云:“真君十一年六月(450年)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
太武帝誅殺崔浩及北方士族,使得鮮卑酋豪失去了制衡,導致了太武帝末年的政治混亂,這使得北魏政局又回到了皇室與宗室、外戚、宦官、代北酋豪相互爭斗的局面。文成帝與獻文帝兩朝的用人政策,轉而以尚念勞資歷為主,據《魏書》卷5《高宗紀》載:“冬十月丙辰,詔曰:“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后,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而這對不善文治的鮮卑酋豪是很有力的,據統計在文成帝時擔任地方州刺史、鎮將的人數共42人,而為鮮卑等北族人士29人,占近70%。[14](P190-193)漢族豪族則在北魏文成帝時的統治集團處于明顯的劣勢,屬于被支配的階層,他們往往需要通過與皇室姻親聯姻等方式,才有可能進入統治集團上層,如頓丘李氏就是如此。[15](P499)在仕進上,漢族士族子弟升遷也極為緩慢,如雖然高允頗得諸帝寵信,但其子高懷,“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2](卷四八《高允傳》,P1090)殘酷的國史之獄使北方高門士族對于入仕于北魏朝廷有著很強的禁忌,如在獻文帝時頗受重用的漢族豪族武威賈秀,對于朝廷以門第讓自己的子弟出任郡守一事推辭,以免使得北魏朝廷感到有士族政治之嫌,《魏書》卷33《賈秀傳》載:“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于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為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圣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又如曾遭受此重創的太原郭祚在孝文帝朝廷為官時還心有余悸,《魏書》卷64《郭祚傳》:“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干,蔫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于誠至。”此時任用漢臣人數大為減少,豪族出仕大部分是以祖蔭與降附的途徑,并無一人是出于自愿出仕或由朝士推薦。此時長期入仕于北魏朝廷的漢族豪族,大多以保身全家為首要目的。如渤海高允為了迎合信奉佛教的太子拓跋晃和文成帝,由奉道改崇信佛教,并練就一番喜形不著于色的本領,如廣平游雅曾說:“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2](卷48《高允傳》,P1077)而漢族士族官僚在官場小心謹慎也成為漢族士族家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恒農楊椿在其家誡中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2](卷58《楊椿傳》,P1290)然而,由于國家行政的需要,北魏仍然要任用一些漢族豪族,如趙郡李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秘書 下 大 夫 ,典 掌 要 切 。”[2](卷36《李敷傳》,P833)又 如 文 成帝曾以高允為榜樣,對其左右不識文化的鮮卑酋豪子孫加以訓斥,據《魏書》卷48《高允傳》載:“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這是拓跋浚與拓跋弘兩位君主雖不主動征用漢人,而漢人仍能仕進的原因。[1](P45)
綜上所述,北魏作為以拓跋鮮卑為核心的胡族在北部中國建立的胡族政權,為了保證自身統治者的政治地位,無論是在國家體制的設置、還是在國家權力的執掌上,都帶有著濃厚的胡族排他性質。由于北魏國家脫胎于草原游牧部落聯盟體制,對于北魏皇帝而言,既要使鮮卑部落酋豪作為國家統治的支柱而使其執掌國家權力,又需要將其納入到受其支配的國家體制之中,對于部落酋豪而言,由于部落聯盟時代形成的權利共享、平等的意識根深蒂固,難以受皇權的壓制、官僚體制的管束,因而在北魏國家體制的設計上存在著自然矛盾的之處,從而使得北魏前期圍繞著最高統治權的政治殘殺不斷爆發,因此,根本不存在實行門閥政治的客觀環境和制度性需要。這也決定了作為被征服者的漢族豪族在被納入北魏國家官僚體制之后,只能充當咨詢顧問的角色,如超出北魏國家代北酋豪掌權的權力結構為其群體所劃定的政治空間、介入到皇權和代北酋豪的政治沖突,就只能是身死族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