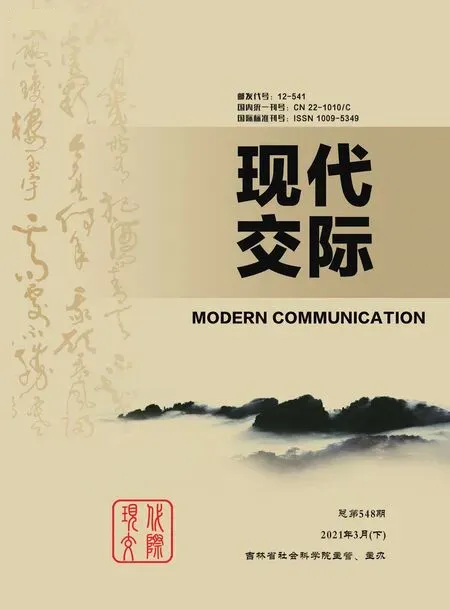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研究述評
李童顏
(大連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8)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1]這個要求提出以后,廣大理論研究者和實際黨務工作者圍繞組織力展開了系統研究,通過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梳理,既有利于發現此前眾多研究的成績和不足,又為此后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
一、關于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重點提出組織力概念以后,黨政界和學術界眾多學者很快就開始對“組織力”這一內涵進行深入研究。《基層黨組織如何提升組織力》一書沿用中組部李小新文章的觀點,認為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是指基層黨組織通過資源整合、結構優化、制度完善等多種手段和策略以實現對上落實各項任務、對下團結動員群眾、對內加強有效管理的時間目標而需具備的六大能力,分別是政治領導力、組織覆蓋力、群眾凝聚力、社會號召力、發展推動力和自我革新力。[2]
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黨的基層組織力的特殊組成部分。一方面,有一些學者指出,高校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是一種“能力”。郭茜認為,高校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是“高校基層黨組織憑借自身的組織體系和組織資源,對師生進行引導、整合和動員的能力”[3]71。常靜認為,對于高校而言,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是“黨組織在黨支部書記的領導下,落實黨的工作要求和立德樹人目標的一種能力”。[4]張慶玫和王展認為,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指高校基層黨組織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教育引導黨員、組織凝聚師生、推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能力”,[5]通過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學者將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當作由不同的力組合而成的“合力”。比如,陳哲和王涇認為,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領導力、行動力、協調力、服務力、學習力以“合力”方式體現在高校基層黨組織的發展與建設過程中的有機整體。[6]7蘇明華、黃敬聰等人認為,高校基層黨組織主要是包括教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的基層黨支部,其組織力為動員力、發展力、監督力、管理力、執行力、知識力、戰斗力、凝聚力形成的合力。[7]42
通過對現有關于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內涵的研究成果的梳理來看:黨建工作者以及其他學者們在研究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概念時,都突出了基層黨組織教育、管理、監督、服務黨員職責,強調如何將師生黨員組織起來去高效地完成黨中央給予高校的任務和時代使命。但是在看到眾多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著些許不足。第一,有關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文獻中,沒有提及其概念的理論來源,探究不夠深入,導致一些研究直接沿用他人的概念;第二,有的研究成果單純地將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看作狹義的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忽略了組織力在高校中的實踐性和針對性;第三,有的研究成果雖然考慮到了高校基層黨組織不同于企業、機關等基層黨組織的特殊性,但沒有注意到高校基層黨組織可以分為校黨委、院(系)級黨組織、教職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三個層級,每個層級的組織力應有所不同。當然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商榷的成果,比如: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與黨員凝聚力、群眾組織力是否是相同的意思;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施力者是否只針對師生黨員,群眾是否應該作為受力群體被考慮在內。
二、關于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所存在的問題研究
從當下的研究視閾來看,大部分學者從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角度提出了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進程中的一些共性問題。比如,蘇明華等人指出,“多數教師黨支部黨員把學科發展與科研人物擺在第一位,而忽視了黨支部政治功能的發揮與思想政治建設”[7]42,李慶朋[8]、陳育勤[9]等人也有類似的觀點。何莉煒和安娜注意到很多年輕的兼職書記因其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威信力弱且號召力不強,而導致“黨支部書記選優配強不夠到位”[10]的問題;郭茜指出“黨內政治生活與黨員未發揮主體的實際作用”[3]73的現象,陳哲[6]10、趙北琳[11]等學者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不難發現,研究學者們有的闡述緊扣“組織力”的構成要素,有的以黨支部的領導為主體,使研究更具有說服力和代表性。
眾學者們對高校基層黨組織提升組織力存在的問題的探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果實,但是通過對現有學術成果的梳理來看,最大的不足就是沒有將高校基層黨組織看成一個系統。也就是說,很多的研究成果雖然主觀上是在探索高校中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提升問題,實際上忽略了校黨委、院(系)級黨組織、教職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每一層級的組織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其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自然各有迥異,不能一概而論。其次,有些研究沒有將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與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這三方面出現的問題進行區分。單從字面上看,一方面,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包含于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中,但既然設定了組織力建設這一概念,就要區別于政治建設、思想建設這些其他的黨建內容,其突出問題便要明確指出;另一方面就是組織力“建設”與組織力“提升”的問題,“建設”指的是建立、設置,形容的是一種從無到有的狀態,而“提升”指的是提高、提拔,形容的是從低到高、從弱到強的狀態,因此其出現的以及面臨的問題當然不盡相同。最后,一些學術研究的研究方法,給人一種直接套用前人研究成果的感覺,如此“換湯不換藥”地去反復研究,對解決問題幫助不大。要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去考察、調研,深入到高校各個層級的黨組織中去,這樣才能得到一手資料,才能進行下一步研究。
三、關于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的對策研究
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研究的重點,最終還是要找到切實可行的提升組織力的對策。現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果將高校基層黨組織作為系統來研究,導致所給出的對策沒有落實到具體層級。例如,薛小平認為要從“突出政治功能、優化組織設置、強化隊伍素質、創新方式載體、深入聯系師生、聚焦立德樹人”[12]六個方面來提升高校組織力。白皓和李淑云建議從“突出主體功能、堅持‘三會一課’制度、創新工作方法”[13]三個方面來提升組織力。曲一銘從“強化服務理念、提高服務能力、壯大服務隊伍、改善服務方式、完善服務機制”[14]五個方面提出建議。華樂指出,要從突出政治功能,筑牢思想“主心骨”,優化組織體系,加強規范化標準化建設四個方面增強政治領導力、思想影響力、組織覆蓋力、自我革新力和發展推動力。[15]從整理的資料來看,可以將這些研究者的成果做以下幾個方面的總結:一是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性,堅定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二是創新已有組織機構、運行機制和活動方式,跟上時代潮流;三是對內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對外聚焦群眾需求。以上研究成果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索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提升路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還有一部分學者聚焦于某一層級,給出的建議更值得參考。例如,針對院(系)級黨組織,周源源認為首先要“合理配備人力資源”,發揮院系黨組織書記的“頭雁效用”;其次建立健全制度體系和滿意度評價機制,既要分工明確又要協同合作;再次,院系黨組織要對青年知識分子做到引領其思想、關心其生活的、支持其工作,讓青年教師黨員有強烈的身份認同感;最后,院系級黨員群體加強自身的思想修養以及學習和實踐能力,以順應時代的變革。[16]針對教職工黨支部,尹朝暉指出要從“優化黨支部組織體系、發揮黨支部組織功能、增強黨支部組織活力”三個方面來提升教職工黨支部的組織力。[17]針對學生黨支部,郝穎建議利用網絡培養學生黨員及干部隊伍的同時,“挖掘培養一批政治敏感度高、思想意識先進、網絡交流能力強的學生網絡意見領袖”,通過互聯網去引導正確的輿論導向。[18]
從現有的學術成果來看,在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提升路徑研究上,對策方面有了一定的積累,雖不乏良策,但是總體上看仍然存在以下幾點不足。首先,所提對策的針對性不強,有些研究成果其實就是針對加強黨自身的建設所提出的意見,并不是針對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這一特定內容展開的研究,這些成果雖然可以對后續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參考,但這畢竟是兩種不同層次的概念,還是需要高校黨務工作者針對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展開特定的研究,以探尋切實可行的提升組織力路徑。其次,不將高校基層黨組織層級進行區分,會導致提升對策的實際操作性減弱,眉毛胡子一把抓,問題得不到解決。再次,很少有學者將校黨委、院(系)級黨組織、教職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這三個層級同時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這實質上是忽略了高校基層黨組織是一個由三部分黨組織構成的有機整體,也忽略了校黨委、院(系)級黨組織、教職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這三個層級之間的關聯性。最后,提升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建設更好更強的基層黨組織,更是為了建設讓人民滿意的高等院校,提出對策的角度應放在高校這個大的格局上,而不應只局限于高校基層黨組織。
四、結語
組織力這個概念提出以后,廣大理論工作者展開了大量研究,高校中的實際黨務工作者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各界學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就高校這個平臺總體而言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特別是像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豐富內涵、顯著特征等方面,這種有關高校黨組織組織力基礎理論的闡釋明顯不夠深刻。探索高校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存在的問題,還需要做大量實地調研和考察,找出癥結所在,這樣才能提出對提升組織力有針對性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