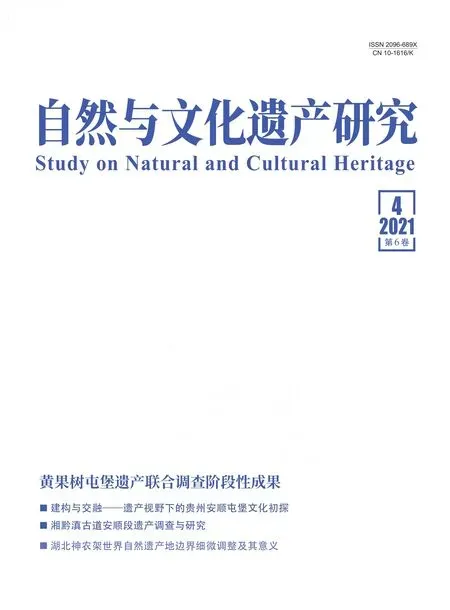走出“原真性”
——試論人文區位學視角下的泉州文化遺產
孫 靜
(泉州師范學院 中國泉州文化遺產研究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文化遺產在過去30年間已深入影響并改變著中國地方文化。文章想要回應以下問題,中國早期社會科學學派——燕京學派①燕京學派指的是20世紀初由吳文藻創立,以費孝通、林耀華、田汝康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化,該學派是繼承了英國功能主義學派的治學傳統,講求社區研究的田野調查方法。所主張的“人文區位學”對于當代遺產理論和研究具有何種借鑒價值和意義?以此視角剖析處于世界文化遺產進程中的泉州,是否將有助于反思遺產體系中存在的“原真性”議題?人類學或可以“人文區位學”為方法論介入中國的文化遺產運動進程。
1 伊勢神宮命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文化遺產名錄及公約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動建立人類文明共同文化財富的長效機制。始建之初的黃金標準《威尼斯憲章》是以傳統建筑的物質形態,尤其以石質這類恒定性特征的建筑材料為依據來規范操作指南的。這一指南被詬病最多的是它根植于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論,將物質性(身)與精神性(心)相分離②WIJESURIYA G.Towards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heritage[J].Built Heritage,2017(2):1-15.,其具體表現為“紀念碑主義”③紀念碑主義指的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起始于對紀念碑及遺址的建筑、立面、形態的物質性保護。紀念碑主義是對西方文明的風土建筑和物質遺跡進行保護的一種理念,以《威尼斯憲章》為代表。和“原真性檢驗”④原真性檢驗指的是文物或文化遺產是原真的描述……是原初的、創造的、非重復的、獨一的、真誠的、真實的、特別的、名副其實的,未經過偽裝、模仿或是其附屬品。。對前者的批評在于它根植于歐洲古典的歷史建筑概念:城堡、宮殿、大教堂、修道院、寺廟、金字塔、陵墓和巨石。這種紀念碑主義迷戀于大小,并賦予那些規模大和造價高的文明的物質遺跡以特權[1];對后者的批評在于它貶低了東亞、非洲和大洋洲等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忽視了文化多樣性。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日本制定并通過《奈良真實性文件》。這一文件制定的背景便是要對以往建筑保護及其原真性宗旨提出質疑,且在跨文化比較中推動文化遺產名錄關注到文化相對性。這一文件生成的背景是法隆寺的木構建筑形成對歐洲古典石質建筑的挑戰,前者表現為臨時性的、替代性的建筑理念;后者則是恒定的、靜態的建筑理念。
然而,伊勢神宮比法隆寺更能啟發人們思考遺產的實質:“它不是建立在永恒和實體之上,而是建立在事物的短暫和虛體之上”[1]。伊勢神宮位于日本三重縣,是日本重要的神道教社,至今仍保留有日本古老的“式年遷宮”⑤伊勢神宮是日本神道教的重要空間。每隔20年拆毀一次,在相鄰平地擇址重建,循環往復。根據官方記載,這一傳統已經存在了1 300多年。神宮最近一次,即第62次伊勢式遷宮于2013年完成,下一次將于2033年開始。儀式。每隔20年的周期性儀式重建意味著舊有的建筑實體須被毀滅。法隆寺或許讓以歐洲學界為主導的委員會意識到了其他文明與歐洲在建筑保護實踐中的文化差異,伊勢神宮則象征著一種以無常幻滅為特征的佛教循環時間哲學觀對追求永恒性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戰。正是后者開啟了對長期主導世界文化遺產的《威尼斯憲章》的全面反思。
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代的到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遺產體制所引發的爭論與質疑。遺產體制運行的悖論在于,其黃金準則“原真性”恰恰導致了各民族文化在追尋“原真性”過程中不得不舍棄、掩蓋其民族和地方文化內涵的豐富性,使其迫于“登錄”和被“展示”的需求。文化遺產公約及其操作指南是落后于本地實踐的,是切割了當地文化完整性的。后者恰恰應當是前者的啟發,而不應在前者的指揮棒下委身于任何一種被構建的“原真性”。
2 人文區位學
泉州繼2013年當選首屆“東亞文化之都”后,2020年又以“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之名,正式向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邁進。泉州的遺產化歷程,無疑也將會是超越或委身“原真性檢驗”,兩者擇其一的命運。泉州完全可以像伊勢神宮一樣,超越文化遺產保護的傳統界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規則制定者們提供新的啟迪。在泉州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實現這種超越和突破的學科路徑之一即是引入燕京學派所提倡的“人文區位學”。
考古學家孫華認為,泉州古城是因海外貿易而興,城市肌理逐漸擴建形成不規則形態的商港城市,屬于“隨形就勢”類型。該城市類型最重要的城市功能要素除了地方城市都具有的衙署外,城市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的遺址、遠洋商船停靠的港口遺址、隨海舶而來外商集中居住的蕃坊遺址、古代不同國家和文明文化交流的遺存、城市郊野生產外貿產品(主要是瓷器)的遺址,以及將這些外貿產品運輸到城市港口的道路、橋梁等遺存都應該受到關注⑥孫華.中國古代城市的類型:兼談泉州城的歷史地位(中國泉州文化遺產研究院“物質性、遺產與文明”國際學術系列講座紀要,載于該研究院公眾號),2020年10月。。“隨形就勢”反映的即是泉州城市形態、肌理與其生態、地理環境的關系。與伊勢神宮不同,泉州的文化遺產價值擴展在對其城市肌理、山水生態、交通要道、城鄉關系、內外貿易關系的全面把握之中。不得不說,這種復雜性恰恰是泉州文化遺產的價值所在。
要把握這一復雜性,除了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對過去的研究之外,起源于社會科學大本營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學在方法論上所堅持的“社會調查”也架起了空間研究與社會結構分析的橋梁,為處于文化變遷中的遺產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發。
2.1 人文區位學的特點
人文區位學的傳統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它的基本方法來自生態學。所謂區位,就是ecology。人文區位學指的就是對人類共同體適應于更大范圍的社會環境這一過程展開的社會人類學研究[2]。
芝加哥社會學在進步主義時代的美國,面對方興未艾的社會調查,在破與立的交錯中尋求社區何以成為共同體的答案[3]。芝加哥學派開創之初就形成了兩個研究傳統與方向:一是關于城市空間利用的人文區位學,研究城市空間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二是社區研究,關注的是人們適應城市空間環境的社會過程[4]。后者由帕克(Robert Park)帶來中國,對“燕京學派”影響至深。
燕京學派所繼承的人文區位學,具體表現為社區調查,也就是要求學者到田野地去做實地調研。通過對個案進行深入分析和發掘,積累豐富的描述性田野資料,從局部來認識整體。燕京學派之所以對帕克帶來的新視角充滿興趣,是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也同樣面臨著社會文化變遷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身處文化遺產歷程中的泉州,也處在文化變遷的歷史潮流中,同樣面臨著破與立的問題。
2015年3月,泉州市政府規劃的閩南文化生態園建設項目啟動,該項目將泉州老城南部老街區納入文化遺產保護框架內。這一項目以“見人見物見生活”為目標,力圖使規劃設計符合該區域的歷史文化基調。見人,即由居民所結合成的社區;見物,即社區具有文物價值、歷史價值的文物及建筑;見生活,即在前兩者基礎上鋪展開的當地人具體且豐富的生活世界。此三者指出了泉州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遺產保護原則,而人文區位學呼吁的正是研究者通過長期且深入的調查,梳理這三者所構成的人文生態。
在實踐中,平衡三者關系卻并不容易。在視角主義主導下,對“物”進行修繕管理,最易受關注、出成果。“人”和“生活”的意味和內涵卻不易被“見”,因而也最易為政府所忽視。
2.2 超越傳統的人文區位學
要面對泉州這樣一個具有漫長歷史傳統的區域,傳統的人文區位學還存在局限性。彼時的美國,帕克將城市看成人性的實驗場,認為人文區位學和人類學有著有趣的關聯,因為城市內部所蘊含的基本沖動與原始社會的并無二致[3]。帕克的繼承者們未全然理解其所言的對城市中的人性洞察,而將城市視作是無歷史的斷面,忽視其縱向歷史維度。也就是說,受生物學啟發的“人文區位學”里包含著某種“生態論”,以及當時流行的“社會形態論”,其研究并未充分給出歷史的“地方感”[2]。在面對泉州這樣具有歷史文明積淀的地域時,亟須開展橫縱交錯的人文區位考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王銘銘教授所領銜的人類學專業碩士、博士生的調研團隊曾在泉州進行過幾次此類實驗,分別圍繞安溪鐵觀音茶葉[5]、泉州城南3條古街[6]以及惠安小的宮廟和祠堂[7]展開。2013年,在對安溪鐵觀音的調研中,他們認為鐵觀音中包含著安溪人對“人——物”“人——人”“人——神”關系的獨特感知。處于傳統與現代、手工與機械猶疑中的安溪人無疑要回應對這一廣義人文關系,以便度過鐵觀音危機。2015年,他們對泉州城南老街區的研究更為直接地踐行具有“歷史感”的人文區位學。該研究反思了地方文史敘述的宋元繁榮中心論,考察了作為生活和社會過程的完整體系的文化及其水系與宮廟體系之間的關系,繼而說明人、神、物3種力量如何在社區中交融并生。2016年,人文地理視角的引入,使得對惠安小人文生態及其社區歷程之關系的考察更為深入。這個研究讓他們意識到,社區或鄉村并非現代文明進程的敵人,它們是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相互關聯共生下形成的完整生態人文體系,整合了人、物、神諸生命因素,自身有著強大的創造力[8]。
在這些調查與研究中,他們試圖呈現時代閩南區域文化中的廣義人文關系(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之間的關系)結構和動態面貌。他們認為,任何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都是人、物、神諸“存在體”共處的場所。要研究社區,就需要重視這3類“存在體”之間的關系[9]。
在實踐中,處理三者關系并不容易。城市化帶來的發展壓力常常使得“物”的價值優先被考量,“人”和“生活”的價值處于次要地位,或主要服務于前者。三者關系的梳理也往往滯后于對“物”的保存、管理與修繕。同時,往往是具有年代價值的古物為人們所好。
2.3 泉州:復合的人文世界
傳統的人文區位學構建了空間研究與社會結構分析之間的關系,而面對具有漫長歷史文明傳統的泉州,筆者呼吁一種具有“歷史感”的人文區位學。這種人文區位學既考察了它在人文地理意義上的“社會形態”,還將泉州置于諸文明交融復合的歷史生成論當中。換句話說,作為遺產主體的泉州即是一個“復合的人文世界”。
泉州與世界體系的碰撞恰恰證明,世界性的海外貿易并不是在15世紀歐洲興起后才出現的。借用施堅雅的中國歷史結構分析,泉州的區域發展周期可被分為:①漢人在邊陲地帶的內部拓殖期;②唐中后期至元代,泉州海外交通核心地位和內部政治經濟中心地位的形成期;③元末至清,區域性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動引起的泉州核心地位的式微期[10]90。“在從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形成之前,由一座中國東南沿海港城帶動起一系列海外貿易活動,其所跨越的空間范圍,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中間范圍包括南洋、印度等地,在此范圍內流動的物品與符號,包括了東西方各主要文明的成就,其廣度并不亞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0]73。早就浸淫于世界體系中的泉州,或者說生長于世界主義的泉州,其文化底子便天然具有一種復合人文主義的意味。
具體而言,泉州“城”與“市”的此消彼長,展現了帝國是如何映照在泉州作為“城市”的歷史之上的。這一復雜過程從歷史深層結構上反映了泉州人文傳統的復合性。“明以前的泉州,盡管也為城墻所包圍,但其市的一面更為突出;而明以后,盡管圍城未擴大,但得到了加固,市這一面的重要性則退讓于城這一面”[10]111。傳統國家可能并不像以往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較為封閉的社會,其文化多元的程度反而可能達到一個空前狀態。海洋成為13世紀之前泉州城市發展的重要通路,其社會文化形態應以“文化世界主義”來加以形容。這與拉鐵摩爾[11]描述的因北方游牧民族對南方農耕文明的擠壓所導致的文明南移有所不同,泉州所處的山海之地理特征迫使人們走向冒險與財富并存的海洋。然而,這樣的嘗試與探索在明朝建立后不久便逐漸終止。
許多歷史學家對明清以來帝國在海洋貿易上(或對外貿易上)的保守主義有過闡釋。從知識論的角度看,這種保守主義是由儒家的“性理之學”發展而來的“內圣之學”,即追求個人有限生命的道德圓滿。儒家的“內圣之學”在政治經濟上的表現即為對外海禁、對內綏靖、社區教化等政策。這樣的意識形態導致的是自明帝國起,由傳統國家向絕對主義國家的蛻變與演進。與之相伴的是,由原來沒有邊界的帝國逐漸轉為有明確法律意涵的、規定性的、疆界的國家。此時,泉州城市中“城”的一面逐漸凸顯,也就是起防御保護作用的軍事功能逐漸得到增強。與海防建設幾乎同步展開的還有地方基層系統,都圖鄉、鋪境系統到清朝時已十分完備,滲入城鄉各個角落。與此同時,泉州地理、城市、房屋、寺廟和衙門等“物質性”遺存無不浸潤著理學、易學的宇宙觀。比如在明清方志中,泉州地理往往被劃分為5個部分,即“星野”“山川”“封域”“城池”以及“鋪驛”或“市里”。這5層的劃分是“五服”古制的城市空間的縮影。除此之外,官方還要組織祭典。通過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方位宇宙觀的移植,帝國的形象和意識形態在地方得以吸納與展演[10]179-205。泉州成了中國微觀宇宙的象征,此外這一象征體系還以年度周期儀式的方式不斷被強化。
綜上所述,泉州的地方史始終與帝國彼此映照。一方面,明帝國在民族國家的世界浪潮之中逐漸由傳統國家邁向現代國家;另一方面,明朝又漸漸形成了“內圣之學”上達廟堂以海禁綏靖的國家主義形式加以彰顯,或下至鄉間以民間教化的形式加以表達。顯然,泉州的 “復合人文世界”便是在“治”與“亂”的辯證之中實現的,這與 “城”與“市”的歷史辯證恰好吻合。泉州港的形成與繁榮,源自其“夷夏雜糅”的復合人口結果和文化特性,即定義為“亂”。明以前,“市”之所以能發展起來,乃是對“亂”的漠不關心。而明以后,尤其是元末泉州10年內亂,“亂”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要以徹底的“治”來改變現狀,那么給予“生生”的空間就很小。這時候商盜泛濫,與之相伴的是“城”的空間加強。
除此之外,由宏觀史學落回微觀社會生活史視角,還要強調泉州人日常中所蘊含的年度周期儀式也為這一“復合的人文世界”提供了重要論據。泉州存在3套主要的年度周期儀式:第一套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被宣布為“法定節日”的儀式;第二套是由地方文化管理部門創造的以地方文藝類型的展演為核心內容的周期性“藝術節”;第三套則是存在于民間的周期性儀式活動,包括以家為中心的祖先祭祀,以每月二度的土地公誕辰慶祝為周期的儀式以及鋪境儀式[10]59-60。從本質上說,年度周期儀式就是歷史、文化與權力的集合,或者說是不同的權力通過選擇歷史來選擇文化的結果[10]61。
可以說,從公共儀式切入社會,是人類學家有可能展開具有歷史意味的“人文區位學”研究的一種方式。費孝通曾在祿村農田中對“消遣”進行了論述,被消耗在儀式性活動的時間沒有增加勞動價值,從而為其社會秩序的維持提供了文化基礎[12]。燕京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田汝康通過研究擺夷社會,對這一公共儀式作出了更核心的闡釋,他認為除了消耗之外,公共儀式還有助于宗教“超越性”的營造[13]。同時期,許光筆下的祖先祭祀也試圖創造一種延綿連續的時間感和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14]。這一時期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志都從公共儀式中呈現出一種歷史時間,通過社區年度周期的規定與生命周期的布置,勾勒了具有歷史連續性的人文傳統。王銘銘團隊曾以居住在城南老街區的李媽[6]為例描述過泉州日常生活中所蘊含的這種“歷史感”。李媽的儀式生活是由社區宮廟各神明的誕辰慶典及其家戶中的祖先祭祀構成的,周期性的節慶占滿了她的生活世界,她的生活節奏也由這些節慶調整著。也就是說,既可以認為這是泉州李媽消遣空閑時間,也可以將其視為泉州人對超越性和神圣性的追尋。這種追尋使泉州人與現代性的斷裂時間保持距離,而與一種綿延的多重歷史建立深切且動態的聯系。
作為遺產主體的泉州,其歷史與現狀皆彰顯了一種復合人文主義。這不僅僅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而且具有方法論的啟發。在傳統的人文區位學基礎上,筆者認為地理和社會的環境或生態,都有深刻的歷史性。關系論的考察,不拘泥于區位或社區的橫切面研究,而更重視前后相繼的歷史關系,尤其是注意到作為靈驗的遺產——公共儀式的重要性。
2.4 原真性的表現之一:好古主義
這種靈驗的遺產,賦予了“物”之外的生活世界以意義與價值。同時,泉州人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儀式也對“物”的好古主義提出了異議,因為擁有儀式生活的泉州人往往對深切的歷史及其蘊涵的道德真理抱有敬畏,而不是“物”本身。
“原真性”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對年代價值(或稱之為古老、懷舊)的追尋。2019年4月15日,法國巴黎圣母院發生大火,其頂部閣樓遭到大火侵蝕而毀壞。大火催生了文化界對西歐文明的反思,但作為文化遺產保護專家,最為關心的仍是修復問題。這一場修復在法國引起了爭議,到底是修舊如舊還是引入創新設計元素?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依然是這場爭論的核心。然而有意思的是,這場大火燒毀的本身就是建筑師維歐勒·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在1859年大修時加建的一部分。
修舊如舊的邏輯起點即是保護建筑實體的原真性,100多年前加蓋的閣樓部分算不算“真”?多久的年代長度才算“真”?“真”的內涵和定義因而被時間性拉伸具有彈性。甚至遺產界本身對此也爭論不休,其實踐也不斷挑戰這一定義本身。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是沒有完工就成為世界遺產的教堂——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天主教大型教堂——圣家族大教堂(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又譯作神圣家族大教堂,簡稱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該教堂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師安東尼奧·高迪(1852——1926年)于1883年接手設計和建造,而在他去世時,教堂才完工了不到1/4,直到現在也還沒能建造完成。以“古老”來衡量,沒有完工的遺產,又何以具有年代價值被冠以“世界文化遺產”呢?
因而,文化遺產國際學界本身便對此疑義紛紛,各國在實踐中也未遵循同一套原真性原則。那么,對泉州文化遺產實踐的啟迪之一應當是:“原真性”框架或許無須被毫無保留地接受。“舊”“古老”或“傳統”不一定要成為衡量“原真性”的唯一標準。以木質為主要建筑材料的東亞地區,其文化遺產實踐過程必然會遭遇以年代為考量的“原真性”檢驗,泉州也不例外。伊勢神宮以神道哲學的儀式性重建已對其提出根本性挑戰。筆者一再強調的是,這一框架與泉州的歷史經驗之間存在差距,它本身亦是可被挑戰的,何況是在這一框架下指導形成的“年代價值”。
3 結束語
毫無疑問,人文區位學是20世紀社會科學學界提供的一種重要方法論,回應變遷中的空間及社會。泉州的復合人文世界,試圖超越傳統人文區位學,啟發后者更具“地方感”和“歷史感”。然而,作為遺產主體的泉州與這一復合人文世界之間是否存在溝壑取決于前者是否會陷入“原真性”博弈——這是自伊勢神宮以來非西方學界對歐洲中心主義、物質主義所提出的重大挑戰。
“原真性”框架下對“物”的地位強調,對“古物”的重視本身便值得反思。“懷古”的追求是近代以來人類深陷于單線歷史價值體系,并將“古老”置于“落后”一端的觀念所致。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曾提出,現代人區分了事實與崇拜,并將二者重新整合。他以“事實拜物教”這一概念來說明現代拜物教形態。他指出,我們現代人表面上區分了主體與客體、事物與表征,但其實又悄悄把它們重新整合[15]。世界文化遺產體制的運行與這一現代拜物教具有某種深切聯系。拉圖爾對其的揭示可以啟發我們走出“原真性”,恢復對“具有歷史感”的人文區位學的關注。
在這一視角下的泉州所蘊含的哲學是更為總體性的,更為思辨且動態的——既蘊含在其“治”與“亂”的城市史中,也蘊含在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中。其中,公共儀式生活從未遠離他們。歷史如同祖先一樣,常常通過儀式的方式重返社會。具有“歷史感”的人文區位學,亦不是一種好古主義。它是一種對人文、生態與社區的“總體性”把握。這種“總體性”沒有將過去和現在、歷史與現實、古老和當代、主體與客體相割裂。因而這種“總體性”下的復合人文世界亦是面向未來的、開放的,在其“生生”的情狀中對滲透著拜物教的現代社會發出淡淡的嘲諷。